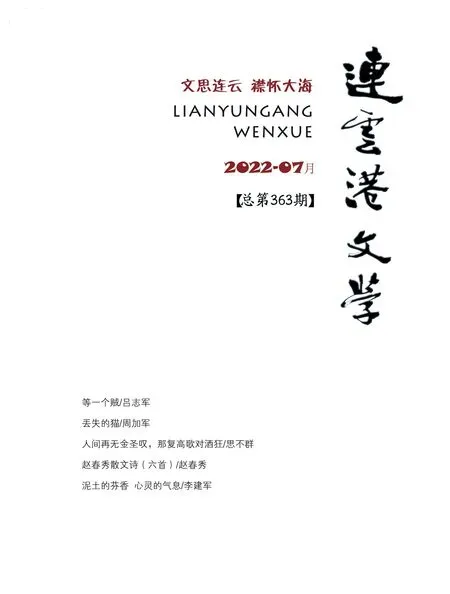等一个贼
吕志军
把门关好,小锄头上的泥巴除净收笼,院子里清理的草洗了,整齐地摆在水泥场,凳子挂在屁股墩,关上堂屋门,灭了屋檐灯,亮开睡房灯,撕下蓝布裤褂,枕上红色塑料绳捆绑的棉裤枕,扯过被子把自己腰腿裹住,不用开关,就用灯绳,趁手。头顶的灯绳拽拽,个蹦一声,窝进黑暗。
东西安稳了。张克俭给暗夜里的自己说。
屋顶儿子刷白的,墙上女儿贴过纸,被儿红绸面白里,枕头黄翠华塑料丝搓的红绳捆,现在都是黑的,只有张克俭的眼珠子圆圆瞪着,泛出浑浊的微光,白内障猫眼般,把黑暗戳了两个窟窿。黑暗像水一样漫过,把小窟窿慢慢、慢慢淤满填没。
东西安稳了。子女进城后,张克俭就这样对自己说,过后他被黑暗吞噬,连梦也没有一星半点。
张克俭很奇怪自己不做梦。以前他梦见自己买了自行车,二八加重,飞鸽的,一村人围过来看,看他给车杠车把车架细密地缠软塑料绳,如果能行,他连辐条也想缠个花花绿绿。梦见自己和黄翠花去地里摘棉花,她腰上的布兜越摘越大,像婆娘怀孕肚皮快速鼓胀,他跟在后面总是摘不满臂弯的竹笼,总偷瞅黄翠花鼓鼓囊囊的屁股。梦见架着柱娃走十里地看《地雷战》《飞虎队》,踩明晃晃路面跌进一汪湖,在水里喊着救命,救柱娃。衣服干了继续去赶另一个地方的《地雷战》《飞虎队》,脖子上又被柱娃尿湿。柱娃进城了,张克俭和黄翠花说自己做的梦,黄翠花说你啷个(陕西关中方言,语气词,有时虚指某个人,哪个、谁;什么、那个之意)老糊涂了,柱娃现在开着汽车上班,住的高楼洋房,啷个还尿(陕西关中方言,理睬之意)你,尿也是尿马桶,一摁按钮刺啦净得泉水儿样。张克俭说我真梦见了,柱娃儿子给柱娃媳妇尿了一怀。黄翠花说你啷个说的哪个儿子?她又生了一个我才看大送进幼儿园去了。那幼儿园啷个好看……张克俭说,有咱村里幼儿园好看?黄翠花说,你说啷个话嘛,咱村里幼儿园能有滑滑梯王子宫殿蹦蹦床?柱娃儿子上的市里最好的幼儿园,啷个进门费都要六万元,你一辈子给我攒的几个钱?张克俭脸没进被窝,说柱娃媳妇给买的枕头太软枕着做梦哩,我爱硬枕头。黄翠花说啷个我把青砖还是换回来?张克俭打了黄翠花一拳。黄翠花开箱子翻,翻了几条柱娃儿子退下的衣服,新的舍不得,扯出一条张克俭的棉裤卷了捆扎住塞在张克俭脖下。张克俭说,裤面穿绒了,合适。可是枕头绳子才揉绒,一天他起来干了一晌活黄翠花还不起床,一摸,黄翠花像出笼要捎给柱娃的馍样,身子都凉了。
黄翠花走了,张克俭再也不做梦。他拽灭了灯使劲想,还是半个梦都没有,只有一双猫眼样的眼珠子,烫出来黑夜的窟窿越来越小,小得也要看不见了。
张克俭听见有脚步声,他很欣喜自己又恢复做梦了。他看见老李走过来,到床边把灯扯亮吆喝声声说,你还睡,沟蛋子(陕西关中方言,屁股蛋意)都晒焦糊了。张克俭想回答,看见的只是黑,老李吆吆喝喝拉他套车去上粮。
老李就爱上粮,谁让他没白没黑地和老婆捣做,一口气生了八个,走个亲戚像赶了一溜串猪羊,他不上粮就没钱买油买盐。鬼儿子一戳戳进去,我晒得干嘣嘣的粮才给个二等。龟儿子牙是猪牙还是狗牙,我咬出的是脆渣渣,他咬出的是噗沓(陕西关中方言,绵软意)。我一等粮就比你的多了两块钱,张克俭劝。两块?我扯两丈布,还不做几套衣裳?你看你看。老李随便抓一把儿女搡到张克俭面前,这还叫衣裳吗?沟子(陕西关中方言,屁股意)都在外面,咋个上学校?
张克俭说,你吆喝啥啊,他们没有车还是没有房?老大是省物资局处长,老二是教书先生,老三是副镇长,最不济的老七,做生意一年也能挣个二三十万。老李把张克俭一攮,你咋光说好听的,我老八你咋不说?张克俭说,老八在天津上大学,你还想咋(陕西关中方言,干什么意)?老李脚往地上一蹬,想咋?一年学费三万,生活费两万,哥你说我这五亩地一年就是刨六季,能刨出五万来?张克俭说,你不能,他上面的七个哥姐能。老李嘴一撇,你可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谁家不是一本难念的经?
老李转身走了。张克俭想和他说说柱娃,可是老李头都没回一下。张克俭看见自己躺着,不是老李说的站着,他看见老李不是穿着儿子退下来皱皱巴巴的酱色西装,而是黑衣服,没边没棱,没腰没腿。
老李才走,朱香椿抱着孙女进了门,乖乖,叫爷爷。张克俭拉着脸说,东西个(陕西关中方言,什么意)爷爷,你把我叫叔哩,你孙女咋个叫我爷爷?朱香椿摇孙女手,孙女手攥着拨浪鼓,卟咚卟咚卟咚咚。叔你还老封建,城里人见了黑头发的叫叔叔阿姨,白头发的叫爷爷奶奶。张克俭说,黑头发的还有哥哥姐姐,白头发的还有太爷太婆,你叫我太爷!朱香椿孙女说,爷爷的白胡子像山羊,爷爷是山羊生的吗?朱香椿笑得弯腰,把孙女溜下地,你爷爷就是山羊生的。孙女又问,奶奶白毛毛,奶奶是绵羊生的吗?张克俭说,嗯嗯啊,你婆娘家在绵羊窝。朱香椿把孙女拨浪鼓拔过来,不许胡说,我的娘家在朱家寨,我是你外婆。
张克俭给朱香椿倒了水问,你在城里住得惯?朱香椿说,住不住得惯由不得自己,喔(陕西关中方言,语气词,那个意)女子不是东西,和婆婆合不到一搭,人家叫娃自己吃饭,她说人家不管娃;人家用勺勺喂娃,她说人家把娃嘴戳了。他们上班走,人家累了睡会儿,娃尿了裤子,她进门就叨叨人家把娃不当娃,那么小的人,那么嫩的皮肤,经得住尿渍吗?人家买了纸尿裤,又嫌人家买得便宜的,把娃大腿都勒红磨烂了。人家受不了走了,我就得顶上受罪。张克俭说,你不哄得好好的,看你这乐得。朱香椿说,叔你再嫑寒碜我了,女是自己养的惯的,我这是打碎牙还得咽进肚子,我给谁说去,左右都是打自己脸。张克俭说,你抱回来,我帮你带看。朱香椿说,叔吔(陕西关中方言,语气词)你再不敢说这话,那就是要了女的命了,班不好好上,一会儿一个电话,乖乖吃了吗乖乖睡得好吗乖乖裤子干着吗?外人听着这是命根子。回到家抱一会儿就把娃往我怀里塞,妈你抱会儿我胳膊疼死了,妈你带她下楼溜溜去我睡会儿瞌睡,我这妈是生了大的还生了小的,我都七十了还得受着!孙女玩了半天张克俭的胡子,厌了,奶奶去外外去外外,拉着奶奶往外拽。张克俭眼见朱香椿被拽进一栋高楼里去,陷进黑暗里。
张克俭看见黑,听见有脚步声,窸窸窣窣。黄翠花老上山,他的眼睛昏花模糊了,耳朵灵敏起来,他听见脚步从大门踅进来,侧身进了堂屋,在堂屋四处里摸索。桌子上铺塑料格子布,布上有一把斧头,他白天才搭了坻石磨得光亮锋利,槐树起了花开得繁茂,一根枝桠伸到檐口,起风会挂瓦,明天准备端梯子上树,砍掉那根斜枝。枝桠根段溜直,截下晾干,能做锄把。顶段有弯曲,恰好可以做根拐棍,走路不能老是沟子墩上挂个凳子。斧头旁边是一只洋瓷碗。柱娃媳妇买回的细磁碗已经摔碎几只,这只洋瓷碗是公社时候用的,柜子里翻出来,竹筷搁在上面很般配。晚上为了剜净院地里的草,碗筷还没来得及洗,肯定会有老鼠享用残羹冷炙。东墙旁边是皮沙发,柱娃雇车拉回来,上面铺了隔布,出去游转累了,或者中午太阳晒乏,可以在上面靠会儿。张克俭不喜欢在沙发上睡觉,睡觉有床,而靠着不能解决腰背的困乏,因而他觉得沙发实在多余,上面总是随手扔着伞、镰刀、甚至捡回来的半截砖块。自行车倚靠西边墙。柱娃说这辆车子可以进博物馆,风雨五十年,是父亲的伙伴,每根辐条是岁月的见证,它载来了柱娃和妹妹,也载走了女主人黄翠花。可是新装修的房子敞亮通透,它又实在有碍观瞻,柱娃意思是张克俭喜车,可以给他买辆新自行车挂在墙上,以便儿女进城后的日子可以睹物念旧。但遭到张克俭极力反对,张克俭说你把我扔了可以,扔它不行。张克俭闲暇会拿砂纸打磨锈迹,擦抹瓦圈和轮轨。早些年还曾买了辐条,把断了缺了的辐条全部换新补齐。近些年他干不动了,也会偶尔在车身上靠一会儿,陷入莫名其状的情绪,或许他会想起从山里驮炭,暖和一屋的冬天;或许他会想起载着黄翠花赶集,给她千挑万选一截花布;甚至想重新骑上它,去看看爱上粮的老李和他的八个子女,或者为女儿带孩子心里有苦的朱香椿。可是他只能想想,长叹口气窝进被窝里去,期望能摸见黄翠花,热热的而不是她冰凉的身子。
另外两间房子都有家具,但张克俭几乎不去,一间堂屋,一间睡房,一场院子足够他折腾。他更多的时间是坐在院门口,门开大,眼瞪圆,看远处,以及更远处。
门口的人越来越少,他的眼睛越来越花,耳朵却越来越灵敏。
张克俭听见脚步的挪动,进那个不去的屋子,从里面出来,折回到堂屋,悄悄推开半掩的睡房门,又退出去。
东西安稳了,张克俭说。他也给脚步声说。脚步声不是老李,不是朱香椿,更不是柱娃黄翠花。
他听见脚步声突然跑出去,把洋瓷碗上的筷子碰落下来。张克俭喊了声老鼠,然后遗憾地重新陷入黑暗,跌进寂静里。
张克俭像所有老人一样起得很早。老了没瞌睡,赖在床上假装也没有。昨天剜的嫩草蔫了。张克俭把草收起来喂猪,才想起猪早没有了,猪圈鸡圈都拆了,变成敞亮的水泥场面。围墙是石柱栅栏豪华气派,凉冰冰的。张克俭掇了凳子坐在院地,甩动小撅头深深地翻土。一条蚯蚓扭曲,他捏住,把它扔到远点的地方。几只白色虫子急急爬出来,他轻轻刨平前面的土坷垃,让它们从容地逃走。他细细捏碎土块儿,均匀地扑撒开,又用弯把小锄犁出小沟。待沟两边捏摸整齐划一,把那些嫩草重新摆进沟里,埋上,端盆接了水浇过。
看到斧头,张克俭想起昨天计划的活计。他把斧头别在沟梁上(陕西关中方言,腰间意),就像年轻时候进山砍柴一模一样。他吆喝着一帮弟兄呼啦啦进山,专拣端正直插云天的松树砍,砍倒,咔咔咔剃光枝桠,嘿吆嘿吆扛到山脚,赶着牛车拉回来盖房子。他给黄翠华说,四间正房,两间偏厦,住一家人。他记不清自己进了多少趟山,砍倒了多少松树,当一排房子高大站起的时候,一村的人都来放鞭炮,都来吃上梁酒席,黄翠华嘴都笑歪了。现在,跟他砍树的狗子、猪娃、山羊都不在了,房子拆了,起了新楼。一切抹平了,就剩这根老槐树。
张克俭扛梯子,第一次竟然没扛动。第二次嗨了一声,动了,差点摔倒。他生气地把斧头拔出来扔在地上。
张克俭看着梯子生气,看着看着到了中午。
康茹噗沓噗沓走进院子。
康茹是老王头的老婆,养了三儿两女。康茹问老张你吃了吗?张克俭看着梯子说吃了。康茹说谁惹你不高兴了?张克俭说没有谁。康茹说那你还不吃饭?张克俭指指碗,康茹看见碗里有饭末。康茹说我要走了。张克俭问你干啥去?康茹说,移民搬迁,镇里给了一套房,自来水煤气灶热水器都齐活了,让去镇里享受。张克俭说,嗯嗯,我知道。康茹说,村里没几个人了,柱娃接了你好几次,你也该走了。张克俭说,嗯啊,他妈殁了柱娃就接我走,可我这院子咋办呀?康茹说,我的庄基交了,人得往好处去,那边人多好说话,还有养老院。张克俭问你啥时候走?康茹说我今个下午走,车一会儿就来了。张克俭生气地说你急着死呀?明天走!康茹说车都说好了。张克俭说明天走,我叫柱娃回来接你。康茹说不了,麻烦。临走又说,村里这两天有个蓬头男人,走来走去的,听说洪水冲来,他去救人,自己的老婆孩子却淹死了,家破人亡,精神似乎出了问题——道听途说,谁知道真假呢。你晚上把门关好。
张克俭胡乱做了饭,吃了收拾房子。他把沙发上的塑料袋收了树枝抱走斧头塞进柜子底,隔布叠好去了,把桌子挪到沙发旁边。之前,柱娃买好沙发发现没有茶几,张克俭说我不去城里你们偶尔回来一趟要茶几供谁?不要了,桌子就是茶几。桌子挪过来配了沙发。张克俭烧了一壶水灌进电壶,拆了柱娃媳妇买回来的茶具,置在电壶旁。翻出来女儿扔掉的一个皮包,把箱底攒的一些钱装进包里,大拉开拉链放在桌头,旁边又散了几颗糖果。临睡前点上一根敬神蜡,用纸卷了纸筒,围住蜡烛头,使得这盏灯火不像电灯样明,也不像暗夜般黑,恰如城里宾馆墙根的夜灯。
张克俭裹住自己窝进被窝,昨天有人进了屋,他要捉贼。
村里的夜没有一颗星星,屋里的一星蜡烛朦胧住一村的寂静。张克俭静静地等。昨晚筷子滚落,他喊了声老鼠,他知道贼不会空手而归。
张克俭眼睛瞪得圆圆的。他听着,听着,门缝里的烛光越来越黯淡,终于,两个混沌中的小窟窿被黑暗填没。
张克勤进了屋。张克勤是张克俭的弟弟。
哥哥,张克勤坐在床边叫。
哎,张克俭回应。
你吃了吗?张克勤问。
吃了。
你睡得好吗?
好。你咋回来了?张克勤随女儿去了北京,女儿说,爸爸,北京是首都,我不可能经常回来看您,您就走吧。张克勤对张克俭说,我知道我一去就回不来了哥哥,我不去。张克俭说你去吧,庄基地都卖了。张克勤说我是个不孝的,把祖产弄没了。张克俭说有我守着呢,放心走吧。张克勤现在却回来了。
我想你啊,想咱们庄子啊。
你咋回来的?
飞回来的。
你又没翅膀,张克俭笑了。
我从火葬场烟囱飞回来的。
张克俭猛然坐起来,他握弟弟的手,却只握到两截袖管。弟弟你的手呢?
在这儿呢,张克勤指自己的腿,那双腿跟他进山砍树被砸断过。
张克俭去摸腿,也是两截裤管。弟弟!
我很好。哥哥你好吗?
我也好,我也想你,想爹,想娘,想柱娃和他妹妹。
你想黄翠花吗?
张克俭想说话,可是喉咙堵得厉害,发不出声。
柱娃伸手过来摩挲他的喉咙。
柱娃?
哎。
你干什么呢?
工作,每天忙不完的工作。
你车里拉的啥?
给你买的米,面,油,菜,还有城里最有名的糕点。
你吃。
我吃过。
你吃。
你吃!
给我妈吃。
给乖孙子吃。
啷个一起吃,黄翠花抱着孙子说。
张克俭挡住众人,他听见脚步声,贼终于来了。
贼悄无声息推开院门,蹑手蹑脚地进了堂屋,犹疑一会儿,听见张克俭均匀沉重的鼾声,终于在沙发上坐下。他剥开一颗糖扔进嘴里,香甜让烛光显得柔和而温馨。他熟练扯出钱包的钞票,津津有味地数起来,嘴里轻声附和:一,二,三……
张克俭清晰地听见贼的声音,他向众人压压手,做出“嘘”地警告,悄悄说,听,他在数,四,五,六……
他冲过去,贼却飘走了,把张克勤柱娃黄翠花都带走了。
天又亮了。张克俭坐在院门口,院门大开着,镰刀菜刀锯子斧头圈住他脚,像一窝狗娃,仰头看他手里的拐杖。这是他见过的最合适的树枝,把儿弯曲,恰好握手,稍下有一处凹,等待累时放另一只手;身子溜直,指向地面。挨近地皮的下端,分出小小三个叉,牢牢抓地。天意。张克俭心里赞叹,拐杖在手里捋来捋去。剁去握手和分叉处的多余,细细削去树皮,镰刀慢慢刮削,两端茬口变得圆润,身子变得细腻光滑。槐树的味道四散,冲得张克俭满眼是泪花。他爬上树捋槐花。黄翠花早早扫了地,等槐花铺了厚厚一层,掬了冲洗,热水焯了,和面粉搅拌,撒了调料,再搅拌,上笼屉蒸。不多时候,槐花麦饭的香味从各个瓦缝窜出,窜来一村的人。老李提了筐子,朱香椿挎着笼子,都来揽地上的槐花。不一会儿,槐树被欢声笑语淹没了。张克俭坐在树叉嘿嘿笑,看着厚厚一层白渐渐没了,地面重新显露,才扑通跳下,圪蹴在树下卷烟丝。黄翠花说,啷个今天像过节一样。张克俭说,就是,像过节一样。
张克俭会在某个时候再爬上树,扑打一层白白的槐花,大声问你烧好水了吗?黄翠花在厨房远远地应,早好了,啷个等着呢。张克俭说,那你还不掬?黄翠花张开双臂来掬,一怀一怀的槐花,一锅一锅地焯。那些槐花黄了,蔫实了趴在菠萝里,竹席上,风得干干的,爆米花一样。黄翠花把它们装了一袋又一袋,边装边号,这是给柱娃的,这是给他妹的;这些给老李,他吃饭的嘴巴多;这点给康茹,老汉死得早,一个女人家,扛那么大麦捆,遭孽呢。
张克俭伸拐棍拨拉槐花,拨到了球球的腿上。球球生下来圆乎乎胖墩墩,都说这娃是福命,谁成想十三岁还不会说话,身体一个劲地横长,真的长成球。待到十四能说话,也是含混不清,好在村里人明白他连喊带划的意思。
球球。
大爷。球球爷的爷和张克俭的爷是一个爷。球球嘴里说话,手不停比划着,指张克俭的拐棍,你打我。
张克俭说,我拨拉槐花,没打你。
槐花在哪?球球四下里找,头仰起目光落在槐树上。他扯张克俭的拐棍,我打。
张克俭拐棍压住球球的脚,又指凳子。球球坐在张克俭面前。
你打呼噜了。
我没打。
你就是打呼噜了。
我静静的,安稳。
这个球球爱较真,尤其和张克俭,爷爷孙没大小,一天不和大爷张克俭顶牛就闲得慌。张克俭像球球一样大时,球球说大爷我给你割稻子,稻子穗穗散了一地;大爷我给你掀车车,张克俭越拉越重,是球球在往后拽;大爷修房我给你上瓦,没走几步一抱瓦跌碎了,好几顿的口粮钱。那时张克俭烦得踢他;现在,张克俭天天盼球球来,球球就是不见人。
大爷你真的打呼噜了。
我真的没打。
你真的就是打呼噜了。
没打。
打了。
嗯,我好像打了。
我也要拄拐棍。张克俭想起来,这个父母已经离世的孙子,独自在村里,走路摇摇晃晃,是该拄拐了。
你多大了?
五十多,大爷。
哪有,你还是个娃。
大爷,真的,五十三。球球伸出三个指头,又来扯张克俭手里的拐。
另给你做。张克俭不丢手说,这是给康茹的,康茹昨天迁走了,她不知道,这根拐杖越用越轻快。
晚上,张克俭点了蜡,桌上撒了糖果,又往女儿扔掉的包里装了钱。他在屋里四下走,最后把钱包塞在西边房间空着的床下。要修新房,腐木烂瓦旧床旧柜都扔掉了,这床是新买的,席梦思,柱娃和媳妇回来睡。现在床上遮了罩布,布上是厚厚的灰。房门先是合着,黄翠花走后张克俭把门打开,再也没有关过。张克俭跪下,把钱包塞在两指宽的床地缝,又觉得太过隐蔽,把一张钱扯出一角,露在外面。
东西都安稳。张克俭窝进黑暗。
夜黑静得一丝风都没有,仿佛能听见槐花嘣嘣绽开的声音。白天爬树砍树,张克俭躺在床上,才感觉胳膊腿儿腰身都是酸疼的,眼皮也坠得厉害。
他疼痛而舒心地等着,等着。
黄翠花从外面寻猪草回来,满脸的汗,放下挑担,毛巾擦了把汗,瘫软在屋檐下,张克俭端水转身出来,黄翠花已经依着土墙睡着了。
你打呼噜了。张克俭摇她。
我没打。黄翠花强睁开眼睛。
你就是打呼噜了。
黄翠花真的打呼噜了,张克俭胳膊掏过她的腿,把她抱到床上。
柱娃开车回来了,柱娃媳妇下了车,柱娃俩儿子下了车。柱娃从后备箱搬东西,米,面,油,蔬菜,还有滑滑车。
这是菜,这是菜。张克俭指着院地的绿色,嘴上很生气地斥责。
我买的有机菜,无公害。柱娃说。
我种的有害?张克俭显得更生气。
黄翠花和柱娃媳妇帮手拿东西,张克俭一把把柱娃小儿子举到空中。乖乖高不高?
爷爷我要下来。柱娃儿子在手里挣扎。大儿子很快搬了梯子爬到树叉上坐下,晃荡着腿给弟弟招手。小的却不敢上。张克俭夹住两肋,帮柱娃小儿子爬梯子,也坐上树叉。
跌了!啷个小爷吔。黄翠花踩住梯子脚,在树下喊。柱娃和媳妇笑得咯咯咯咯。
张克俭听见柱娃进了堂屋,他没有看见钱包。他心不在焉地剥了颗糖塞进嘴里,举着蜡烛四下里找。张克俭能听见他在掀桌布,拉开抽屉,在神前桌的下面扒拉。他放下蜡烛,打开了手机电筒。
然后柱娃进了席梦思房间。
柱娃。张克俭喊。
哎。
你又打牌输了?
我没有打牌。
那你找钱?
我给娃找学费。
你不是有工资?
这点钱还不够塞牙缝,两个儿子,上学,培训班,艺术班,还得给他们攒买房钱,娶媳妇儿……
谁让你修村里的房?
你们要住啊。
柱娃,你是败家子。谁还在村里扔钱?都去城里了。
张克俭举起拐棍,想抽打柱娃,哪怕是做做样子,可是拐棍沉得举不动。他听见柱娃从床底扯出钱包,夹在腋下,关了手机电筒,盘腿坐上沙发,又剥了颗糖扔进嘴里,咕噜咕噜地舔。
柱娃。黄翠花进来,给柱娃擦嘴角流下的涎水。
妈,很甜。柱娃说。
黄翠花扬起手掌,给了柱娃一耳光,啷个叫你偷吃,叫你懒,叫你不争气。
柱娃哭起来,黄翠花也哭起来。张克俭把头埋进被窝,他不敢哭,他要看庄子。
太阳又出来,张克俭起了床,拐棍倒在床边地上,弯腰捡起,腰身一阵酸疼。他慢慢拄拐走出来,走到大门口。坐下看远处,雾蒙蒙的,远处一片混沌,更远的地方,天地合为一体,只有拐棍槐木的香悠荡出来。
东西安稳,张克俭看着圆乎乎的太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