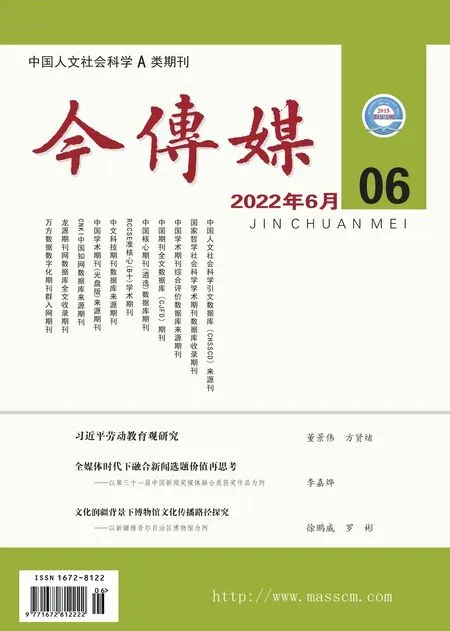互联网语境下纪录片的美学特色
——以 《围城随笔》为例
吴连磊
(河北传媒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1430)
近10年来,我国纪录片创作主体从基本由传统电视专业制作团队主导逐步发展为与民间制作团队并驾齐驱,播出渠道也更加立体、多元。近几年,《早餐中国》《人生一串》《守护解放西》等一批互联网纪录片,以多样性、融合性的流媒体呈现方式涌入大众视野,这些全新的创作主体带来了不同以往的创作观念。《围城随笔》系列既是导演阿伦的零散旅途,也是关于城市、田野和村落的故事记录,其通过新颖的视角切入、朴实的内容呈现、灵动的结构表达,阐释了浪迹山河湖海、记录大国小民的主基调,展现出“万物互联”时代下纪录片新的美学特点,以独特的视角与诗意的镜头语言解构中国的人文地理。
一、低视线的切入角度
传统纪录片多从高角度的视点切入,利用全知视角引领观众走进故事。例如,《舌尖上的中国》《河西走廊》《风味人间》等纪录片,优美的画面配以字正腔圆的旁白,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产生共情。但是,这种视角具有一定的强加性,它不是抛出一个观点让观众去思考和评定,而是在纪录片中直接告诉观众某个观点,观众难以看到事物的全貌,也无法理性地进行判断和思考。
纪录片 《围城随笔》从导演的第一视角推进叙事,利用第一人称营造出平行视点,低角度的切入给观众带来了别样的思考体验。在第一集 《勒不是重庆》中,导演用重庆话进行拍摄与叙述,从第一视角出发与被摄者对话,撑起纪录片的整体叙事;第五集《内蒙,游牧的森林》,客观展现了小镇人口老龄化与经济衰退的问题;在第六集 《甘南,点亮的地平线》中,导演将镜头聚焦追逐梦想的“迷恋哥”,他放弃安定生活成为了一名快手主播,梦想从新疆徒步到西藏。对此,导演并未表明自己态度和观点,而是将探讨与思考留给了观众。《围城随笔》的影像呈现方式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结构,虽然导演偶尔也会抛出一些态度或观点,但会强调这只是个人理解,不会强加给观众,影响观众的理性思考。朋友般娓娓道来的故事穿插着颇具生活气息的对话,使得 《围城随笔》突破了以往纪录片的高视点;采用与观众平等对话的视角,使观众不再仰视纪录片,从而赋予影像平和力;体现观众的主体地位,拉近了观众与屏幕的时空距离,让纪录片更具烟火气。
二、韵味而不失水准的文案功底
《围城随笔》的文案拥有震人心魄的力量,触动人心的文案水准贯穿整部纪录片。导演阿伦在回复网友评论时说道:“视频的基础还是文字,只是用画面来讲故事而已。”文字塑造世界的力量,可抵千军万马,在 《围城随笔》中,文案显得格外客观与生动,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简单直白却不失俏皮元素
在第一集 《勒不是重庆》中,“我每次都是从上海跳出来,从这里,浪荡到那里”“低头走稀泥巴烂路,抬头看最霸道的风景”……这些文案直白平叙,但在原汁原味重庆口音旁白的衬托下颇显俏皮,这是与以往恢弘庞大的纪录片叙事语言最鲜明的区别,这种“幽默”充满生活气息,更易激起观众的乡土情节,唤醒他们的年少时光,引发情感共鸣。
(二)人物对话与旁白巧妙结合
据笔者调查,人物对话与旁白结合的叙事模式在纪录片中并不多见,但两者的结合,却能在推进叙事的同时变换节奏,增加戏剧元素。在第一集 《勒不是重庆》中,画面呈现交通茶馆时,旁白为“还好我认得老板儿!”,紧接着便是茶馆老板与导演阿伦的对话,老板:“你不喝茶吗,啊?”阿伦:“我不喝茶。”老板:“你不喝茶请不要在里面拍哈!”这段对话与旁白相结合的叙事,充满了戏剧张力,让纪录片充满喜剧色彩。《围城随笔》每集的时长约为25分钟,这种叙事模式使纪录片在故事化叙述中形成了戏剧性的节奏变化,让观众在长时间观看中并不觉得枯燥无味,提高了纪录片的完播率。然而,这种叙事方式需要创作者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文案功力。
(三)简约语句勾勒思想深度
“在我们年少轻狂的时候,梦想就是一根骨头,但在快到不惑的那一年,那根骨头就会渐渐地变成心里的一根刺,对于没有过骨头的人,可以任凭世界的捶打痛击和不讲武德,因为不曾得到,那就无所谓失去,但对于心里有刺的人,要么学会遗忘,要么就切肤疗伤,待山河云开雾散,再对江湖说一句,洒家就不会好自为之”。这是阿伦在 《甘南,点亮的地平线》中对勇于追梦的“迷恋哥”发出的叹想,既接地气又不失纪录片文字的魅力。其实,触动人心的文案在纪录片中并不少见,但能够与内容紧密结合的却不多,一些人文纪录片备受观众诟病,正是因为其颇有无病呻吟的意味。对此,《围城随笔》提出了很好的解决思路:以小见大,透过小人物、小故事去讲述平凡人生,结合真实故事,诉说写意文案。当观众对纪录片的角色产生认同感时,文字的力量才会逐渐彰显,意境才会得到升华。
三、第一人称代入性叙事
与国内多数纪录片所采用的叙事方式不同,《围城随笔》从导演阿伦的视角来展开叙事。我国纪录片受英国纪录电影流派的影响较大,“画面+解说”的格里尔逊模式被较为广泛地运用。在纪录片中,解说词起到扩展信息、推进叙事的作用,一般情况下是采用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来进行讲述,例如,《话说长江》《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第三极》《公司的力量》等。全知视角下的解说词常以画外音的形式进行多角度剖析,推动叙事发展,但这种叙事视角可能会导致观众疏离,容易陷入说教、教化的桎梏中。
从观众角度来看,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下的纪实影像以“展示”为主,而第一人称平行视角则以“代入”居多。与第三人称视角相比,第一人称视角的独特功能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第一人称视角为限制性叙事视角,“我”在影片中叙述故事,只能是“我”收集、拍摄到的画面,既让影像更具现场画面感,也让观众产生代入感。这一点在 《围城随笔》中展现得十分突出,旅行式的拍摄方式具有偶然性,导演在片中的遭遇与所提的采访问题也都是突发、随机性的。竹内亮导演的作品 《好久不见,武汉》,叙事方式与 《围城随笔》十分接近,同为第一视角叙事,第一视角讲述人,让纪录片的内容呈现减少了严重的脚本痕迹。竹内亮导演在其导演手记中表述道,他们团队只会提前策划拍摄的整体思路,不会提前与被采访人见面,具体的采访问题也都是现场随机提出。虽然两部纪录片的主题和内容不同,但部分创作观念却不谋而合,这种“偶然性”赋予了纪录片更多的色彩。第二,第一人称视角在叙述态度上具有兼容性,既能通过旁白与画面对现实进行客观展示,又能体现出创作者的思想态度。纪录片的策划、拍摄、剪辑往往都带有创作者的个人意志,因此,没有绝对真实客观的纪录片。“客观”与“真实”是一个契约,纪录片的“真实性”或“纪实性”之所以能成立,其前提是创作者和观众双重默许的“假定性”。在 《围城随笔》中,第一人称视角的解说词既承担了解释说明、拓展信息的任务,又展现了创作者的观点。例如,在第四集 《贵州,看不见的山地 (下集)》中,对侗族传统建筑被现代建筑所取代的现实,纪录片的解说词平静地表述出导演的观点:这既公平,也自然,毕竟谁都有权力,去追求更好的生活和便利。客观真实呈现与主体意志表述有机结合,成为了 《围城随笔》的一大特色。
四、充满动感的节奏韵律
“节奏”一词在影视语言中较为主观,但却真切地潜藏在每一部影视作品中。众所周知,剧情片的核心是故事,而讲述故事就会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甚至是更复杂的剧情结构,这就会产生影片的叙事节奏。一般而言,剧情片的矛盾比较突出,故事呈现也更加具体,因此,其节奏表现会更鲜明。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是优秀剧情片的必备要素,也是影响观众观感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剧情片把控好影片节奏,其趣味性和可看性才会增加,影片的完播率也才能有所提升。相对而言,纪录片具有较强的纪实属性,在节奏把握方面更有难度。如何在纪实的基础上,更好地讲述故事的起承转合,避免枯燥无味,这是众多纪录片导演面对的共同问题。与节奏平缓、娓娓道来的纪录片不同,《围城随笔》的叙事节奏转换自然,主要通过解说词、音乐、剪辑等手段,将故事讲述得张弛有度,增添了可看性。
(一)解说词
解说词在纪录片的视听空间里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需要勾勒起整个故事画面,带动故事节奏。在第四集 《贵州,看不见的山地 (下集)》中,导演阿伦在苗族村寨时的画面解说词为:“村宴结束后还有篝火表演,那原本是我最期待的环节,结果还没开饭,一场大雨则突然而至。”在这句解说词出现之前,画面呈现了盛装打扮的苗族姑娘过当地传统节日——“茅人节”的场景,导演阿伦与青春活泼的姑娘对话,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也带动了观众的情绪。但解说词讲完后,纪录片激昂的节奏也像熊熊燃烧的烈火被大雨浇灭一样,再度回归平静。在第七集 《新疆伊犁河谷,冬与春之歌》中,讲述哈萨克族牧民时的解说词为:“夕阳西下,艾力莫骑着骏马,从远方赶回了家,牛羊的归音开始逐渐清晰,毡房的炊烟也就袅袅升起,我站在远方闻着羊肉的香气,想着我会说上一口上好的哈萨克语,一定飞奔过去……嘶溜嘶溜,算了,下次一定!”这段解说词既俏皮,又充满诗意,完结了艾力莫一家的故事,并将情感节奏推向高潮。紧接着一句“在一个没有手机信号的偏僻山谷里,有一家只有当地牧民才会光顾的草原小酒馆。”又开始了新的故事讲述,高亢的情绪回归平缓,重新激起了观众的探索欲。解说词塑造的节奏变化在 《围城随笔》中运用得相当自然顺畅,成为了纪录片创作的一大利器。
(二)音乐
在纪录片创作中,音乐对烘托气氛、强化情感节奏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以 《河西走廊》为例,其主题曲 《河西走廊之梦》由著名作曲家雅尼创作,音乐苍凉悠远,雄浑古朴,既有宏大灵动的和声,又融合西部元素,展现了河西走廊的壮丽风光与厚重历史。此外,《千年回眸》《命运悲歌》等配乐也十分契合纪录片的风格。总体而言,音乐能够串联起作品脉络,使得观众产生持久的记忆和深远的回味。在《围城随笔》中,音乐的运用也是独具匠心。第一集《勒不是重庆》开篇有55秒的配乐使用了音乐作品《我是重庆崽儿》,重庆方言的演唱契合了纪录片拍摄山城特色的需要,加快了原本平缓的节奏,调动了观众的注意力,推进了叙事的发展。第七集 《新疆伊犁河谷,冬与春之歌》第6分20秒处,导演阿伦因冬雪被困在赛里木湖湖边,画面配音使用了当地气象电台播报天气的声音片段,并采用了渐弱处理,接着,又一段轻快生动的音乐渐起,与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仿佛等待着新疆春天的到来。这段配乐运用得十分巧妙,既凸显了新疆冬天酷寒的环境,也展现出人们对初春的期待,情绪从悲转喜,节奏也从哀伤压抑过渡到了欢快轻盈。由此可见,音乐的合理运用是纪录片节奏和谐转换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剪辑
纪录片是编辑的艺术,爱森斯坦曾说:“摄影机拍下的、未经剪辑的片断既无意义,也无美学价值,只有在按照蒙太奇原则组接起来之后,才能将富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视觉形象传达给观众。”对纪录片这种视听艺术而言,画面剪辑是构建故事节奏最直接的方式。由于单位时间内镜头的切换速度直接决定节奏的快慢,因此,画面过渡效果以及升格、降格等特效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节奏变化。在第八集 《东海,等到风平浪静》中,从3分54秒片名呈现完开始,连续6个镜头的时长都在5秒以上,加之徐徐的叠画特效,使得画面节奏更为舒缓,情感状态也更加松弛;在出租车司机“枸杞岛谢霆锋”出现的时候,画面在15秒内使用了8个镜头,以快切的方式简要勾勒出人物的日常工作,打破了之前平缓的叙事节奏,让观众产生紧迫感。通过镜头速度的切换实现节奏自然流畅地转变,灵活善变的剪辑技巧为纪录片增添了几抹亮色。
五、结 语
随着数码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平台的发展,纪录片创作者的数量不断增长,纪实作品的种类和数量也日益丰富。当前,风光纪录片举不胜数,人文纪录片也不在少数,但两者结合后能够走进观众内心的却寥寥无几。《围城随笔》通过清新自然的影像风格与焕然一新的美学特色,给予观众更多的内心触动和情感体验,传递出纪录片创作的新声音。纪录片创作者要时刻对世界充满好奇,在游历中完成与历史、世界的对话,重新理解自我;要通过影像表达手段创作出共情的美学表达,才能在时间长河里经久不衰,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