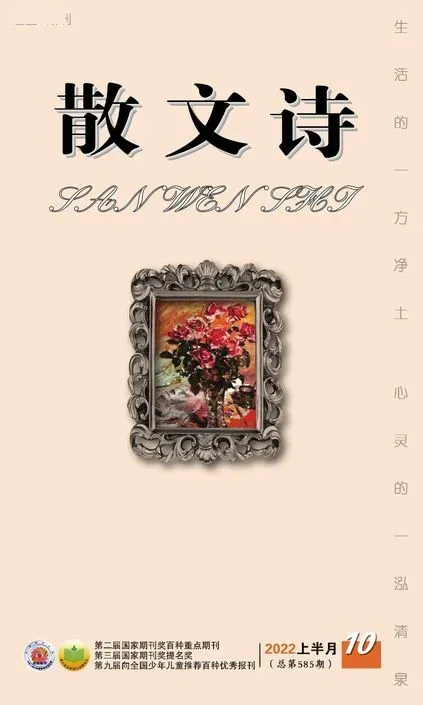真实的世界
◎鲜 圣

沂蒙魂
一幅画卷: 凄美的画卷, 壮美的画卷, 秀美的画卷都是你。
八百里蒙山沂水, 山高水长, 没有哪一块土地能像你一样,承受风雨的击打, 经受战火硝烟的洗礼, 以及流血、 牺牲的考验。
血沃大地, 千山万壑都是战场, 一草一木都是兵器。
红, 是你最醒目的颜色。 漫山遍野开出的花朵, 都是血泪印染的芬芳, 在弥漫。
岁月的刻度上, 镌刻着你刻骨铭心的伤痕, 留下你悲壮英勇、不屈不挠的坚贞和意志。
金戈铁马, 不是一座河山的游戏。
山川沟壑, 也不是埋伏的最佳战场。
但铁蹄, 日本的铁蹄, 就践踏在你的胸膛上, 屠刀, 就横在你的脖子上。 面对强盗的掠夺和侵略, 你以群山的巍峨, 以排山倒海之势, 汇聚起一棵小草的力量, 汇聚起一棵松柏的力量, 汇聚起无数砖头、 瓦块和镰刀、 斧头的力量。
渊子崖村, 不大, 但可以摆开阵势, 与来犯之敌决一死战。
那一刻, 山河涌现出悲壮, 草木涌现出血性, 每一个沂蒙人,都是这块土地上站立起来的刀戈。
这些石头, 有棱有角, 也有自己的灵魂。
坚强、 硬朗的石头, 在沂蒙山上支撑大山的伟岸。
太阳升起, 山冈上, 熊熊战火缭绕大地。
最后一块布做军装, 最后一口饭做军粮, 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 当民族灾难降临在这块土地上, 沂蒙人揭竿而起, 从村庄、田园里齐刷刷站出来, 站成了一道道铜墙铁壁。
崎岖的山路上, 他们把小米当作子弹, 肩挑背负, 领头的人叫沂蒙红嫂明德英, 叫沂蒙六姐妹, 也叫小米、 煎饼和独轮车。
沂蒙人, 热爱这块土地, 山川河流是他们长相厮守的家园。
每一寸土地, 都是他们的血肉。
当年的沂蒙人, 把信仰和忠诚, 写在了八百里群山之间, 用乳汁和血液供养着革命的队伍。 大山可以作证, 江河可以作证,血染的江山到处都是红色的歌谣在传唱, 《沂蒙山小调》, 悠扬婉转, 回荡在万里山川。
风雨的洗礼, 一块土地变得格外厚重。 车轮滚滚, 留下的辙迹, 可以深到草木的骨髓里。 小米喂养的胜利, 是你永远的荣光。
孟良崮的硝烟, 已经化作彩虹。
红嫂的故事, 已经融入民族的血液。
沂蒙军魂, 就是扎根在你怀里的苍松翠柏, 就是永放光芒的一轮日月。
大山, 高昂自己的头颅; 花朵, 倾泻自己的灿烂。 瞩目, 我久久凝视。 沂蒙精神的火光, 今天又迸发出新的力量。
赣州的歌谣
今夜, 我在宋城的楼台上设宴, 宴请千年前的那缕月光, 我在月色沉淀的画布上, 滴落水墨, 勾勒一幅古老的繁华景象。
我在浮桥的一泓浅水中, 为你洗砚。 用墨染的长河, 书写宋词的光芒。
雨, 可以接着下。 阳光, 可以接着来。 我在等你, 站在古城的围墙下, 眼望雕花的楼阁, 乐曲缓缓, 山水的长吟如此缠绵。触手可及的古墙, 还有历史的温度。 一棵草, 羞涩地在雨中沐浴, 和我的羞涩一样。 落在瓦屋上的阳光, 骄傲地扑腾, 闪动着神性的翅膀。
我来, 在赣州, 一个过客所能做到的, 只有停顿在它的旧事里。 旧时光, 浸润我的视野, 让我的血液, 化作流水, 化作一声惊叹的表白, 让我在它的古老中, 像一个寻觅者, 漫游在它的史册上。
我在街衢上徘徊。 四野无人观望我的举止, 我可以大胆地进入一个沾满婉约和豪放的酒吧, 弹奏一曲相思, 一曲惆怅, 一曲被雨水和阳光共同席卷的爱恋。 酒盏里, 盛满云霞, 开满娇艳的杜鹃花。
高耸的慈云塔, 肃立, 静默, 讲述着赣州的风云烽烟。
宝福院里的一池莲花, 开得纯粹而雅静。 膜拜, 瓷窑里的火焰, 还未熄灭, 龟角尾码头上, 来来往往的人流, 像移动的船只, 水中的投影, 越来越密集。
寻觅一处灯火, 就有无数的陶罐在发出亮光。 我在平平仄仄的脚步声里, 望见了从宋词里走来的女子, 倩影, 在水中荡漾。
仿佛你, 就是赣江的一滴水, 把我的笔锋打湿。 你铺展的画卷, 是红色的旗帜在托举一片江山, 回望大地, 红色的韵叹, 是你歌谣里的最强音。 仿佛你, 就是穿越赣江的一叶小舟, 在绿水青山之间徜徉。 这叶小舟, 穿过了无数激流险滩, 正缓缓地驶入历史的新水域。 客家人, 把汗水和智慧, 植入这片炽热的土地, 一扇保持完整的雕花窗户, 透出一缕新的阳光。
我继续在赣州的怀抱里, 书写自己的日记。
记下了这些古朴, 这些遗风里的风骨;
记下了这些葱郁, 这些山冈上的绿阴;
记下了这些荣光, 这些世代传承的热血;
记下了一座城, 古老与现代交相辉映的乐章。
我还会重走一段古街, 重回一座古楼。
重新回到宋城厚重、 斑驳的墙砖前, 寻找当年月光留下的痕迹, 把浸润在赣州古宋遗风里的歌谣, 经久传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