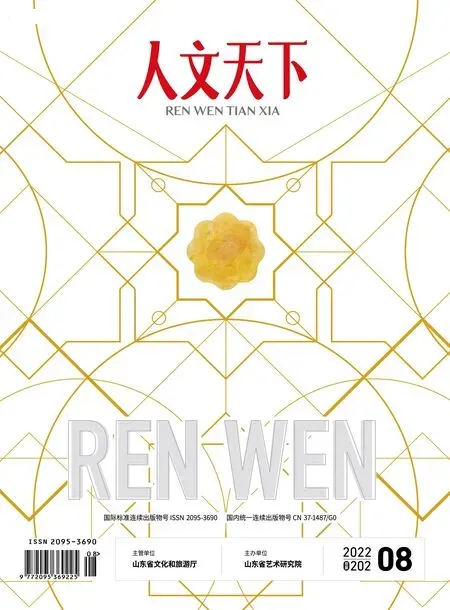戏曲艺术中女扮男装艺术形象成因与意蕴探析
——以黄梅戏《女驸马》为例
■ 刘天胤
戏曲艺术与中华文化相伴而生。作为黄梅戏经典曲目之一的《女驸马》,主要讲述了冯素珍为救爱人女扮男装进京赶考,中状元、成驸马,巧述真相,夫妻团圆的传奇故事。剧中最令人惊喜的就是女主人公冯素珍敢于突破封建社会对女性束缚的抗争精神,以及她女扮男装救李兆廷于水火,塑造了有勇有谋、聪慧过人的艺术形象。本文将以黄梅戏《女驸马》中冯素珍这一艺术形象为核心,联系相关作品,梳理戏曲作品中女扮男装艺术形象的成因,追问其艺术特色,探寻其背后意蕴。
一、诸因交互:女扮男装演绎的成因
《女驸马》因其曲折的情节、悦耳的曲调、流畅的唱腔而深受欢迎。明代剧作家徐渭曾写下《女状元辞凰得凤》的戏剧作品,不可否认,这对《女驸马》戏曲艺术具有一定影响,而且此前也早有女状元的民间传说。无独有偶,豫剧《花木兰》的故事也可以从北朝民歌《木兰辞》中得到印证。为何戏曲艺术中能够产生一批女扮男装的艺术形象,并在百年流变下得以稳定且大放异彩?笔者分析,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女扮男装的根源在于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性别束缚。正是由于传统社会出于男性和女性的生理差异,对二者的社会身份进行了明确的差别对待,才有了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以来“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划分,以君王、父亲、丈夫为核心的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很深。从先秦《诗经》中弃妇对自身遭遇的控诉,“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到建安时期蔡文姬作《胡笳十八拍》抒发内心之苦,再到明代冯梦龙笔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受尽欺凌的妓女形象,无一不是对女性卑微地位的反映。从这一角度来看,女扮男装这一艺术形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古代男女不平等,女扮男装展现出的抗争精神也在明清时期成为反礼教的代表。
其次,戏曲艺术作为高度综合性的艺术,文学文本的启发、诸多表演要素的支撑共同构建了女扮男装艺术形象的强烈戏剧性。一方面,我国民间艺术向来有传情达意的传统。《诗经》按照题材可以分为“风、雅、颂”三类,其中的“风”为国风,就是周代各诸侯国的民歌。天子派遣采诗官于各地采诗,借助民歌的形式,就把各地的民意汇总至中央。从《女驸马》的传唱能看出,这一故事既唱出了百姓的心声,也是其美好心愿的写照,希望女性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捍卫婚姻幸福,此外,抨击了冯氏父母嫌贫爱富、棒打鸳鸯的封建家长势力。另一方面,戏曲作为高度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吸收文学作品的思想情感、故事情节等要素,综合了乐曲唱段、舞台表演等表现形式,才成就了“女驸马”这类本身就极具戏剧性特征的艺术形象。恰恰是以舞台为中心重塑艺术叙事,才呈现出女驸马的独有魅力。舞台表演不同于剧本阅读,这样的艺术形象在舞台上更具视觉冲击力,天然更具戏剧性和颠覆性。
最后,女扮男装也离不开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影响。任一文艺形象都不会凭空产生,就算有意违背现有观念也是受其影响所致。诚如列许登堡所说,反其道以行也是一种模仿;圣佩韦也说,尽管一个人要推开自己所处的时代,但仍要和它接触,而且接触得更着实。因此,反叛也好,顺时也罢,都是当时哲学思想孕育的产物。一方面,中国社会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浸润,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对戏曲创作带来巨大的影响。当剧中女性被逼上绝境时,被儒家“知其不可以而为之”的奋发精神感召,突破生活中的常理,便诞生了女扮男装的传奇故事。于是冯素珍在紧急关头选择铤而走险,女扮男装为情郎诉说冤屈。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市民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儒家“心学”流派,呈现出对传统哲学思想的反叛。阳明心学强调“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的思想,认为理与人的天性本是一件事,并无二法,因此顺从了天性中的需求,便符合了“理”的约束。就冯素珍的遭遇而言,夫君被诬陷,自己又要被逼改嫁,这样不公的待遇显然与人性不和,与天理相悖,于是她女扮男装的举动虽带有反叛色彩,却与心学思想一致。
由此,以冯素珍为代表的女扮男装的戏曲艺术形象,其产生根源是封建社会巨大的性别沟壑,得益于戏曲艺术的高度综合性而直接成型,也深受中华传统哲学思想的浸润。这才形成了反抗却不追求颠覆的,于理不合、于情相谐的女扮男装艺术形象。
二、矛盾书写:女扮男装戏曲演绎的特征
诚如黑格尔曾指出:“在戏剧中,个人目的与他人和环境的冲突,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在《女驸马》的戏曲情节中“矛盾重重”是显而易见的——有冯家嫌贫爱富与冯素珍对困窘一时的李郎情深义重之间的矛盾,有封建时代媒妁之言难以跨越与男女真情不能割舍之间的矛盾,还有冯素珍作为女性的无助与她扮作男儿跳出无奈之间的对抗,从中可以归纳出临时越界、双重虚拟的艺术特征。
(一)临时越界:环境矛盾激化的产物与化解
通观多部涉及女扮男装形象的戏曲情节,这一形象都具有临时性特征。女性形象选择女扮男装大多是环境矛盾激化的结果,以女性身份无法化解矛盾,于是她们选择临时越界,扮作男子,应对矛盾。而在矛盾化解之后,她们没有继续以男子身份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利,而是如凯旋将士“卸甲归田”一般,重拾女性身份。这促成戏曲舞台上女扮男装艺术形象临时越界的特征,这一前一后两次惊险跨越自然也是剧作的中心看点、戏剧矛盾的焦点。《女驸马》中,冯素珍在李郎被父母诬陷收押后,想到自己一介女子无处说理,无奈之下,她女扮男装突出重围,借用李郎姓名,扮作男子进京考取功名以搭救心上人。这时,她完成了第一次身份转变。男子身份的扮演也不是一帆风顺,女扮男装的冯素珍中状元后,马上被媒人刘大人指婚给公主,“女驸马”这一荒诞的名词就诞生了。
那么,冯素珍如何从男子变回女子,如何向公主尽诉衷肠,如何在殿前引导皇上承认自己的身份,这第二次性别跨越是核心焦点。这一矛盾的化解直接促成她舍弃男性身份,名正言顺与夫君成婚,以贤妻形象成就佳话。因此,剧中冯素珍由女性身份转化为男性,再由男性转化为女性的两个关键过程,就是环境矛盾不断激化再到化解的过程。
(二)双重虚拟:情的渲染与弥散
戏曲的魅力之一在于虚拟性。虽然情节是虚构的,但经过艺术手法的处理,人们愿意相信一个个美丽的梦。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是戏曲艺术本身的虚拟性。主人公以代言的形式,说唱演绎的内容都生发于“情”字。其中包含了叙事中的事情,也包含了自白中的感情。所以第一重虚拟是戏曲艺术本身的假扮性中具备的虚拟,通过情感勾勒出独立于现实世界的舞台艺术空间,让戏曲中看似松散的唱段演绎融为一体。
而有女扮男装艺术形象的戏曲作品中显然存在第二重虚拟——女性人物要扮作男性形象,于场上要瞒天过海,于场下要引发共情。戏曲艺术是舞台表演艺术,从戏服装扮再到唱腔都要令女扮男装者与其他舞台要素融合。以《女驸马》为例,扮相虽是一袭红袍的状元郎的男子扮相,但观众很容易发现女扮男装的打扮。而唱腔方面,表演者虽有意模仿男声,但更加纤细婉转,若男声是山、女声是水,那么这冯素珍女扮男装的唱腔宛如山中之玉,温润透亮。
那么,为什么这种能被一眼识破其性别的艺术形象会被历代观众认可?无外乎是共情者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女驸马》中,冯素珍的心愿是救出惨遭诬陷的相公,她是封建社会中不公的受害者,站在了道义一边,她含情脉脉的自白不断感染着观众。当观众与人物共情,看似不合理的第二重虚拟也成了能够说服众人的真情所在。可见,女扮男装的艺术形象在戏曲舞台上相较于其他形象,通过双重虚拟性这一特点,更加突出了情的作用。
三、女扮男装艺术形象的意蕴
中华美学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因此,我们可以从戏曲表演背后看到悠远的意蕴、深层的内涵。结合上文呈现的艺术特征,女扮男装艺术形象的意蕴可以从艺术形象本身上升到抗争精神与抗争性之间的斗争表现。
(一)反叛与无奈:抗争中的世态炎凉
从戏曲文本发生的故事背景来看,这种女扮男装是女性的反叛。封建社会的女性要谨遵“三从”“四德”,大家闺秀更是困守闺房。争取作为人的基本自由和掌握自身命运,是封建社会女性不敢奢求的梦。这一形象的反叛精神就体现在,冯素珍作为女性也能考取功名,花木兰作为女性也能建功立业,祝英台作为女性也能读书恋爱。女扮男装的形象下,她们做了寻常女子不能做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她们所争取的只是被平等对待,她们换做男儿身份时的新奇、喜悦和惊奇也反衬出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多么备受压迫。冯素珍在坦白自己的女性身份后说道:“公主生长在深宫,怎知民间女子痛苦情?王三姐守寒窑一十八载,刘翠屏苦度了一十六春,还有前朝英台女,生生世世爱梁生。”这些女子也都是受尽摧残,均留下了悲剧。
因此,《女驸马》中冯素珍的喜,虽说是反叛后的欢呼,也能看出反叛后的无奈,因为她无力争取自己的幸福,只能通过伪装来求安稳。因此,这是更深层次的,家庭、社会和时代一起施加于命运的悲剧。戏曲作品以喜乐的形式展现一个女子的默默承受与挣扎。这样的艺术形象催生人们思考与关注,促成了剧目的传唱不息。
(二)情感与理性:戏曲场上的自然意境
王国维在论述真正之戏曲时指出,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考据作品是否为“代言体”,即剧中人均以第一人称进行自我表达。因此,戏曲作品中,人物流露心声,把稚嫩的心头话都唱出来,并未被指称为“荒唐”,而是人物的真情而已。哪怕是《女驸马》这样涉及女扮男装而故事情节百般曲折,冯素珍扮作男装考中了状元,也要自顾自地“解说”一番,“是我顶替李郎之名前来应试,不料中头名状元”,高兴到极致,她还要再唱一段:“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元。中状元、着红袍,帽插宫花好啊好新鲜。”把冯素珍的心声完完整整地唱了出来。这样过于明白的表达套用日常生活的逻辑自然显得荒唐,但这就和小孩子藏不住心事一样,自然而然地全说出来罢了。这也正契合了王国维在评点戏曲美在何处时所说:“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这种自然而然的戏文,以歌舞演绎出来,就把人物心声呈现在舞台。一时间,这朴实自然的意境,直教观众震撼——世间冷暖都能被直白地说出来,尔虞我诈的世俗都能被唱明白,这与生活中对情绪的克制,对言行的忍耐,对个人形象的维护形成了反差。
特别是在以《女驸马》为代表的、存在女扮男装艺术形象的剧作中,冯素珍敢扮作男子进京科考,敢在帝王面前道出身份,敢在众人面前痛斥封建家长“嫌贫爱富贵”,这都是女性人物心声的自然流露。如此自然的意境把人的真实心境鲜活地呈现在舞台上。其间的“真”与“假”确实存在,但假的是表演程式,真的是人物性情;这逻辑与荒唐也真实存在,只不过荒唐的是有违常理,逻辑走向却从不违背人间道义。
(三)阴阳与归并:突破对立的传奇视角
中国古代先民曾提出“阴阳学说”,“一阴一阳谓之道”(《周易》)。道分阴阳,天地、日月、生死、五行、八卦都在阴阳对立统一的变化中生生不息。与之相对应,性别中也体现了阴阳之说,“所谓夫夫妇妇而家道正矣。天之道一阴而一阳,人之道一男而一女”,女子为阴,男子为阳,两者本是独立的、对立的。但在女扮男装的戏曲形象中,产生了特殊的调和现象——阴阳的归并。男女的性别对立本是通过婚配结合走向统一,但在女扮男装的艺术形象身上,她们自己就成了阴阳归并的产物——男性和女性的经历、视角在她们身上同时具备,融为一体。
《女驸马》中,当冯素珍还是女子时,她代表着阴面,被困深闺,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好心救济李兆廷,却成了父亲诬告他的罪证。而在冯素珍女扮男装之后,就实现了视角的跨越,男性的身份让她看到了代表男子的阳面。这时,她可以经历男子才能经历的世事,如考取功名、迎娶公主等,以女性的视角体验属于当时男子的经历,阴阳的对立或矛盾在这时归并为一。因此,冯素珍的女扮男装之身,既以男性的身份紧握自己的命运,挑战封建家长制的权威,又以女性的视角为广大女性同胞尽诉衷肠。
这样阴阳并归的女扮男装之身超越了性别对立时的局限性,她们可以看到男权社会中“不在场”的女性命运是怎样的。如前上文所提及的《女驸马》中,冯素珍向公主和皇上阐述代代女子的不易。女扮男装的艺术形象可以超越男女各自所属的视角局限,看得到社会宏观的恩怨情仇,也能阐明最难看透的闺中情、女人心。而阴阳的并归也是对传统的超越,女扮男装的视角突破也超越了个人的局限性。她们的存在就是一种倔强精神,不断反抗、试探,最后遵从内心又找回了自己的女性身份,这也是对自我的更深层次的认可。在经历了世道繁华之后,还能找回本心,能够拿得起放得下,更能体现女扮男装艺术形象的境界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