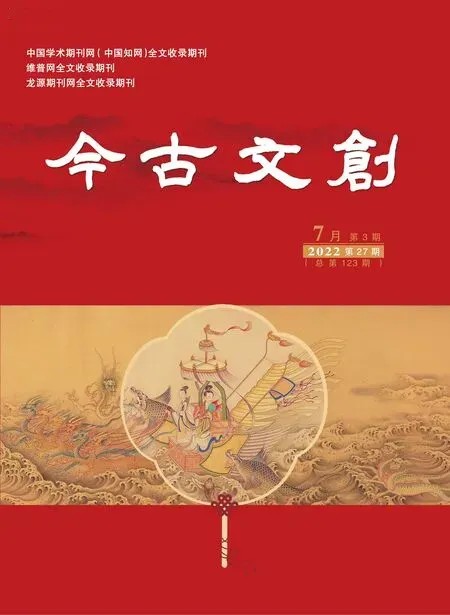二元对立视角下《食罪人》中的生存困境分析
◎谢雪琳
(烟台南山学院 人文学院 山东 烟台 265700)
一、引言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著名的女作家,她创作的小说、诗歌、儿童文学等不仅见解独到、主题鲜明,而且叙事简洁、技巧创新。其作品多反映“作者对人类命运(特别是女性命运)、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生命的价值的独特思考。”因此不仅在加拿大,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并且收获了国际上众多文学奖,更有“加拿大文学女皇”的美誉。通过查阅资料可知,对阿特伍德作品的研究多集中在其长篇小说上,如《使女的故事》《可以吃的女人》《羚羊与秧鸡》等等。研究角度主要有女性主义、生态批评、后现代叙事等方面。
相比之下,研究者们对于阿特伍德短篇小说的关注却较少。短篇小说《食罪人》首次出现在阿特伍德第二部短篇小说集《蓝胡子的蛋及其他故事》中,后来又被选入1996年伦敦版《跳舞女孩及其他故事》短篇小说集。对于该作品的研究,有2012年杨雪琴的论文《女性精神深处的冷静剖析:析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短篇小说“食罪者”》,通过对主人公、故事情节及结尾进行分析,聚焦于女性的自我选择,体现了阿特伍德对社会文化心理的关注,让读者明白女性必须克服巨大的历史惰性和心理惰性才能走出男权的压制的牢笼。还有2018年何璐娇、刘明录的论文《论〈食罪者〉中的主体生存焦虑》,从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角度来分析主人公的生存焦虑,从而揭示作者对自我本质和后现代主体状况的思索。
小说《食罪人》套用民间故事,描写了患有精神危机的“我”与心理医生约瑟夫之间的故事,并通过食罪人与施罪人、男性与女性、消极自杀与无奈生存这三组对立,展现了后现代人们的生存困境,因此,从二元对立角度对该作品进行分析可以帮助读者更加全面地理解作品所传达的意义。
二、二元对立理论
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盛行,有“现代语言学之父”之称的索绪尔在其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了一系列二元对立概念,如:能指与所指、历史性与共时性、语言与言语等,这成为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他认为,语言结构就像科学研究,因此,应该使用如二元对立这样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分析。分析的过程需先将研究对象分解为一些结构成分,再从中找到既相互对立又互有联系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或结构又总是呈相互对立的状态,以此形成区别和对比,从而在另一层面上产生新的意义与价值,研究者因此可以从不同角度重新认识并把握对象结构的复杂性。因为二元对立现象广泛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所以,该理论也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分析方法。多年来,学者们在借鉴索绪尔二元对立理论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创新研究该理论。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曼·雅各布森将一对新的对立项:选择与组合,引入到诗歌的分析中,得出“诗歌作用把相同原则从选择轴投射到组合轴”。他指出,选择与组合是诗歌语言的主要模式,同时也是造成诗歌复义的主要原因。
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将二元对立理论引入到人类学研究上,最为著名的就是他对于古希腊俄狄浦斯神话的分析:将神话现象进行分解,然后按照共时与历时这对对立框架重新组合,最后发现其深层结构,得出“俄狄浦斯神话反映了人类对自己起源的思考”这一结论。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是位颇具矛盾的学者,虽然从未给自己定位,但他的著作与思想却明显地具有结构主义特征。他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是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自我封闭的体系……只有通过找出文本中的代码或二元对立才能解释文本中隐藏的信息”。如上文分析,小说《食罪人》中存在三组二元对立,阿特伍德正是通过这些对立与冲突的矛盾展开故事情节,反映后现代人们的生存困境。
三、《食罪人》中的二元对立
(一)食罪人与施罪人
“食罪人”是存在于基督教文化中的一类人,同时也是一种职业。在小说开篇,阿特伍德就介绍了它:“多半是在农村,有一种人,叫做食罪人。每当有人临死的时候,食罪人就会被请去。那家人会准备一顿饭菜,摆在棺材上面……食罪人会狼吞虎咽一番,还会领到一笔钱。他们相信,那个行将就木的人一生中所积累的所有罪孽会从他的身上移走,转到食罪人那里。食罪人因而完全被别人的罪给撑得饱饱的。”食罪人在这里充当罪孽新的宿主的作用,每吃一餐,她们就多负担一层罪,罪孽日积月累,终会将其吞噬。在基督教教义中,饕餮罪,即贪吃、暴食之罪为七宗原罪之一,历来受到谴责和讨伐。这里,食罪人在吞食别人罪孽的同时,正是犯下了饕餮罪,那谁又会主动成为她们的食罪人,减轻她们的罪孽呢?因为食罪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尽管她们消去了已故人们的罪孽,但并不会因此得到尊重,相反,大家认为“她身上负的罪业实在太过深重,谁也不愿意和她扯上一点关系;一种灵魂的梅毒,就可以这么说吧。甚至连和她说话都是忌讳,当然了,又该叫她去吃饭的时候除外。”从中可知食罪人的命运十分悲惨。
在小说中,身为心理医生的约瑟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现代社会的食罪人。他通过倾听病人们的痛苦,即吞噬他们的罪孽,来为他们治病。文中的约瑟夫其实代表着耶稣,二者都承担着痛苦来完成上帝对人类的救赎,不同的是,耶稣“因受苦难而得以完全”。他依照上帝的旨意来到人间,经历着世上的苦,直到被钉在十字架上,达到了苦难的顶峰,因而也获得救赎上的完全胜利。耶稣顺从地将生命献上,使人们可以因此洗净自己的罪孽,从而进入到上帝的荣耀中。
因为所受的苦难,耶稣具备足够的能力去救赎世人,但约瑟夫的施救之路却异常艰辛。文中对约瑟夫的描写“趿着绛红包的皮革卧室拖鞋,鞋跟的地方已经踩平了,鞋尖磨坏了,还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开襟羊毛衫,烂泥一样的米黄色,一看就是地下室里清仓甩卖的便宜货,嘴里抽着烟斗,他的头发斑白稀疏……”再对比耶稣的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二者之间强烈的反差更加突出约瑟夫生活的压力与不易。不仅如此,他的“办公室就像他本人一样邋遢,闻起来像是没有倒掉的餐盘,脚臭、穷酸潦倒和呼出的浊气。”生活如此潦倒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总是收一些其他人来碰都不愿意碰的特别穷的病人,另一个原因是他三次婚姻都失败了。作为一名心理医生,他在工作中吸收了太多的痛苦,承担了太多的压力,他十分渴望理解,于是他希望“我”作为他的食罪人,希望“我”倾听他的痛苦,但是“我”却并不乐意。“我”认为,付钱给他并不是“要听他讲他家里的植物……是为了让他能听你讲你自己的故事”。并且当约瑟夫询问是否喜欢他时,“我”虽然语气平静,实则怒不可遏地拒绝了他。此时的“我”是以施罪人的身份存在,只希望约瑟夫可以吞噬“我”的痛苦,却并不愿意做约瑟夫的食罪人,来减轻他的痛苦压力。这种对立的身份使约瑟夫的痛苦得不到排解,最后,他被无边的罪孽吞噬了,某天在修剪树枝时,从六十英尺高的树上掉落下来。
(二)男性与女性
“二元对立来源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只认可二项中被社会所尊崇的一项,即所谓的‘中心’或‘本源’,因而从本质上来讲,二元对立要求的是一种对自封为‘中心’的‘我’的趋同,因此任何背离‘我’的‘差异’都是无法容忍的。”正是这种思想,加深了男女之间的差异,从而强化了男性的支配权利,女性因此沦落为“他者”的附属地位。例如,当约瑟夫给“我”讲述食罪人故事时,他用“她”这个字眼,这意味着 对于约瑟夫来讲,这些食罪人本身的性别并不重要,因为在他看来食罪人就是女性。他将食罪人被罪恶吞噬的结果转移到了女性身上,这种无形的歧视使女性成为被动的受害者。
再如文中“我”及约瑟夫的三位太太一样,都没有自己的名字,因为名字代表着一个主体真实的存在,是个人身份的象征,所以以我们为代表的女性只能扮演为人妻、为人母这类依附于男性的角色。正如法国著名女性主义者西蒙·德·波伏娃指出“女性生活在一个按照男性观念建立起来的世界中,其生活准则是根据男性的愿望建立起来的”。在父权制思想牢笼的禁锢下,女性并不被提倡有自己的想法,一个聪明的女人会被叮嘱说,为了你们自己着想,“应该去挨一刀,把大脑额叶给切了”,所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食罪人》中那么多的女性都存在精神危机,阿特伍德正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她们对自我的生存和与他者的关系的困惑与迷茫。
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立还体现在双方互相不理解这方面。作为约瑟夫的一名病人,“我”的生活是如此不尽人意,如此徒劳虚妄又看不到尽头。“我”与丈夫处于半离婚状态,他住在别的地方,而“我”的两个儿子正处于青春期,我们之间的交流也很少,因此,“我”的心理和精神上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看不到现实的意义,所以,我希望约瑟夫能够让我相信现实是完美无缺的。但是,约瑟夫却赞成“我”的说法,他说“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一大坨屎”,“我们唯一拥有的就是这世界……只能因地制宜。你不会无力承受。不会有人向你伸出援手。”5从约瑟夫平时生活及工作状态中也可以知道现实的无奈。
约瑟夫有过三次失败的婚姻,在他的葬礼上,第一任太太对“我”说:“我和约瑟夫住在一起的时候,一天到晚会出事,半夜两点钟打来电话,每次都是要自杀,那时候发生的事情,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作为一名医生,约瑟夫深受病人们尊敬,“他们当中有的人觉得他就是上帝本尊。”但是,他的食罪之路却给妻子们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三任妻子都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婚姻最后都破裂了。约瑟夫独自承担离婚及工作带来的痛苦,他渴望得到女性的理解,也曾寻求“我”的帮助,但“我”也没能理解他,觉得他对我的需索超过了我所能给出的限度。没有人愿意成为他的食罪人,他的灵魂因此得不到救赎。阿特伍德认为:“两性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础,良好的社会环境能促进和谐的两性关系,反之亦然。”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性与女性都是受害者,而造成双方对立的原因正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两性关系的误解。在这里,阿特伍德“将男性与女性放置到相同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审视他们的存在与精神状况……她对于人类精神世界的关注并非仅限于女性,而是涵盖了两性和对整个人类状况的关怀。”
(三)消极自杀与无奈生存
在阿特伍德的小说中,生存是其固有的中心主题,但事实上, 阿特伍德对于生存的关注多来源于她对死亡的思考。《食罪人》中,心理医生约瑟夫的死贯穿全文,表面上看他的死是一场意外,因为树枝将花坛的阳光挡住了,他想去修剪,所以才从六十英尺高的树上掉下来。实际上不难发现,这里许多事物都具有象征意味:六十英尺高的树代表着约瑟夫日积月累的罪孽,而树挡住了花坛的阳光则意味着他所承担的罪孽太过严重,已经将他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完全吞噬了,他试图去修剪树枝时,却发现早已无能为力。正如他的第二位太太对“我”讲,“他不是摔下来的”“他过得并不快乐”“他很擅长撑门面”,她是想暗示“我”约瑟夫是自己跳下去的,但“我”并不愿意去相信约瑟夫的阴暗面,“我”希望他永远如看上去那样:可靠、能干,睿智和清醒。约瑟夫曾问“我”有没有最讨厌的人,并说自己长久以来,一直对八岁时住在其隔壁的男孩怀恨在心。因为他从小是在贫民窟长大的,生活艰苦,但他会在自己家门口那块坚硬的煤渣地里种植向日葵,虽然仅存活一株且营养不良,但属于自己的向日葵象征着他的希望。然而,向日葵却被这个男孩拔掉,这不仅粉碎了他的希望,也使他产生杀死那个小孩的决心。
在小说结尾,“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约瑟夫,还有一个人拿着一朵硕大的黄色鲜花,试图令约瑟夫关注他,然而并没有引起回应。从前文可以看出,这个人就是小时候拔掉向日葵的那个小男孩,这朵黄色的花是向日葵的暗示,也是小时候约瑟夫的希望所在,但他选择了忽视,表明其内心心灰意冷,再也承受不起生命的负担了,不再找寻希望,就此放弃生命中曾最珍惜的东西。幼时的创伤一直令约瑟夫无法释怀,而长大后的处境却愈加艰难,最终,他选择跳下来,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得到解脱。
约瑟夫离开了,虽然他选择了一种消极的行为,但在如此冷漠又艰辛的生存环境中,他的选择不足为奇。然而那些一直以来以施罪人身份存在的,极其依赖约瑟夫的病人们,他们该何去何从?当“我”听到约瑟夫死讯时,“我”火冒三丈,为他擅自抛下我们不管而生气,“我”不相信这个事实,希望是他开的某个玩笑,接着,“我”非常迷茫,一直思考“我该怎么办?”因为长久以来,一直是约瑟夫当“我”的食罪人,倾听“我”的痛苦并给出建议,“我”并不能够真正独立起来。正如当约瑟夫问我“你被困在了岛上,现在你得决定如何尽力去应对”时,“我”回答,“直到获救嘛?”他说,“救援嘛,死了这条心吧。”“我”说,“我做不到。”从中可以看出虽然我对男权社会现状很不满,但是当遇到困难时,首先想到的还是依赖男性的救援。在约瑟夫葬礼上,“我”注意到并没有食罪人,于是,“我”开始焦虑,“我不知道约瑟夫会不会有什么让他良心不安的事情……我还是觉得这就像是哪里疏忽了一样。那么约瑟夫的罪过怎么样了呢……那些罪恶就在我们四周盘旋,抛在空中,在那一只只低垂的头颅顶上。”这时,“我”已经产生了作为约瑟夫食罪人的意识,这是“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现实和文化心理对‘我’塑造的结果。”因此,当梦到约瑟夫让我将那些外表是星星月亮形状实则是他的罪孽的饼干吃掉时,虽然“我”觉得“这些实在是太多了,说不定我会恶心的。也许我能把他们退回去,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于是接受了食罪人的身份。弗洛伊德认为,“梦里所梦的是真实 (真实的回忆) 的呈现,而相反的,那些梦里所表现的其他事物则是梦的愿望而已。”梦境看似离奇,实则在虚实之间反映出做梦者潜在的心理状态,也表现了“我”在约瑟夫去世后,被迫成长,被迫找寻出路的无奈。
四、结语
如耶稣一样,约瑟夫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洗净人们的罪孽,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走进上帝的荣耀中,生活反而更加艰辛与迷茫。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分析《食罪人》,可以发现后现代人们的生存困境:人们之间孤立、冷漠,男性与女性互相不理解。然而,极度偏僻孤独的生存状态会使人异化,因为它必然会压抑人的情感和欲望、造成人性格畸变,严重甚至还会自杀,这就解释了《食罪人》中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患有心理疾病。在这压力重重的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既是对方的施罪人,又是食罪人,互相排斥又依赖,因此,唯有不断调整自己,不断去适应才能更好地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