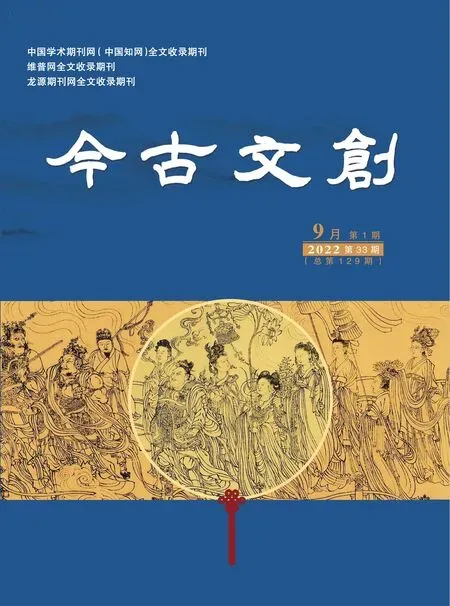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阐发
◎郑毅平
(重庆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渝北 401120)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并由其后继者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形成、发展和绵延流传下来的文化精华,“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理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逻辑理路,对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精神文化需求,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提升文化自信、文化软实力,构筑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纵向承继中因“扬弃”而独具特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植于农耕自然经济和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马克思曾经指出,“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的差异主要来源于社会存在的不同。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在自然面前显得渺小无力,不得不以群居的方式生存。社会存在中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在人类早期文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也间接促成了人类文明间的差异。我国所处地域,大部分是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水流纵横,“农耕经济”占据主流。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带来了天然的优势。“稳定的农耕生活,使得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了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以及熟人社会‘长幼尊卑’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中华文明。
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世界上不同国家间相互竞争的大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每一个人的需求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商品经济逐渐替代了自然经济,世界交往不断扩大,那些古老的文明国家都或主动、或被动的被卷入到资本全球化浪潮之中,那些服务于封建统治的社会意识、那些古老文明传统文化的根基通通都被“摧毁”了。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在这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是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为口号的资本主义文化以及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文化全球化进程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世界交往的形成,不仅促进了物质生产力的提高,而且促进了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世界各国的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相互交流、竞争和借鉴。为了能提升中华文化竞争力,我国文化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和推陈出新。旧有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家庭血缘为纽带、伦理道德为规范的中华传统文化,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的要求,但由于社会意识内部各要素,有继承性和相互影响性,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就成了时代的呼唤和必然的选择。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双向奔赴中相竞争而发展繁荣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然而,任何一个科学理论,都需要不断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运用有其特殊性,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面临着不同的基础条件、发展阶段、文化差异、国际局势等,自然也要求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不顾各国的实际情况,照搬照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才适用的理论,就可能将这些理论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依存、渗透和转化。在中国大地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互依存,二者缺一不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可动摇。中华文化则博大精深,历经数千年的兴衰更替依然生机盎然,在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艺术、哲学等多个领域都有深厚的底蕴,在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还相互渗透和转化。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践向我们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血脉”和“独特标识”,马克思主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指路明灯,二者在中国人民“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伟大实践中,相互渗透和转化。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相互竞争中走向升华。中华文明及文化,发源于两河流域,在社会意识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马克思主义则不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商品经济”盛行,社会进入“大工业”时代,资本家以购买劳动力的方式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更加剧了工人的苦难,为了实现大多数人的幸福,马克思开创了以“消灭私有制”为核心,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内容,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既有上述差异,也有竞争。这种竞争则主要体现在,作为社会意识,二者都会争相对社会存在产生能动的反作用,其结果是先进的社会意识,推动社会存在的发展,而落后的社会意识,则阻碍社会存在的发展。在这样一种竞争中,二者会有规律的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向奔赴,最终发展繁荣、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同频共振中因成功而更加坚定
“以西为师”的迷梦破碎后,俄国十月革命为我国展现了一条全新的发展路径。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借五四运动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彻底批判,人民旧有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被否定,中华文化的合理内核则被保留了下来,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发展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方向。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光辉典范。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十分重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强化了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引领与指导,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炼、宣传和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共鸣和强烈反响;倡导全社会坚定了文化自信,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完善了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巩固了思想教育主阵地;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精神,延续了红色基因、传承了红色血脉。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鲜活的实践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及时回答了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实现了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展现了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自觉和责任担当,中国人民在文化上更加自信、思想上更加统一、经济上更加富裕、政治上更加坚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事实向我们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方向。
时代呼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紧密的结合。100年来经过无数革命先烈的接续奋斗,中华民族终于从饥寒交迫、受人欺凌中,“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中国人民的奋斗之路仍将继续,但也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在经济领域,发展速度放缓,产业亟待转型升级,资源消耗巨大,环境污染严重;在民生领域,人口老龄化加剧,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求更多元化、高质化,“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了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在精神领域,仍有许多人思想空虚、迷茫、理想信念缺失,以金钱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盛行;在国际关系领域,后疫情时代来临,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际竞争加剧,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外国势力经济上悍然发动贸易战,政治上不断挑衅,而思想文化上则继续沿用针对苏联的和平演变策略,借助各种渠道向中国人民兜售“普世价值”和“民粹主义”等错误思想,借以消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合理性,以期动摇我党的执政根基。为了应对日益加剧的风险挑战,加强人民的思想建设,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就尤为重要。推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成了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期盼。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同向征进中因相近而更易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诸多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极为相近。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都以唯物辩证法为哲学基础。中国早期的“五行学说”,在社会上占主流地位,有广泛的影响力,被用以解释天体星象、生老病死、中医脉理等各种现象,虽受社会历史条件限制不够发达,但它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认可运动是物质固有属性,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一脉相承;中国最早的哲学著作《易经》提出“变易”思想,将事物的运动发展当作过程来看待,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不变的,它还将64个卦象分为了32对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体现了唯物辩证法“联系”“发展”和“矛盾的对立统一”的观点;“善不积不足以扬名,恶不积不足以毁身”(佚名《易传·系辞传下》)、“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李耳《老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王充《论衡》)等名言警句,则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量变质变等规律”。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都注重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相结合。中国人自古就十分重视实践,儒家思想倡导“学而优则仕”(孔子及弟子《论语·子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曾子《礼记·大学》)、“知行合一”(王阳明),鼓励用学到的知识改造这个世界。虽没有认识到实践决定认识,但已然通过生活经验总结出了“近山识鸟音,近水知鱼性”(佚名《增广贤文·上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的结论。虽未得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也深刻地认识到从结果去反思理论是否正确的重要性,形成了中国古代的经验社会,并用各种历史著作和故事去警示后人,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十分相近。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有共同的理想与价值追求。在对未来理想社会畅想上,中国古人面对现实的压迫和苦难,曾提出“世界大同”(戴圣《礼记·礼运篇》)的社会理想。在大同社会中,全民公有、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得其所、各尽其力,与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极为相近。在价值观上,中华优秀儿女,始终有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日知录·正始》)的家国情怀,“民贵君轻”(孟子《孟子·尽心下》)的人民理念,人的社会属性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公共性”与马克思主义坚持的“人民性”极为相似。
五、结语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呼唤,历史和现实都向我们证明二者能够结合,也必将在结合中走向更光辉的未来。在建党百年之际,我们应该认真领会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定文化自信,重塑中华文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