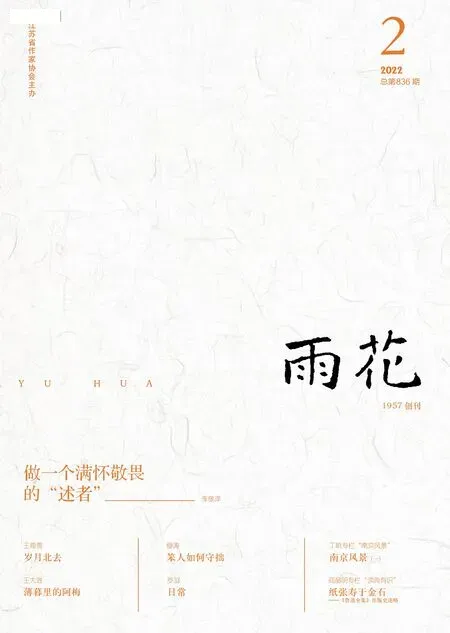做一个满怀敬畏的“述者”
——在“凤凰文学之夜”的演讲
李敬泽
来到南京,往往触类而思,因物兴感。昨天开会的时候,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孙晓云的字,是宋濂的《阅江楼记》,“阅江”是看尽一条大江,“见波涛之浩荡,风帆之上下”,也是读一条大江,从六朝风骨读到今日。这便是金陵气象,外人来此,往往目眩神摇。
金陵有“慨而慷”、有“今胜昔”,有“虎踞”、有“龙蟠”,还有“凤凰”。这两天开“凤凰作者年会”,天地之大,品类之盛,身处其间,我是诚惶诚恐,越发地不敢伸腿不敢张口。苏童老师、毕飞宇老师、韩东老师,还有刚才的各位,哪一位都是比我更好的作者,都写出了比我更好的作品。特别是下午见到了丘成桐先生,我马上想到:人和人之间的DNA 差别据说只有千分之一,但这千分之一有时就是千里万里,邱先生在云端上,而我的数学才华只够在地面上加减乘除。
作为一个作者、一个文学人,登阅江楼,那是我所欲也,我怕的是上“阅书楼”,我很怕去书店,也不爱去图书馆。每次去书店、去图书馆,我都觉得特别受伤。面对那么多书,你真会觉得,天下的真理和道理都被人说完了,天下的好故事都被人讲完了,天下的美辞章也被人写尽了。而且,他们还写了那么多!这个时候,你就会陷入自我怀疑,回到家,面对电脑,孤灯长夜,搜索枯肠一个字一个字写下去,这到底有多大的意义?世间是否真的就少你这一本书?这次参加“凤凰作者年会”,对我来说,就相当于泡了一次书店与图书馆,内力大损。但是,转念一想,这样的境遇和这样的想法,其实不仅我有,我们的老祖宗、我们的孔夫子,他也和我一样。
孔夫子“述而不作”。他一生不承认自己是一个“作者”,他不打算成为一个作者。这是因为,孔夫子觉得,面对自然大化,面对人间万象,面对先人的智慧,我们只能谦卑地做一个“述者”,我们无法成为“作者”。
在中国传统中真正确立起“作者”这个概念,是自司马迁始。写一部书,藏之名山,传诸后世,这部书的后面立一个不朽的作者。然而,在我们整个的古典时代,“述”的精神依然是文学的基本精神,所谓“文以载道”,就是承认在我们的书写之上和之中,有一个更高更大的“道”,我们的“作”不过是在“述”道。我们的小说,四部古典,都很伟大,但其实,直到现在,它们的作者是谁也不过是姑妄言之姑妄信之。这不仅仅是文化条件所限,那些作者,《三国演义》的作者、《水浒传》的作者、《西游记》的作者,还有《红楼梦》的作者,他们也许真的不太在意自己是张三还是李四,是施主还是吴子,他们把自己看作一个述者,故事天下流传,他们只是再讲一遍。人家告诉我们,《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但是,我们读一读《红楼梦》的第一回,雪芹把自己的名字放在那里,但他并没有承认自己就是作者,他只是说我在悼红轩里“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已经有了一个稿子在那里,这个稿子在石头上,我只是一个“编者”,是个编辑。这是谦虚,也是大骄傲,因为孔子所做的事也不过是披阅增删,孔子就是一个伟大的编者、述者。
这件事到了现代就不一样了,我们必须是个作者,否则就什么都不是。“作者”完全是一个现代概念,我们设定,一个“作者”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因为独一无二的自我必须通过作品实现和展开。这时就没有什么编和述了,他是在创造。什么叫作“创造”?就是要有光,于是有了光,创造这个词就是“作”,是孔夫子不敢说的,孔夫子不认为自己在面对自然、面对传统时可以说:我在“创造”;在西方,古典艺术的根本原则是摹仿,这也是“述”,后来上帝死了,才有了浪漫主义的“创造”。现代性设定和建构了这么一个“创造”的概念,在“创造”的背后,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非常了不起的“自我”。这个自我是一个意义中心,由自我出发,我们去创造,去实现这个自我;所以创造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我们确实有一个了不起的、独一无二的自我。
很好,我没有意见。自现代以来,所有的作家都是这么想的,我也常常这么想。虽然我也常常觉得,这很像我家的那只猫,它最喜欢的游戏就是循环论证,自己追咬自己的尾巴。
但是,我们现在又进入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时代。在过去,成为一个作者、写一本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可慰平生,可告祖先;但是现在,刷一刷微博,看看朋友圈,你就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人都成了作者,每个人都觉得:我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自我”,要天天展开,要言说、表达和创造。这当然是好事,天大的好事,但有时我也会想,我们真的有那么多来自自我的东西需要表达吗?我们真的有那么独特以至于不说不足以平天下?我们以为自己是作者,是不是此处应该念平声,我们其实只是“作”者?
互联网时代是一个盛产自我的时代,你到微博上、到朋友圈里去看看,每日每时我们都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自我的碎片,天天都有一地的鸡毛。当然,这其实也是在给平台打工,是为互联网资本日复一日不计报酬地生产劳动,这种劳动,是以不断地生产“自我”、不断地输出无数“独一无二的自我”为形式的。
赶上了这样一个时代,或许可以让我们重新理解,艺术中、文学中的“自我”,到底是什么?这件事如果展开谈,今天晚上谈到半夜,可能还是没法说清楚。索性我就跳过论证,直接说出结论—我不认为自己是什么“作者”,或者说,我并不首先要成为一个“作者”;当然,我也不敢说自己是一个创造者,我并不相信,我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自我,尽管人和人的差别可以像我和丘成桐先生那么大,但是,我并不想站在这个千分之一的差别点上顾盼自雄,我宁愿向着那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敞开,向我们的孔夫子学习,努力做一个“述者”。
多少年没见的老朋友郭平,他写了一部书,叫作《广陵散》,他写的是古琴。我相信自己是一张琴,也许是一张好琴,也许是一张破琴,好琴破琴都是那七根弦,金木水火土文武,这世界的风吹拂着我,人类的手拨动着我,我才发出了声音。面对着山河大地,面对着人间万象,面对着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伟大祖国与时代,我想做一个满怀敬畏、倾尽全力的“述者”。
做一个“述者”也不是容易的事。孔夫子“韦编三绝”,我们也要《每天挖地不止》(林那北小说),还要《嚼铁屑》(甫跃辉小说)。同时,我也认为,不能仅仅在现代尺度里看待我们的志业,在更长的文明尺度上,在一个科幻式的宇宙视域里,“述者”可能是更重要的,正如孔夫子比我们所有人都重要一样。所以,只好向孔夫子学习,做一个“述者”,在“述”中去争取那一点点的“作”、一点点的“创造”。
“凤凰”是一定要飞的。凤凰于飞,翙翙其羽,在飞起来的凤凰身上,羽毛五色斑斓。在座的都是凤凰头顶上的毛、翅膀上的毛,而我希望自己能够聊附凤尾,做凤凰尾巴上的、小小的一根羽毛。随着凤凰的高飞,也许,我也能够跟着飞起来,看到波涛浩荡、风帆上下,同时,在凤凰的《不老》(叶弥小说)中想象自己的不老。
但不老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身体终究都会老去,我们的那点浮名也会变老,直至烟消云散;只有山河、岁月,这个壮阔的人间,才会真正地、永远地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