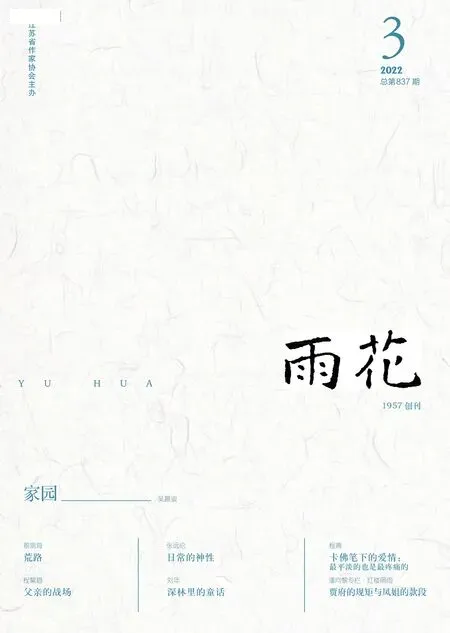1998年的望远镜
周齐林
多年后,当我把目光重新聚焦在十三岁那年的黄昏,当时的我正在家里津津有味地看着动画片。夜的幕布缓缓落下,闷热的空气里开始有了些微凉意。这个看似普通的黄昏,随后就露出它狰狞的一面。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荧幕,沉浸在动画片所营造出的欢快世界里。当动画片结束,我从虚拟世界中剥离出来时,突然发现屋子里只有我一人,隔壁的叔叔婶婶家都大门紧锁,堂哥堂姐堂妹们都不知踪影。突然而至的寂静,如潮水般朝年幼的我涌过来。寂静加大了我的恐慌,正当我疑惑不解地把目光望向窗外苍茫的大地时,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忽然在村子中央响起。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我心底升腾起来。这是至亲去世才会有的哭声。撕心裂肺的哭声裹挟着无边的黑暗向我扑来。我慌乱地锁上门往哭声的源头奔去。仿佛一只落单的鸟,我在黑夜中横冲直撞,向聚集的人群奔去。
很快,我看见村里人都聚集在枣金婶家门口的空地上,朝不远处黑漆漆的大门内张望。一盏微弱的灯火在屋内闪烁,枣金婶的大女儿躺在地上撕心裂肺地哭喊。我艰难地挤进人群,而后站在哥哥身边。哥哥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他像是沉浸在眼前的恐怖气氛里还没缓过神来。
片刻后,屋内出现一阵骚动,紧接着枣金婶僵硬的身体被村里几个年长的人从楼上吊了下来。昏黄灯光的映射下,我看见枣金婶如钟摆般在半空中左右摇晃。战栗来袭,哥哥迅速握住了我的左手。我也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夜越来越深,黑压压的人群潮水般纷纷往各自的家门涌去。作为枣金婶家的族亲,母亲需要留下来帮忙处理后事。“你们俩先回家睡觉。”母亲把手电筒递给我们哥俩,吩咐我们早点回去。曾经与枣金婶在池塘里摸田螺的一幕幕不时浮现在我脑海里,恐慌在我心底弥漫。回到家,面对家里那张木床,我率先下手,抢到了靠里的位置。哥哥看了我一眼,脸上现出无可奈何的神情,他没有与我争执。窗外洁白的月光透过窗格子映射进来,面窗而睡的哥哥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又起身把窗户闭紧。屋内的灯一直亮着,我们不敢关灯,飞速旋转着的电风扇在耳边呼呼作响。我紧握着哥哥的右手,每隔几分钟就会叫他一次。在呢,我还没睡着。哥哥说道。为了让我安心睡觉,哥哥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我握着他的手,像是握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哥哥很快就睡着了,面对我的呼喊,他“哼”了一声,算是对我的回应。哥哥的声音弱了下去。我再次呼喊哥哥的名字,却得不到任何回应。哥哥完全睡着了。整个世界只留下我面对这苍茫的夜。我无处可藏,只能翻身趴在床上,仔细听着周遭的声音,哥哥熟悉的鼾声在耳畔响起。屋外传来一阵凄惨的猫叫,我迅速抓过薄薄的被单把自己紧紧裹住,只露出两个眼睛。高度紧张过后换来的是疲惫,我终于昏昏沉沉地睡去。
次日醒来我睁眼一看,哥哥睡的位置已经空了,房间里寂静无声,我抓着衣服一跃而下,匆匆跑出了房间,逃到了屋外的那片空地上。明媚的阳光让我从恐慌中回过神来。村里人正聚集在空地上津津有味地议论着昨晚的事情。听说有一团鬼火每晚都会从窗外跃入枣金婶家中。村里人议论纷纷。
这个夜晚的恐惧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殆尽,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心底生根发芽,慢慢变得浓重起来。
十三岁成了我生命的分水岭,经过那一晚的恐惧后,我的性格变得忧郁敏感,那个曾经大大咧咧、调皮捣蛋的小孩早已消失了踪影。
十三岁之前,我觉得生命是一个可以循环往复的圆圈,十三岁的那年夏天,我才知晓生命是一条有终点的短线,而且波澜起伏。生命意识的突然觉醒,让我渐渐感到大地的悲凉。一刹那间,我就长大了。我常背着双手,少年老成地走在故乡的小路上。有次走到村庄中央,我看见村里两家人正为建房子地基的事情而争吵着。“不要吵了,你们迟早都会死的。”看着他们争得面红耳赤的样子,我忽然疾步上前,故作深沉地说道。我刚说完,一个巴掌扇在我脸上,我直感到脸上火辣辣的。许多年后的今天,我能理解当时的自己说这句话背后的深意。没想到当时的我操之过急,说出了诅咒人的话。
枣金婶和母亲是闺蜜。晨曦时分,枣金婶常提着一桶衣服在水波荡漾的池塘边浣洗。她最擅长做炒田螺。从池塘里摸上来的田螺放置几天,吐完泥,清洗干净,从菜园子里摘来新鲜的葱,剥好蒜子,一切准备就绪后,枣金婶就开始炒田锅了。很快,一盘香气扑鼻的炒田螺就出炉了。通常我负责去池塘摸田螺,她负责炒。因为炒田螺,我和枣金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以至每次见到我,她总会亲昵地抚摸我的头。
火与水如影随形,寂静的水面倒映出火的影子。枣金婶的去世让我深陷在巨大的悲伤里。记得以往每年的中元节,枣金婶都会带着我去靠近三岔路口的池塘边点燃一盏灯火祭奠先人,任灯火自由漂流,在夜风中摇曳,直至燃烧殆尽,重新坠入黑暗中。
池塘边是三岔路口,村里每每有人故去,都会把其生前睡过的草席放在三岔路口焚烧。枣金婶下葬那晚,我用坚硬的纸壳折了纸船,而后在上面放了一盏灯火。我蹲在那里,把纸船缓缓放入池塘中。夜风袭来,水面起了波澜,纸船迅速滑行,灯火左右摇曳着。暗夜里,我默默祈祷,看着纸船渐行渐远,朝彼岸奔去。船至池塘中央,夜风变大,灯火骤然间熄灭。属于枣金婶的生命之火已熄灭。
我童年的记忆总是定格在十三岁,如果说枣金婶这盏生命之火的熄灭是关于火的记忆,那么与水所发生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几乎占据了我的整个童年。
晨曦时分,晨雾弥漫,村里人在池塘边洗衣服,木槌敲打在衣服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池塘被一层淡淡的雾气笼罩着。卖包子的人骑着自行车在云雾里穿梭,清脆的铃声响彻大街小巷,整个村庄被晨露打湿了。到了黄昏,夕阳映射下的池塘波光潋滟,大黄牛在岸边慢悠悠地啃食青草,沾满泥巴的孩子一个个跳入水中,奋力向前游去,他们在比谁先游到对岸。谁输了就要去池塘边水草密集的地方割一竹篮子青草给胜者。故乡那十多亩鱼塘是我们幼时的游乐园。鱼塘的主人凤娇奶和她老公五宝爷每年都会在广阔的鱼塘里投放鱼苗。这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当凤娇奶和五宝爷在屋内打盹时,年幼的我们就光着身子在鱼塘里嬉戏,摸田螺、打水仗、网鱼。巴掌大的村庄因了这十几亩水塘的存在而变得充满诗意。
薄暮下,广阔的池塘以平缓之躯走入记忆中的那个盛夏时节。十三岁的我踩着池塘底下柔软的淤泥,在水中穿梭着。烈日高悬,荡漾的水波带着一丝热意,我不时沉入水中,打捞着藏匿在淤泥中的田螺、贝壳。池塘水深一米五,沉入水底的过程中,夏日的热意慢慢消失,水底的凉意迎面扑来。在强烈光线的照耀下,池塘底部暗黑的淤泥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我反复沉入水底打捞,漂浮在水面上的脸盆渐渐地盛满了田螺。浮出水面的那一刹那,忽然,不远处传来一阵熟悉的咳嗽声。我抓着装满田螺的盆子,迅速往岸边游去。岸上的菜园子里无处可躲藏,去年深秋弥漫着桂花香的桂花树已被挖走。咳嗽声愈来愈近。来不及上岸逃走,情急之下,我沉入水中,躲在了密集的水草下。
水的阵阵波澜差点暴露了我的藏身之处,潜藏在水底的我听见脚步声越来越近,凤娇奶穿过池塘间的小路,来到了菜园子旁的水草边。她迈着碎步,东张西望着走过来。她的那双裹过的小脚走得有点慢,憋在水里几乎窒息的我渴望她走快一点。透过水这面镜子,我看见凤娇奶站在岸上,眼神掠过广阔的池塘,而后停留在水草密集的岸边。远未散去的波澜吸引了她的目光,有那么一瞬,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密集的水草。她拾起几块石头,使出浑身的力气,把石头抛向水中。一块石头险些击中我的头部,一块石头打在我的胳膊上。我忍着疼痛不敢吭声。透过水的缝隙,我看见凤娇奶正欲搬起一块更大的石头,这一幕让我倍感恐惧。我正欲浮出水面缴械投降,广阔的池塘对岸忽然传来一阵小孩子下水嬉闹的声音。嬉闹的声音把凤娇奶吸引了过去,也给几近窒息的我解了围。我迅速上岸,消失在午后的风里。
田螺交给母亲去墟上卖,买田螺的人不多,那时村里山清水秀,每一条水沟里都能找到田螺,快散墟时小镇饭店的老板低价把母亲手中的一篮子田螺全都收了。母亲用卖田螺换来的钱买了一斤猪肉给我们哥俩改善伙食。
那个摸田螺的下午之后几天,经常去池塘边转悠的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以往活蹦乱跳的鱼忽然变得死气沉沉起来,它们有气无力地在水面上游荡着,露出灰黑的脊背。
1998年的盛夏,十三岁的我站在阁楼的窗前,正盯着一尾摆动着尾巴在池塘边缓缓游动的草鱼。
我放下手中的望远镜疾步下楼,跑到池塘边时,鱼摆动着尾巴又游回到了池塘深处。我失望而归。一整个下午,我仿佛侦察兵一般拿着望远镜盯着水面上的一举一动。鱼在跟我玩捉迷藏的游戏。我反复几次丢下望远镜下楼,行至池塘的一隅,鱼却不见了踪影。随后的几天,我始终没看见鱼的影子,这是一条脱了鳞的草鱼。又一个烈日暴晒下的午后,我猎人般守在鱼经常出没的地方,等待着鱼的出现。村子里静悄悄的,当午睡的村里人都沉浸在梦乡时,我却如守卫般孤守在岸边的草丛里。我渐渐如泄了气的皮球般欲转身离开时,寂静的水面却突然起了波澜。那条熟悉的草鱼突然浮出水面,出现在我眼前。相比于前几日,这条草鱼游得愈加缓慢了。我看见这条草鱼摇晃着尾巴缓缓游进了池塘浅水区的一角。我怕丢失机会,挽起裤脚,瑟缩着走入清凉的水中,小心翼翼地把它赶进了浅水区的角落。鱼没有垂死挣扎,我轻易就抓住了它。它张着嘴巴冒着泡,静静地躺在我的手掌里,仿佛早已做好束手就擒的准备。我迅速躲进了一旁藤蔓纠缠的菜园子里,而后脱下衣服紧紧地包裹着那尾草鱼,往家的方向飞奔而去。
家里捉襟见肘,我渴望多抓几条鱼来减轻母亲的负担。那段时间,爱笑的母亲一直眉头紧蹙。
如一尾鱼般逆流而上,去南方打工的父亲已两个月没有寄钱回来了。以往每到月底,村里邮递员清脆的铃声就会准时在家门口响起。邮递员会递给母亲一张五百元的汇款单,有时是八百。到了月底,我看见母亲不时地朝门口不远处的小路张望。我倚靠在阁楼的窗户前,手拿着望远镜,注视着小路尽头的一举一动。焦急的等待中,穿着绿衣骑着绿色自行车的邮递员出现在视线里,我紧握望远镜的双手禁不住颤抖起来。邮递员越来越近了,他哼着欢快的歌曲。我和母亲满是期待地看着他。他却没有停下来,而是一闪而过,只留下一句“这个月你家没汇款单”。母亲的眼里明显多了一份焦急,家里只剩五块钱了。几天后,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母亲他们老板暂时发不出工资的事,特意嘱咐母亲一定要去向大伯他们借一百块,别饿坏了正在长身体的我们。次日太阳快落山时,母亲挎着一个大竹篮出去了。快天黑时,我远远地看见母亲回来了。空空的竹篮里早已盛满饱满的毛豆。
在昏黄的灯光下,母亲带着我们开始马不停蹄地剥起来。母亲说今天晚上要把这一竹篮毛豆剥完,明天早上拿到集上卖。微弱的光线把母亲躬着的身子映在满是灰尘的墙壁上,一颤一颤,左右晃动着。
剥到十二点,我就支持不住了。母亲看着我一脸疲惫的样子,叫我们哥俩赶快上床睡觉。夜半醒来,门檐下的灯依然亮着,我隐约听见母亲剥毛豆发出的声音。第二天晌午时分,我欣喜地看见母亲篮子里的毛豆没了,换来的却是满篮子的生活用品和蔬菜。一篮子的毛豆只能暂时缓解家里的困境,我渴望着在摸田螺之余,能多抓几条鱼上来贴补家用。带着这个天真的想法,我时常晃荡在池塘边。
整个村子静悄悄的,抱着草鱼的我慌张的脚步声惊醒了蜷缩在狗洞中的老黄狗,它迅速站起身,一脸茫然地朝我吠了几声。我故作镇静,捡起地上的一块石头作出欲砸过去的姿势。狗咕噜了几声,像是怕了,躺了下来。午后的风疾速从我耳边吹过,我像一阵风一般迅速往家的方向奔去,当我稳妥地把鱼放在狭小的水盆里,终于深深地舒了一口气。母亲揉着惺忪的睡眼打着呵欠走了出来。许多年后我依旧记得那一幕,当母亲看见水盆里躺着五斤重的草鱼时,她无神的眼底忽然冒出一丝光亮。鱼有气无力地在水里游荡着,母亲看了鱼几眼,忽然对我说道,把刀拿来,这鱼染上了脱鳞病,必须尽快杀掉。
这条奄奄一息的草鱼在寒光闪闪的菜刀面前也不再挣扎。疾病已把它对死亡的恐惧消耗殆尽。母亲忙活了一整个下午,终于把五斤重的草鱼收拾干净,而后把一大半的草鱼炸出金黄的色泽,一股浓浓的香味弥漫在整个厨房,屋顶上缕缕炊烟缓缓朝天际飘去。那个晚霞满天的黄昏,母亲走进了家里的菜园子,她摘了一捧新鲜的辣椒,缕缕炊烟之下,屋子里弥漫着辣椒爆炒新鲜草鱼的香味,让人嘴馋不已。薄暮时分,祖父在院落的梧桐树下支了张桌子,一边喝着母亲去年酿的米酒,一边把一小块炸得金黄的草鱼夹入口中,津津有味地咀嚼起来。因了这条草鱼,平日里在祖父面前小心谨慎的我陡然间也变得肆无忌惮起来。鱼让我暂时获得了家里的话语权。
鱼染病的消息不胫而走。次日,午睡时分,当我又来到池塘边晃荡时,看见隔壁的坨坨也像昨日的我一般,坐在池塘旁的庙宇边默默注视着水中的一举一动。相遇的那一刻,我们彼此对视了几秒钟,又各自心知肚明地走开了。很快,一条草鱼从池塘中央慢慢朝边沿游过来。我和坨坨正摩拳擦掌准备把猎物抓入囊中时,不远处响起五宝爷熟悉的脚步声。五宝爷早就发现了我们,他抬起拐杖,朝我们指了指。我们对视了一眼,垂头丧气地往回走了。那个寂静的午后,五宝爷把给鱼买的药撒入鱼常出没的地方,而后拄着拐杖围着鱼塘巡视。这十几亩鱼塘是他的命根子。我站在阁楼的窗前,用望远镜注视着五宝爷的一举一动。直至夜的幕布降落下来,五宝爷才起身踏上了回家的路。老黄狗跟在他后面,不停地摇着尾巴。
几日后的午后,我看见那一条条曾在死亡边缘苦苦挣扎的草鱼又变得活蹦乱跳起来,仿佛吃了灵丹妙药般。此刻,它们成群结队地在池塘中央冒着泡,仿佛在向我示威,而我正在一旁废弃的庙宇里打盹。
春去秋来,寒冬迅速降临。那年冬天,村里占地十多亩的鱼塘在经过几个昼夜的抽水之后,新鲜的淤泥露出了水面,一条条草鱼的脊背隐约可见,从池塘边路过的村里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恨不得立刻下去抓几条鱼上来。鱼塘已五六年没有抽干水抓鱼了,乡里人左顾右盼,收鱼的行动迟迟没有动静,抽水机抽水的速度也放缓了。每个人眼底都有一条鱼,时间一长,村里人渐渐泄了气,他们眼中的鱼也渐渐消失。他们再次经过鱼塘时,看见在鱼塘边转悠的五宝爷,脸上就露出鄙夷之气,心底暗暗骂道,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抓鱼吗,搞得像防贼似的。五宝爷有自己的算盘,这十几亩苦心经营的鱼塘,每一只鱼苗,都是他精心挑选,亲自把它们一条条投放到水中的。这是他承包鱼塘的最后一年,年过七旬的他已没有精力再承包下去。他必须抓住这次干鱼塘的机会,储备足够多的粮食来供他们夫妻俩过冬。属于他生命的寒冬已悄悄到来,痛风经常把他折磨得满头虚汗。每一条鱼都相当于一根过冬取暖的柴火,他不想旁人抽掉过多的柴火,让他深陷在凛冽的寒风里。
透过记忆的望远镜回望过去,那年冬天再次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村里人渐渐等得没了耐心。对于干鱼塘的具体时间,我有了最初的判断,自从抽水机的速度放缓之后,我就把好奇的目光从鱼塘转移到了五宝爷身上。
在故乡,每逢遇到嫁娶、建新房、干鱼塘等大事情,总会挑一个黄道吉日,上三炷香,并三鞠躬,以祈求保佑。许多年过去,这些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风俗礼仪早已被城市的气息给吞噬得一干二净。
薄暮时分,我拿着一台灰旧的望远镜一路奔跑着回到了老家。每天从学校回来的傍晚,我总会爬上阁楼,透过窗格子注意五宝爷的一举一动。五宝爷的房子是一栋三层楼的洋房,就在我家不远的地方,中间隔着两三栋房子。借助望远镜的放大,五宝爷的一举一动清晰地呈现在我面前。我一下子感觉自己成了监控者,而年迈的五宝爷则成了我眼中的猎物,我久久地注视着,等待最后的精准出击。终于,冬至这天傍晚,通过望远镜,我看见五宝爷在二楼的观音像前上了三炷香,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这个意味深长的细节长久地回荡在我的脑海里。这是每次干塘惯用的仪式。
那天晚自习回到家,墙壁悬挂着的时钟,时针已经指向十,鱼塘边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觉得五宝爷干塘的时间应该会选在凌晨两点左右。我定下了闹钟,果然,当闹钟把我从睡梦中叫醒时,我推开门,跑到小路上朝鱼塘的方向张望,那边已是灯火一片。干塘的行动比预料中提前了半个小时。我返身叫醒了父母和哥哥,他们兴奋而又焦急地穿上长筒雨靴,纷纷往鱼塘的方向奔去。
屋外寒意袭人。抽干了水的鱼塘裸露出新鲜的淤泥,周遭人影寥落,在黑夜的掩护下,我隐藏在自家菜园子长满藤蔓的一角,慢慢下到鱼塘里,把一条条巴掌大的草鱼抓入随身携带的水桶里。村庄的人陆陆续续从睡梦中醒过来。池塘仿佛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他们。一条条搁浅在淤泥中的鱼奋力挣扎着往泥土深处躲藏,却始终躲不过村里人狡黠的眼睛。昏黄灯光的映射下,一条条搁浅的鱼露出灰黑的脊背和鱼肚白,它们的面容清晰可见。多年后,当生命的河流慢慢干涸,那一晚在池塘边抓鱼的村里人大都已步入人生的暮年,他们也如搁浅在岸的鱼一般,等待着死神的收割。
那一晚家里收获颇丰,抓了不少草鱼和黄骨鱼,田螺和青灰的小虾子也装满了两水桶。我特意留了一小饭盒的草鱼带到学校,送给了自己喜欢的女生兰。
遥远的人和物在望远镜的无限放大下,仿佛就站在自己的眼前。透过记忆的尘埃,我看见十三岁的我拿着望远镜正仔细打量着暗地里喜欢的兰。暗恋是一个人的精神游戏,它如空中楼阁般美丽却又虚幻,她近在眼前,却又无法触摸。兰嘴角有一个酒窝,笑起来十分迷人。她的一颦一笑都让我着迷。一天中午我从家里吃完饭匆匆返校,走至校门口,恰好撞见她和她的闺蜜挽着手出校门。羞涩的我扭头假装没看见,待彼此走远我禁不住回头张望时,恰好她也回头朝我张望,彼此眼神交汇的一刹那,一股电流在我全身流淌开来。现实当中的回眸迅速延伸到梦境中。随后的几年时间,我时常会梦见这样的场景,彼此擦肩而过,却又同时转身回望,眼神相撞。
记忆的血肉已被时光吞噬,只剩下躯壳。然而那一幕至今回荡在我的脑海里,以至每每回忆起来,我都禁不住感到一阵战栗。
面对突然出现在桌子里的草鱼,兰忽然端着鱼站起身,大声说道:“这是谁的鱼?”班里几个调皮的男生忽然嬉笑着说道:“是我的鱼,我的鱼,不吃给我们。”他们边说边嬉皮笑脸地伸出了手。“是不是你送的?你昨天不是跟我说刚在池塘里抓到一条草鱼吗?你小子肯定暗恋她。”同桌笑着对我说道。我的脸顿时红了,支支吾吾地否定。我面红耳赤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却低下了头,长久地沉默着。抬头的刹那,我看见兰气冲冲地把炸得金黄的草鱼“咔”的一声丢在了讲台上。鱼的香味顿时在教室里弥漫开来。很快,饭盒里的鱼被同学们一抢而光。当时的我低着头,面色通红,仿佛被一双无形的手扇了一巴掌。许多年后重新打量过去,我看到了我的胆怯与掩饰。
次日中午在学校食堂吃饭,吃鱼时,一不小心,一根鱼刺卡在了我的喉咙口。我夹菜的筷子忽然停在了半空中,向身旁的同学指了指自己异常难受的喉咙,而后面色苍白地蹲在地上,呕吐起来。这根鱼刺卡在我的喉咙深处,进退两难,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身旁的同学见状立刻汇报给了班主任,而后我被急匆匆送到镇上的诊所。横亘在喉咙间的鱼刺几乎让我窒息,死亡的阴影潮水般把我淹没。半个小时后,我才从痛苦中解脱出来。鱼刺滑入食道,差点穿破食道壁的血管引起大出血,幸好送得及时,不然就糟糕了。诊所的老医生意味深长地说。多年后,每当我误吞鱼刺,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时,那种熟悉的逼近死亡边缘的窒息感就汹涌而来。那一刻,我就会想起身患食道癌的祖父弥留之际上气不接下气的场景。一根细小的鱼刺,引来了死亡的巨大阴影,它让我一次又一次深刻地体验着人在死亡边缘徘徊的感觉。
我误吞鱼刺险些致死的经历并没有在班里引起多大的波澜。劫后余生的我回到教室里,观察着兰的一举一动,发现她仿佛没听闻这件事一般。班里一些不相熟的女生用关切的眼神看着我,问我好点没。我渴望兰能回头给我一个关心的眼神,但什么都没有。
那个星期五的黄昏,晚霞烧红了半边天,晚风吹拂,喧嚣的校园顿时寂静下来。我拿着望远镜快步走到教学楼的顶楼,倚靠在栏杆上,看着她挽着她同桌萍的手一步步朝学校大门的方向走去。此刻,她离我这么近,近在眼前,仿佛伸手就可以触及。放下望远镜的刹那,我看见她已走出校门,然后往右拐,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一股怅然若失的感觉在我心底流淌开来。
两个月后,兰转校到县城的重点中学读书,熟悉的座位顿时空荡荡的,次日班里一个瘦小的男生坐在了她的位置上。透过望远镜看着她远去的身影,我颇为失落。中考那年,我以两分之差与县里的省重点中学失之交臂,最终被一所普通的高中录取。班里考取县里省重点的有八九个人,其他都考取了普通高中。高中三年,在县里省重点高中读书的同学常会来到我读的普通高中找曾经的初中同学聚会。倚靠在窗前,我经常能听见兰熟悉的笑声。我想去一睹她的芳颜,却忐忑着始终没迈出一步。每次听到兰“咯咯咯”的笑声,我总会疾步跑到教学楼顶,掏出望远镜,而后在望远镜中注视她的一举一动。我看到她熟悉的发型、嘴角漂亮的酒窝。她仿佛就在我的怀抱里,触手可及。班上有许多同学有望远镜,他们用此来细细打量自己喜欢的女生。同桌辉暗恋青春性感的英语老师,每天晚自习后,他总会用望远镜观察昏黄灯光弥漫的房间里,老师的一举一动。英语老师丰满的胸部牵引着他日渐躁动的心。
我幻想着暗暗努力能与她考取同样的学校,给她一个惊喜。但最终我只考取了一所很普通的学校,而她则考取了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无形间距离越来越大,我只能不停变换记忆望远镜的焦距,不停打捞她的身影。多年后在初中同学的一次聚会上,兰提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当年我被鱼刺卡住的事件。“我那时好替你担心呀,我还知道那时塞在我抽屉里的草鱼是你送的,只是我那时不敢早恋。”兰笑着说道。记忆带着一种魔力,许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在多年后的今天得到了回应。我以为兰早已忘却。从同学口中我得知兰的老公出轨,现在她正和他闹离婚。一根情感的刺插在她的体内,始终无法拔出。
鱼塘抽完水几年后,年过八旬的凤娇奶得了一种怪病,她身上的皮肤慢慢烂掉,一触摸,皮肤就掉下来,阴暗的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恶臭。玉林婶不时来到我家中,向我母亲讲起凤娇奶的情况,眼中满是恐惧。凤娇奶仿佛池塘中一条身染脱鳞病的草鱼,慢慢蜕掉身上的皮囊,往死亡深处游去。
深夜望着故乡哗哗流淌的河流,年幼的我陷入沉思当中。时光的河流也彻夜不息地流淌着,它不管不顾,按着自己固有的节奏往前行走。村里的人都活在时间里。一股无法挣脱的力量裹挟着他们前行。半个月后,埋入泥土深处的凤娇奶挣脱了时间的束缚,她停留下来,固定在时间的某个角落,如琥珀一般。她走出了时间,她在时间之外,而我还在时间的笼子里。我们彼此回望着,时光把我们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直至记忆变得模糊。
池塘如一面镜子映射出世事的模样。年幼时我对望远镜的喜爱,只不过因为它能映射出我对世事的好奇和对远方的渴望。随着时光的流逝,望远镜的意义慢慢变得复杂,成为一种深沉的隐喻。
在成长的步履里,我渐渐离故乡越来越远,如望远镜般把目光投向未知的远方。
世界上第一台望远镜其实叫窥视镜,这个命名简单而直接地抵达事物的内核。望远镜带着一丝窥视别人生活的意味。遥远的事物总是弥漫着陌生感,它容易引起他人的好奇和窥视欲。当一个人深陷在当下烦琐的事务中,他总是渴望通过对远方的眺望或行走来暂时抽离沉重而琐碎的当下。
人在窥视中得到满足和真相。自从与女友分手后,很长一段时间,好友凯经常失眠。凌晨两三点,当别人响起甜蜜的鼾声,他还在床上翻来覆去。对面那栋出租屋的四楼住着一对年轻的情侣,他们在附近的KTV 上班,每天总是凌晨两点多才下班。深夜回到出租屋,年轻情侣在房间里亲热。声音回荡在寂静的夜空,落入失眠的凯的耳中。此后,每天凌晨两点半,他都会准时拿起望远镜,窥视对面那对年轻人亲热的场景。那对年轻人的一举一动时刻牵引着他躁动的心。他甚至知晓女人屁股上有一颗痣。看着这对幸福的情侣,他就想起过往的自己也曾过着这么水乳交融的日子。只是自从女友离他而去,屋子里的一桌一椅都变得伤感沉重起来。直至有一天深夜,他看见那男的带回来一个陌生面孔的女人。他忽然下楼,捡起一块石头,狠狠地朝那窗户投掷过去。
我忽然想起2020年的奥斯卡最佳获奖短片《邻居的窗》。拥有三个孩子的艾利夫妇深陷在琐碎的生活中,时常感到疲惫。透过望远镜,她看到对面楼上公寓搬来了一对小夫妻,小夫妻没有孩子,搬进来的这一晚忘情地亲热着,窗帘也忘记拉上了。艾利夫妇羡慕他们有着生活的激情和浪漫。于是拿着望远镜窥视这对小夫妻的生活慢慢成了艾利的生活习惯,对方的快乐和浪漫映射出她的疲惫和麻木。然而有一天,艾利透过望远镜窥视到这个年轻女人的老公正身患绝症,才恍然大悟。当艾利在羡慕对方无忧无虑的生活时,对面公寓的女人却在羡慕她过着拥有三个小孩的平凡而又温馨的家庭生活。
望远镜下的事物如此清晰,却无法抵达它的内核。当你羡慕别人时,别人却在羡慕你。
许多年后,当我从异乡回到故乡,暮色中站在菜园子里,看到曾经水波荡漾的池塘已经被夷为平地,一栋栋三层的小洋房矗立在上面。池塘边曾经绿油油的菜园子已是一片荒芜。母亲如钉子般深深钉进故乡的土壤里,已锈迹斑斑。属于她的那块菜园子依旧绿油油一片。她在里面种茄子、辣椒、玉米、白菜、冬瓜。正是寒冬,菜园子里的包菜、蒜苗、葱、白菜苔正郁郁葱葱。左右两旁紧挨着的两块荒废的菜园子是二叔和三叔家的。二叔和三叔他们全都在深圳打工,二叔在工地上打零工,二婶在酒店里洗碗,三叔在工厂做保安,三婶在工厂的食堂做饭。他们只有年底春节将近时才回来一次。镇里墟上的蔬菜贵,二叔和三叔家每次回来过年都是去母亲勤耕细作的菜园子里摘菜吃。像村里许多人家一样,二叔和三叔也把自家的几亩地给了村里的其他人耕种。
菜园子不远处是老屋。推开老屋的大门,我看见年幼时的那台望远镜静静地躺在桌上,它被厚厚的灰尘覆盖着,结满蜘蛛网。世界的焦距千变万化,时光的脚步在这台望远镜里停了下来。走出老屋,回头的那一刹那,我看见一只蜘蛛倒挂在梁上的蜘蛛网里,一只误入蜘蛛网中的苍蝇正垂死挣扎着。在时光织就的网里,我也是一只不断挣扎着的苍蝇。
记忆被砂纸打磨,许多事情变得模糊不清。暗夜里回头重新打量过往,曾经看得很重的事情在记忆的天平上已经变轻,在时间的侵蚀下,我的记忆力逐渐变弱,头发变白,记忆的重量也跟着变轻。我通过一次次还乡来激发那些潜藏在隐蔽角落的记忆。仿佛手握一只无形的望远镜,只有回到故乡才能找到回忆的焦距,才能让那些模糊的记忆慢慢变得清晰。
深夜,洁白的月光洒满整个村庄,稻田里蛙鸣阵阵,清冽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稻香。眼前的一幕让我仿佛置身于多年前的那个盛夏,恍惚中,我看见当年的我坐在月光下的田埂上看着溪流慢慢流入干涸的稻田里。在一些场景的激发下,那些温暖的记忆才会如此清晰地再次浮现在我脑海里。时间是很奇怪的东西,它把很远的事情推到你面前,你却束手无策,只能徒增伤感。
有许多年未静静仰望夜空了。故乡的夜空寂静、深邃而悠远。我想起年幼时,盛夏的夜晚,我躺在院落散发着阵阵凉意的竹席上,目不转睛地望着繁星闪烁的天空发呆。一旁的父亲已经入睡,均匀的鼾声在耳畔响起。如水的月光洒落在大地上,洒落在一花一草一木上,打湿了寂静的村庄。几只萤火虫在半空中飞舞着,它们在墙头的稻草上停留了一会儿,转瞬又闪着光朝更远的方向飞去,仿佛打着灯笼游玩忘了回家的孩子。村庄深陷在梦境中,不远处的小巷里传来熟悉的犬吠声。整个村庄的人仿佛都睡着了,只留下我独自面对苍茫的夜。夜越来越深了,空气中的湿气愈来愈重,凝结成细小的水珠,打湿了入睡人的梦。
我深陷在失眠的河流里,时刻渴求着睡意的小舟前来施救。突然,灵机一动的我一跃跑到阁楼上,取来望远镜,仰躺在凉席上,用望远镜观察着深邃的夜空。简陋的望远镜只让我看到漆黑的夜。透过望远镜,我看见那条匍匐在地的黄狗被一阵风声惊醒,它警觉地站起身,走出了院落。这条与我一样在尘世活了十三年的黄狗,却已走到了它的暮年。它已老眼昏花,双脚无力,跑起来远不如年轻时那么步伐矫健。一条步入晚年的狗依然在固守着它作为一条狗的职责。一个人活到十三岁,还处于青少年时期,未来的日子还很漫长,而一条活到十三岁的狗,它的身子已慢慢走入泥土深处。这条老黄狗是凤娇奶家的,我透过望远镜看见出了院门的老黄狗蹲在无边的寂静里,蹲在苍茫的夜色里。它张望着眼前熟悉的夜,像是想起什么,许久才起身回到院落的那个狗洞里。凤娇奶六十岁那年在墟上买下这只狗崽。十三年的时光,狗走完了人生的春夏秋冬。现在,它和凤娇奶一样各自走在生命的暮年,牙齿松动,行动迟缓,视力远不如前。
月亮在云层里穿梭,月光照在我稚嫩的脸庞,我看见老黄狗在晚风里把自己蜷缩成一团,渐渐一动不动,沉入梦乡。我在望远镜里打量着一只老态龙钟的狗。月亮慢慢隐匿到云层中去,夜顿时漆黑了几许。院落也跟着暗了下来,院子里的物什适才还能隐约看见轮廓,转瞬都陷入黑暗中。黑夜一层层把我包围,睡意来袭,转眼间把我吞噬。
有许多年我丢失了对望远镜的热情,甚至遗忘了它的存在。一次返乡,老屋里布满灰尘的老式望远镜勾起了我的回忆,再次激发了我对望远镜的热忱。
回去后,我特意从网上购置了一台专业的望远镜。夜幕降临,在阳台上,架起望远镜,透过它,我看到了月球表面上的陨石坑和环形山,看到了浩瀚星空中闪烁着的繁星。我强烈感受到了人的卑微与渺小。我焦躁的心在望远镜不断变化的焦距里似乎也跟着消减了许多。对生活日渐麻木的我因为一台望远镜,似乎渐渐找回了仰望星空的心。
夕阳映射下的东江波光粼粼,不远处有一群人在放生。他们每人手里提着一桶鱼,蹲在江边,一条条地放入水中。我看见一个戴着鸭舌帽的中年男子,手持望远镜追踪着他适才放进东江的鱼。一直看着鱼摇摆着尾巴游入东江深处,他脸上露出一丝微笑,才放心地转身离去。这是一群信佛的人,每个月的十五号,他们都会用善款从集市上买来大量的鱼,而后在这里放生。
放生的人群走后,静坐在东江边的垂钓者迅速把阵地转移到适才放生的地方。我看见一条被放生的草鱼缓缓游入东江深处,几分钟后,几米之外的垂钓者迅疾拉起钓竿,欣喜地把它放入水桶中。一边在放生,一边在杀戮,亦如医院里一边是呱呱坠地的婴儿,一边是太平间里日渐冰凉僵硬的躯体。
透过记忆的望远镜,我看见自己如一尾鱼般正沿着时光的河流顺流而下,昼夜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