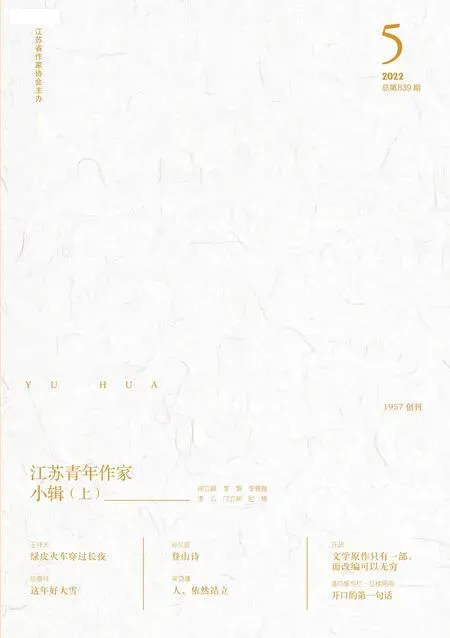出行
邝立新
放在多年前,李凯对“子承父业”是不以为然的,况且他的父亲只是文星镇上的中巴车司机。那时文星镇到县城的柏油路还未修通,父亲每天就在坑坑洼洼的乡村石子路上来回奔波。他跟着跑过无数回,中巴车外面灰头土脸不说,里面也是乌七八糟。臭烘烘的鸡鸭笼、嗷嗷叫的猪仔、污浊不堪的秽物、孩子的哭闹声,声音和气味混杂在一起,简直让人窒息。有人问他愿不愿意接父亲的班,不到十岁的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愿意。
没想到二十几年后,他却成为文星镇上第一个网约车司机。他回到文星镇时,并未想过要开网约车或出租车。他最初盘算开一家旅馆。这几年前来观光旅游的人不少,但文星镇并没有像样的酒店或旅馆。他想着租一座独门独院的大房子,收拾出五六间房。住宿之外,还提供餐饮、KTV、导游、出行等服务,做成一条旅游产业链,一年下来能挣不少钱。但文星镇派出所的张所长立马就把他的计划扼杀了。张所的理由是他有案底,不宜从事特种行业。他当着张所的面忍不住发飙,开旅馆算什么特种行业?!不爽归不爽,他也明白“胳膊拧不过大腿”的道理,只好把这个商业计划搁置在一边。
他的B 计划是开一家餐馆。本地菜没什么搞头,土里土气不说,每家饭馆的菜肴大差不差,只能拼命打价格战。他要做高端粤菜,错位竞争。鲍鱼、烧腊、烤乳猪、虾仁蒸饺、深井烧鹅,从广东那边请厨师。来镇上旅游的客人,珠三角一带的居多,加上本地人出于好奇尝鲜,要是有一家正宗粤菜馆,生意应该不会太差。父亲坚决不同意他的计划,说文星镇这消费水平,人均七八十不得了,你开一家人均两百的餐馆,就等着亏钱吧。他不死心,自己找人谈合作、租门面。但找来找去,也没有合适的地方,这个事情也不了了之。
做网约车不必看谁的脸色。只要一辆车、一台手机、一张C1 驾照,谁都可以做。话虽如此,李凯还是开了文星镇网约车的先河。柏油路通车后,从文星镇到县城只需半小时,坐中巴车也很方便。但他想的不是县城的生意。从文星镇到广州、珠海、东莞、佛山这些城市,两三百公里路程,其间中巴车、火车、公交车、地铁转四五趟,费时费力不说,钱也没少花。李凯这些年混迹两地,不光是大路,那些小街小巷他也寻得着。人们只需花五六百元钱就能安全便捷地到达南方某个犄角旮旯,不啻为一桩利人利己的好买卖。
李凯做过很多生意,倒火车票、摩托车拉客、贩卖水货手机,甚至搞传销,风生水起时手下也有十几个小弟。如今回到文星镇做网约车司机,算得上龙困浅滩。父亲说他今后可以接他的班,好歹有口饭吃。他并不认为自己会继承父亲的事业,至少他没有去开那辆灰头土脸的中巴。他按照自己的心情接单、载客。虽然回到文星镇、回到父亲身边,他仍然是自由的,这一点对他而言极为重要。这也是他离开南方那些城市的原因。
网约车生意并不好。不客气地说,几乎无人问津。他暗自揣测,还是消费习惯的问题。文星镇用智能手机叫车的人不多,也许到节假日外地人涌入,生意才会有所好转。但这个想法很快就被现实所击溃。一位叫李乾勇的文星镇人,之前骑摩托车拉人送货,攒钱买了辆比亚迪F3 后,也在“出行”APP 上注册成为网约车司机。奇怪的是,李乾勇的生意比他好许多。他想,是自己技不如人,还是车子没别人好?可两者都不成立,事情有些蹊跷。
他不好去问李乾勇,这等于变相承认自己输了。为了招徕生意,他每天开着车在文星镇上转悠。如此,油费倒是用去不少,收入却少得可怜。在镇上等客人时,人们好像约好了一样,径直走到李乾勇那边。有时只有他一辆车,客人走到车边,跟他打声招呼,竟然转身离开了。他做了个“出行八折、长途从优”的广告牌放在挡风玻璃后面,但情况依然如故。李乾勇这些年没怎么离开文星镇,人们熟悉他、愿意乘他的车也正常,但不至于如此排斥自己。
有次李凯忍不住叫住一个想乘车又转身离开的人,问他为什么不上车,是不是受到李乾勇的威胁。那人支支吾吾,说自己不坐车,就是到这边晃晃,瞎晃晃。他也不好继续追问。但李乾勇车子一来,那人却屁颠屁颠上了车,让他眼里几乎冒火,把烟头摔在地上,狠狠地骂了一句。父亲让他不要急躁,说你虽是文星镇人,但出去这么多年,跟外地人也差不多,过段时间混个脸熟,自然有人坐你的车。父亲还让他考虑成家的事,都一把年纪了。
直到有一天,一位年轻女孩坐上他的车,这种状况才略有改观。女孩看起来只有十七八岁,穿着牛仔裤、白T 恤,长头发,成熟装扮之中透露出稚嫩。女孩先是看到李乾勇,神色有些惊慌,转身打算离开。然后看到他,慌忙上了车。一路上,他跟女孩有一句没一句地聊起来。女孩说她在县城上高中,叫李真,别人都叫她真真。他对这个女孩并没有什么印象。算起来,他离开文星镇时,这位叫李真的姑娘只有几岁,互不相识也正常。真真的父母都在广东打工,一年到头难得回来一次,她平时跟着爷爷生活。李凯把真真送到县城后,说这次不收她钱。真真问为什么。李凯有些难为情,说这是他的第一单生意,就算做活动。真真说那更应该收钱,不然以后生意不好做。他象征性地收了五块钱,因此对真真多了几分好感。这女孩年纪不大,却很明事理。
一天深夜,他已睡着,手机却突然响起。电话那边说有人突发心脏病,需立即送县医院。他看看时间,凌晨两点。他抓起一件衣服,出门发动车子,一脚油门冲了出去。病人抬上车,他也没多问,一路专注开车,只花了二十来分钟就送到医院急诊室。还好抢救及时,病人脱离生命危险。那家人后来对他千恩万谢,说那晚真惊险,李乾勇手机打不通,县里救护车开过来也来不及,不是你帮忙,人就没了。李凯想,人家第一时间还是愿意找李乾勇,心里不是滋味,但场面上还是说说笑笑:没什么没什么,都是分内之事,再说你们也不是不给钱。也许因为真真和这件事,他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
那天送完真真回来,李乾勇向他靠拢过来,递上一支烟,觍着脸说,祝贺凯哥,今天开张大吉、红运当头,头一回还是小美女。李凯说,都是托你的福。李乾勇说,哪有哪有,真真可不是一般的女孩子。李凯说,不就是高中生,有什么不一样?李乾勇没有正面回应,他吐出一口白烟说,对了凯哥,你在外面混得挺好,为什么要回来跟我们抢饭吃?李凯说,有饭大家一起吃,不存在谁抢谁的,再说文星镇发展不错,年纪大了,叶落归根嘛。李乾勇说,你还年轻呢,你的故事我们都听过,当年也是威震一方。
说年轻也不年轻,再过几年,他就四十岁了。最近这二十多年是怎么度过的,想起来毫无头绪,似乎都没有什么稳固的恒久的回忆,倒是在文星镇那些时光他依稀还记得。父亲顾不上管他,他跟几个人在学校附近晃荡,有了钱大家就去县城打桌球、看录像、轧马路。后来他离开文星镇,在城市凭手艺谋生。到了这个年纪重新开始晚不晚,他也吃不准,但他没有太多的选择。
真真两周坐一趟他的车,车费15元。别人叫他的车去县城,他一般收30 元。他把真真当作自己的幸运乘客。她第一个上他的车,才有后面源源不断的客人。真真的话不是太多。他有时问起学校里的事情,真真也不愿多说。有次他无意说起之前的经历,她倒是很有兴趣,问了很多细节问题,比如他是做什么工作、收入如何。他的长途生意也渐渐打开局面。前段时间有人坐他的车去虎门,回来也没放空,来回就有近千元收入。他在文星镇有了立足之地。
一个周日傍晚,他把真真送到县城。天色已经暗淡下来,他看着真真往巷子里走去,几条人影不知从哪里闪出来,尾随其后。他察觉到不对劲,把车子停在路边,也跟着斜进巷子。他看见几个女生将真真团团围住,起初言语争执,后来竟然动起手来。他赶上前去大喊一声,你们想干什么?!那几个女生说,跟你有什么关系?他说,少废话,真真是我妹,谁动她试试。几个女生见他来者不善,气焰矮了半截,嘴上不肯服软,身体却很诚实地往后退,很快消失在巷子里。他把真真拉起来,问她怎么样。她拍打着身上的泥土,喘着粗气说,还好,她们几个菜鸟,能把我怎么样?不要嘴硬,我带你去吃点东西吧,给你压压惊,李凯说。我带你还差不多,你还没我熟悉呢。也行,上车吧。
十几年前,他经常在县城里晃荡,那时学校附近还是绿意葱茏的菜地,他在里面摘过西红柿、拔过白萝卜,如今都盖起了商业街。他们找了一个烧烤摊,地方不大,生意还不错,里面吵吵嚷嚷。他要了两瓶啤酒,给真真也倒了一杯,说你也可以喝一点,马上满十八岁了。真真倒也不推辞。真真后来告诉他,她跟那几个女生也没什么大仇,学校拉帮结派成风,女生也有小团体,不加入团体就会受欺负,她们拉她入伙,她不愿意(主要是不喜欢为首的女生)。加上平时宿舍生活有摩擦,她也不愿低头,所以那天她们把她堵在巷子里,准备把她教训一顿,让她长个记性。她们吃准了她就算挨了揍,也不会去学校告发她们,这会让她的生存境地更加险恶。真真放下酒杯说,读书挺没劲,我不想读了,反正也考不上大学。李凯劝她还是好好念完高中,说不定有机会上大学呢。真真说,就我们那破学校,每年能上一本的不到十分之一,像我这样的成绩,连陪跑都算不上,纯粹就是炮灰。退一万步说,就算考上二本、三本大学,毕业照样找不到好工作,还不如早点出去。
李凯就吃了没文化的苦头,年纪轻轻出去混社会,文化程度不高,只能干粗活笨活,甚至做了违法的事自己还不知道。但他的话似乎也没什么说服力,他不知道现在的文凭到底还值不值钱,甚至不明白二本三本有多大区别。他只知道,文化程度太低在南边也找不到好岗位,只能进工厂做女工。这个年代还去流水线上当工人,每个月累死累活挣三五千,有什么意思?李凯看到一对母女经过,有说有笑,随口问真真,你爸妈呢?他们什么意见?
真真情绪激动起来,说,提他们干吗?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不了解学校,也不了解这个社会,他们只会打工。李凯说,他们挣钱不都是为了让你上学吗?真真说,是,也不完全是,我两年没见到他们了,要是能见到他们,我会跟他们好好谈谈。李凯有些冲动,你要是想见他们,我可以带你去。真真说,你说真的?李凯说,当然是真的,去一趟广东还不简单?等你有时间我们开车去。真真说,我爸妈不放心我一个人,他们又长年不回来。
吃完东西,李凯把真真送回学校,一个人往文星镇开。他左手搭方向盘,右手夹一支烟。烟雾飘到窗外,很快消散在空气中。他笑着摇摇头,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到了这个年纪还这么冲动。有些话脱口而出,自己都没料到。但既然说到就要做到,不就损失一点钱和时间吗。能让真真跟她父母见个面,这些都不算什么。他这样想着,身体里涌动着一股气流,以至于见到李乾勇时,面色还有些红润。李乾勇笑嘻嘻地说,凯哥,是不是交了桃花运?春风满面。他板着面孔说,也没什么,接了一个长途单。李乾勇说,长途单?是真真吗?她要去广东?他说,没有没有,她去广东干吗?
从文星镇往南方走,经过南风坳,有一段盘山公路。汽车沿Z 字形往上爬,再弯弯绕绕下来,这是文星镇人的噩梦。李凯第一次坐长途大巴去广东时,车上许多人经受不住没完没了的盘绕,吐得人仰马翻。以至于有些害怕坐车的文星镇人,听到“南风坳”几个字,就会下意识地呕吐。他倒是天生不晕车,甚至闻到汽油燃烧的气味还会莫名兴奋。到广东没多久,他就跟车子沾上了边。先是摩托车,而后轿车、客车。他双手搭在摩托车上,感觉就像坐在饭桌前,左手酒杯,右手筷子,一边喝酒,一边吃菜,摩托车仿佛嵌入肉身,快慢自如。如今回到文星镇做网约车司机,似乎也顺理成章。
其间,李凯跑了几趟广东。有的是老人带着大包小包去儿子家里,说是去帮忙带孩子。儿子为了省事,直接叫了李凯的车。车子经过南风坳时,他尽量开得稳一些,不停跟他们说话。那些从未出过远门的老头老太,不知不觉过了这道坎,自然感激不尽。有的带着行李出去,年纪跟他差不多大,大部分是念了大学出去的,在广东那边找到一份正经工作。人送过去,他很少在那边逗留。有时连饭都不吃,就往回赶。那边当然有他的朋友、兄弟,只是他不想跟他们联系。既然离开那个圈子,就不要再跟他们牵牵扯扯。
放寒假后,真真开始找他谋划出行之事。他以为真真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她真要去广州。她说出发前千万不要跟她父母说,如果说了,他们肯定不同意,这趟出行就泡汤了,还不如“先斩后奏”。他想想不无道理,便答应了她的要求。不光没对她父母说,也没有告诉她爷爷。每天跟他抢生意耍嘴皮子的李乾勇自然也毫不知情。他只是跟父亲说自己要出去几天。
那天中午,他从县城文庙广场接了真真,往城外驶去。驶上高速那一刻,他甚至有一种私奔的感觉。真真掩饰不住兴奋。她说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而且不是跟着父母。她让李凯放《成都》。到了副歌部分,她也跟着大声唱起来:“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唱得颇为投入,虽然有些荒腔走板。走了一个多小时,两人情绪渐渐平静下来。
他问真真,那天为什么上他的车,而不是李乾勇的。真真说,他——不是什么好人。他说,怎么不好?真真却不肯多说,你多接触接触就知道了。两人一路聊着,天色渐渐暗淡。再往前就是南风坳,李凯问要不要上山。真真说,走吧,只要你不犯困。李凯开车就没犯困的时候。他最高纪录开过四十几个小时,从广州开到大连,也不过腰有些疼。他点了一支烟说,那我们就走吧。盘山路曲折盘旋,忽而往东,忽而往西。他走过许多回,倒也还算熟悉。只是到了晚上,山上没有路灯,全靠汽车大灯照亮前方。无数蚊虫在雪白灯光中飞舞,有些直接跌落在挡风玻璃上。
快到山顶,路却行不通。山体塌方,堵了半侧路面,一辆车大约是没看清,直直冲撞上去,车身横将过来,把另外半边路面挡得死死的。李凯和真真下了车,车上空空如也,驾驶员已不知去向。他们察看了地形,实在没办法移动车辆。打了110,警察说明天一早来处理。还有几个小时天就亮了,掉头开回去危险不说,也不划算。这是去往南方的必经之地,不如坐在车上等天亮。已是农历冬月深夜,又在海拔大几百米的山上,相比白日,气温骤降十几度,车外如同冰窟。汽车怠速担心油不够,熄火又经不住冻。还好车上有件厚实的军大衣,他们坐在后排,把大衣盖在身上,渐渐感到一丝暖意。
大灯熄灭,窗外顿时陷入黑暗,四周阒寂无声。过了一会儿,他借着月光,隐约看见大山和树木青灰色的轮廓。偶尔有猫头鹰和不知名兽类的叫声,增添了几丝恐怖感。他们像被文明世界抛弃的人类,在这荒郊野外忍饥受冻。还好不是一个人,即使有什么情况,比如冻死、饿死,或者被野兽攻击,至少还有个人陪伴,李凯不由伸出手臂搂住身边的女孩。
真真没有太多抗拒。他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他很笃定地认为,这肯定不是香水,而是女孩身上散发的体香。密闭车厢里,气味无处遁形,进入鼻腔、进入肺腑。他说,你——还好吧?呃,我是说冷不冷?真真说,都怪我,这个时候不该上山。没事,不要担心,天亮就有人来的,只要过了南风坳,再开上一两个小时就能到你爸妈那里。我不担心,不是还有你在这里吗。
身上渐渐暖和了一些。正是腊月上旬,月亮如一把镰刀挂在空中。李凯跟他的伙伴经常在夜里出动,也练就了野猫般的夜视力。他能在黑黢黢的夜里辨识一辆车的品牌、型号,也能在没有路灯的巷子里奔跑。天眼系统,红外监控,让他这些“能力”失去用武之地。此刻,他透过玻璃窗看出去,却什么都看不清。窗外只有晦暗的天空、山峰和树木,以及星星点点的灯光。
我们来玩真心话大冒险吧,真真忽然说。什么真心话冒险?李凯问。就是把你平时最不愿意告诉别人、最不想说的经历讲出来。通常都是一问一答,今天就我们两个人,干脆轮流讲吧,你先讲,等会儿我来讲,你敢吗?
李凯说,有什么不敢的?他摸出一支烟,掏出打火机点燃,烟头在黑暗中发出幽暗的红光。他缓缓说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起?可能是初中吧。我妈去了外地,一年到头也看不到人。我爸说她跟着别人跑掉了,不要想她。他整天喝酒、赌钱,不怎么管我。我的成绩不太好,班主任找我谈了几次,我没放在心上。我对读书越来越没兴趣,想着早点出去。班上有个叫赵小刚的,经常带我玩。有一次,他说带我去另外一所学校玩。我跟着他走了几里地,到那里天都黑了。他对地形很熟悉。我们从围墙爬过去的,他让我在下面看着,他钻进宿舍,没过多久就出来了,身上多了几件东西。第二天,他带着我坐车去了县城,看录像、打桌球、唱歌,玩了整整一天才回来。当然都是他付的钱,我没问他钱从哪里来的。后来他又在夜里带我出去了几次,我渐渐明白了那些钱的来历。有一次,我们被学校保安抓住了。他们把我们关在房间里,威胁要把我们送到派出所。小刚趁保安不注意,解开绳子,把我也放开,我们俩爬窗户跑了。再后来,我就没上学了。我跟父亲说,我不是读书的料,还不如早点出去打工。我爸劝我几次,看我心意已决,也就不管我了。到了广东,我没什么好的地方可去。在模具厂、玩具厂干了大半年,我受不了那种生活,天天加班,搞得筋疲力尽。巧的是,我在东莞又碰到小刚。我们约好一起做事,配合很默契,我开车,他干活,来钱快也刺激。有一次搞了几万块,全是绿色的“富兰克林”。也有失手的时候,有一次摩托车撞上街头消防栓,我和小刚都飞了出去,断了几根肋骨,小刚摔成脑震荡,反应也慢了许多。看守所也是几进几出。从此以后,我们就开始做生意,卖手机、保健品啥的,有赚有赔,都不是什么大买卖。再后来年纪大了,就回了文星镇……
外面刮起了大风,风声拂过树林穿过山谷,发出骇人的声响。李凯的声音淹没在呼啸的风声里。他想起有一回住在海边,海浪翻涌,跟这个声音很像。那天,他跟一个女孩待在一起。第二天早上,女孩却悄悄离开他,没有留下任何信息。那是他最落魄的时候,生意失败,兄弟翻脸,多年积蓄化为乌有,最基本的吃住都成问题。他一开始不想去找她,走就走吧。几个月后的一天,他喝醉了酒,忽然很想见她。女孩却换了号码,微信消息也发不出去。两人从此再也没见面,那女孩就这样从他的生命中消失了。
真真看他沉默无语,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也开口说道,说实话,我羡慕你的经历,相比之下,我的生活简直就是一张白纸——当然也不完全是白纸。说来不怕你笑话,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我上小学时父母就去了广东,刚开始每年还回来一两趟,后来次数越来越少,这几年很少回来,也不知他们在忙什么。我跟着爷爷生活,上了初中后我开始住宿,我爸妈也不想让我每天跑来跑去。大概初二的某个星期六,我放假走路回家,有个人开摩托车从我身边经过,在前面停下来。他问我去哪里,我说文星镇。他说他可以载我回家,我说我身上没钱。他说没事,他顺路带我回去,不收钱。我看他不像坏人,就上了他的车。这个人就是李乾勇。后来他就经常送我去学校或回家,刮风下雨都不间断。我其实心里对他蛮感激的。如果,如果不是后来那件事,我也许会把他当作很好的哥哥。真真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黑暗中,她的身体颤抖着,李凯似乎能看见她的脸色变得绯红。真真艰难地断断续续地说出李乾勇对她做的事。虽然言语混乱,他还是大致明白了她的意思。
李凯不知该对真真说些什么。他也好,真真也好,都是这个世界的弃儿,被父母抛弃,被朋友抛弃,被社会抛弃,却又无处可去、无处可逃。如果不是母亲离开、父亲放任,他也许会走上另外一条路。但事已至此,似乎说什么都迟了。他搂着真真的肩膀,喉咙发出浑浊的近似呜咽的声音。
两人倚靠着,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李凯被窗外的光刺醒,虽然隔着眼皮,他还是能感受到光线和温度。睁开眼,他看见真真靠在他的肩膀上,发出轻微的鼾声,嘴角还挂着明亮的液体。他笑了笑,仍然保持原来的姿势。窗外那些青灰色的山峰、树木,渐渐现出清晰的模样。乱石和泥土依然堆在路上,那辆抛锚的车却不见踪影。车是什么时候开走的?还是失去重心滚下了悬崖?为什么他们没听到动静?他仔细回想着清晨的情形,真真醒了过来。
障碍清除,下山的路程也畅通无阻。花了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就从南风坳开了下来。沿着高速又走了一个半小时,上省道,转县道,沿着那些被重型货车压出两条印痕的柏油路,他们进入一座巨型工业区。放眼望去,千篇一律的白墙蓝顶厂房。真真说,她父母就在这家叫“立益精密”的模具厂里。李凯说那赶紧打电话啊。真真说,没用的,他们上班不准带手机,等中午吧,他们会出来的。这段时间,他们去小店里买了广东肠粉。李凯怕不够,特意多买了一份。两人把三份肠粉吃得精光。吃完以后,人也精神了很多。
到了中午,穿蓝色工装的工人纷纷涌出来,大部分人神情呆滞。真真拨了电话过去。电话那头的人语气惊诧,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真真会出现在这里。没过多久,两人从蓝色人流中走出来。他们比李凯想象得要老一些,额头、眼角、脸颊布满细密的皱纹。也许是晒不到太阳,肤色有些苍白。真真介绍李凯给父母,说这是送她过来的司机,也是文星镇人。李凯感觉真真父母看他的眼神有些奇怪,不过也没多想。四人找了间小餐馆坐下。真真跟他们说起自己是如何到的广州。母亲说,你来怎么不告诉我?我们也好准备准备。父亲也说,你这样贸然过来,搞得我们措手不及,连个住的地方都没安排。真真说,我就待一两天。母亲说,难得来一趟,好好玩几天。三个人絮絮叨叨说了好久,询问起家里的房子、爷爷,还有她的学习成绩。李凯坐在边上插不上嘴,便借口出去抽烟,走到餐馆门口。餐馆外面五花八门的店招、轰鸣而过的摩托车、丝丝缕缕的大榕树,勾起他许多回忆。这样的城市有一个好,无论你是身无分文还是腰缠万贯,都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活下去。
不管怎样,你要去试试,你试都不试,怎么知道自己不行?读书还是有前途些,你看我们整天在这里的流水线上做,就是赚点辛苦钱,那些大学生,进厂没多久就坐办公室、打电脑,事情少,人轻松,钱还比我们多……两人说话的声音高起来。真真也在努力表达自己的看法。之前对李凯说过的话,她对父母又说了一遍。但是父母并没有把她的话当回事,而是反复跟她说读书如何如何。她跑这么远,如果只是想做通父母的工作,未免有些天真。
真真父母来不及请假,下午回到流水线继续上班。李凯和真真在附近找了家小旅馆,开了两间房。李凯洗了一个热水澡,躺在床上刷了一会儿手机。有几条是李乾勇的信息,问他去哪里了,怎么见不到人。他想想没回复。暖风吹拂,他很快就睡了过去,但睡得并不安稳,隐约听到说话的声音,又听不真切。被一泡尿憋醒时,他发现房间里已经暗下来。看看手机,差几分钟就到六点。他胡乱洗了把脸,关掉水龙头时,再次听到了说话声。
听起来像真真母亲的声音:你知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从小就没人管,上初中时偷东西被学校开除,到了广东飞车抢劫,非法传销,到处借钱不还,他爸都要跟他断绝关系,这次回去估计也没那么简单,文星镇人防他都来不及,你怎么还敢搭他的车过来?父亲也说,李乾勇不是也开网约车吗?怎么不坐他的车?真真听到这句话,毫无征兆地喊出来:你们了解他吗?你们又了解我吗?你们在我身边待了多久?他就不能改邪归正、浪子回头吗?还说什么李乾勇,他就是禽兽,禽兽都不如……那边传来真真的哭声。房间安静下来。
真真和她父母出现在他面前时,神色看不出什么异样。真真母亲甚至表现出某种过分的热情,似乎想掩饰什么。吃过晚饭,他们乘地铁去看“小蛮腰”。城市夜色中,通过LED 变换颜色的塔身展现出婀娜姿态。地面广场上有人唱歌、吹萨克斯、卖小饰品、跳广场舞,还有许多人骑车、散步、练字。江面上浮着几条游轮,船舱里灯火通明,坐满了游客。灯光倒映在水面上,形成层层叠叠的五彩光晕。游船缓缓移动,水面上的光晕随之破碎、消融。
真真和父母走在前面,李凯跟在后面。如果不知晓那些秘密,他也许会以为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没有人知道他们好几年没见面,以及真真所经历的事情。很多东西谈不上对和错,就像母亲当年离他而去。他当时也不明白,心中的埋怨、愤怒化为叛逆,化为与父亲的对抗。长大后他渐渐理解母亲,也许她也有自己的苦衷,只是无处倾诉。三人走进高楼,坐上观光电梯。电梯缓缓升起,随即提速。李凯耳内有轻微压迫感。真真父母神色也有些紧张。电梯越升越高,他干脆闭上双眼。直到电梯门打开,压迫解除。
从近六百米的高度俯瞰,整座城市一览无余。灯光铺陈而去,如同河流缓缓流淌,直至城市边缘。真真掏出手机,对着城市夜景拍起来。李凯站在真真父亲边上,掏出香烟,却想起一楼过安检时打火机已经被收走。他把香烟放回烟盒,很随意地说道,有空你们也回去看看,真真毕竟是女孩,不在身边,她有些事情也不好对你们说。真真父亲说,我们过年过节不回去,也是想多挣钱,等她考上大学,还得花一大笔钱。他说,钱当然重要,但有比钱更重要的事。真真父亲说,什么?他本想说些什么,话到嘴边却有些迟疑。这时,对岸放起了烟花。一道道光束冲向天空,“轰”地炸响,在空中绘出彩色图案。
回去的路程顺利许多。真真不像来时那么兴奋,坐在副驾驶座上长久不出声。在南风坳山上绕来绕去时,她甚至睡了过去。李凯为了不犯困,抹了风油精在太阳穴和人中上。气味弥漫开来,真真咳了两声,也醒过来,迷迷糊糊地问他到哪里了。李凯说,刚爬过南风坳,现在往下走,你再睡一会儿。真真说,不睡了。过了一会儿,真真又说,我想好了,回去把书念完,无论考上考不上,给他们一个交代。李凯说,你能体谅他们的心意,也算没白来一趟。真真说,谢谢你,说实话,来之前我都快要崩溃了,很多事情没人可以商量,又特别抗拒考试。李凯说,想明白就没事。真真说,那个李乾勇的事,请你答应我,不要跟别人讲,我跟爸妈也没提起过。李凯说,明白。
车子开到文星镇,差不多下午五点。太阳已经沉到西边,整座村庄笼罩在落日暗红色的余晖中。李乾勇在桥边等客人,瞥见他们,脸上有些疑惑,笑嘻嘻地说,原来你们一起出去,难怪呢,真真,你爷爷还问我你去哪里了,我说我怎么知道,真真又不是我的人。真真站在边上没搭理他。李乾勇接着说,你们这成双成对的,出去度蜜月啦?凯哥,胃口不错,老牛吃嫩草啊。李凯说,你他妈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李乾勇继续觍着脸说,对,我是狗,你们就是狗男女。李凯看着李乾勇油腻的面孔、潮红的鼻子,以及被烟熏得发黄发黑的牙齿,忽然觉得有些反胃,他的手几乎下意识地推出去。李乾勇踉跄几步,很快反应过来,向他扑来。他侧身躲开,借力将李乾勇推倒在地。李乾勇爬起来,他一脚踹过去。李乾勇躺在地上,喊着“打人啦,打人啦”。边上有人围拢过来,却无人敢上前。他捡起半截砖头,一步步向李乾勇走过去。
——以新乡学院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