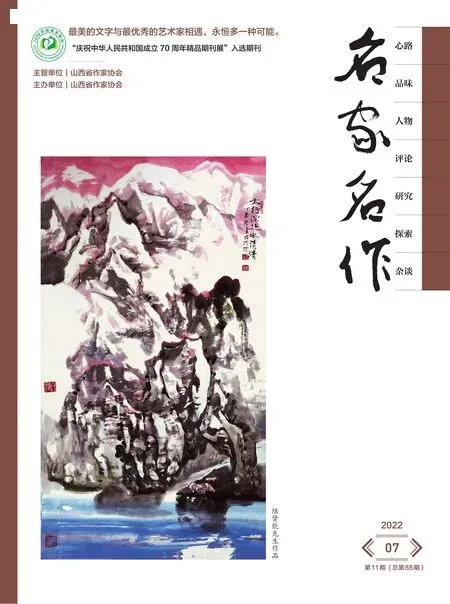基于图尔敏模型的先秦论辩研究—以《墨子》为例
蔡 慧
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发展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我们现代所讲的中华传统文化大多可以溯源到这一时期。“百家争鸣”时期最突出的特征便是思想大碰撞。所谓“争鸣”,即论辩实践活动。诸子百家都参与到这一时期的论辩实践活动中,从而促使思想在碰撞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似可以说,如果没有诸子之间的论辩,便不会有“百家争鸣”的繁荣。
不过,目前学术界对诸子百家思想的研究大多是对各家思想的独立研究,而且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各家思想的解读和阐发。这类研究固然可以深入地挖掘各家思想的内涵和价值,但也容易忽略各家思想是在论辩实践活动中建立起来的这一事实。这导致我们缺乏对先秦思想动态的、整体的历史认识。本文则是从论辩实践活动的角度,以《墨子》为例,探讨先秦思想的发展脉络,并借助图尔敏模型对先秦论辩加以分析。
一、《墨子》中的论辩方式与图尔敏模型
墨家擅长论辩,并专门研究过论辩。西晋鲁胜曾作注称,“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墨辩注·序》)后世学者在鲁胜的基础上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统称为《墨经》或《墨辩》。墨家有关论辩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墨经》之中。
关于论辩的结构,《墨经》中有“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墨子·大取》)其中,“辞”便是需要确立、希望他们接受的观点。“故”是用于确立观点的依据。《墨子》中有“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墨子·大取》)可见,“故”的作用便是去妄。“理”是指“故”可以用来确立“辞”的理由。《墨子》中有“今人非道无所行,唯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墨子·大取》)于是,“理”就像是从“故”通往“辞”的道路;如果没有“理”这条道路,那么即使有再充分的“故”也很难确立“辞”。
关于“类”,《墨经》有言,“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墨子·大取》)由此可知,“类”也是作为确立“辞”的理由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墨子》将“故”“理”“类”三者区分来谈,称“三物必具,然后足以生”。(《墨子·大取》)可见,“类”是不同于“故”和“理”的。那么,作为立“辞”的理由的“类”又具体起到什么作用呢?
回到论辩实践活动中,论辩实践活动显然不会是一个静态的文本,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论辩实践活动中,会同时存在多种不同的言论。而论辩的目的则是要在众多言论中确立自己的观点,即“论求群言之比”(《墨子·小取》)。在这一过程中,立“辞”就不仅要说明“辞”是如何得以确立的,还要说明为什么这样可以确立“辞”。其中,“故”和“理”的作用在于说明“辞”是如何确立的,而“类”的作用则在于说明“辞”为什么这样便被确立了。正所谓,“以类取,以类予。”(《墨子·小取》)
因此,我们看到,“故”“理”“类”虽然都是确立“辞”时的理由,但是“故”“理”“类”三者的作用却是不同的。尤其是从论辩实践活动的角度看,三者各自的作用是互相不可替代的。
由于“墨辩”是在论辩实践活动中提出的论辩方式,考虑到传统逻辑的论证分析方法往往是静态的文本分析,所以,用传统逻辑的方法分析“墨辩”往往会忽略论辩中的实践活动特性。因而,我们需要以一种新方法分析动态的“墨辩”,这种方法便是图尔敏模型。
图尔敏模型是实际的法律论证作为参考而建立起来的论证模型。图尔敏指出,在法学模型中,提出一个论证的过程包括主张、根据、担保、支援、限定词和反驳这六个功能要素。其中,主张、根据和担保是基本功能要素,在每个论证过程中都会出现;支援、限定词和反驳属于补充功能要素,并非所有论证过程中都存在。
对照图尔敏模型,不难看出,图尔敏模型中的一些功能要素与“墨辩”的“三物”是可以对应起来的。其中最明显的一组对应是,“辞”对应着“主张”,这是因为“辞”和“主张”都是有待确立的观点。因为“故”是用于支持“辞”的,而“根据”是用于支持“主张”的,所以“故”与“根据”对应。另外,“理”和“担保”的作用都是保证“故”与“辞”(或“根据”与“主张”)之间的支持关系成立的,因而,“理”对应着“担保”。
于是,我们看到,《墨子》中提出的论辩方式实际上已涵盖了图尔敏分析的全部基本功能要素,满足基本的图尔敏模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可以认为:其一,《墨子》中提出的论辩方式满足一般的论证模型,而非中国先秦所特有的论证方式;其二,图尔敏模型可以用于分析《墨子》中提出的论辩方式。
然而,我们也看到,“类”与图尔敏模型的各个功能要素都是不能完好地对应的。“类”的作用是确保“故”和“理”确实可以用于确立“辞”的,而图尔敏模型中并没有涉及这类作用的补充功能要素。所以,“类”并不能对应到图尔敏模型中。因此,《墨子》中提出的论辩方式其实可以看作是对基本的图尔敏模型做出的另一种扩充。
“类”之所以是对图尔敏模型的另一种扩充,我们可以尝试着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分析其中的原因。“类”在论辩中的作用是说明“为什么”的,而不是说明“如何”的。然而,在法律论证领域,由于学术传统的影响,论证的提出者与质问者具有相同的学术背景。这便使得,无论是论证的提出者,还是论证的质问者,接受的是相同的思维训练。因而,在法律论证领域不会出现“为什么”的质问,凡是质问“为什么”者是无法参与到法律论证中的。然而中国先秦的论辩实践活动中并不存在这种统一的思维训练,所以,有关“为什么”的问题在论辩实践活动中便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只有论辩参与者在“为什么”的问题上达成共识,论辩实践活动才能顺利地进行下去;否则会容易产生鸡同鸭讲的效果。因而,“类”相当于为论辩实践活动规定了“活动范围”。
二、基于图尔敏模型的“墨辩”评价标准
图尔敏模型在分析并评价论证时具有领域依赖的特点。所谓“领域依赖”是指,在不同领域中评价一个结论是否得到辩护的标准是不同的。图尔敏模型是对实际生活中的论证做出的非形式化分析,而实际生活中的论证可能发生在不同领域中。这些不同的领域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个具体的“论坛”,论证的提出和批判性审查都是发生在具体的“论坛”中的,参与到“论坛”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行为显然要遵守各自“论坛”的标准。
在图尔敏的《论证的使用》一书中,关于论证的评价标准提出的核心观点是:论证只有适合没有最好,因为论证只存在领域内的比较,而没有领域间的比较。从一个领域移动到另一个领域,要注意不同领域的论证形式的风格和方式的差异。
基于图尔敏有关领域依赖的分析,我们看到,图尔敏模型的评价标准其实是一种可扩展的评价标准,这种评价标准的可扩展性使得根据图尔敏模型做出的论证评价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进一步说,在图尔敏模型中,担保作为根据可以支持主张的保障,其之所以可以起到保障作用的依据也是多元评价的,或者称领域依赖的。因而,担保所起到的保障作用并非是对“真”的保障,而仅仅保障了根据可以支持主张,这也就是图尔敏所谓的保权性原则。保权性原则允许在接受根据的条件下得出具有可废止性的主张。
从保权性原则来看,图尔敏模型显然不会建立起传统逻辑中的“有效性”的评价标准;相反,图尔敏模型的评价标准是更多地侧重于语用上的“生效性”。对于“生效性”,通俗地讲就是在实际的论辩实践活动中产生效果。不难看出,“生效性”恰好是“墨辩”所追求的。《墨子》曾对“辩”做出过说明,“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墨子·小取》)从中可见,“墨辩”是有着明确的现实追求的。所以基于图尔敏模型做出的“生效性”评价是符合“墨辩”本意的。
回到“墨辩”之中,按前文分析,“墨辩”中的“类”是无法对应到图尔敏模型的任何一个功能要素上的,“类”是对论证的“活动范围”做出的规定。从图尔敏模型的评价标准来看,“类”的规定性实际上就相当于“论坛”。我们从《墨经》对“类”的说明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墨经》中有多处都提到了“类”。除了前文提及的《大取》和《小取》中有关“类”的说明外,《经下》中也有“推类之难,说在之大小”(《墨子·经下》)和“异类不吡,说在量”(《墨子·经下》)的说法。“推类之难,说之在大小”表明论证是否生效,与选取的“类”的范围有关;“异类不吡,说在量”进一步表明“类”所规定的范围不同,论证是无法保权的。因而,我们看到,“类”其实是判断论证是否生效的评价标准,人们是依据选取的“类”的差异来评价论证的。在这个意义上,似可以说,“类”实际上就是“墨辩”中的领域依赖;“墨辩”是否成功依赖于论辩实践活动依赖的领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墨子》中提出的论辩方式是一个完整的论辩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既包括论证的结构,又包括论证的评价。而“墨辩”又以“三物必俱”(《墨子·大取》)的方法将论证结构和论证评价巧妙地融合为一种整体考虑,使得“墨辩”可以直接应用于各类不同的论辩实践活动,这也是“墨辩”相对于图尔敏模型的独特价值。
三、《公输》中的论辩实践活动分析
明确了“墨辩”与图尔敏模型的对应关系后,我们接下来将以《墨子·公输》篇为例,具体分析“墨辩”在论辩实践活动中是如何应用的。
《墨子·公输》一文中记录了墨子与公输盘和楚王之间发生的两次论辩。
在墨子与公输盘的论辩中,墨子提出想请公输盘替他杀人后,公输盘表明自己的态度,“吾义固不杀人。”(《墨子·公输》)从公输盘的回应中可以看出,公输盘所立之“辞”是“不杀人”,而立辞之“故”是“吾义”。进一步分析也不难看出,公输盘立辞之“理”是“义不杀人”(奉行义的人不会去杀人)。
不过,墨子却指出了公输盘的说法中存在漏洞:“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馀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馀,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墨子·公输》)墨子指出,公输盘并非不杀人,而是“不杀少而杀众”。所以,公输盘自称的“吾义”与不杀人的“义”并非同类。换言之,公输盘口中所言之“义”并不属于“义不杀人”的领域。所以,公输盘的论证是失效的。
正是由于墨子发现了公输盘“义不杀少而杀众”的问题,论辩的结果是“公输盘服”(《墨子·公输》)。
在墨子说服了公输盘后,又与楚王发生了论辩。在与楚王的论辩中,墨子含蓄地指出楚王是有窃疾的人。具体地,墨子首先诱导楚王说出立辞之“理”,即自己所有优于邻人所有却仍欲盗窃邻人的人是有窃疾的。其次,墨子提出立辞之“故”:楚国所有优于宋国所有,而楚王仍想占领宋国。并且,墨子指明,“臣以三事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墨子·公输》)最终,楚王只能无奈地回复“善哉”。所以,墨子的论证是生效的。墨子指出的“为与此同类”恰说明楚王与有窃疾之人属于同一领域。
通过以上“类”扩充的图尔敏模型的分析,我们既可以看出墨子与公输盘和楚王之间的论辩的结构。并且,在评价论证是否生效的时候,我们遵循了《墨子》中“类”的评价标准。在这个意义上,似可以认为,用“类”扩充的图尔敏模型分析《墨子》中的论辩,相较于传统逻辑的分析,更加符合“墨辩”的本意。
四、结语
在上述分析《墨子·公输》中的论辩时,我们其实是根据“墨辩”理论构造了一种“类”扩充的图尔敏模型。这种“类”扩充的图尔敏模型并非图尔敏提出的扩展模型,而是将图尔敏模型与“墨辩”相结合而做出的新发展。这种新的“类”扩充的图尔敏模型更加注重“类”在论证分析与评价中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图尔敏模型与“墨辩”的结合并非机械的叠加。事实上,图尔敏模型与先秦论辩研究是具有内在共通性的。李先龙和张晓芒曾基于图尔敏的论证思想提出了逻辑史中的问题历史化研究。可见,将图尔敏模型与“墨辩”相结合是有内在合理性的。这种“类”扩充的图尔敏模型不失为研究中国先秦论辩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