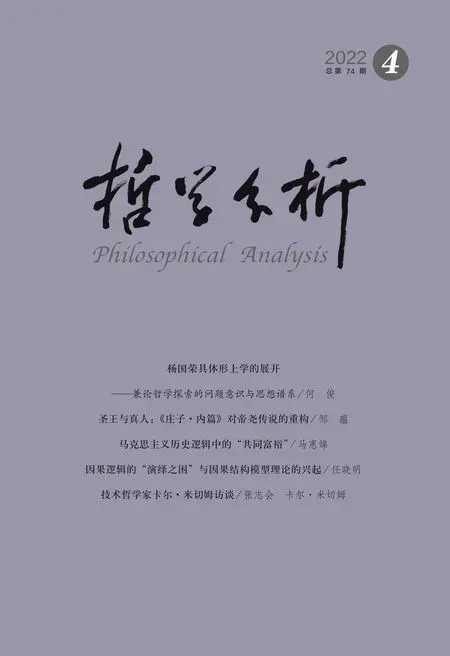生成的主体间性:双向预测与意义建构
何 静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以“计算—表征”为核心的第一代认知科学研究范式的衰落,以“具身性”(embodiment)为核心的第二代认知科学研究范式悄然发展起来。这种新的研究范式主张:认知并非大脑基于抽象符号的计算和问题的解决过程,而从本质上说是主体在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具身行动能力。沿着这一理论思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试图通过主体与世界间具身的、情境的动力循环来解释不同的认知过程,如知觉、情绪和行动 等。
第二代认知科学的研究范式孕育的新观点和新方法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认知的研究。社会认知关注主体对自我和他者的判断、理解和评价。历史上,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哲学讨论主要有:类比论证、归纳论证、行为主义论证和符号语言论证等。然而,这些经典的哲学论证基于理智主义的哲学传统和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导致了自我与他者之间无法消弭的不可通达性。近年来,第二代认知科学研究范式的支持者们一方面积极吸纳现象学和社会科学中关于“交互主体性”的考察,另一方面受益于认知科学中关于社会感知的经验研究成果,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生成的主体间性”理论。这种理论强调社会交互过程的具身性本质,主张主体通过特定情境中的第二人称交互过程达成了对他者的 理 解。
就研究现状而言,生成的主体间性理论仍然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这种精细而复杂的主体间性过程背后的认知机制是什么?大脑和身体在第二人称式的交互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主体对他者熟练的回应能力仅仅是社会性本能吗?主体如何依据无意义的感官输入形成对他者有意义的理解?这样的疑问不仅是生成的主体间性理论亟待解决的理论难题,也是“他心问题”这样古老而常新的哲学难题的核心关 切。
本文将要表明:积极吸纳认知神经科学中关于预测心智(predictive mind)模型的研究成果,以及引入中国哲学中关于“事”的敏锐洞见,能够为生成的主体间性理论所遭遇的困境提供新的理论出路。一方面,预测心智的理论模型能够为主体间的动态交互过程提供脑与神经机制的说明;另一方面,通过将由主体间性和实践性共同担保的“事”的维度纳入社会交互过程,一种基于“事”的主体间性理论将为我们提供一种更清晰、更具说服力的社会交互理 解。
一、生成的主体间性
客观主义将认知视为对外部世界的映射(mirroring),认为心智是自然之镜;主观主义将认知视为心智对外部世界的投射(projection),认为世界是心智之镜。前者忽略了认知主体的主动性,而后者无视世界的现实存在。不过无论是客观主义还是主观主义,都患有“笛卡尔式的焦虑”——对确定性和客观性的渴 望。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生成主义(enactivism)试图将认识论从“心智—世界”之间对立的严格逻辑中释放出来,以反笛卡尔的方式重新理解认知主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它主张:主体所认知到的世界既不是心智对外部世界进行表征的结果,也不是心智的臆造之物,而是主体通过身体的知觉—行动,与特定环境中的结构特征进行耦合而生成的。简而言之,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表征关系,而是认知—行动的耦合关系。在这一图景之中,主体和世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认知系统,认知是这个系统涌现的结 果。
如胡托(Daniel Hutto)所说:“生成主义认同这样一种观念:心智是从有机体自治的、自组织的、自我复制的行动中涌现出来的。这些行动从本质上说是有机体与环境之间嵌入的、具身的交互,并且这些交互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发生并不断发生改变”。这种生成的认知观是与第一代认知科学中经典的表征主义截然不同的解释框 架。
以接抛球运动为例。按照表征主义的解释框架,当球从对方手中飞过来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对球的速度和轨迹进行计算,并根据计算结果迅速向身体发出运动指令,而后身体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移动抓住球。这种表征主义的解释将认知看作是“后—知觉”(post-perceptual)的大脑过程——认知发生在知觉过程之后,其功能是解释知觉和指挥身体运动。
不同于表征主义的解释进路,生成认知反对将认知看作是一个孤立的、离线的、对表征进行处理的大脑神经活动过程,而主张认知过程在本质上是一个大脑与身体的知觉—运动、具体情境进行持续的动力耦合过程。这种大脑—身体—环境之间的动力耦合过程包含了神经生物学过程、身体运动、情绪以及来自环境的调控过程等。因此,当我们看到对方手中即将抛过来的球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行动涉及大脑中的视觉皮层、前运动皮层、抓住球的欲望、对行动后果的判断以及手与手臂运动等等。其中任何一个参数的变化,将导致知觉产生相应的变化。假如接球的主体是一个先天高度近视的人,那么他对事物距离的感知以及采取相应行动的方式便会异于他人;假如这是一场比赛中决定胜负的赛点球,那么主体将更迫切地想要赢得这个球。类似地,一个体力透支、负重前行的登山者,会比其他人觉得路程更长、崎岖难走。这意味着,身体结构、健康状况以及情绪等会极大地影响认知主体对外部世界的知觉体验和行 动。
这个“外部世界”既是物理的,也是社会的。在社会情境中,主体对他者的理解过程也不是一个对他者的心智状态进行表征和计算的过程,而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包括物理环境、社会角色、文化等)依据他者运动的动力过程、姿势、面部表情、语音语调等,与他者进行交互进而感知他者的意图和情绪的过 程。
这意味着,在社会情境中,主体对他者的理解过程并不是主体对某个外部对象的单向表征过程,而是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之间进行双向协调的动力学过程。这使得“互动过程本身的动力学在使这种行为成为可能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核心的角色。当行动主体试图与一个无回应的搭档进行互动时,互动无法实现……相反,其行动的成功完成根本上取决于他们在与他人的相互联结(coupling with)中所包含的动态属性。给予和索取、来回往复的相互过程成就了各方的行动”。在此意义上,主体间的理解就是两个主体之间彼此定义、相互规范而达致某种一致性的过程(如两个伐木工人一起用锯子砍倒了一棵大树)。然而,这种基于彼此调节而达成的一致性,并不意味着主体双方行动的绝对同步。相反,主体双方往往在不同步和差异之中生成对他者行动和意图的理 解。
想象一下双人共舞的情形。两名舞者需要通过持续的动作协调,以呈现出浑然一体的韵律之美。当一名舞者向前迈步并伸出手的时候,另一名舞者也作出了相应的回应:向对方迈出步伐并伸出手放到对方掌心;紧接着那名舞者向后有节奏地退了两个小快步,另一名舞者也随之跟着节奏向前跟进两步……舞者双方不间断地调节自己的身体重心和舞姿,向对方传递自己的身体—力量(body-weight)和行动意图,以维护整个舞蹈的和谐与稳定。这种主体间的动作协调具有“双向引导(bidirected)的特征,他们建构了彼此的行动方式。因此,‘协调’意味着一名舞者的运动流能够以流畅的方式‘流入’另一名舞者并由此成为另一名舞者运动流的一部分”。如我们所见,在双人共舞的情形中,一个主体的行动变化,引发了另一个主体行动的变化,反之亦然,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了实时的、延展的联合运动知觉。一个主体是自身经验的主体同时也是他者经验的对象;主体在影响他者的同时把他者的变化带回自 身。
这种循环往复的交互作用正是生成的主体间性所强调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双向规定。自我、他者以及具体的情境构成了一个结构耦合的整体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自我与他者之间持续的交互引发了系统中上行的因果作用,同时具体情境中蕴含着的规则、文化、习俗等反过来又控制和调节着自我与他者之间下行的因果作用。社会性的理解就在这种双向作用中生成。在构成数量更大的系统中,多个主体间的多种多样的行为(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等)依赖一定的规则相互作用,从而构成更大规模的社会机构、组织或群体行 为。
我们欣喜地看到,不同于传统的表征主义进路,生成的主体间性重新思考了大脑与身体、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强调了自我、他者和世界之间复杂的相互渗透对主体间性理解的重要作用,突出了知觉与行动之间的深刻联结,呈现了一幅更为丰满的社会认知图景。不过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大脑、身体和世界的相互作用到底是如何被彻底地整合在一起的?在社会性情境中,无意义的感官信息又如何转变成对他者有意义的理解呢?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本文将通过神经科学中关于预测心智模型的研究以及中国哲学中关于“事”的考察,对上述问题进行探 究。
二、主体间的双向预测
第一代认知科学中的表征主义将认知视为大脑对表征的加工过程——始于感官输入,终于对运动系统的指令。第二代认知科学中的生成认知将认知看作是涌现自身体、大脑和世界之间持续的交互过程。在生成认知的图景下,主体对他者的理解过程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在具体情境中与他者进行双向协调并达致某种理解的动力学过 程。
这种生成的主体间性思想有着两个理论硬核:具身性和情境性。具身性强调了身体的行动影响大脑如何对他者作出回应,以及他者如何通过身体行动向对方呈现自身的情绪、欲望和意图;情境性强调了世界中的结构如何塑造并限定大脑所接受的刺激特征。因此,生成的主体间性仍然将大脑看作是认知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器官,但大脑“从主演降为联合主演——即在认知的产生中成为与身体和世界同等的伙伴”.这意味着生成的主体间性需要在大脑—身体—世界的框架中,诉诸一种不同以往的关于大脑工作方式的理 解。
近年来,神经认知科学领域中新兴的预测加工(predictive processing)理论受到了哲学家的极大关注。预测加工理论提出,大脑就好像一个推理机,基于先验的知识和当下的感官输入,运用贝叶斯推理对知觉信息进行解释。这种理论的核心不是大脑对感官证据的被动接收,而是对知觉的主动预测和积极建 构。
作为一个多层级的生成模型(generative model),较低层级的大脑神经环路首先对输入的知觉信号进行先验预测,而后持续地将已有的预测结果与源源不断的感官输入进行匹配。如果结果一致,大脑就直接根据预测结果对知觉进行解释;一旦结果有出入,较低层级的神经环路会将误差提示传入较高层级的神经环路,同时较高层级的神经环路通过发出身体运动指令以“改变知觉输入或者通过改变内部状态以调整识别密度”的方式来修正预测误 差。
这个修正预测误差的过程,就好像科学家不断地将实验数据与理论假设进行比较的过程。当预测误差产生的时候,大脑或者像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家那样,根据数据改变预测;或者像一个有偏见的科学家那样,坚持预测结果并挑选那些仅符合预测的实验数据;又或者像一个伪科学家那样,固守自己的理论而忽视真实的实验数据。由此,著名认知科学家巴瑞特(Lisa Barrett)强调,预测和预测误差之间的平衡决定了知觉经验有多少来自外部世界,又有多少来自大脑。通过“频繁的预测,你体验到的是一个你自己创造的,经由感官世界检验的世界。一旦你的预测足够正确,这些预测不仅会创造你的感知和行动,还能解释你的感觉所代表的意义。这是你大脑的默认模式”。
举个例子来说,当你夜晚独自一人在公园散步的时候,突然听到脚边的草丛中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这时候你的已经大脑预测到“可能有蛇”。同时,大脑会根据这一预测结果启动你的身体运动,如逃离这条蛇。这就是说,在还没有觉察到之前,你的身体就已经不自觉地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如通过急促的呼吸加剧肺部和收缩,以增加血液中的葡萄糖为细胞迅速提供能量,以及肌肉释放更多的乳酸,从而为肌肉作好拉伸和收缩的准备等。当然,你很可能也同时意识到在城市的公园中不太可能有蛇出没,所以这可能只是风吹动干草发出的声音。因此,为了消除可能的预测误差,你决定将身体靠近草丛一探究竟……因此,在还未确定是否真的有蛇之前(处理来自真实世界的视觉信号输入之前),大脑就已经完成了启动身体的预 测。
我们看到,在此过程中,大脑的预测过程与身体行动、外部世界紧密相连。一方面,大脑中无时无刻发生着的预测,指引着我们的行动、解释我们的知觉;另一方面,大脑根据当下的感官证据,通过采取身体行动的方式来降低预测误差。这种“大脑—身体—世界”之间的动力循环,被称作“积极推理”(active inference)。通过积极推理,感官输入作为调整预测结果的参数,行动作为改变预测对象的手段,在预测加工的框架中得到了统一,并由此赋予了知觉以具身性和交互性的特 征。
正如克拉克(Andy Clark)所说,预测加工理论的核心并非大脑的表征——“某种来自大脑内部模型的信号:并且世界隐匿在知觉的面纱之后。相反,预测加工是一种高效且低成本的策略,它的执行和成功取决于行动”。大脑并不是被动地接收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而是主动建构关于外部世界的假设。并且在无法直接与外部世界进行接触的情况下,大脑依赖身体行动来调整预测的误差,令我们与世界之间的持续耦合成为可 能。
正是在此意义上,预测加工所刻画的大脑具身的和动态交互的工作方式能够与生成认知的理论图景相融。大脑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离线的推理机,而是作为更大有机体(鲜活的身体)的一部分,持续地与周围环境进行耦合并最终形成关于世界的预测。在社会情境中,主体感知的对象是一个与自身有着高度相似预测模型的他者。因此,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说,主体间的交互行动和理解过程就是两个在个体形态上相似但又存在差异的推理系统进行双向预测的过程——在我预测你的同时,你也在预测着我。而“评价与更新我对你行动解释的标准与理解一般意义上的行动和知觉的标准是一致的,即预测误差的最小化”。
具体地说,大脑基于已有的社会交往经验以及观察到的行为或听到的言语等感官证据,对他者的心智内容和行动进行预测:“这里的感官证据可以是我听到的言语,从这些言语中我推断出你试图传达的观点。我不仅能够通过预测你可能还会说什么别的来检验我的推断,而且还可以通过自己说些什么,然后预测你会如何回应。同时,你将会把相同的策略用于我所说的。当我们之间的预测误差变得足够小时,大概就达成了对彼此的理解。”换言之,当主体间的预测模型通过相互调节和引导而达到某种一致性的时候,理解就是必然产生的结 果。
作为一种凸显神经生物动力的理论模型,预测的心智模型从神经机制的层面将主体间性描述为两个预测系统持续进行双向预测的过程,为生成的主体间性提供了一种非还原的自然化说明,揭开了主体间交互过程的神秘面纱。我既是预测者又是被预测者,既是自身经验的主体又是他者经验的对象,他者既是我预测的一个部分又是调节我自身行动的一个原因。在预测加工的模型中,大脑不再是仅依据内部表征,而是作为更大的“自我—他者—世界”具身系统中的一个部分,与不断变化着的他者的行动、姿态、情绪以及情境等变量进行持续耦合的预测系统;主体不再是一个对他者的行动和意图进行观察的旁观者,而是通过积极推理和具身行动与他者进行动力学回应的参与 者。
三、基于“事”的共同意义建构
在脑与神经机制的层面,预测加工模型将复杂的社会交互看作是双向的大脑预测过程,为我们理解主体间性提供了新的科学证据与理论启示。然而,在预测加工的模型中,无论他者的行动和情绪多么富有意义,它们的给予方式和价值仅体现在与大脑预测结果的相容或背离。在此意义上,主体间的交互行动就是大脑为最小化关于他人预测误差而衍生出来的手段。那么,在社会情境中,无意义的感官信息是如何转变成有意义的理解呢?换言之,主体间的交互过程如何建构对他者心智和行动的理 解?
当我们看到他者愤怒的表情的时候,我们不仅基于大脑的预测加工机制将这种特定的情绪特征识别为“愤怒”,而且还不自觉地基于这种情绪所承载着的意义作出回应,如感到害怕、惊讶或愤怒等。尽管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说,这些情绪都是经由大脑的预测加工过程产生的,彼此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别。但事实上,我们所创造的意义往往要比给定的信息丰富得多。他者的愤怒是因为被不公正地对待,还是由被人挑唆导致的?他者会因此作出过激的行为吗?在实际情境中,我们往往会基于特定的情境和文化,赋予“愤怒”这一神经生物学的预测结果以不同的意义和功能。神经生物学模型不关注也无法解释“意义的生成”这样的认识论问题,而中国哲学中关于“事”的洞见则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 源。
在中国哲学传统中,“事”泛指主体所采取的多样行动。这里的“事”既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不仅涉及主体与物质对象之间的互动,也涉及主体间的交往。一方面,主体对世界的认识基于所行之事。韩非子说:“事者,为也。”这里所说的“为”即主体在现实世界中所采取的行动。因此,“事”的展开就是主体作用于世界的过 程。
《尔雅》以“劳”和“绩”来定义“事”,以表明“事”还包含着主体基于行动而获得的变革世界的成果以及关于世界的理解。奥斯汀说的“以言行事”也表明“言语”和“认识”也表现为主体的所行之事。这意味着,在主体做事的过程中,外部世界中的对象才逐渐展开并由此参与主体生活世界的形 成。
另一方面,事既包括“做事”,也包括“处事”。做事首先与物打交道,处事则更多地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做事的过程中,“既需要交往双方相互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也有赖于彼此间的默契。交流和沟通主要借助于语言层面的对话和讨论,默契固然也关乎领会……默契以‘事’的参与者之间的彼此了解和互动为条件,并相应地离不开一定共同体中的社会关系”。正如加洛迪(Mattia Gallotti)和弗里斯(Chris Frith)所说,对主体间性的理解离不开对主体为何(why)、如何(how)以及何时(when)进行交互的探究,“在主体参与到特定的交互情境中去之前,那种非还原的主体间模式还只仅仅是一个潜在的模式”。这就是说,主体总是在多样之事的磨练中,认识自己、理解他人,并通过与他人的行动的耦合而达成与他人的合 作。
由此,从神经认知科学的视角看,主体间的理解与合作以主体大脑的预测加工机制为生物学基础;然而从更广阔的实践层面看,主体间性的达成始终蕴含在主体“做事”和“处事”两个维度中。这种基于“事”的主体间性理解将我们的视域从较低层级(lower-level)的神经机制层面,带入更宽广的、更高层级(higher-level)的人类合作层 面。
首先,“事”表现为一种关系性(relational)存在观。中国哲学视域中的“事”具有本源性意义——它是建构主体与世界以及主体与他者关系的主要方式。海德格尔强调,“此在”与他者的遭遇是“经由世界”发生的。也就是说,主体对他者的理解总是直接是与“事”的工具性或社会性情境联系在一起。正是通过日常实际的情境,“此在”才遭遇了他者。这是最初的、原始的与他者遭遇的本质。主体在与他者相遇的时候,所遭遇的不是一个其他的心灵或者是作为需要进行解释的他者,而是与自身共同参与活动的联合行动主 体。
因此,主体首先从“事”中来理解自身与他者的共在,并由此形成了第一人称复数的“我们—模式”。图梅勒(Raimo Tuomela)将“我们—模式”定义为:多个(两个及以上)个体以共同的目标为导向,通过承担相应的角色来实现某种联合行动或达至某种共享的心智状态。因此,我们—模式实际上导向了一种主体间进行合作性行动的实践承诺:“一个群体中的成员A具有某种完成X的共有意向,当且仅当:A以完成X中他应该做的事为意向;并且A具有如下信念:如果这个群体中的其他个体也能够完成各自需要完成的任务,那么X可以通过合作而实现;并且A知道,这个集体的所有成员都相信:通过良好的合作,X可以实现。”其中,X是合作性行动,在这种合作性行动中,主体也不再是一个纯粹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与其他个体紧密相连的社会性个体。由此,布莱特曼(Michael Bratman)主张我们—模式作为“一种事件状态,存在于参与者的态度以及这些态度间的关系之中”,而无法被还原到单个主体的心智状 态。
其次,“事”的展开过程是一个主体不断赋予对象以意义的过程,涉及主体和他者共同生成的融合性的意义建构。基于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社会事实”和弗莱克(Ludwik Fleck)的“认知共同体”概念,威尔逊(Robert Wilson)主张:多个主体共同承担的行动以及由此建构的社会情境,构成了主体认知的社会基础。以科学家群体进行科学研究为例,威尔逊描述了个体科学家如何在科学共同体中形成融合性思考的过程。一方面,个体科学家的研究和思考总是作为更宽泛的科学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而嵌入其中;另一方面,科学共同体本身却不拥有超越个体的思考能力或心智状态。换言之,尽管科学家的思维成果只能处于个体科学家的头脑中,但由于它受到了其他科学家以及整个科学共同体的不断建构,无法被还原到纯粹个体的思维过程。
因此,当主体与他者“共处一事”的时候,主体和其他主体并非彼此独立的,而是进入一个共享的社会情境之中,一个共同参与的意义建构过程。尽管一个主体无法按照控制自身的行动和意图那样控制其他主体,但是会将主体间或群体的信念和欲望纳入自身,并通过与其他主体的意图、语言和行动的耦合而形成的思维和行动已经超越了自身而体现出融合性的特征。例如,当我和你一起观看音乐剧《法兰西之光》的时候,我不仅经验和感受了这部著名的音乐剧,而且还知道你正在和我一同观看。我们之间的相伴随以及互动将直接影响我对这部音乐剧进行感受的结构和质量。换言之,你参与了我关于《法兰西之光》的经验,这种有他者参与的经验迥然不同于单个主体所拥有的独立经 验。
再次,“事”的展开过程包含了规范性的维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曾提出了三个问题:我可以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第一个问题与认知相关,而后两个问题则更多地与评价和规范相关。与之相应,规范性一方面与认知层面的判断——“我可以知道什么”相联系,另一方面又与实际情境中的行动选择和展开——“我可以做什么”相连。哈贝马斯进一步把规范看作是“普遍化了的行为期待”,多个主体共同做好一件事的有效性基础就是“关于有关价值的共识或者基于相互理解的一种主体间性承认”。
这意味着,行事的规范不但能够引导主体的行动取向和思维过程,起到范导性的作用,而且能够帮助主体建立一种理解图式,以更好地预测参与者的行为,降低自身和他者行动的不确定性。多样之事中蕴含着多样规范,这些规范规定了在当下事件情境中,主体应该具有何种信念和欲望,应该采取何种行动才是符合特定规范的。例如,两个人初次见面,如果其中一人先伸出手,那么他就会期待另一人也会伸出手去握手问候;在美国,你在餐厅用餐后,餐桌服务员会期待你支付一定的小费等,这些都是社会规范的要求。当然这些社会规范并不能先天地获得,对这些规范的理解和运用需要在“事”中不断举例、示范和习得。一个主体社会化的过程,就是不断通过模仿和训练,学习在多样之事中如何做才是规范的过 程。
最后,在“事”的展开过程中,主体的感受构成了其重要的方面。感受不同于感觉。认知意义上的感觉主要是基于“感官与对象之间的互动,感受则不限于感官活动,而且更在于认知意义上的感觉具有分析性的特点……比较而言,感受则更多呈现综合性的特点,情感、意欲、意愿、想象、感知、理性诸方面在感受中的相互关联及表现为不同规定之间的互动,也体现了感受本身的综合性”。
这种具有综合性特征的感受尽管基于来自感官的信息,但本质上是主体在知觉外部对象和他者过程中所拥有的状态。这就是说,感受具有意向性。一方面,它是主体对诱发情境作出某种特定的反应,因此感受往往与特定的情境中具体的他者相连。它向主体传递了那些在情境中对主体而言有意义的信息。例如,我因为莎士比亚戏剧中那些深沉而优美的语言而产生的愉悦感;我因为朋友获得职位晋升而兴奋不已等。另一方面,感受是对主体身体内部状态的调节。如詹姆士(William James)所说,如果伴随恐惧的身体变化被去除了,心跳仍然平稳、眼神仍然坚定、面色正常、说话坚定、思维清晰,那么恐惧还剩下些什么呢?因此,主体的感受并不是隐匿在头脑中的神经元活动,而是能够在表情和行动中得到表达和传递。而当主体感受自身的时候,感受的是自身身体的状态,以及自身和他者在具体事务和情境中的位置。在事的展开过程中,正是这些丰富多彩的感受作为某种情感纽带将主体和他者连接起来,达成某种统一或彼此的认 同。
四、结语
我们如何感知并理解他人的问题是社会认知的根本问题。随着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兴起,以“具身性”和“情境性”为理论核心的生成的主体间性理论,反对将社会交互看作是主体对外部世界的表征过程,而强调主体通过特定情境中的第二人称主体间性过程达成了对他者的理 解。
然而,这种主体间性的认知机制是什么?以及那些感官信息如何构成主体对世界和他者的理解?这样的问题成为了主体间性理论亟待解决的理论难题。预测加工模型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为生成的主体间性所强调的第二人称式的动力交互过程提供了自然化的认知科学解释。大脑就好像一个预测引擎,基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生成模型建构起对外部世界的预测。在此框架中,主体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就是一个基于大脑动态自组织的预测过程;主体在外部世界中的行动就是以降低错误预测误差和信息加工负荷为目的的认知参数。在此意义上,社会性理解同样以预测加工模型为神经生物学基础。主体间性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多个主体进行持续的双向预测的过程。这样一来,大脑、身体、他者、行动就构成一个相互嵌入的系统,它们为了达成降低预测误差的目的而彼此协同、相互串 联。
然而,这种神经科学的解释无法解决另一个棘手的问题:主体如何形成对世界和他者的理解?梅洛—庞蒂曾经将主体在世界中的感知过程比喻为“键盘的游走”过程:一个键盘四处游走,尽管锤子的动作是单调而无意义的,但是键盘主动让自己的不同按键接受锤子的敲打,从而形成了不同乐章。这一比喻传递给我们的意思是,主体所获的来自外部世界的“输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主体主动呈现给世界的方式决定的。换言之,主体和世界实际上是彼此决定的关 系。
然而,要更好地理解这种关系,就需要我们跳出预测加工的神经科学框架,进入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的维度。因为无论预测加工的模型如何精细,我们都难以单纯地通过感知的概率性信息流来解释主体间的意义建构过程。中国哲学中关于“事”的洞见,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意义世界的窗户。它不仅在本体论层面彰显了主体与他者以及世界的关系性存在,而且在认识论层面强调了主体如何在实际的境遇中与他者相连,并赋予自身和他者的行动以意义。这种以主体间性和实践性共同担保的“事”的展开过程,为主体间的交互提供了现实的框架和结构性样本,将主体和他者通过相互选择和彼此规范捆绑在一起。在多样之事中,主体间通过强有力的交互,以积累性的方式参与了彼此对世界的理解,创造了凭借一己之力绝不可能完成的人类工程(如建造金字塔、修建长城),形成了具有规范性特征的文化习俗与社会制度 等。
可以看到,这种基于“事”的共同意义建构视角,与预测加工模型对社会交互的自然主义说明高度相符。它们都反对将大脑与身体、知觉与世界割裂开来,强调大脑、身体和世界间持续的交互作用。在社会情境中,主体不再是被动接受刺激的旁观者,而是与他者因为具体的事务而联结的积极的参与者。只有在具体的事务中,主体才能明确自身的问题解决域以及行动规范,并以动力学的方式积极引导和调节自身的社会性行为,生成关于世界富有情感的、有意义的理解。不过,如何进一步理解文化、习俗、规范和层级神经预测间的相互作用,将是未来社会认知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 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