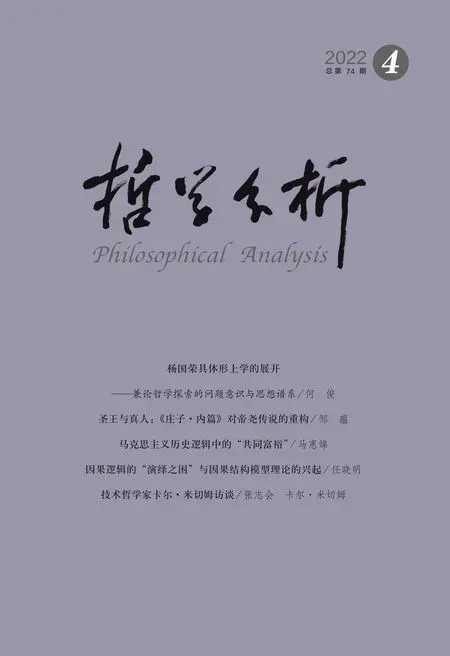马克思在爱尔兰革命道路问题上的转变
祝薪闲
在爱尔兰革命道路问题上,马克思经历了一个自我修正的过程。1869年12月,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长期以来认为可以借英国工人阶级的崛起来推翻统治爱尔兰的制度。我在《纽约论坛报》上总是维护这种观点。但是我更加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现在又得出了相反的信念。只要英国工人阶级没有摆脱爱尔兰,那就毫无办法。杠杆一定要安放在爱尔兰。”紧接着,在次年写给齐格弗里特·迈耶尔与奥古斯特·福格特的信中,马克思不仅重申了上述观点,即“不是在英国,而是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而且进一步补充道,“这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换言之,马克思本人曾清楚明白地承认:他在《纽约论坛报》时期(1851—1862)一度以为,爱尔兰的社会状况取决于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进展情况,但是在1870年前后,他转而认为,爱尔兰革命不仅是撬动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杠杆,而且是撬动全球工人运动的杠杆。对此,美国政治学家奥古斯都·尼姆茨评价道:这是“意义非凡”(most significant)的转变,马克思不仅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找到了“杠杆”(lever),而且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观点,这个杠杆“并不在工业较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之中”(did not reside exclusively in the advanced industrialized capitalist world)。如此一来,把马克思在爱尔兰问题上的转变与其历史道路理论结合起来研究,就成了恰当的并且是必要的。更为要紧的是,这样一种研究将为我们探讨中国革命,尤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于马克思历史道路理论的贡献,打开广阔的学术空 间。
一、《纽约论坛报》时期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革命道路问题的讨论
如果说马克思在爱尔兰革命道路问题上确乎经历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转变,那么我们首先需要追问的是,在这一转变发生之前,马克思对爱尔兰的革命道路有着怎样的判断,马克思所说的他“在《纽约论坛报》上总是维护”的观点究竟是什 么?
1853年,马克思曾先后于《纽约论坛报》第3699号、第3816号发表文章《国防—财政—贵族的死绝—政局》与《印度问题—爱尔兰的租佃权》集中讨论了爱尔兰的革命道路问题。马克思明确提出:“取消合并派的鼓动纯粹是政治运动”,“保障租佃者权利的运动则是具有深刻的根源的社会运动”。对此,我们不妨就上述两种运动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以便发现此时的马克思在爱尔兰革命道路问题上的基本判断。取消合并派,顾名思义,主张废除1801年英国同爱尔兰的合并,即废除英国政府在镇压了1789年爱尔兰起义以后强加给爱尔兰的合并。从表面上看,取消合并派的核心诉求似乎是爱尔兰的民族独立,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1835年,取消合并派的领袖、领导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在同英国辉格党达成妥协之后,立即完全停止废除合并的诉求,只是迫于群众运动的压力才不得不在5年后重建了取消合并协会,并且继续坚持与英国统治阶级相妥协的道路。可以说,爱尔兰资产阶级自由派只不过是利用了废除合并这一当时在爱尔兰“深得人心的口号”,以争取英国资产阶级对爱尔兰资产阶级的某些让步。也正因如此,马克思才会将取消合并派的鼓动指认为纯粹的政治运动。那么,在马克思看来具有深刻社会根源的保障租佃者权利的运动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在爱尔兰,土地租佃者通常会对其耕地进行灌溉、排水、施肥等,总之,用马克思的话来讲,“租佃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把自己的资本投入土地”。随着这部分资本的投入,土地得到了改良,远在不列颠岛上的爱尔兰土地所有者就会要求租佃者缴纳更高的租金。租佃者要么选择让步,要么只能被新的租佃者取代。后者由于受惠于前一位租佃者投入的资本,自然有能力支付更高的租金。这样一来,来自英国的地主就能轻而易举地将一代又一代爱尔兰农民的劳动连同其资本一道,攫为己有。爱尔兰农民没有别的出路,他们或者因自己的勤劳,或者因自己的懒惰,沦为赤贫。于是,被逼入绝境的爱尔兰农民开始向英国政府要求,保障租佃者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租佃者的权利还不是租佃者对土地的直接权利,只是租佃者对土地进行改良、投入资本的权利。尽管如此,这一要求在马克思看来已是极其必要的,毕竟英国已经通过没收土地、扼杀工业、动用武装力量“颠覆了爱尔兰的社会生活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丑恶的‘社会条件’”,在那里,贪婪的英国地主可以对爱尔兰人民“为所欲为”,但马克思同时也指出,爱尔兰人的力量还不足以“对这些‘社会条件’进行革命”,只能诉诸议会,要求对社会条件进行调整。
至此可以说,马克思在《纽约论坛报》上的说法大致体现了其在爱尔兰革命道路问题上的两个基本观点。首先,在马克思看来,爱尔兰是不可能在爱尔兰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领导下发动革命的。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尽管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爱尔兰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革命性,但他从未否定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诉求本身,马克思所否定的是爱尔兰资产阶级自由派以民族解放诉求为谈判筹码向英国资产阶级谋求妥协的道路。其次,马克思认为,爱尔兰农民对于保障租佃者权利的要求才是一场真正的社会运动,但是,以当时爱尔兰农民的力量还无法将这一社会运动上升为社会革 命。
诚然,爱尔兰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妥协性与爱尔兰农民力量的有限性直接影响了此时的马克思对爱尔兰革命道路问题的判断,但是对于马克思而言,爱尔兰问题的关键还不限于此。1855年3月,《新奥得报》第127号刊发了马克思一篇名为《爱尔兰的复仇》的文章。马克思不仅在文中再次揭露了爱尔兰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虚伪,并且明确指认:“爱尔兰的祸根”即土地所有制关系。换言之,在马克思看来,爱尔兰要想取得革命胜利、实现民族独立,就必须打破现有的土地所有制关系。但是,受英国革命影响,爱尔兰土地所有制关系正让位于英国土地所有制关系,小租佃制度正让位于大租佃制度,旧土地所有者正让位于现代资本家,于是马克思认为,这场由英国革命导致的、正在爱尔兰社会展开的根本变革,进一步削弱了爱尔兰革命的社会基础。综合以上因素,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才会以为,撬动爱尔兰革命的杠杆不在爱尔兰,而在英国。澳大利亚历史学家伊恩·卡明斯称其为“以英国为中心的爱尔兰解放道路”(an Anglocentric approach to the liberation of Ireland)。
二、转变的第一步:爱尔兰必然会从英国独立出去
1867年11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过去我认为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为什么会在此时改变自己的观点,认为爱尔兰必定会从英国独立出去呢?或许恩格斯给马克思的回信能为我们带来一些启发。恩格斯以为,正是托利党人在曼彻斯特的拙劣行径“真正完成了英国同爱尔兰的彻底分离”。那么恩格斯为什么又会作出这一指认呢?1867年,在马克思看来既是“具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倾向”又是“下层等级的运动”的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芬尼亚运动遭遇重大挫折。3月的武装起义失败后,芬尼亚社的领袖凯利和迪集被捕。9月,芬尼亚社社员在曼彻斯特对囚车实施武装袭击,凯利和迪集成功获救,但另有5名芬尼亚社社员当场被捕。为了证明这些芬尼亚社社员有罪,托利党人在对其进行审判的过程中“采用了假证明和一些无耻的手腕”。最终,3名芬尼亚社社员于11月在曼彻斯特被处决。这一事件迅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用恩格斯的话来讲,正因为这3位殉难者,对凯利和迪集的营救才成为英雄行为,在“爱尔兰、英国和美国的每一个爱尔兰儿童的摇篮旁边”被反复歌唱。更为重要的是,正如马克思所言,芬尼亚运动在“接受了英国政府所给予的血的洗礼”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发生在曼彻斯特的政治处决“揭开了爱尔兰同英国的斗争的一个新时期”。
进入斗争新时期的爱尔兰革命,在坚持自身民族性质的同时,与国际工人协会、英国工人阶级的关系也变得密切起来。尽管这种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讲仍然是不稳定的,甚至是非公开的,但是,马克思和他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中的亲密同道显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托利党人审讯芬尼亚社社员并对他们进行判决的过程中,英国工人阶级在英国发动了一场由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马克思的倡议下组织的支援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大规模运动。其间,总委员会甚至批准了由马克思草拟的致英国内务大臣格桑·哈第的意见书——《在曼彻斯特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和国际工人协会》。该意见书明确指出,英国政府依据假的证据与错的判决处决犯人是一种“政治报复”而非“司法行为”,相反,减轻判刑才是“公正之举”,是“政治上的明智”。在执行处决的前两天,仍然有约两万工人参加了伦敦的请愿活动。马克思本人也坦言:“我已竭力设法激起英国工人举行示威来援助芬尼亚运动。”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建议英国工人“在自己的纲领中写上取消合并这一条”,他认为“这是一个英国政党在其纲领中所能采纳的使爱尔兰获得解放的唯一合法的,因而也是唯一可能的形式”。可见,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英国工人阶级对于爱尔兰革命主要具有“催化剂”(catalyst)的作用。
诚然,发生在曼彻斯特的处决的确不失为马克思作出爱尔兰必然会独立之判断的重要原因,但这显然不是能让马克思改变观点的根本原因。从他在1867年11月末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到,马克思认为,自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爱尔兰遭受大饥荒以来,英国在爱尔兰统治的经济内容与政治目的就进入了新的阶段,“清扫爱尔兰的领地”成为英国在爱尔兰统治的“唯一含义”。由此,爱尔兰彻底成了一个“没有地主”的“农业区”,对于爱尔兰人而言,英国政府只不过是“大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工具”。尽管“愚蠢的”英国政府对于这一变化一无所知,爱尔兰人却知道这一情况,并且用“极其明确和极其有力的方式表明了他们对这件事的认识”,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爱尔兰会要求“自治和脱离英国而独立”,要求“土地革命”,要求“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以抵制英国”。无独有偶,马克思在《1867年12月16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所作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提纲》中重申了上述观点,即自1846年以来,英国对爱尔兰的压迫“虽然形式上不那么野蛮了,但实质上却是毁灭性的”,这种压迫只会有两种结果,要么“英国自愿解放爱尔兰”,要么“进行一场殊死的斗争”,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具体言之,在马克思看来,“谷物法”的废除、英国在爱尔兰所进行的农业方面的改造、英国“济贫法”在爱尔兰的推广以及“积债地产法令”的颁布等给爱尔兰社会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为此,爱尔兰将不可避免地从英国独立出去。在基于上述《提纲》所作的报告中,马克思的态度更加强硬,言辞也更加尖锐。他说:“爱尔兰问题不单纯是个民族问题,而是一个土地问题,生存问题。不革命,即灭亡,这就是当前的口号。所有爱尔兰人都深信,如果应该有所行动的话,那就得立即动手。英国人应该要求爱尔兰分离,让爱尔兰人自己去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别的一切措施都是无济于事的。”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马克思在1867年末修正了自己以往的判断,转而认为爱尔兰必然会从英国独立出去,但是,他关于英国人能够给爱尔兰人“合法的手段”实行土地革命、“英国自愿给爱尔兰以自由”“英国人应该要求爱尔兰分离”等说法同时也表明,对于此时的马克思而言,爱尔兰必然会独立,但这一独立完全有可能因为英国人的自愿放手而实现,并不必须要诉诸社会革 命。
三、马克思观点的完全转变:革命的杠杆一定要在爱尔兰
1868年之后,马克思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观点——爱尔兰必定会以土地革命为起点,经由全面的社会革命实现独立,并且爱尔兰的社会革命将会成为撬动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杠杆。马克思在1868年4月致库格曼的信中写道:社会革命必须从土地所有制开始,“首先是爱尔兰的地主所有制,然后是英国的地主所有制”,最终,这场革命的受益者将会是英国无产阶级。依照马克思的判断,英国无产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就是“推翻英国的土地寡头”,而要想推翻英国的土地寡头,就必须摧毁他们在爱尔兰的前哨,“因为当英国的土地寡头政权在爱尔兰还保持着自己的非常巩固的前哨时,它在英国本土的阵地就不可能摧毁”,而要想摧毁英国土地寡头在爱尔兰的前哨,就要让“事情掌握在爱尔兰人民自己的手中”,即让爱尔兰人成为自己国家的立法者和执政者。一旦爱尔兰人获得自治权,在爱尔兰推翻大地主所有制就要比在英国推翻大地主所有制“容易得多”,毕竟土地所有制问题在爱尔兰“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民族问题”,如果说土地寡头于英国人而言是“传统的显贵和代表人物”,那么土地寡头于爱尔兰人而言则是“令人深恶痛绝的民族的压迫者”。换言之,马克思一方面看到了爱尔兰的大土地所有制是英国土地寡头最坚实的“堡垒”,一旦这一堡垒被爱尔兰人攻破,英国的土地寡头也就必然会在英国被推翻,而这恰恰“为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前提”;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土地问题是关乎每一个爱尔兰人及爱尔兰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何况爱尔兰人比英国人更热情,更富于革命性”。基于以上两个判断,马克思得出结论:攻破英国土地寡头的堡垒、消灭英国土地寡头、为英国无产阶级革命创造前提条件,这件事情在爱尔兰要比在英国本土容易得多,因此,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杠杆一定要放在爱尔 兰。
然而,这条将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与英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却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内部以及英国无产阶级内部遭到了质疑。后者无法理解,马克思为什么会一再主张,英国无产阶级要在对爱尔兰的政策方面同英国统治阶级一刀两断,要和爱尔兰人行动一致,甚至要以自由联盟的关系取代起自1801年的合并。为此,马克思不得不反复强调:“这并不是出于对爱尔兰人的同情,而是基于英国无产阶级利益的要求。”他不得不要对爱尔兰革命与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在关联作出更为详尽的阐释。马克思提出:比较容易察觉的是,英国资产阶级和英国土地寡头对爱尔兰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他们“都想把爱尔兰变成一个纯粹的牧场”,都想让英国资本安全地在爱尔兰发挥作用,但是还需要看到,英国资产阶级在爱尔兰“还有更重要得多的利益”——由于租地日益集中,爱尔兰只能不断向英国市场输出自己的过剩人口,这必然会降低英国本土工人阶级的工资。如此一来,英国工人不免会把爱尔兰工人看作致使自己生活水平降低的竞争者,甚至产生“憎恨”。于是,在英国的工人阶级实际上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即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前者对后者“怀着宗教、社会和民族的偏见”(大致就像美国各蓄奴州的白人贫民对待黑人的态度)。可以说,英国无产者“变成了本民族的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而爱尔兰工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加倍地报复英国工人”,“把英国工人看作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的同谋者和愚笨的工具”。对此,英国统治阶级所要做的就是不断加深这种对立,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对立不仅是英国无产阶级“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而且是英国资产阶级“能够保持它的势力的秘密所在”。也正因如此,马克思反复强调:只要爱尔兰的大土地所有制还没有被推翻,英国工人阶级就无法摆脱英国资产阶级的统治,伦敦中央委员会的特殊任务就是要让英国工人阶级意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在爱尔兰革命道路问题上的转变并没有停留于此。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说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杠杆在爱尔兰,那么全世界工人运动的杠杆也就在爱尔兰。在马克思看来,英国作为“资本的大本营”、作为世界市场的统治者,“对工人革命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这一方面是因为英国有着比任何地方都更加成熟的消灭大地主所有制与资本主义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只有在英国,阶级斗争以及工人阶级在工联中的组织才具有一定的成熟度与普遍性。一旦英国,这座“资本的首都”“大地主所有制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堡垒”被爱尔兰革命攻破,就必然会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于是,马克思明确提出:国际工人协会“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而加速这一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爱尔兰独立”。可以说,马克思直到这里才彻底完成了在爱尔兰革命道路问题上的转变。此时的马克思不仅认为爱尔兰一定会通过自身的社会革命从英国独立出去,并且认为爱尔兰的社会革命最终会成为撬动英国无产阶级革命乃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杠 杆。
四、马克思在爱尔兰问题上的转变与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研究
需要充分意识到的是,马克思在爱尔兰革命道路问题上的转变决不是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变化。要知道,马克思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杠杆放在爱尔兰,也就意味着马克思并没有把撬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杠杆放在工业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这样一来,马克思在爱尔兰问题上的转变就把我们引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研 究。
对于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惯有以英国学者特奥多尔·汕宁为代表的批评家将其解读为“单线决定论”(unilinear determinism),即人类历史发展道路受制于自然规律式的进程——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完成,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绕道而行。然而,马克思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杠杆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真正发展和完成的爱尔兰,这件事情完全推翻了对马克思历史道路理论所作的一切单线决定论的解读。于是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在爱尔兰革命道路问题上的转变表明,马克思正逐渐转向某种“民族自决的超历史原则”(supra-historical principle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面对这一观点,首先应该立即予以回应的是,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完全没有转向“超历史”的可能。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指出,所谓历史规律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而“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因此,决没有“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然而讽刺的是,直到马克思晚年,仍然有米海洛夫斯基之类的批评家将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指认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在这些批评家看来,马克思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是在为一切民族的发展指出一条必定要依循的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对此,马克思只能无奈地回应道:“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是一把“万能钥匙”,看似放之四海而皆准,却无法帮助我们理解任何现实的历史,因为它“最大的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可见,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非但不可能转变为超历史的,而且一贯就站在它的对立 面。
其次需要说明的是,民族之于马克思历史道路研究的意义。在马克思看来,一切历史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都要时刻把握住,“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并且这个能动的主体,即社会一定是“既定的”(其既定性大致表现为,社会不仅是处于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社会,而且是具有特定实体性内容的社会)。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研究也不例外。也就是说,当马克思在讨论爱尔兰革命道路问题的时候,就其方法论而言,是以既定的爱尔兰社会(在马克思看来,就其“社会”方面而言,它更像是西方的印度斯坦的社会)为研究前提的。这个既定的爱尔兰社会既是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普照的光”支配的社会,又是有其特定艺术、宗教、语言、风俗、历史、民族文化等实体性内容的社会。可以说,各民族的特点及其传统本是马克思历史道路研究的前提,因而根本不可能成为其所谓超越历史的基 础。
既然马克思在爱尔兰革命道路问题上的转变是以其对爱尔兰社会所作的研究为前提的,那么马克思在改变观点的关键时期究竟有何研究成果呢?1868年3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了自己在爱尔兰社会研究方面的新发现。在钻研了毛勒的多部著作后,马克思提出,尽管毛勒的这些书“具有真正德意志的博学”,但他对克尔特人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完全看不到克尔特人对于法国公社所有制的影响。不同于毛勒“硬把法兰西的公社所有制的发展完全归于日耳曼人的征服”,马克思强调,克尔特人早在11世纪就已经有了“完全共产主义”的法令汇编,并且在某些地方已经发掘出了“克尔特形式的原始公社遗迹”,换言之,在爱尔兰民族的原始时代中,马克思发现了某种和“社会主义趋向相适应”的东西。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在爱尔兰革命道路问题上的转变,非但不是对其历史道路理论的否定,而且确乎是作为一个绝佳的例证,论证了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研究不是脱离既定社会的抽象议 论。
五、余论
对于马克思在爱尔兰革命道路问题上的转变,我们还应看到的是,当马克思基于对爱尔兰社会的研究最终提出,爱尔兰革命将在实现爱尔兰民族独立的同时成为撬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杠杆的时候,他所指出的这条爱尔兰道路呈现出了一个鲜明的特征——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独立斗争的同一。就这一点而言,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可谓遇到了和19世纪的爱尔兰社会极为相似的历史处境。对此,中国社会又是如何回应的呢?十月革命为中国社会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用毛泽东的话来讲,中国人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但是这样一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在中国尚未爆发过欧洲那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如何能够完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同时实现民族独立?诚然,马克思在1870年前后明确将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杠杆放在爱尔兰——这个和中国一样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社会,这个和中国一样同时面临着阶级斗争与民族独立斗争双重历史任务的社会——的做法的确在理论上为中国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支撑,但是,由于爱尔兰革命最终没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上取得胜利,因此,这条阶级斗争与民族独立斗争同一的道路在中国是否可行就成了一个有待中国革命实践去回答的问 题。
在中国革命实践展开的过程中,毛泽东认为,依照中国社会的实际条件来看,“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这革命的“第一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它既非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也非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而是适用于处于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具有过渡性但同时也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民主主义。这种新民主主义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民族的特点相结合”。那么,中国的这场“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究竟具有怎样的特点呢?毛泽东以为,对于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而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即“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必须依据各自的具体条件执行这一原则。在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各国,内部没有封建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在那里,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经过长期的、合法的、不流血的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即便到了有必要发动战争的时候,也要首先攻占城市,然后进攻农村。中国则不同,于内没有民主制度,于外没有民族独立。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然要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与此同时,广大的农村地区以及占全国百分之九十的工农人口也意味着,这场主要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对象的革命,必然要以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群众为基本动力。最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同时实现了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于现实的历史实践之中印证了马克思在爱尔兰革命道路问题上所作的历史性判断——无产阶级革命完全有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得到充分发展、民族尚未实现独立的社会中取得胜利。可以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于马克思历史道路理论确有其显著的 贡 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