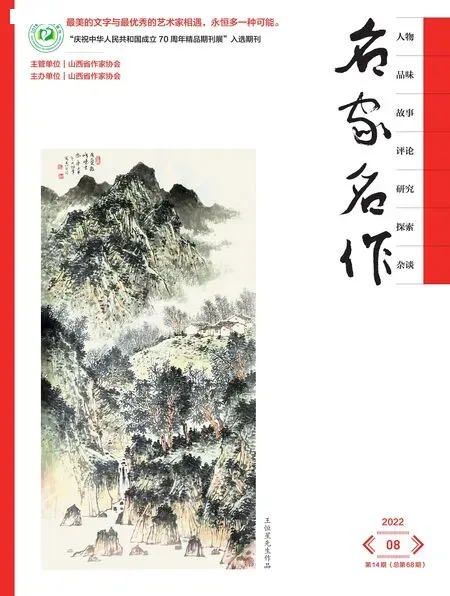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在人工智能和艺术之间
王元泰
一、面对人工智能之“矛”
“艺术越来越科学化,科学越来越艺术化,两者在山麓分手,有朝一日,将在山顶重逢。”现如今科学和艺术的高度结合,验证了福楼拜预言的正确性。人工智能的诞生,也为人们谈论“科学和艺术”提供了新的语境。如果将人工智能艺术作品与人类艺术间的较量比作一场“攻防战”,那么率先发起攻势的是“人工智能之矛”。
近年来,人工智能克服了技术与应用间的巨大障碍,在信息识别、图像处理、云计算等方面均大有建树。在此基础上,人工智能开始涉足“艺术”领域。2017年的冬季达沃斯论坛,一个名为3RNP绘图机器人通过捕捉实物、图像识别、输出成像一连串的动作,实现了人工智能的“自主”绘画,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叩开了艺术之门。2018年10月25日,纽约佳士得拍场上,人工智能作品《爱德蒙·贝拉米肖像》以43.25万美元的价格拍出,这一市场行为震惊世界,随之而来的多是批评言论,认为技术开发团队Obvious小组的作品不具艺术性。国内相关的标志性事件是微软“小冰”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成功举办个展,并顺利毕业。“小冰”的展览名为《或然世界 Alternative Worlds》,其化身为6个不同时代的女艺术家,展示了百余幅完全独异的作品。此次人工智能艺术作品的公开亮相,不仅得到了官方认可,也提高了其在公众心中的知名度。“小冰”在学术界掀起了一股讨论热潮。
伴随讨论的深入,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实验室也开始建立,2021年5月20日“aai艺术与人工智能国际论坛2021”在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暗房报告厅举行,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艺术与人工智能实验室随之建立,代表国内对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研究迈向专业化,这也是人类对人工智能艺术所作的积极回应。
对人工智能作品和人类艺术之间关系的探讨,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在不反思艺术概念的情况下,把“人工智能作品是艺术”当作预先肯定的结论。这种判断在未经定义时谈论艺术现象,很容易导致艺术概念的无意识滑移。第二类讨论是对上述观点的纠正,力图先确定艺术的概念,再讨论人工智能创作。曾经,艺术被视为人类区别于人工智能的“净土”。但随着微软“小冰”、3RNP等智能技术带来的冲击,人们不得不思考本体论意义上的艺术问题。因此,第二类讨论热衷于追问人工智能作品是否属于艺术,人类艺术和人工智能艺术的边界在哪。然而,现阶段最需要的同时也是最欠缺的其实是第三类讨论。当问出“人工智能可以创造出艺术作品吗?”这类问题的时候,无疑要首先界定艺术概念本身。这需要预先勾画出一个边界分明、充满棱角的艺术本体,再依照本体模型对人工智能作品的种种属性加以分析。然而,此举有悖于艺术概念的发展。自希腊文Τέχνη和拉丁文ars诞生以来,作为概念的“艺术”便始终变动不居。尤其在当代语境下,想界定“艺术”更是难上加难,以至于许多理论家干脆放弃这项劳神费力的工作。肯尼克宣称:“并不存在一种所有艺术品所共同具有的属性。”卡勒用以界定“文学”概念的话同样适用于艺术领域,他认为“文学就像杂草一样”,因人而异。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对何为艺术的探讨,毕竟艺术概念在历时层面如何变动,在共时层面依然能体现出相对的稳定性。重要的是,研究艺术概念时需要注意共时性原则,研究艺术与人工智能时也需要让二者共享同一时空。因此,除了用既往的艺术概念检视人工智能,还应该注意到人工智能作品对现有艺术观念的反作用,这是讨论该问题的前提。
人类在讨论人工智能与艺术时,难以避免人本主义的立场。于是“人工智能艺术和人类艺术的边界”被代换成“人类艺术创作所不能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本性”。人本主义立场使用不当,就会不自觉地建立一道人工智能永远不能翻越的概念围墙,以确保艺术是只属于人类的净土。这正是本文题目的由来:人们看似在客观研究艺术概念,实际上却在打造一面人工智能无法攻破的盾牌。这场艺术与人工智能间的较量逐渐演变成:究竟是人工智能技术之矛更加锋利,还是人文学者打造的具有排他性的艺术概念之盾更加坚固?
二、解构人类艺术之“盾”
目前,艺术与人工智能战场上交火最集中的区域是创造性。不少学者将创造性视为人工智能无法达到的艺术本性,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艺术概念史已将创造性抬至空前高度,二是人们对人工智能创作方式所作的分析。
将创造和艺术紧密联系在一起,始于近代。最早的希腊文化中没有与创造意义对应的词汇,类似的只有形容一切技术手段的制造,反映出希腊时期人们对绘画、雕刻等艺术形式模仿自然的坚定认识,以柏拉图的“模仿说”为典型代表。而人们对诗歌的看法恰恰相反。由于诗歌是受到女神缪斯灵感启发的产物,它既不受法律规则的限制,得以表现出自由属性,又不是对现实简单的模仿,得以表现出创造属性。因此,诗歌和现今绘画、雕塑、音乐等艺术门类是分庭而立的。而诗歌的创造属性在中世纪受到了冲击。此时的创造专指无中生有的能力,卡西奥德说:“被制作出来的事物和被创作出来的事物不同,因为我们能制作却不能创作。”因此,想将创造与艺术合二为一,需要完成两项工作,一是让创造重回诗歌,二是重整艺术概念,使之纳入诗歌,并将纯技艺的门类排除在外。第一项工作由波兰诗人沙比斯基在17世纪首度完成,他在评价诗人写作时明确使用了创造这一概念,并且为了平滑过渡,用中世纪的语言形容诗人的创作。第二项工作更加复杂,它不仅要求理论家在众多艺术门类中寻找个别门类间的共性使之独立成一个共同体,还要求这个共同体在日后体现出创造性的可能。根据塔塔尔凯维奇的研究,弗朗索瓦·布隆德尔在176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将建筑、诗歌、雄辩、喜剧、绘画、雕刻、音乐、舞蹈以和谐为共性准则放到了一起,不过没有将它们命名为艺术。第二个贡献者是查尔斯·巴多,他在前者的基础上,剔除了雄辩,变喜剧为戏剧,并以“美术”命名这些与技术和科学独立的艺术集团。而后又过了半个世纪,技术与科学终于不再被称为“艺术”,曾经建立的“美术”概念与古老的“艺术”概念终成一体。同时期内,无中生有的创造性定义被瓦解,伴随着诗歌被纳入艺术体系内,创造也从诗歌内部延伸到艺术领域中,最终创作者和艺术家变成了同义词。至此,创造性成为艺术的重要属性,这是人们用它来评判人工智能作品的根据。
人工智能的创造得益于深度学习在语言、图像等方面的成功应用。深度学习本质上是对人类大脑分层模式的模仿,通过前期建立的计算机代码,人工智能对输入的海量信息进行分层处理,按照从底层到高层的逻辑顺序总结提炼目标数据,再利用得到的数据模型进行艺术创作。对比人类在艺术领域苦心建立的创造性标准,人们发现了人工智能“伪创作”的种种理由。总结来看,非议主要有如下几种:第一,人工智能作为创作主体不具有主观能动性,只是被动地接受指令,按目标形式产出作品;第二,人工智能的创作不具有新颖性,因为所有作品都只是数据的演算,而数据来源则是人类曾创作过的“旧艺术”,因此人工智能作品只是“旧艺术”在形式上的重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创造;第三,人类的主体意识是艺术创作的重要源泉,人工智能只是机械地执行程序命令,不存在主体性,更无情感、生命、伦理可言。这些论据看似板上钉钉,似乎已经给“人工智能跻身艺术创造”宣判了死刑。可事实上,正如艺术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概念,创造在当下同样是一个游移不定的词汇。如果人们认定创造必须包含主观能动性、新颖性、富含意识和情感这些要素,人工智能的确被排除在外,那代价是居于这种创造内涵之外的、曾被肯定的人类艺术作品也将被彻底除名。
盾牌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主体意识。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艺术源于人类对外在世界的主体性认识。本文无意于讨论未来人工智能是否会具备自主意识。毕竟在主体性膨胀的当下,艺术领域中早已掀起一股去主体意识的力量。施坦伯格面对贾斯帕·约翰斯的代表作《带面孔的靶子》这样评价道:“在《带面孔的靶子》(Target with Faces)里,我注意到一种可怕的价值倒置。在无思维的非人性或冷漠中,有机的东西与无机的东西被等量齐观。”
自启蒙时代以来,主体性概念日益膨胀,而约翰斯的作品则将这一价值倒置,呈现出一种等量齐观,用中国古代哲学术语讲便是“齐物”,即去主体性。如果认为人工智能缺少主体意识而否认其创造性与艺术性,那么也会有一部分既已认定的现代艺术需要为此牺牲。从另一个角度讲,人工智能的艺术品和人类的艺术品同框展出时,观赏者不需要也无法看出作品背后的主体性意识。观赏者会在接受作品的过程中,自然地为其赋予主体性——来自观赏者的主体意识。一件艺术品的意义在这种情境下变成它激发了观赏者什么,而非它本身想表达什么。也就是说,即便从理论上人工智能艺术缺少意识、情感等,但当它作为艺术呈现时,观赏者会从自身主体出发,为艺术品添上“人性”的内涵。而就艺术欣赏而言,人们都是从作品显现出的结果推究创作者的意图和情感,创作者本身的意识无从知晓,因此也不会影响欣赏环节。所以,强调人工智能艺术不存在主体性的做法似乎在理论上行得通,但丝毫影响不了人类对人工智能作品的欣赏,人们依然会将“属人性”赋予“非人的”作品。主体性意识的区分无异于在人类与人工智能间划了一道透明的边界,在理论上取得了成功,却在现实里显得无力。
三、从“矛盾相向”到“矛盾共存”
回顾人类学者为建构人工智能艺术边界做出的各种努力,其结果难以形成共识。某种程度上,每一种结论,无论关于创造性还是主体意识,都有一种画地为牢的倾向。艺术发展至今其概念难以定义,这既是艺术泛化的结果,又是艺术不断超越自身、表达各种可能性的成果。而人类为了区分人工智能所设下的种种艺术边界,不仅不能为艺术的多元发展起到正面作用,反倒可能将艺术彻底送上象牙塔尖,成为一种仅存于精神的崇高信仰。
面对人工智能锋利的长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显然不是明智之举。诚然,在人工智能与艺术之间决心划清人与智能的界限是在所难免的,这或许也是人工智能时代人之为人的根本立场,是不可放弃的。但在理论研究层面,如果固守阵地,不断为围墙添砖加瓦,或许真的抵挡了人工智能对人类艺术的侵袭,却也牺牲了人类艺术更广泛的发展可能,最终只能是自掘艺术坟墓,从另一个角度败在了智能手下。
于是,问题最终又回到“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与智能如何共处”上面。这个经典问题涉及诸多方面,而就人工智能与艺术来看,对人类主体性的突出,也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对人类主体性的限制。不远的将来,类似问题会频频出现,尤其当真正意义上的强人工智能降临时,伦理问题、精神问题等每一块属于人类的领地都将成为“矛盾之争”的战场。对人类而言,是牺牲一部分空间以换得稳定的领地,还是任由可能性发展而直面被剥夺“净土”的风险,需要审慎地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