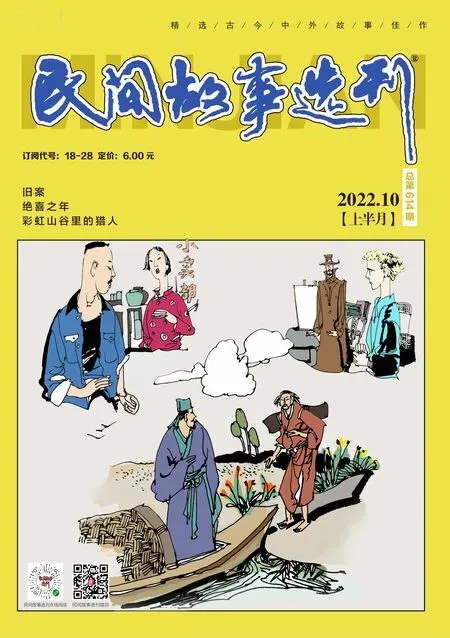村口的窑帽子
◇文/ 沈碧荷
孙岙村是个远离城镇的小山村,有山有水有农田,弯弯的运河从村中来回贯穿而过,村里的年轻人热衷于上城里打工,老年村民居多,随手丢弃垃圾更是见怪不怪。
就在这几年,一到节假日,城里的年轻人纷纷走进孙岙村,古村好似被揭开层层面纱,村民面水而居的屋面各自改成了店面房,各具风味的特色小吃,本地土特产纷纷上架,也吸引了外镇的商家来此开店投资,加上马头墙下的烟火味,虽然离城镇远,旅游业带动了商业的发达,也有年轻人重回村子。
孙岙村的石牌楼、石坊间保护得较好,又经政府的初步开发,山村虽然申请重点保护村落还未批下来,但已然成了远近闻名的古村,一到假日,古村很聚人气。
年轻的大学生村主任钱峻上任不久,年轻人有活力,在领导面前表了态,一定要把孙岙村打造成红红火火的旅游古村。他召集村民召开动员大会,宣传党的方针和富农政策,几次下来,村民已达成了共识:拆除违规建筑、旧房修复、废除陋习、树立文明新风……经过一个月挨家挨户的动员,古村有了新的面貌。这不,为了更好地查漏补缺,村主任钱峻每天晨跑都要经过村里的大小街道,以便能够发现问题及时落实解决。
跑到村口的钱峻看见孙明叔趴在窑上,这窑已说不上年代有多久远,好像早就淡出人们的记忆,很少有人提起它。眼前孙明叔外衣被树杈挂住了,上又上不来,下又下不去,一个刨地的姿势让老人累得够呛。钱峻跑上去连抱带拉把孙明叔放到草地上,老人一阵阵咳嗽缩成一团。
几块分化的砖头堆叠,分辨不清窑的外形,年老的村民还会提起窑帽子,大多是指代所属的方向。早先村民图个方便,废弃物随处乱扔,窑帽子上垃圾堆得山高,路过村口一阵阵恶臭,钱峻和青年志愿者拉走了十几车垃圾,现在留下个“帽子”的形状,汽车进村在这处要拐个硬弯。现在好了,窑帽子已被列入拆除之列,进村的小车也将通达不少。
等孙明叔缓过气来,钱峻向老人道:“孙明叔,你好早啊,不要到窑帽子上去,掉下来可怎么办,过几天施工队来拆窑帽子。”钱峻来不及关顾老人的表情,向前跑去,只听见老人自言自语地念着什么。钱峻又追上去一句:“孙明叔,这事就这么定了,不要再上窑帽子了。”想着窑帽子拆除后,村口土地的宽阔,再立块孙岙村的牌匾,大气又漂亮,钱峻心里很是舒心,脚步也欢快了很多。
几天后的早晨,晨跑的钱峻在村口看见孙明叔和儿子孙皓,搬着砖头往窑帽子上垒,钱峻不觉皱起了眉头,孙皓向钱峻打招呼:“主任早!”“不是说好了吗,窑帽子要拆除,还垒它干什么?”钱峻心想,拆除窑帽子的事情已顺利解决了,就等施工队到来,不想父子二人还搞不明白的样子,钱峻心里不免有些懊恼。
这天一上班,钱峻把孙明叔和儿子孙皓请到了办公室,等父子俩落座,钱峻就开门见山地说:“孙明叔,不是跟你说了,为了建设新孙岙村,挡在村口的窑帽子一定要拆除,为什么还要再去加固?”
孙明叔脸上露出难言之色:“主任不怕你笑话,我是舍不得窑帽子。”钱峻一听却笑开了:“孙明叔,我先问你,我们现在这个村你满意吗?”“满意,满意,真的满意!”老人连想都没想点着头说。“你看看村口的窑帽子,不仅占位子,还破破烂烂的,就像一件破衣服,挂在新房子里,太碍眼……”钱峻正说在兴头上,不承想孙明叔站起来大声说:“再破再烂,就是不能拆!拆了就是数典忘祖!”他抖动着下巴呼哧呼哧地喘上了,脸色憋成了绛紫色。
钱峻气得真想拍桌子,担任村主任以来还没有碰见过这么犟的老头,可一想毕竟孙明叔在村里德高望重,闹僵了不好。看孙明叔这么坚决,也许有什么隐情,钱峻拉过孙皓问:“本来说得好好的,怎么一时变卦了,到底是为了什么?”孙皓苦笑着说:“阿爸这几天煮碎米粥一样自念自听,好像和我们总长太公有关系。”看来真的是有缘由,钱峻给孙明叔添了茶水,要他慢慢道来。
原来,曾经的孙岙村居住的都是姓孙的人家,辈分最大的被推为总长太公,村里大小事情都是总长太公说了算。有一年先遣倭寇顺着运河摸进来,也许是孙岙这地方人勤物丰,也许倭寇想捞一些好处再走,倭寇到了孙岙强抢民女,被孙岙村总长太公引领的村团军逮个正着,一举绞杀倭寇。
谁知更猛烈的战事正在酝酿,第二天、第三天聚集了更多、更凶残的倭寇,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一个孙家姑娘躲在村口窑里半个月不敢出来。
孙家姑娘在窑里没有食物,昏沉中依靠野藤的水汽才存活下来。一年又一年,在孙岙村土地上,孙家子孙得以生息繁衍。孙明叔说到这里,已是泣不成声,一旁的孙皓也陪父亲落泪。孙明叔说:“主任,虽然窑帽子没有什么用,可我还是觉得舍不得,就是舍不得,我老头子也不是有意和你唱对台戏。”
听完孙明叔的讲述,钱峻沉默良久,然后走向窗口,望向窑帽子的方向,虽然被一群建筑物阻挡着,但他还是久久地站着没有说话。
“孙明叔,要是我猜得不错的话,你第一次被我看见上窑帽子,是去看那根树藤。”钱峻面向孙明叔说。
“是的,我父亲在世时说过,窑帽子旁都是古树,烧窑的柴火都是从运河运来的,早先孙家人在村旁砍树是要被人唾弃的。”孙明叔说话音调高了起来。
“孙明叔,你见过窑吗?你还记得窑本来的样子吗?”钱峻来了兴致。“我小时候看见的窑也是破落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外面黄泥糊糊,还烧过砖来着,不过窑的样子家谱里有的,画得清清楚楚。”孙明叔听出了苗头,心里不免有些高兴。
“孙明叔,这样好吗?村里开个会商量一下,让窑帽子恢复原来的样子,让古迹焕发生机也是我们的责任呀。说不定孙岙村因为窑帽子而名声远播呢。”
不久,在孙岙村口,一座窑帽子很是显眼,旁边竖着一块“孙岙村”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