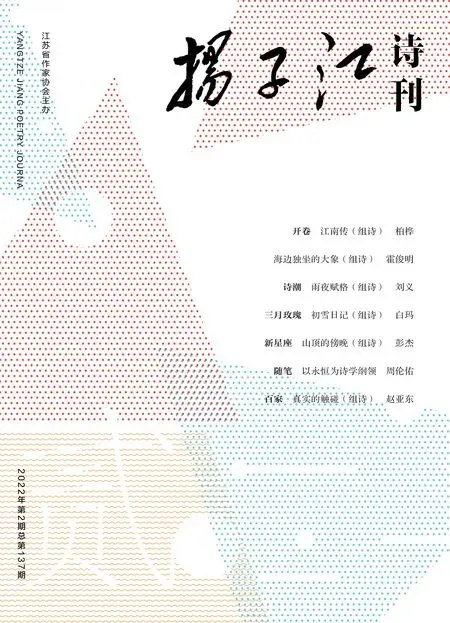中年人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读霍俊明组诗《海边独坐的大象》
王单单
通常诗评家评论别人的诗歌,需要调动自身从阅读、写作实践以及思考中获得的美学经验,对他人之诗做出感性或客观的阐释,凸显出来的是一种“向外”的透视能力。而诗评家写诗,展现的却是一种内视视角,在这一过程中,或许他毕生所学的诗歌理论会陡然失效,让他从语言进入诗性内部的并非诗歌理论的指引,而是因评论的需要对诗歌所产生的阅读感受。这种阅读感受会在无数次的持续与加深中,确立一种自我认同的诗歌标准,这个极度个人化的“诗歌标准”,或许就是促使其推开诗歌大门的力量。评论家与诗人之间,隔着经验与情感的汪洋大海,区别是评论家站在岸上沉思,诗人却在海里遨游。但是自新诗产生以来,有些站在“岸上”的评论家,却裸呈自己,跳进诗的大海中,自己成为自己的摆渡人。
读霍俊明的诗歌已经将近十年了,从最初的诗集《怀雪》《一个人的和声》到《有些事物替我们说话》,以及不时在网站、公众号等自媒体上消遣性的零散阅读,我始终对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勤奋、灵气与智慧赞叹不已。
最近读霍俊明的诗歌,是这组《海边独坐的大象》,这个组诗的名字,让我想起已故青年导演胡波生前的最后一部电影《大象席地而坐》——冗长、沉闷、压抑,现场感极强。我很难揣测霍俊明为这组诗取名为《海边独坐的大象》的真正用意,也无意从中获得解读其诗的有效密码。但是关于大象,有资料显示,“在非洲肯尼亚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非洲大象能辨认其他100多头大象发出的叫声,哪怕是在分开几年之后。来自英国南部萨塞克斯大学的科研人员在位于肯尼亚的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录了一些母象用来联系的低频的叫声。这些声音是大象用来确认个体的,也是用它组成一个复杂的社群网络的一部分”。由于大象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回忆”这种时间回溯的思想活动也会与人类有着超乎寻常的相同之处。因此,“大象”与“独坐”这样带有明显情绪化的词语联用时,其精神意旨就会有“移情”倾向,这个标题传递给我的画面是一种深邃的回忆与无尽的怅惘、大象的沉默与海浪的喧嚣、孤独的肉身与水天一色的空阔,而这些所烘托出来的心灵寓言,构成了诗歌内容“不可告人”的部分。此时,我又一次想起由格利高里·考伯特执导的纪录片《尘与雪》,片中大象的缓慢、温和、忧伤,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随着纪录片中美国著名演员劳伦斯·菲什伯恩的吟诵,“羽变火,火变血,血变骨,骨变髓,髓变尘,尘变雪”,诗便从此展开了。霍俊明的这组诗,再一次印证了此类观点,“诗歌是记忆的影子”(何塞·埃米利奥·帕切科),“什么是诗?‘哦,它是一些记忆’”(罗伯特·勃莱),“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 (约瑟夫·布罗茨基)……
这组诗中,《甘蔗田禁区》带有明显的故土情愫与少年记忆。它可能仅是一个很不起眼的景象,位于镇村结合部,却因为它的“刺目”“经过那里的短短几分钟 / 空气瞬时变得甜稠 / 更多的 / 还有袭来的莫名恐惧”而成为诗人一生中难以忘却的记忆。“我经过时它们正在生长期 / 如同我也还在饥饿中”,从“饥饿”一词,我们似乎能看到那个时代贫瘠颓然的历史镜像,而当我们读到《甘蔗田禁区》的最后一节,“我只记得 / 它们黑森森的一片在风中摇晃 / 躯干上有白色的斑斑印渍 / 偶尔夹杂着不知名的鸟叫声 / 它们应该尝过或衔着 / 村里和小镇人所不知的那种甜”才恍然大悟,诗人的真正意图并非是“往记忆里滴进糖汁”,而是通过它所氤氲或烘托而出的生活之“苦”和甘蔗的“甜”之间形成强烈反差,诗的力量因此就在这类“反差”中获得自然的升华。相比之下,《水梯》是一首诗意的生发稍显平淡的诗,但这里的“平淡”隐藏着诗歌生成的方法论,甚至是一种写作上的“策略”,表面上看,诗人只是写了一个废弃的铝合金梯子,在被“曾经攀爬的人 /修剪行道树的人 /检修风车和路灯的人 /凿掉路边山体即将迸裂的石头的人”用完之后,遗弃在湖水中并“已渐渐招惹了水草的绿衣”的普通场景。但诗人天生的共情能力可在万物身上寻找到替身,从“废弃物也在寻找它的安身或葬身之所”这个句子中可以得知,本诗的意旨似乎已经触及到关于生死的终极命题,但诗人如果依托这个点继续深刨,那即便诗意的纵深因此而获得,也难免使这首诗在写作的铺陈和推进上落入俗套。霍俊明当然是深谙此道的高手,至此笔锋一转,轻描淡写,“尘世的脸在金属的反光中 /跟随着湖水 /一起微微抖动”似乎写得很轻,事实上并非如此,“一首诗的主要特征是最后一行”(布罗茨基语)恰恰是因为这种举重若轻的写法,它才让全诗变得神秘、隽永、意味深长。《恍如己身》和《甘蔗田禁区》《微型地窖》等有相同之处,那就是对于乡村生活和少年经验的召唤,用诗歌擦拭某种情愫在时间的流逝中所蒙上的灰尘,“渐渐煨熟的香气弥散 /我再次回到自己的身旁 /恍如己身 / 灰烬温热而我仍是少年……”为了接纳出走的我们于时间中再一次返回,诗在此过程中成为心灵的建筑——它从记忆的深处拔地而起。
这里我想特意说说《微型地窖》这首诗,细读之后,很容易想起谢默斯·希尼的名诗《挖掘》。两首诗歌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写到了“父亲”,都写到了劳作甚至细化到“挖掘”这一具体行为,比如《微型地窖》中写到“父亲在后院 /趁着土层还不太板硬 /他用右脚踩着铁锹 /一点点插入 /铲起的土又一次活了过来”,谢默斯·希尼在《挖掘》中写到“他在挖土。 /粗劣的靴子踩在铁铲上,长柄 /贴着膝头的内侧有力地撬动”(袁可嘉译)。两首诗中,两位不同时空里的父亲,都在做着相同的行为,需要踩着铁锹或铁铲才能将其插入泥土。两首诗里都出现了动词“踩”,这是一个极度传神而又准确的词,通过它能形象地描绘出两位年迈的父亲劳作的样子,甚至还能传达出某种执着不屈的精神。希尼《挖掘》里的父亲虽然上了年纪,但仍然强壮、利索、喜欢喝酒,尚有几分美国西部片中老牛仔的样子。霍俊明《微型地窖》中的父亲朴实、勤劳,“个子本来就不高 /此刻越发矮小了”符合中国农业文明背景下“父亲”的普遍形象。虽然两首诗歌都是从“父亲”的“挖掘”开始,行文或者诗意指归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希尼通过父亲“挖掘”这一行为,进而联想到了自己的写作,“但我可没有铁铲像他们那样去干。 /在我手指和大拇指中间 /那支粗壮的笔躺着。/我要用它去挖掘”。从形而下到形而上,希尼把写作看作是一个挖掘的过程,唯有在语言中保持足够充沛的精力,执着与专注地“一直向下,向下挖掘”方可达到“看清自己,使黑暗发出回声”(谢默斯·希尼《个人的诗泉——给迈克尔·朗利》,黄灿然译)的写作意图。霍俊明的《微型地窖》所要表达的,更多是偏向于对时间的重构和对生命的思考。“父亲挖出了一个宽深一米的微型地窖 /他小心翼翼将青萝卜摆放到里面 /像是完成乡下的古老仪式 /上面盖上一块木板/再铺上几层稻草”,或许这仅只是对一个简单的生活场景的描述,但它的铺陈是在诗歌的场域中展开的,而诗歌语言天生的多义性、模糊性、暗示性、隐喻性等功能会将这个场景从单一的呈现裂变出多种解读可能,这是“诗”对现实场景的选择,也是“现实场景”入诗之后获得放大与升华的原因。当此诗结尾处“不久的将来 /它们将重回黑暗中去”这一句出现时,再一次将诗意的指向引领到更为开阔的地方,给予读者遐想的同时,也让诗歌的意境抵达了更为深邃和悠远的领域。
事实上,最初阅读这组诗歌,我已留意到,亲情主题在霍俊明的诗歌中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这组诗里《微型地窖》《小镇上的父亲》《站在砖墙上的父亲》《红花结莲蓬,白花结藕》皆属此类写作。在霍俊明早期的写作中,“父亲”“母亲”“堂哥”等意象的密集出现并不多见。我不知道这是否喻示着霍俊明心灵上的某种归属与“还乡”,或者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生命在漫长的人生征途上面对无望的虚空时,会被“回忆”重新灌装,写作也因此成为怀旧的方式。读到《站在砖墙上的父亲》时,我被诗中清晰动人的“父亲”形象一下拉回河北唐山丰润县大刘庄村,这是诗人霍俊明的老家,前些年我曾驻足于此,见过他的父亲。那是一位清瘦、内敛、慈祥的老人,在我们酒酣之际,霍俊明“撺掇”他唱一曲评剧为我们助兴。原本以为他会扭捏一下,殊不知老父亲往桌边一站,端起酒杯,引吭而歌,气息平稳,声音清脆,座中食客无不听得惊叹叫好。在我看来,“父亲”不仅是一种称谓,更像是一种宿命。从“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诗经·小雅·蓼莪》)到“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木兰诗》),从“何时天狼灭,父子得安闲”(李白《幽州胡马客歌》)到“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白居易《卖炭翁》),及至现当代文艺作品朱自清的《背影》、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梁晓声的散文《父亲》、鲁敏的小说《墙上的父亲》,甚至是筷子兄弟演唱的歌曲《父亲》,等等,几乎所有文艺作品中的 “父亲”都有一个荒凉的背影,即便是在文明背景与我们大相径庭的美国诗人沙朗·奥兹的诗歌《父亲》里,其“父亲”形象的终极意味仍然是荒凉的。这种“荒凉感”的形成具有若干原因,有家族传承、社会担当、亲情责任、老之将至等,甚至与华夏文明与历史的深层原因有关,所以,在《站在砖墙上的父亲》中,霍俊明如此写道:“另一双手一直在空中张着 / 有些东西 /时时落在上面/又顺着指缝滑下来 /但那并不是命运本身”。这其实已是在某种程度上对文艺作品中父亲形象的“荒凉感”作出了回应。
在《奔赴》《麂子》《读重症打鼾者80年代的日记》《恍惚的松针在黑夜里》《更深的惶恐》《停顿》《一天即将进入另外一天》等诗歌中,诗人对当下“人”的生存环境以及现实遭遇表达了内心的隐忧,不论是被削掉一百米的山、山坡深暗的褶皱、晨练的人踩出来的路,还是高速路主干道出口越来越多的堆积物以及如约而至的墓地等,这些色泽黯淡的意象在诗人笔下被赋予了深深的时代印记,与之伴生的是“疲惫”“瘦弱”“恍惚”“惶恐”等词,也能从中窥探到时代巨轮之下,一部分人的精神脸谱和内心图像。读这些诗歌,就像是在看一部寓意深刻的现实主义题材大片,每一帧画面的背后都藏着诗人对于人的生存空间的关切以及对自我心灵的救赎。在这个过程中,诗人时而出离于语言,时而又进入诗歌的内部,他既是创作者,又是自己笔下的抒写对象,“原本山川,极命草木”。于这人间疲于奔命的每一条生命,都是诗人的替身,都可以成为诗中的“我”,他们替诗人活着,并尝尽人世的酸甜苦辣,最后通过诗人的笔触,将其和盘托出。诗人的感同身受让“众我”归“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便是创作的全部过程。
当我反复阅读霍俊明组诗《海边独坐的大象》,发现他这些年的写作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那就是从早期“显而易见”的抒情性走向更为内敛和含蓄,从语词与技法的表征转向心灵的纵深,将“故作高深”的思想(哲理)内化为“诗”的自然流露,无论形式或内容,皆能抵达一种沉静、素朴之美。我不知道,这样的转变是否得益于他多年来一直整理和研究其师陈超的诗学笔记。写诗的人大多知道陈超先生的名著《生命诗学论稿》,我认为,其最大的诗学贡献,并非建构了一套独属于陈超先生的完整的诗学话语体系,也并非是为干瘪、枯燥、套路式的诗歌评论语言提供了一种端庄、新颖的诗意表达,而是陈超先生在《生命诗学论稿》中,将“人”作为一种写作本体置于语言和抒情的核心地位,第一次诚恳而又坚定地拉近语言和身体的关系,“生命诗学正是陈超诗歌批评的一个基点,坚持诗歌的本体依据,深入文本并进而揭示现代人的生存、历史和语言之间的张力甚至严酷关系。换言之,无论是陈超的文本细读,还是从历史、现实和哲学视野对诗歌本体功能的探论都围绕着生命——生存——语言——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展开”(霍俊明《“真正的先锋一如既往”——〈生命诗学论稿〉生成史兼论一个时代的出版生态》)。在这本书中,陈超先生没有鼓吹抒情的高蹈、语言的诡谲以及智力的炫耀,而是一味强调语言对于身体的寻找,强调生命、生存、甚至是生活的细节作为抒发基础的重要性,包括“求真意志”和“噬心主题”等。从霍俊明《燕山林场》《石家庄原来有这么多高楼——悼陈超》等一批诗歌,以及这一组《大象在海边独坐》中,我都深刻感受到,“身体”作为一种写作的生命根基,在霍俊明的写作中越来越具体、可感,有血有肉。“中年人看到了另一个自己”(霍俊明《一天即将进入另一天》)于不动声色处引人入胜,这是独属于成熟的“中年写作”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