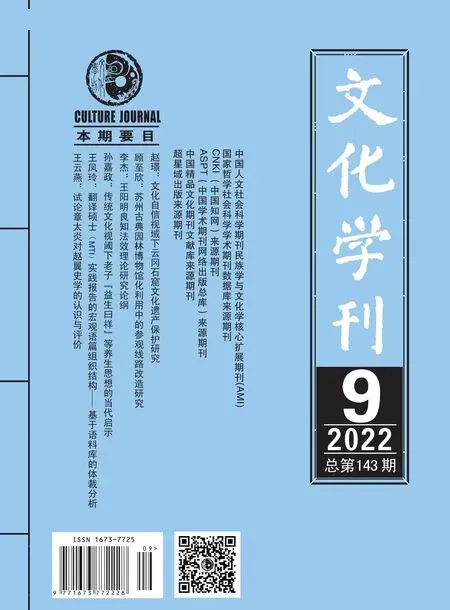从论辩角度看先秦引诗赋诗的实用意义
韩静文
先秦时期,人们在外交场合常常通过引诗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即赋诗言志。人们引诗来规劝君主,讽刺对手,小国的大夫更通过引诗来讨救兵、解纠纷,向敌国示威。《论语》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虽多,亦奚以为[1]135。”孔子也认为,学习《诗经》如果不加以运用,那么学再多也是没用的。这些都直接肯定了《诗经》的实用价值,尤其是在政治外交方面的论辩价值。
一、引诗的原因
(一)普遍性
先秦时期,引诗现象十分普遍。无论是历史叙事散文,还是诸子说理散文,都引用了大量《诗经》原文。《论语》云:“不学诗,无以言[1]178。”孔子认为,《诗经》对于言语的表达非常重要,尤其是在重要的外交场合,《诗经》成为外交官们普遍使用的“语言密码”。李春青在《论先秦“赋诗”“引诗”的文化意蕴》中提出:“观《左传》等史籍引诗,尽管引者所要表达的意思与诗句本身固有的意义往往风马牛不相及,往往极为隐晦难测,但听者却从不错会其意,……这说明‘诗’在当时的确是一种在贵族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交往话语系统,每首诗,甚至每句诗都有某种不同于其原本意义,但又较为固定的交往意义[2]。”
由此可见,引诗在先秦时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普遍存在的行为,尤其是外交行为。在一些重要的外交场合,外交家们出于种种原因,无法直言自己的观点和目的,只能通过引诗或者吟诵《诗》来隐晦地传达自己的思想,而听的人不仅能够听懂对方的“诗”外之音,还能够继续从《诗》中选择合适的语句与之对应,这说明外交家们对《诗》十分熟悉,甚至《诗经》有可能就是外交家们必修的教科书。因为只有这样,引诗这一行为才能在各个诸侯国显得如此普遍且游刃有余。
(二)权威性
《诗经》之所以作为权威存在,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人们对古籍文献非常重视,尤其是儒家对古籍文献的重视。《论语·八佾》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26。”朱熹解释说:“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才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以取证,其文献不足故也[3]。”朱熹认为正是因为文献的缺失与不足,才导致二国的历史无法证实。虽然孔子所说的“文献”包含“典籍”和“贤才”两部分,但是也说明“古籍”具有很强的实证性,是可以被信赖的历史材料。另外,《国语》中也指出,天象是神人的指示,而古籍则是先贤的智慧,所以作者认为任何事情,如果大的方面不遵从天象,小的方面不遵从古籍,必然会遭致祸患。可以说,人们对古籍的重视加深了《诗经》的权威性,也促使人们愿意通过引诗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其次,“诗言志”是古人对诗歌本质的一个基本认识,《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4]6-7。”基于这样一个认识,诗歌从一开始就是作者内心真实的写照,尤其是对理想抱负的呈现,而不是简单的声乐享乐。因此,人们十分重视“诗”这一表达形式。而且在春秋战国时期,赋诗被广泛运用于各种社交场合,人们不仅通过赋诗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还通过赋诗来考察他人的修养与志向。《左传·昭公十六年三月》云:“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赋《野有蔓草》……子产赋《郑之羔裘》……子大叔赋《褰裳》[5]1376。”这是一则关于赋诗言志非常典型的例子,韩宣子通过郑国大臣赋诗,来了解郑国意图,说明“诗言志”在当时具有合理性与普遍性。
(三)实用性
《诗经》的产生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现实而艺术”的,它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更有很强的社会功用和实用价值。早期的“颂”本身就是祭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所谓“古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人们非常重视祭祀时演唱的“颂”,“颂”也因此象征着高贵与严肃。先秦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诗歌的出现必定伴随着一些仪式化的过程,这就使得诗歌的地位更加重要。“风”和“雅”虽然出现的时间较“颂”晚一些,但也承担着重要的使命。《诗经》的编辑主要是通过采诗和献诗完成,贵族社会希望通过“诗”来了解风土民情,进而达到讽喻的目的,所以“风雅”不仅反映了社会现实,还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孟子曾经说过:“王者之迹熄而《诗》亡”[6]209(《孟子译注》),如果贵族阶级采诗的事情废止了,《诗》也就不存在了。《毛诗大序》也指出,《诗》是先王用来经夫妇、成孝敬、美教化、移风俗的,所以闻一多在《神话与诗》中提到过:“诗似乎没有在第二国度里像它这样发挥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是全面的社会生活[7]。”
除了《诗经》的社会功用外,《诗经》的实用性还体现在具体论辩过程中。上文说道,赋诗言志是先秦时期一种普遍行为,人们通过引诗来抒发情感、说明问题、论证观点。但是《诗》又不仅仅是引文或论据这么简单,《诗》在言志的过程中承载着其他功用,尤其是在外交场合与他人论辩的时候,《诗》能够帮助论辩者准确、生动地表达观点、摆明态度,使论辩话语既符合外交礼仪,又能有力辩驳与回击。尤其是对于周旋在各个大国之间的小国而言,引诗更是一种说话艺术,巧妙的引诗可以帮助小国化解大国的言语挑衅,《诗》的暗示性和留白感更是为小国争取了一丝生存和喘息的时间。这都说明了《诗经》有一定的论辩价值和意义。
二、《诗经》的论辩性意义
(一)举例
古人在进行论辩的时候,常常会借助《诗经》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引诗”不仅提高了论点的可信性,也使抽象的问题变得生动可感、易于理解。

墨子在《明鬼下》说:“子墨子曰:‘《周书·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若鬼神无有,则文王既死,彼岂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书》之鬼也[8]。”墨子认为古代先王是承认鬼神的存在的,为了能够让后世子孙知道,他们就把鬼神之事写到书上。然而后人有人怀疑这些书究竟是否存在,于是墨子就直接引用《大雅》原文,用文王死后伴随上帝左右的故事来证明鬼神的存在。
(二)暗示
《诗经》的作者在表达某个观点的时候,有时不直抒胸臆,而是用比兴的手法隐晦地说明问题。比如《硕鼠》一诗中,人民把贪得无厌的统治者比作老鼠,生动形象地展现出统治者的贪婪;《甘棠》一诗则把茂盛的甘棠树比作召公,体现了人们对召公的赞美和怀念。比兴手法的广泛使用,说明《诗经》本身具有很强的象征性或暗示性。论辩者正是利用了《诗经》的暗示性,使他的观点既含义深厚,又委婉深曲。
《鲁语·诸侯伐秦鲁人以莒人先济》曰:“豹之业,及《匏有苦叶》矣,不知其他[9]125。”《匏有苦叶》云:“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4]190”,《毛传》解释说:“以衣涉水为厉,谓由带以上也。揭,褰衣也。遭时制宜,如遇水深则厉,浅则揭矣[4]190。”关于《匏有苦叶》的主旨,历来众说纷纭。《毛诗序》认为是:“刺卫宣公也。公与夫人并为淫乱[4]190。”现代学者则更倾向于这是一首描写女子在济水边等待未婚夫的诗。然而不论《匏有苦叶》的作者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这首诗表达的是一个过河的含义,所以叔向向管理船只的官员说:“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济而已。鲁叔孙赋《匏有苦叶》,必将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9]125。”
此外,《鲁语·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曰:“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飨其宗老,而为赋《绿衣》之三章[9]139。”文伯的母亲为了给文伯娶妻,为此宴请了主管礼乐的家臣,并且吟诵了《绿衣》第三章的内容。《绿衣》第三章曰:“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讠尤兮。”郑玄认为:“女,女妾上僭者。先染丝,后制衣,皆女之所治为也,而女反乱之,亦喻乱嫡妾之礼,责以本末之行[4]163。”(《毛诗注疏》)此种说法值得讨论。因为《鲁语·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又云:“师亥闻之曰:“善哉!男女之飨,不及宗臣;宗室之谋,不过宗人。谋而不犯,微而昭矣。诗所以合意,歌所以咏诗也。今诗以合室,歌以咏之,度于法矣[9]139。”师亥认为,古人有赋诗言志的传统,诗可以隐晦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志向,所以他借吟诵前人的诗来表达对婚事的态度,并促成婚事,是符合法度的。这进一步说明,《诗经》在具体使用上具有某种暗示性。
(三)引出话题
论辩作者有时候想要提出他的论点,会先通过引诗来引出他的问题,然后再进行具体论证。比如《孟子·万章章句上》云:“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6]228?’”杨伯峻《论语译注》解释说:“诗见《齐风·南山篇》,舜时自然无此诗句,万章说:‘信斯言也,宜莫如舜’,不过以为舜时当时也有此礼而已[1]230。”万章对于“娶妻必告父母”这一传统存有质疑,甚至是舜本人也没有做到这一点。虽然舜在那个时期不可能看到《诗经》,但是万章通过引用《齐风·南山》中的诗句同舜联系起来,以引出这一话题。
(四)升华总结
有时候作者往往不在论辩之中引诗,而是在结尾的时候引,达到提纲挈领、总结全文的效果。
春秋时期,周王室逐渐衰微,各诸侯国内部统治阶级之间争夺权势,《郑伯克段于鄢》讲的就是一个母子兄弟反目的故事。郑伯的母亲生他的时候难产,所以憎恨郑伯,与郑伯的弟弟共叔段联合起来背叛郑伯。于是郑伯打败共叔段,放逐了他的母亲。后来郑伯十分后悔,在颍考叔的帮助下又和母亲和好如初。《左传·郑伯克段于鄢》在最后说:“《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5]15-16?”作者在前面写了许多不孝之事,又在最后点出了他的主题,即突出一个“孝”字。虽然《左传》在思想内容上主要反映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但是这则材料所反映的是作者意识到引诗的位置不同,其最后达到的效果也不同。
《论语》记载: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1]9。”朱熹解释这段话说:“诗卫风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贡自以无谄无骄为至矣,闻夫子之言,又知义理之无穷,虽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诗以明之[9]58。”子贡不仅熟知《诗经》,而且能够举一反三,灵活地运用《诗经》。他通过引用《卫风·淇奥》中的句子来对之前的提问进行总结,正是孔子想要的正确的学习态度。这也从侧面说明,引诗对于论辩双方确实具有总结与升华的作用。
(五)类比
在论辩过程中,作者常常通过对比不同事物的相似点,或者相同事物的不同点,来论证自己的结论。《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今也南蛮鸟夬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6]133对于楚国这样的国家,孟子没有直接铺陈阐述其不好之处,只是通过引用《鲁颂》来与陈相做对比,认为像周公这样的圣人都要攻击楚国,可陈相却背叛了自己的老师向其学习,这只能是越变越坏。
《孟子·告子章句下》云:“《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6]305。”《凯风》与《小弁》两首诗都是与亲情相关的,《小弁》有怨而《凯风》无怨,公孙丑对此并不理解。孟子在这里引用这两首诗,实际上想说明白一个问题,那就是亲疏之间的关系。孟子认为《小弁》之所以有怨,是因为对父亲的过错大,过错大而不怨,是疏远父母的表现;《凯风》之所以无怨,是因为母亲的过错小,过错小却抱怨,反而会激怒自己。孟子抓住了两首诗的相似性,并进行类比分析,终于得出他的观点,即孝顺父母要像舜一样,要一直依恋他们。
综上所述,《诗经》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人们通过引诗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不仅因为《诗经》具有普遍性和权威性,更重要的是因为《诗经》的论辩性意义。在交际过程中,人们可以通过引诗来例证自己的观点,或者委婉暗示,或者类比不同。论辩人正是利用了《诗经》的论辩性意义,使他的论辩既生动活泼,又鞭辟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