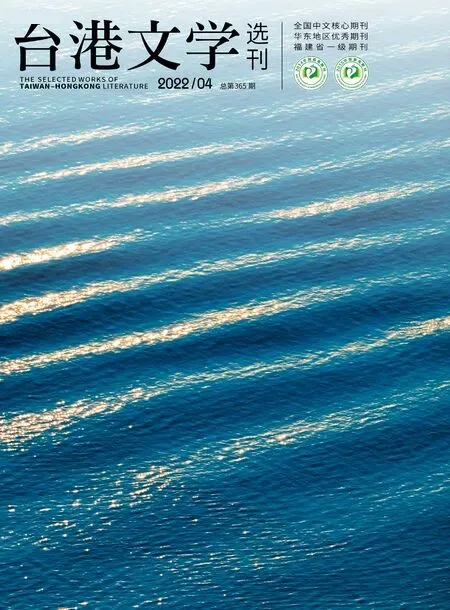木 瓜
■ 袁琼琼(中国台湾)
我跟儿子说:“我下楼去买木瓜。”
我住在11楼,住在墙与墙,壁与壁之间。我坐电梯:更为狭小的,墙与壁框出的空间。要一直坐到楼下,出了整栋大楼,才能看见天色,看见天上的云,墙外头的树,树上正开的樱花; 花瓣是薄薄的,几乎透光的粉红色。看见建筑外,公共空间里砌出的流线型花坛,花坛内种植的绿色植物,密被地面,塑胶似的萤亮和厚实整齐的绿草坪。我小时候的草地没有这样乖巧。这片草地是驯化过的,自带了配合和亲善的意味,明白自己的“演出”性质,标准而华丽,但是奄奄一息。
楼下新开了间小店。听说是果农直营,买东西要先上网去订购,也有少数品项开放零售。我不想“定”购。七十岁的我,生命里许多事情已然确定,我比较喜欢无伤大雅的不确定,不被惊吓的意外。例如上次,在店里买了木瓜。小时候家里时常吃木瓜,之后,除了泰式餐厅里一定会点的凉拌青木瓜,至少五十年,没吃过天然的,蜜甜蜜甜的,实汁实味的木瓜。
为什么就不再吃木瓜了呢?自己也不明白。人生里许多,并非不重要,甚至并非不喜爱的事物,但是就莫名地,从生活里逸失了,例如木瓜。说来也只是寻常物事,寻常到有或没有都无所谓。
小时候眷村里到处都是木瓜树。木瓜很容易生长。吃木瓜时刮下果肉中的黑色种籽,随处一埋,不多久新芽就会冒出来,然后不动声色地成长,再之后忽然就结出木瓜来。我记忆里,还没有不结果的木瓜树。小时候的环境里,零食或水果都是奢侈品,跟鸡鸭鱼肉同等级,得过节才吃得到。或者遭逢重大事件,有人生病或有人过世。但是木瓜是随处都有的。我们可能没把木瓜当水果。它跟“水果”这个词的稀贵感差得太远,却又不是蔬菜,就只是“木瓜”,超然于本草纲目之上,只代表它自己,不在任何分类中。
在我成长的年代,几乎家家有木瓜树,我家也一样,前院里三株,后院只得一棵。因为后院里,父亲把地面全铺了水泥。只在墙角圈出小小一块地面,长一株木瓜树。不是存心留块地种木瓜,恰恰相反,是木瓜树已经在这一小块空间里长出来了,所以父亲才画出地方给它。这块地是木瓜树自己给自己挣的。得证明自己值得活,人家才会给你一条活路。这是那个年代的哲学。
前院木瓜树成长的时候,我正在念小学。我家父母不知为何有个观念,认为老大教好了,下头的弟妹们就会跟着学好。殊不知,“好孩子”这东西跟教养的关系其实并没有那么必然。我小时候因为必须做弟妹们的“楷模”,每每四五点就被我爸叫起来读书。彼时天光都尚未大亮,屋檐下装了灯泡,灯下的我坐在板凳上捧着书打瞌睡,除了深信自己八成不是亲生的所以遭此残害的念头之外,并没在这些苦读的凌晨里学到什么。
不可思议的就是,当时几乎家家都这样。等天色渐亮,就总会看到对门院子里一个跟我一样坐在小板凳上苦读的孩子,简直像镜相或倒影。而且还有声音,不是单一的,是一波又一波,一条声音的河流,含混却又明晰地浮在每一家的房舍之上,像是咒语。后来书里念到了书声“琅琅”两个字,给了这清晨的景象具体的名字。“琅琅”于我,因之并不只是声音,还是画面。有颜色有气味,有那个竭力不想清醒的童年的我。
等父亲发现我低着头不是在看书而是在养神的时候,就让我在木瓜树旁边罚站。开学的头几个月我好像都是站在木瓜树旁边过的。而木瓜树长得比我快,不多久就高过了我。等到木瓜树开花,随后结出小小的梭形果实,父亲的注意力就完全转移了。而我,在那时,还是相信自己与一切事物有神秘连结的年纪,因此就深信木瓜树开花结果是为了“救”我。
我相信木瓜树知道一切。它们站在我家院子里,不动声色,其实什么都知道。早上背着书包心不甘情不愿的小人儿出门之后,是家里的男主人出门,穿着制服,提了个方形包。之后女主人提溜了菜篮出来,一手牵着要上幼儿园的较幼孩子。阳光开始逐渐加温,空气嗡嗡发热,光线温煦而不怀好意,缓缓舔舐着树叶上的水分,木瓜树就用薄而燥的羽状大叶彼此扇来扇去,分享阴凉。
木瓜树,我翻查了资料,寿命只有三五年。但是眷村里的木瓜树,似乎可以长到天荒地老,到处都在,从不同住家的墙头窜出来,越长越高。在少年男女情窦初开,躲在墙边谈情的时候,木瓜树探头望着;两口子吵架,邻舍在门口围了一大圈观战的时候,木瓜树探头望着;大人追着不想挨打的孩子满村子跑的时候,木瓜树探头望着;偶尔,村子里某一户传出哭声,单位派员来帮忙治丧,遮盖大体的担架从墙与墙间的小道通过的时候,木瓜树还是探头望着。我们演出着各自的喜怒哀乐,而真正重复经历着这一切的,其实是木瓜树吧。
曼哈顿的第五大道上,有几株美国皂荚。作为行道树,这种树非常不亲切,它的树干上遍布尖锐巨大的棘刺,“比人的手掌还长”,并且坚硬无比。“倘若你走累了想倚靠树干歇息一下,必定会被扎得头破血流。”这种树之所以长成这样,是为了防止史前巨兽乳齿象啃食它的树皮。虽然乳齿象已经灭绝,不再会有巨型生物来啃食树皮,但美国皂荚依然记得,并且用树皮上的棘刺作为记忆的印记。
植物从不遗忘。我相信木瓜树也如此。用荣格的集体意识的理论,或许木瓜树们也在基因里分享了所有木瓜树的经历和记忆。至少我愿意这样相信。
我切开从小店里买来的木瓜,和儿子一起坐在餐桌前分食。他们习惯的木瓜是加在牛奶里的,打成汁的木瓜。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吃新鲜的木瓜。橘红色的内瓤,满满是清亮的包着薄膜的黑色种籽。至少是看起来,跟我小时候吃的木瓜并无二致。这看似无知的木瓜,或许从神秘的途径感知了我的记忆,它明白自己不止于是木瓜,是更多的,更大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