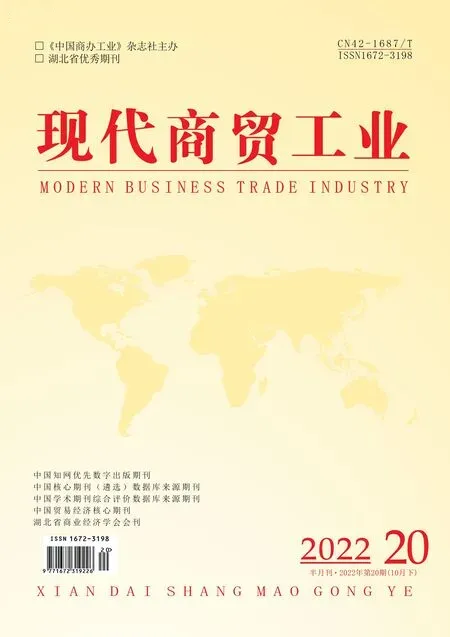法治视角下我国安宁疗护发展问题的思考
丁唯一 彭 娇
(西南医科大学法学院,四川 泸州 646000)
中国自上世纪末开始已经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目前我国六十岁以上的人口已近总人口数量的20%,根据权威机构预测,我国老年人口在2035年左右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将超过25%,2050年左右将超过33%。同时,我国的癌症患者数量也在逐年增加,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每天大约1万人确诊患癌,每分钟大约7人确诊患癌。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患癌人数的增多,伴随人们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人民对生活水平要求的不断提高,发展安宁疗护、提高临终患者生命末期的生存质量,已成为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目前,我国大陆地区已创办大约200多家安宁疗护机构,但基本能够维持运营的不到半数。近年来,我国也为推进安宁疗护的发展出台了相关政策,如2017年,原国家卫计委印发了《安宁疗护中心基本标准(试行)》和《安宁疗护中心管理规范(试行)》等,但其法律位阶较低,且我国尚未构建安宁疗护相关法律制度,导致安宁疗护在临床实践中依然有很多问题难以得到妥善解决。如安宁疗护适用对象的界定;实施安宁疗护需要满足的法律条件等,目前出台的相关规范文件均未能具体解决这些问题。同时致力于发展安宁疗护的相关机构、部门的管理权责不明,在实务操作中病人的诉求得不到重视和尊重,医生在实务操作中顾虑重重……安宁疗护在我国的全面推进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通过对安宁疗护事业在我国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同时借鉴国内外安宁疗护立法的有益经验,以期能为我国未来相关立法的出台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这对于推动安宁疗护事业在我国的快速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建立我国安宁疗护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1.1 适应我国人口老龄化和疾病谱变化发展的现实需要
我国自上世纪末已进入老龄化时期,我们不得不面对一系列问题和影响。随着老年人年龄增大,身体机能不断衰退,使其成为心血管疾病、癌症等疾病的主要攻击对象;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人类的疾病谱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据统计近年来我国居民的主要死亡原因为心脏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及癌症等慢性疾病。而调查研究显示近三分之一的临终患者在生命末期遭受过心脏按压、气管插管等一系列让普通人看来都难以承受的医疗抢救措施,这些措施使得临终患者面临丧失尊严的危险和痛苦。而安宁疗护正是立足于给予临终患者更多的人文关怀,提高其生存质量,从而使每一位临终患者都能有尊严体面的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可见,在未来我国对安宁疗护的需求会不断扩大。
1.2 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要求
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将安宁疗护法律化、制度化作为推进其快速健康发展的手段,已成为各国和地区的一种共识。联合国从人权保障和社会文明进步的角度,强调推进安宁疗护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世界安宁疗护联盟认为各国应将安宁疗护纳入国家健康政策层面,并制定安宁疗护国家法律制度和标准。从西方国家安宁疗护事业快速发展经验来看,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原因是这些国家其安宁疗护事业均已走上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人的一生包括生老病死,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必然应包括临终患者的生命末期阶段,而发展安宁疗护正是解决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的最佳选择。而我国2021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民法典》第1002条明确地将自然人的生命权划分为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两部分,该条文扩大了生命权的保护范围,认为生命尊严既包括活着的尊严,也包括死的尊严,这一条对促进我国安宁疗护发展极其重要。
1.3 医疗卫生资源节约的需求
随着前述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和患癌人数逐年递增的趋势,给我国现有医疗卫生资源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在我国临终医疗救治过程中,由于受到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影响,绝大部分患者家属往往无论临终患者的病况和意愿如何,依然会选择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对其进行积极治疗,而这些治疗不仅不能挽救患者的生命,反而使其在生命末期承受了更多的痛苦,也造成了本就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的浪费。而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一项研究就表明,每支出安宁疗护医疗保险费1美元,就可节约1.52美元的医疗保险费用,据统计在临终患者生命最后一年,施行了安宁疗护比未施行安宁疗护的临终患者节省了2000多美元的治疗、抢救等相关费用。由此可见,安宁疗护理应受到医疗卫生资源本就有限的我国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2 我国安宁疗护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 立法现状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引进安宁疗护理念、理论与服务以来,安宁疗护理论与实践在我国持续发展。笔者对近年来我国安宁疗护相关政策与立法进行了如下梳理。
(1)2016年4月21日,全国政协在京召开第49次双周协商座谈会,会议中明确了安宁疗护的内涵和功能定位,提出应以基层社区医院为重点,建立大医院、社区医院和家庭医生的分工负责和协作的安宁疗护服务体系,这是在国家层面首次推进全国安宁疗护。
(2)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首次将安宁疗护词汇纳入国家健康规划纲要,明确了加强安宁疗护等持续性医疗机构的建设。
(3)2017年1月,原国家卫计委出台《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安宁疗护中心基本标准和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及《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宁疗护实践指南(试行)的通知》,其中明确了安宁疗护中心的定义、床位、科室设置与相关管理规范,并确定了安宁疗护实践应以临终患者和家属为中心,以多学科协作开展的模式,同时对临终患者常见的疼痛及其它症状的治疗、舒缓照护和人文关怀等给予了指导性建议,这也是首次出台的关于安宁疗护的具体规范文件。
(4)2019年12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其中第36条规定“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分工合作,为公民提供预防、保健、治疗、护理、康复、安宁疗护等全方位全周期的医疗卫生服务。”该法从立法层面将安宁疗护纳入国家健康体系。
2.2 存在的问题
安宁疗护引入我国已有30多年,但至今我国尚未制定专门独立的安宁疗护法,安宁疗护在我国法律制度层面还有很多空白不足亟待填补完善。第一,缺乏患者医疗自主权保障的专门立法。对于患者医疗自主权,我国既未专门立法予以保障,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也未触及,导致临床活动中处于生命末期的患者虽然饱受病痛折磨,但由于其缺乏行使医疗自主权法律上的正当性依据,即不具有拒绝无效治疗的权利,即使其已明确表达拒绝无效抢救等医疗措施的意愿,但医务人员害怕日后承担民事甚至于刑事责任,也就不敢遵从临终患者意愿为其停止维生医疗支持系统……从而使得临终患者在各种延命治疗措施中备受痛苦,也就与安宁疗护的目的背道而驰。第二,现有规定中安宁疗护相关内容缺乏完整性和明确性。诸如安宁疗护服务的性质、服务对象、准入标准、服务内容、从业人员的执业要求,包括医务人员对不积极治疗模式的告知义务,临终患者及其家属放弃积极治疗的程序要求等,都亟须以相关法律予以明确具体的规范。
3 其他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安宁疗护立法状况
3.1 英国
从1967年以来,英国开始对安宁疗护服务模式、要求等逐渐予以标准化、统一化。首先,1990年英国政府颁布了《国家卫生服务及社区关怀法》,将安宁疗护纳入国民医疗保险范畴。2002年英国又在各地区设立了“战略医疗保健责权机构”,委派内政大臣负责监管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施行情况。2006年政府出台了《慈善法案》,其中针对服务于安宁疗护事业的慈善机构的注册标准予以了规范。后英国卫生部专门制定了《临终关怀指南》,建立相关的监管制度,要求各相关部门应重视民众的死亡质量。
3.2 美国
由于安宁疗护在美国各州的推广和影响,加州于1976年通过了《自然死亡法案》,开始推行生前预嘱,即在人们意识清醒时,预先设立医疗指示,明确表达处于生命末期时是否接受心肺复苏、延命治疗等医疗措施的意愿,日后医生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执行该生前预嘱。1982年,美国国会就颁布了法令,将安宁疗护纳入国民医疗保险支付计划中。后美国政府于1991年又颁布了《病人自决法案》,该法案规定了患者作为医疗活动的参与者,有权决定是否接受施行于自身的医疗措施。
3.3 我国台湾地区
安宁疗护的理念从1980年开始引入我国台湾地区,发展至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2000年我国台湾地区就通过了《安宁缓和医疗条例》,这是亚洲第一部安宁疗护法案,该法案第4条规定预立选择安宁疗护意愿书,通过法律的形式保障了患者的自主权,体现了对临终患者选择死亡方式的尊重,其第7条明确了不施行心肺复苏术的条件,使得从此在我国台湾地区开展安宁疗护服务过程中不施行心肺复苏术开始合法化。2016年1月6日,我国台湾地区又颁布了《病人自主权利法》,这也是亚洲涉及患者自主权利的第一部法案,其也是为保障患者的医疗自主权、尊重临终患者选择死亡方式权利等目的而设立。相较于2000年通过的《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病人自主权利法》其适用安宁疗护的对象范围有所扩大。
4 建立并完善我国安宁疗护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议
4.1 安宁疗护适用对象的确定
安宁疗护的适用对象即享有安宁疗护服务的人。安宁疗护主要针对临终患者出现疼痛等不适症状予以舒缓医疗,以保障临终患者余下生命的质量,维护其生命尊严。因此,根据医学标准通过法律形式对安宁疗护适用对象进行界定非常有必要。在此,我们可参考美国对安宁疗护适用对象的界定“处于生命终末期的患者,即经主治医师等专业人士确定所患疾病无法治愈,且在近期一般为六个月内无可避免的死亡”。又如我国台湾将末期患者定义为“经医师确定所患疾病无法治愈,且医学证明近期内不可避免的死亡。”借鉴其他立法例同时结合我国安宁疗护临床实践,可将我国安宁疗护适用对象确定为“罹患现有医学条件下无法治愈的疾病,且病情出现无法逆转的恶化,经医师诊断为最后生存期不满六个月,迫切需要安宁疗护服务的人。”
4.2 安宁疗护服务机构的界定与准入
安宁疗护服务机构的性质应介于传统的养老院与医院之间的一类新型医疗机构。它不为健康老人等提供养老服务,也不以诊治疾病为主要的服务内容。其主要的职能是为疾病不可治愈的终末期患者提供减轻疼痛等对症处置服务,从而提高临终患者的生存质量。
安宁疗护机构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减轻病痛、舒缓治疗及心灵抚慰,由此可见,该机构的服务团队应该由临床医师、护士、心理医师及社会工作者等人员共同构成。因此,我们应通过立法对安宁疗护服务机构的硬件设施、机构管理、从业人员资质、资金投入等设立标准予以明确规定,以保障其为临终患者提供更好地安宁疗护服务。
4.3 设立生前预嘱法律制度
生前预嘱是指患者意识清醒且具有完全行为能力时,提前以口头或书面形式签署的,指明当其患有无法治愈之疾病处于生命末期时,接受或不接受某种医疗措施的指示文书。该文书以临终患者内心真实意愿为中心,能确保签署主体意思表示的真实表达,我国应尽快以立法形式确立生前预嘱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这对于促进安宁疗护事业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建立生前预嘱法律制度须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第一,生前预嘱的主体须为年满十八周岁且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理解生前预嘱相关内容后,出于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签署该文书。第二,生前预嘱的见证程序要求,立文书之时须有两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且与当事人无利害关系的公民在场见证。第三,生前预嘱的执行与否,须由两名以上资历较高且执业经验丰富的主任医师或者副主任医师予以认定。第四,临终患者有权对生前预嘱的内容随时进行修改或撤销。
4.4 法律责任的豁免条件
鉴于医务人员为临终患者实施安宁疗护时可能会面临侵犯临终患者生命健康权益的风险,为排除其后顾之忧,我国应设立相对应的法律责任豁免条件,否则安宁疗护在我国的推进将举步维艰。通过参考其他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立法,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在我国安宁疗护实施中法律责任豁免的条件应包括:第一,医务人员应基于职业的道德良知,及时告知临终患者病情及拟提供的安宁疗护服务;第二,医务人员施行的安宁疗护活动应符合合理的医疗标准;第三,没有开展安宁疗护的医疗机构应及时告知患者并将其转诊至能够提供安宁疗护服务的医疗机构,并遵照临终患者意愿不对其实施延命治疗措施。在开展安宁疗护过程中即使发生患者提前死亡等情况,只要符合以上条件,医务人员也无需承担法律责任。
总之,安宁疗护体现了对临终患者医疗自主权的尊重,为其摆脱困境提供了一条新路径,能有效维护临终患者的生命尊严,同时也能促使公众树立正确的生死价值观。因此,安宁疗护在我国予以法治化非常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