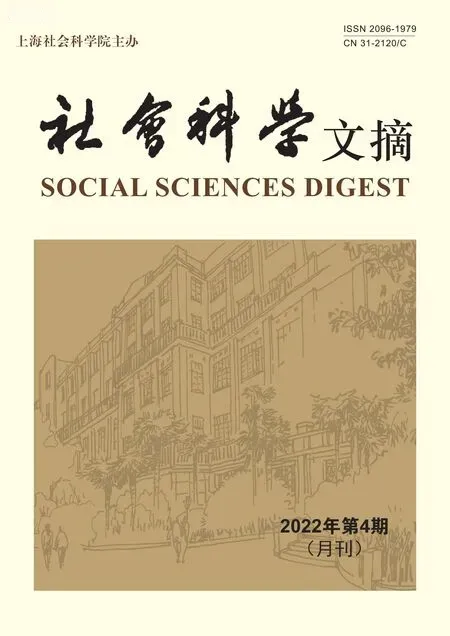社区感:社区组织的新媒体形式与关系连接
文/罗坤瑾 郑裕琳
【罗坤瑾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郑裕琳系中共汕头市委党校科员;摘自《学术研究》2022年第3期;原题为《社区感:社区组织的新媒体形式与关系连接——基于慈善组织义工微信群的研究》;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构建研究”(20AZD057)的阶段性成果】
“社区感”概念自1974年提出,其内涵阐释至今仍存在争议。在新媒介传播视域中,社区感的概念经历了从网络主题乐园团体到脱域、嵌域再到脱域共同体的转变,三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分别是甘斯、吉登斯和费舍尔。在概念的历史谱系中,网络社区感更多的是沿用吉登斯的分析立场,即将社区感视为脱域与嵌域的统一。在中国这样一个血缘、宗法、乡土等文化关系依然浓郁的社会环境中,线下社会圈层的建构法则依然影响到线上虚拟空间中的圈层建构。社区感对慈善组织具有凝聚人心、促进群体融合的作用。慈善组织义工使用微信沟通、联络、组织义工活动。微信使用对凝聚慈善组织机构社区感的意义愈发凸显。本文选取广东汕头“存心善堂”义工协会为研究对象,这是一个既基于特定地理位置的地理基础型社区,又是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关系型社区。研究采用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通过面对面访谈和电话录音两种形式,用扎根理论对12名访谈对象进行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微信对多种社区类型叠加的义工社区感是否有影响?影响义工社区感的因素有哪些?本文期望探究微信对特定群体社区感的凝聚与微信群成员之间的关系连接有何关系。
技术与社会空间重叠的交际转场
(一)新工具:以网络媒介为代表的虚拟共同体
社区感(sense of community)一词最早由社区心理学者Sarason于1974年提出。他将社区感定义为:察觉到与他人的相似性,认同与他人间互相依赖的关系,向他人提供期待的帮助,愿意保持这种互相依赖的关系,个体从属于大型的、可依靠的和稳定结构的情感。1986年,有学者提出“四要素”理论模型,用更具体的术语来定义社区感。他们对社区感的定义与Sarason相似:“成员的归属感,成员彼此间及与团体的情感,成员通过共同承担工作满足自己需求的一种共享信念。”并将社区感划分为四个维度:成员资格、影响力、整合与满足需要、共同的情感联结。正如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所言:“网络真正的价值正越来越和信息无关,而和社区相关。”
在网络传播语境下,人们的交流空间由真实向虚拟过渡。现实中的社区观念、社区感也发生着地理空间的位移。持消极态度的学者认为虚拟社区的兴起意味着传统的基于地缘和血缘的物理社区的衰落,人们越来越依赖于通过社交媒体交流,导致人际关系的疏离和归属感的缺失。蒋建国关注微信化生存带来的社交幻化,认为“越微信、越焦虑、越冷漠”进而导致现实人际交往的疏远。而持积极态度的学者如Armstrong和Hagel认为虚拟社群的成员会将生活上的经验、宗教信仰、健康状况等讯息彼此做沟通和交流,使成员能互相分享内心的喜怒哀乐,进而纾解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在社群中持续地互动,并从互动中创造出一种相互信任和相互依赖的伙伴关系。曼纽尔·卡斯特认为网络社会的崛起使得世界正从具有地理和历史纽带的“地方空间”转向信息社会构建的“流动的空间”,所有认同都是运用历史、地理、集体记忆、宗教启示等构建起来的。
(二)新连接:社区与媒介互动构建的新型共同体
化解人情冷漠是新媒介时代的慈善组织义工微信群结成虚拟社区的意义所在。对于虚拟社区中的网络人际交往,吉登斯区分了两种脱域机制类型,一种为象征标志,另一种为专家系统,二者统称为抽象系统。“所谓象征标志,指的是相互交流的媒介,它能将信息传递开来,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所谓脱域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与象征标志一样,专家系统也是一种脱域机制,它把社会关系从具体情境中直接分离出来。那么,“嵌域”就意指重新转移或重新构造已脱域的社会关系,以便使这些关系与地域性的时空条件相契合。
梅罗维茨认为电子媒介的影像、声音和音乐等表象符号“展示”了感觉和情绪讯息,它既直接又模糊,自然又缺乏精准。所谓的“新”媒介是对先前技术形式的发展或再媒介化。如果将新媒介技术理解为真实世界中人与人交互的镜像,那么微信搭建的虚拟场景实现了点对点、点对多的互动交流方式。微信聊天议题和内容由群组成员贡献,对话题的深度讨论在你来我往中打散,呈现碎片化。微信群更像是一个熟人密布的“大茶馆”。这种互动交流虽然实现了成员间身体和时空的虚拟共场,但碎片化的内容交流、即时随意的回复需要成员的高度关注和参与,否则稍不注意便被群组义工们的聊天内容“刷屏”,无法了解“前因后果”。这种交流不是沟通,难以形成深度的情感体验。这种基于符号化的交流将微信视为符号社交,个体碎片化、漫不经心的阅读导致情感交流被消解。弱关系难以建立牢固的情感认同,反而令主体身份认知模糊,引发社会认同危机。
关系与行为虚拟构建的交往实践
(一)意愿:行动与关系的连接
在互联网信息传播中,繁冗的信息充斥和占据着人们的闲暇和工作时间,表面看来人们的信息极为富足,实则带来的是生命经验的贫乏、碎片化的自我建构与庸俗化的日常体验。当人们反观自我世界时,难免会在信息生产的绝对加速和自我减速间产生“无力感”“丧文化”“佛系”等行动异化。调查发现,义工成员参与互动的动机、主动性及搭建关系的意愿强弱程度均影响着义工成员的社区感强弱。义工群体里年龄较轻的多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学生,他们并无搭建社会关系、拓展人脉资源的目的,也无倾诉情感的精神需求,往往与其他年长的义工之间保持很疏淡的关系,继而难以形成社区感。而义工群体中年女性占据多数也影响到组织整体的交际圈层结构。调查发现,义工中年龄在41—50岁之间的人数最多(33.3%);51—60岁的义工占16.7%;61—70岁的义工占8.3%。年龄结构决定了义工组织的行动导向及交流方式。“富于伸缩性”的中国传统差序格局人际圈和随意性、低门槛的建群聊天的互联网人际圈叠加下,微信群组众多,群与群之间构成多重交织、重叠的关系。受访者在各种微信群中分身无暇,自然选择群内成员间粘性高和日常人际交往强的微信群。
(二)凝聚:身份的群体归属
社区感影响因素之一是成员资格,指社区成员投入到社区中并归属于某种社区的感受。它有五个属性。一是界限,即用以区分群体内和群体外的边界;对于地理基础型社区而言就是地理界限,对于关系型社区而言,它包括共同兴趣或共同人格;二是共同的象征系统,如宗教形象、国旗等,用以帮助和加强社区成员的心理统一感;三是情感上的安全感,包括群体认同、从邻里间的互相帮助而来的安全感;四是个体投资,这种缴纳常常不是货币化的,如花时间参加慈善团体,为群体承担情感风险的活动;五是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研究发现,投入慈善活动的时间与精力越多,获得的成员资格就越强。存心义工协会在特定地理位置开展活动,是具有共同兴趣和共同人格的关系型社区。义工服、勋章作为共同象征体系,既有助于加强社区成员的心理统一感,又是区分群体内外的边界。微信群规的设立、管理和遵守是区分内外群的界限。社会认同理论中的“内群认同”关注群体内部同质性和通过关系而产生的内群体态度改变。人们通过对微信群发布的公共信息形成一个有着强烈归属感的群体。群体身份能为个体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中提供稳定的行为模式,减少个体的不确定性。
(三)提升:采取行为的态度
尼克·库尔德里将“归档”认为是个人时间管理的习惯。微信分享照片这种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档案允许以图像、声音和文本为形式的数据进行大量存储并受到访问,是保存人生印记(lifecaching)和共享归档材料的行为。摄影将个人记忆、集体纽带和社群的历史生产结为一体,这种“归档”方式和空间指向的“在场”越来越紧密地连在一起,在档案和集体记忆间建构了一种新的联系。除了“归档”和“展示”,义工们在现实场景中的活动形成了集体情感的连接,对个体产生深远的影响,通过点赞互动、加微信好友,微信群的“好友”再嵌入义工的现实生活,在微信构建的虚拟场景中,每一次对这份集体记忆的分享、归档都延长着情感体验,加深义工们的社区感。集体记忆的构建是塑造社会认同的重要力量,媒介在集体记忆的保存、传播中扮演核心角色。社区感影响因素之二是采取行为,这里的行为包括义工加入微信群、参与线上线下活动后所采取的行动。访谈中采取积极行为者占比最高为84.2%,采取消极行为和选择性查看行为者各占21.1%。消极行为和选择性查看行为的选择与性格、年龄、工作相关外,还和微信群组过多、语音刷屏、用微信表达不清和聊天针对性不强等相关。
情感回归与人文交流的精神需要
(一)内化:整合与满足的需要
按照社会交换理论的观点,行动者是理性的;理性的行动者为了获得基本的需求而同其他行动者发生交换性的互动关系。慈善组织满足了社会公众某种心理和社会需要,如荣誉感、积功德、自我实现等。在志愿服务的社会交换过程中,民间慈善组织起到了社会中介的作用,即通过吸纳社会公众,使他们成为志愿者,为社会困难群体提供慈善公益服务,从而实现了社会资源效用的最大化。社区感影响因素之三是整合和满足需要。整合是指通过社区卷入,如参加社区活动形成共同的价值观。社区活动的参与有利于彼此熟悉和共同的价值观的形成,而熟悉程度和价值观相同反之也影响社区卷入程度,从而影响社区感的形成。整合是指通过社区卷入,如参加社区活动形成共同的价值观。
中年女性面临家庭和事业的双重压力,在慈善活动中能寻找到一种情感慰藉,向陌生人倾诉情怀不必担忧吐槽会伤害家庭和睦。慈善义工群体成为外地女性移民情感交流的港湾,这符合吉登斯的再嵌入(reˉembedding)理念。所谓再嵌入,指重新转移或重新构造已脱域的社会关系,以便使这些关系与地域性的时—空条件相契合。布劳认为,那些在社会交换中拥有优势资源的交换者会获得社会的权力,并且获得社会交换中的最高报酬——服从;那些拥有权力的人,通过社会交换将权力转换为权威,取得了他人对权力的一种认可。那些对志愿服务高投入且拥有较高专业素养的志愿者就会获得志愿者群体的领导权。通过竞争、分化与整合,存心善堂建立起稳固的志愿者组织体系,有效提高其志愿服务的效率。
(二)共情:群际维系的需要
社区感的影响因素之四是共同的情感联结,包括共享激动时刻、庆典、社区叙事和仪式。在相处中得到的情感联系产生了合作的能力。通过合作的意愿,创造积极的互动,从而解决社区的困难和加强情感联系。社区中的成员可以通过行为、语言等进行这种共享的联结,在相处中得到的情感联系产生了合作的能力。线上线下联动是指义工在实际参与义工服务中,借助微信实现归档和展示等信息分享,虚拟社区与现实社区联动解决社区困难,从而加强情感联系。戈夫曼的场景理论认为,文字书写倾向于提供较正式的前区观点,语音交谈则类似非正式的、即刻的和后区的经历,视频、语音比起文字显得更亲密。在“熟人社会”的虚拟社区场景中成员倾向于使用语音;在彼此陌生的虚拟社区场景中则倾向于文字。
学者普遍认为,共情(empathy)是个体理解他人情感,并做出情感反应的能力,而认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是通过认知参与,理解他人情绪状态产生的原因。“帮助别人”被访谈对象提及,同时描述现场所见场景和参与时的现场体会,“困难”“老人”“可怜”“成就感”是被提及频率最高的词汇。共情是产生利他行为的原因之一,救援现场的感同身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情感动员的作用。柯林斯在《互动仪式链》中以共同关注的聚焦点和社会氛围感为划分依据,将集体情感产生的情境范围做出层次区分,最高层次是互动仪式链,人们在活动中高度的相互关注跟高度的情感连接相结合。在现实场景中,义工群体感受到帮扶对象和义工群体间的情感,形成以关注和情感关联为核心的互动仪式。
结论与展望
微信本质上仍然属于网络虚拟交往,并且带有“符号社交”的基本特征,与现实情感交流有着很大区别。以微信作为社区的集结平台,搭建的场景成为“符号社交”和“现实交往”的桥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空间距离,延长了在场时间,对于现实社交不一定是消解情感,也可以是现实社区的情感体验度在线上虚拟社区的延伸。20—40岁的义工群体,有自己相对固定的现实人际交往圈,倾向于选择群内成员间粘性高的微信群进行互动;而40—50岁的义工,尤其是中年女性,对义工微信群具有较为强烈的社区感。微信群甚至是连接她们与“姐妹们”的关系纽带、情感容器。线上线下活动都需要时间投入,工作时长、忙碌程度等工作性质影响个体参与度,参与义工活动的时间长短、精力多寡直接影响到社区感的强弱;个体自身性格和义工职务所赋予的责任感影响其对义工群的关注和态度,进而影响微信对义工社区感的凝聚。参与度越高、参与时间长的义工,人际圈层和义工群体重叠越多,通过朋友圈分享信息和现实参与活动、产生的情感自然越稳定和可持续,社区感越强。而不常使用微信的义工虽然在虚拟社区并不活跃,但在现实社区的参与也能使其融入其中。因此,技术并未决定社会,而是技术具体化了社会;社会也并未决定技术发明,而是社会利用了技术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