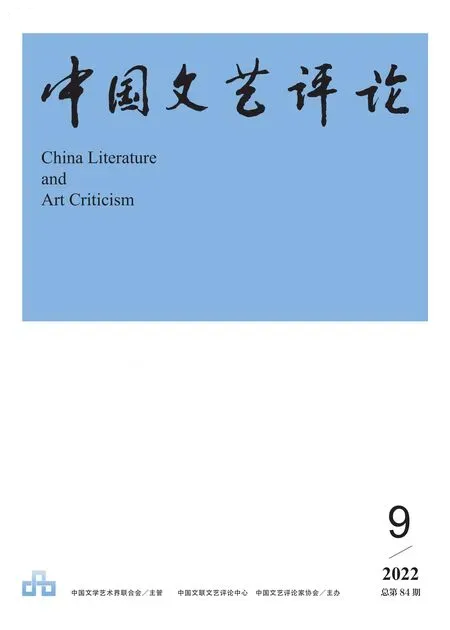美的淬炼如此残酷
——从话剧《主角》看到的和想到的
■ 傅 谨
2019年,陈彦的小说《主角》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2022年,陕西人民艺术剧院和编剧曹路生把《主角》搬上了话剧舞台。将体量如此之大的小说改编成话剧有多种模式,一种是将小说作为创作的素材和灵感来源,编剧完全撇开原著,写出自己对人生和历史的理解;另一种则是从这部八十多万字的小说中撷取部分内容——尤其是其主人公的生活经历,构成一部新的独立完整的话剧作品。而尽量直接从原著取材,将它浓缩并串联成戏剧作品的改编,其意义、价值和难度,一点都不输于将原著作为素材或灵感来源的改编,并且更需要改编者与原著作者发自内心的深刻共鸣。对于《主角》这部获得茅盾文学奖因而已有定评的当代经典,撇开作品另行创作多半有不智之嫌;而假如从作品里选取部分内容,就不得不舍弃其他那些或许同样精彩甚至更精彩的章节,多半会令人感到可惜。所以编剧的取舍眼光和剪裁功夫就尤为重要,在我看来,小说《主角》的整体叙事基本上是两个相互支撑的行动线,一条是从艺术的角度揭示了忆秦娥是如何成为戏曲舞台上的主角的,另一条才是在忆秦娥成为主角的过程中她所经历的磨难。对普通观众而言,后一条线索显然更容易引起共鸣,陕西人艺的《主角》选择了小说主人公经历的这个维度完成话剧改编,不失为聪明的选择。好在作品这后一条线索也非常完整,为话剧对小说原著的浓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图1 话剧《主角》剧照 (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提供)
女主人公忆秦娥遭受的重重挫折和不幸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情感冲击力,不仅是由于她生命中的不幸遭遇,更在于她对人没有任何恶意,也从来不争不抢、与世无争,她靠自己的天分和努力(当然还有机遇的垂青)为人间提供和创造了不可思议的美,然而各种常人无法想象的劫难却一次又一次地落到她头上。话剧舞台上的忆秦娥,让人感到既熟悉又陌生。这里所谓熟悉,是指梨园题材的话剧并不十分鲜见,尽管此前尚无知名的文艺作品以大西北的秦腔名家为作品主人公,但新文化运动以来,杰出的梨园题材小说、戏剧屡见不鲜;所谓陌生,是指话剧如其小说原著一样,将这位与世无争、潜心艺术、不食人间烟火的大艺术家遭受的最难堪的时刻直接展示在舞台上,让人爱怜交加。而正由于话剧撷取的主要是主人公的辛酸,所以它所激起的观众的情感,“怜”的成分又要多于“爱”。
忆秦娥的经历似乎暗示了美的成就必然伴随着磨难,如同金属锻造的过程。美的艺术和金属锻造都是人类文明成熟的重要标志,看似遥远又很相似。金属锻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最为惊心动魄的环节就是淬火,是把炉火中烧得通红的金属器物突然放到冰冷的水里,经历过这种温度大起大落的极限情境的淬炼后,金属就变得既刚且柔、硬而不脆,大幅度提升了材质和用途,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集锋芒与坚韧于一体的刀剑。话剧《主角》用忆秦娥的经历告诉我们,美的艺术也是这样,只不过惊艳的美固然需要淬炼,但忆秦娥终究是凡人,一次又一次的劫难虽然没有把她击溃,但这样的淬炼也确实令人心碎和心痛。
毫无疑问,如果将视野仅仅局限于舞台和事业上,忆秦娥显然是人生赢家。她在短短几年里成为秦腔这个大剧种最具代表性的省剧团主演,她的表演艺术让无数观众痴迷,为剧团、为秦腔同时也为自己争得了无数荣誉,迅速成为大西北秦腔的头牌,所到之处全是鲜花和掌声。但话剧《主角》并不打算给观众讲述一个戏曲名家成功的故事,甚至作者也无意渲染她成长道路上命运的眷顾和伯乐的发现,或者组织的培养、集体的温暖和观众的厚爱;相反,全剧浓墨重彩描述的都是她由于成了主角而付出的昂贵代价。她只是像路人一样度过自己的生命,人生起点低到不能再低,却似乎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多少人一生孜孜以求的梦想。事业上的成功来得如此之自然,不用筹划,无需经营,所有的都似乎水到渠成。但是且慢,正如俗话所说,上帝为你打开了一扇门,就会关上另一扇门,对忆秦娥,上帝开的这扇艺术之门开得太大了,于是就要关上许多扇门去平衡。
忆秦娥是一位放羊女娃,在剧团打鼓的舅舅把她带出大山进入县剧团,又因为舅舅闯了祸,她也受牵连而被发配到伙房烧火。“文革”结束后传统戏重新回到舞台,忆秦娥在伙房里无聊得只能练功,意外地成为其时有能力让传统剧目精彩绽放的稀有人才。对她而言这是幸运之神的眷顾,但不能算“功夫不负有心人”,因为在动乱年代,练功只不过是她躲开烦恼的一种慰藉,一头钻进艺术天地的她,只是借此暂时忘却生活中的烦恼和痛苦,这从一开始就不是她献身艺术的自觉行为。
忆秦娥似乎生来就是要成为主角的,然而艺术对她却并不友好。她确实因出众的表演才华而成为主角,迅速站在了舞台中间,成为秦腔界一颗耀眼的明星,然而成为主角给她带来的不是幸福与快乐,生活中众多困扰、尤其是莫须有的流言和诽谤,朝着她孤独的身影铺天盖地而来。她在舞台上闪耀光芒,登上艺术的顶峰,受到观众的追捧,但是另一面却是越来越多的不幸。她因主演《白蛇传》而萌生初恋,但她的“光焰”逼退了这份美好,她只能无奈放弃,所有人都劝她嫁给那个只为满足其占有欲的花花公子刘红兵。她婚后只想过平凡日子,却与刘红兵生了个痴呆儿,并且目睹了曾经对她千依百顺的丈夫的背叛;离婚后遇到了画家石怀玉,总算有了一段真心相爱的短暂交往,却因此而断送了儿子生命,同时也折断了这双爱情的翅膀。如果说这些遭遇都有偶然性,那么还有四处向她射来的明枪暗箭,她就像一丛高高的箭垛祼露在众人面前,无从躲避。

图2 话剧《主角》剧照 (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提供)
如果还用金属冶炼作比喻的话,话剧《主角》表现忆秦娥成长的锻造过程,更把她经历的无数次令人惊心动魄的淬火摆在观众面前。美的创造过程中那些滥情与温婉的时刻,已经有无数文艺作品表现过了,现在,编剧曹路生要从陈彦小说里抽取表现美的淬炼这个残忍冷酷的过程呈现给观众。当然,话剧《主角》在舞台上展示忆秦娥经历的这一切,并不只是为了博取观众同情,因为同情是强者面对弱者苦难时的反应;也不是为了让观众感慨于忆秦娥因为有超越凡人的坚强意志、终得正果,因为面对所有的不幸,她只有无奈和无助。她吃了一般人吃不了的苦,受了一般人受不了的罪,她成了;但她为成功付出的代价,大到足以让人们退避三舍,因为这样的成功一点也不令人羡慕。所以,观众或许会因此警醒,因为这才是人生的真相。
《主角》从小说到话剧,基本的人物形象与性格一脉相承。在某种意义上,原著塑造得最为入木三分的人物,或许还不是主角忆秦娥,而是对忆秦娥伤害最大的楚嘉禾,这个人物的塑造是《主角》最重要的文学贡献之一。忆秦娥的人生是被动的,楚嘉禾的人生才是主动的。写忆秦娥,写的是她的命;写楚嘉禾,写出了这个人。
楚嘉禾和忆秦娥同时进了县剧团又同时被调入省剧团,一直同台演戏。她们当然不是闺蜜——楚嘉禾眼里根本就瞧不起这位山沟里来的、又被发配到伙房烧火的丑丫头。但偏偏所有她努力投机钻营想要得到的、或者说她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的,都给了忆秦娥。她一直习惯于蛋糕里最大的一块是要自己先得且独得的,但是在这座舞台上,她永远和蛋糕的美味擦肩而过,相反,无须花费任何心思,所有人就主动把最大的一块切给忆秦娥,留给她的只剩渣渣。舞台很大,又很小;舞台是公平的,又很不公。从竞争者的角度看,舞台从来都是名利场,它大到让形形色色的人都有表演的空间,又小到只有极少数人站在中间,其他人都只能是其配角;它的公平就在于优秀的演员终会脱颖而出,它的不公在于聚光灯永远只照亮主角,其他人哪怕只是略逊一筹,就只能做衬托红花的绿叶。舞台是天底下最势利的场所,在这里,优秀和一般之间,或许真就是差之毫厘,但结果却谬以千里。“红花还要绿叶扶”这句话是用来好心安慰绿叶的,对红花,它的作用至多不过是勉强和多余的提醒。
所以,当深信只有自己才配做红花的楚嘉禾不幸成了“扶”红花的绿叶时,她的所有丑行都有了充分的理由。她不肯承认自己是因天赋、努力不够而成不了主角,更无法接受忆秦娥天赐般的成功,虚荣和嫉妒激发出内心潜藏的恶魔,她因心理失衡而不择手段,不只是要成为红花,还要看到忆秦娥毁灭。但《主角》并没有暗示有关忆秦娥的谣言全是楚嘉禾一人之恶,楚嘉禾只是无端捏造了有关忆秦娥私生活的流言的一众人等的缩影,只不过在楚嘉禾身上,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人生失败组的心理变态和丑陋行为。在忆秦娥身边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楚嘉禾”,区别只在于楚嘉禾的心态失衡更为剧烈,因而更具代表性。尤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失败者平日里趾高气扬,自认为是上帝特许的选民,恰恰忽略了成功者之所以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除了天赋,更有努力和专注。当然,他们是拒绝反省的,相反,当旁人、尤其是身边一直鄙视的人因艰辛刻苦的付出换来自己梦寐以求而不得的成功时,挫败的失落激发出加倍的恶意,逐渐孕育出“恨人有,笑人无”的卑劣人格。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他们只是无法接受挫败,更不愿意承认他人的成功和自己的失败是由于先天秉赋尤其是后天努力之差异的结果,于是通过编造虚假并恶毒的谎言构成一个信息茧房,试图借此自我逃遁,减缓挫败的焦虑,实现心理平衡;但编造谣言永远无法靠谣言消除挫败的焦虑,因为最清楚谣言是谣言的,就是谣言制造者本人。路人可能对谣言深信不疑,唯有谣言编造者永远心虚,一步走出,他只能通过不断重复且丰富谣言的方式实现自我麻痹。从这个意义上说,楚嘉禾之类或许算不上大奸大恶,如果造谣确实有益于暂时抚慰挫败者的心理创痛,成功者不妨秉善良之心予以谅解;可惜舞台并不远离现实,世界并不处于真空状态,虚假信息不会局限于挫败者的自我解嘲,谣言会流动并且在流动中被放大,由此构成对成功者无法弥补的永久伤害。
楚嘉禾是时代的产物,恶意编造且散布有关成功者的谣言、尤其是私生活方面的谣言,是当代社会的一颗毒瘤;而戏曲舞台的激烈竞争和剧团僵化的人事制度,则成为这种恶质文化最好的温床。在当代文艺领域,《主角》第一次直接尖锐地将杀人于无形的谣言对艺术、对社会的挑战摆在人们面前,令人警醒。各种流言蜚语对人的杀伤力,不在于它被编得天衣无缝令当事人难以澄清,恰恰相反,许多流言蜚语完全经不起求证。都说谣言止于智者,但即使智者也需要止息谣言的动力,各种出于作恶者内心阴暗与卑劣动机而编造的谣言,巧妙地利用了人类普遍性的弱点,对成功者说不清道不明的嫉妒,传播与议论成功者私生活的不堪时获得的促狭快感,恰好让传谣者与谣言制造者之间形成微妙的同构关系。所以,比楚嘉禾这种人的存在及其恶意编造的谣言更令人深感不安的,是忆秦娥面对四处传播的谣言时的无力感,即使是那些最器重她、最需要她和最亲近她的人也无能为力。忆秦娥偶尔试图反抗,她幼稚地以为真相可以驱除谣言,她想向这个世界证明清白,最终只能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向她一直不屑的刘红兵证明,这才是人生真正的悲哀。

图3 话剧《主角》剧照 (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提供)
话剧《主角》贴近自然的叙事,为当代舞台贡献了一位独特又活生生的“瓜娃”,无数戏剧作品喜欢表现主人公聪明伶俐和积极奋进的人格,《主角》却反其道而行之。忆秦娥出身低微,自幼受人白眼,她与世无争,无数次想要放弃,从来没有成为命运的主人。她生活中的所有,无论成功还是挫折,从来都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相反,一路懵懵懂懂走来,她之所以是陕西方言里典型的“瓜娃”,不仅因为“瓜”,更在于她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瓜”。她不知道天地间有那么多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她和那些自以为是的聪明人的思维与行为相距太远。假如不是因为她“瓜”得根本意识不到苦——从练功时的苦到被各种无来由的攻讦与谣诼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苦,很难一路坚持过来。也正由于她除了唱戏什么都不明白的“瓜”,才给世界奉献和留下了美的艺术、精湛的秦腔表演。秦腔的美是浓烈的、惊艳的,而营造这样的美就要吃苦。说“不吃苦中苦,哪能人上人”都嫌太功利,“瓜”得不知其苦才有成就,这是亘古不变的至理名言、天地间至深的道理。正如剧中的秦八娃所说,戏确实把忆秦娥唱得苦不堪言、肝肠寸断,但假如不唱,只会更加苦不堪言,但是唱戏并不是她的选择,她只是由于“瓜”才成为美的创造者及其化身。
这个世界不缺聪明人,尤其不缺投机取巧的小聪明,世人嘲笑她的“瓜”,但是成就大事业的人,多少都需要这样的“瓜”。但是话剧《主角》并不满足于让忆秦娥在命运及同事的打击中自艾自怜,她仍是有力量的,因为有艺术为其底气,有无数爱美的人为她支撑。她想避世修行以求内心宁静,但是正如莲花潭的住持送她回到尘世时所说,“其实,世上每个人都是很可怜的。”只要超越所有不幸,就是修行,就有宁静。这样的宁静,是放下所有执念,包括对生活中遭受的所有打击释然待之。忆秦娥终究没有被各种不幸以及那些对她的诽谤和中伤压垮,反而由此生出对他人的同情与怜悯,一种无可比拟的大悲悯。
话剧《主角》的事件与细节均十分丰富,全赖舞台叙事行云流水,才在三个多小时里包容了如此丰富的内容。它充分体现了导演胡宗琪的独特功力,场面可大可小、可长可短,行所当行、止所不得不止,既活泼灵动,又一气呵成,节奏紧凑,画面有极强的冲击力,这是胡宗琪对当代话剧导演艺术的重大推进。导演紧紧抓住了“美的淬炼”这根主线,也正因为叙事紧凑,让剧情经常产生出强烈的压迫感,强化与凝聚了戏的内涵。他也大胆运用生动传神的西北方言,满台活色生香。秦腔音乐就像戏里的魂一样,不时在话剧段落中间的空场出现,既延绵了情感,又让舞台更显饱满。戏里偶的运用也恰到好处,在技术层面上,偶的运用首先是为了解决儿童角色的演员不易安排的难题,但又不止于此,导演让偶本身也成为舞台空间的假定性处理的有机元素。
在表演上,主演刘李优优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忆秦娥这个难度极高的角色的扮演。女主人公是因其突出的表演才华而遭遇她所有的幸运和不幸,假如舞台上的忆秦娥体现不出演技的精湛,故事就很难令观众信服。虽然从未接受系统的戏曲表演训练,刘李优优接受了这个角色后,经历半年多像当年忆秦娥那样艰苦的技术训练,终于完成了将忆秦娥立在话剧舞台上这个初看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此外,单团长、秦八娃、刘红兵的扮演者都有亮点,体现了陕西人艺的群体水平,而这样的实力,依然是淬炼的结晶。
戏剧的意义和欣赏戏剧的意义,只能限于观众在戏剧作品中所能感知的范围之内。很多年前,电影《霸王别姬》用“不疯魔,不成活”为人们展示了戏曲演员潜心向内的修炼;今天,话剧《主角》让观众进一步体会了戏曲舞台上的主角“不屈辱,不成活”的赤身向外的痛楚。而归根结底,无论是忆秦娥,还是芸芸众生,最终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终极问题,就是需要经历与承受如此磨难的戏曲人生,其意义究竟何在,这样的千古之问终究无法回避。我不是说话剧《主角》就已经解决了这样的疑难,观众也不会期望看了一部话剧就完全读懂了人生。毕竟,楚嘉禾这类人永远只能活在挫败中,造谣和作恶并不能让她与人生和解,但忆秦娥却有可能做到。因而,《主角》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人生启迪——忆秦娥是不幸的,但她又是幸运的,正如剧中所说:有人就是唱戏的命,好在你把戏唱成了,还有千千万万的人,走上了这条不归路最终还是唱不成。
既然如此,夫复何求?人生哪有圆满,好好走过一生,为世界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