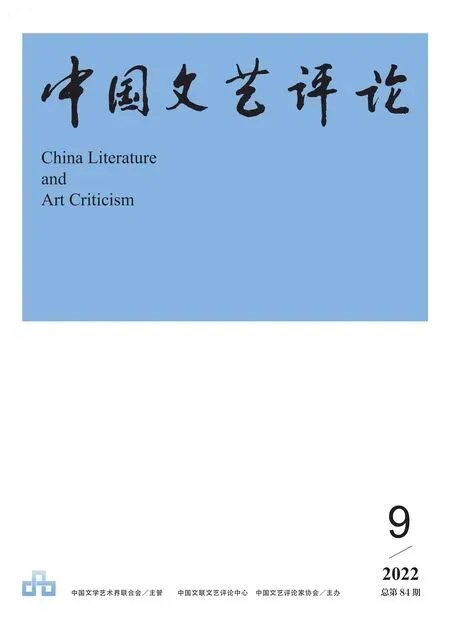民族文艺评论的时代精神与责任担当
■ 金永兵
“民族文艺评论”这一话语范畴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对“民族”作狭义的理解,这种理解对应着英语中“ethnic group”这一范畴,即一个特定范围内出现的种族、氏族的社群。在我国的语境中,这种意义上的民族文艺评论其实更多地是指在评论中发现文化特色、发掘文化遗产的“少数民族文艺评论”;另一种是对“民族”作广义的理解,这种理解对应着英语中“nation”这一范畴,即有共同生活区域、共同文化特征、共同历史传统等的民族共同体,它内部可能包含着多个具体的民族,但是因以上的共同特征而凝聚在一起。在我国的语境中,这种意义上的民族文艺评论主要指“中华民族文艺评论”。
本文在使用“民族文艺评论”这一范畴时兼指二者。因为两种民族文艺评论形态都是不可或缺的,“少数民族文艺评论”主要观照的是“特性”维度,而“中华民族文艺评论”则主要观照的是“共性”维度。不过这里的共性不是绝对的,从世界文艺评论的语境中来看,它同样是一种特性,抽空了具体的特性维度,那么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特质就无从谈起;反之,不谈共性维度,那么就无法在更深层次上理解各民族文艺价值追求的最终指向。二者均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上来说,就是要在民族文艺评论中保留民族特性,同时凸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共同奋斗的价值共性。
民族文艺评论既要遵循文艺评论的一般规律,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发挥好文艺评论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作用;又要看到民族文艺评论在对象方法和功能意义等方面的特殊性与特殊要求,以优秀的文艺评论工作,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民族地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实现民族文艺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方向,发挥好民族文艺评论的思想引领作用
这一从阐发到凝固再到升华的过程具体来说应有两个最基本的着力点。首先是确认自我身份并建构共同的民族文化身份,形成精神文化共同体。民族文艺评论在形塑、发现文艺中“志同道合”的共同价值追求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一部文艺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的客体,面向所有读者只提供一种同样的观点。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不同的演奏中不断获得新的反响与阐释,从而实现价值增殖与变异,成为一种不断变化的新的存在。进一步来讲,民族文艺不只是“一时”的文艺,如盛唐之音、“五四”新文艺、抗战文艺、改革文艺等;也不只是“一地”的文艺,如壮族文艺、藏族文艺等。若想让文艺从“一时一地”中升华出来,形成一种在历史和现实中源远流长的价值追求,必须依靠共同的价值锚点。缺少共同的价值锚点,同一民族的文艺可能逐渐分化,如西方文艺大多源于古希腊,但是却因具体价值追求的变化形成了英国、法国等各国的多种民族文艺形态;与之不同的是,共同的文化价值追求则让中国56个民族的文艺穿越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和几乎与欧洲面积相当的广阔地域仍然拧成一股价值合力。因此,民族文艺评论要展开新时代自我身份的确认、自我与他者及社会关系的确认、新的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帮助读者建立起自我认同和身份归属感。“我是谁?”“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新时代民族文艺要成为这一“社会整合力”,发挥好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理论和文艺治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根本优势与积极作用。
这里可以看出,“民族”不只是血缘地缘概念、历史文化概念,更是一个审美共情概念,民族文艺评论是任何民族理论都离不开的话语资源。血缘地缘、历史文化都无法解释感性体验上的一致,也无法解释对于未来的共同的理解和想象,更无法彰显在奋斗实践中产生的共同精神力量。因此,审美共同体建设是民族文化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层面。文艺的一个重要的探索层面便是思考自我的主体性问题,无论是古典文艺通过人的外在行动来思考人的存在、自我的存在,还是现代文艺通过探测自我隐秘的内心世界来寻求自我认知的可能,文艺、审美都在为自我寻找定位与皈依。民族文艺评论在面对民族文艺作品和文艺现象时,应充分彰显与揭示其内在的中华审美共同体、中华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与价值内涵,并在个体自我意识与社会群体共同意识建设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准,深挖民族传统文艺的新时代内涵
只有充分意识到民族文艺传承和发展工作的复杂性,民族文艺评论才更能如手术刀般地切中要害。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书写为例,贾平凹的《废都》、莫言的《生死疲劳》等作品立足于民族民间文化土壤,深挖文化积累层上的民族现代心理,用魔幻神奇的表现手法观照现实世界,取得了对人类生命的新颖理解。正是通过“魔幻现实”这一新颖的创作形式,这些作品实现了民间小叙事与历史大叙事、历史传说与当代现实间的张力互动。但是作为文艺评论工作者,我们既要看到魔幻现实主义对加强中国当代小说与传统文化联系的意义,更要看到作家们在接受和转化魔幻现实主义的过程中隐蔽的问题。例如贾平凹的“牛的絮语”、莫言的“灵魂转世”在价值指向上实际上是要让价值的形式以“魔幻”的方式疏离现实,进而以荒诞、模糊、戏谑等方式解构稳定的现实价值。这在特定的语境下是一种反思和批判性力量,但是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民族文艺评论必须有能力让这种价值解构重新变成价值建构。
落后思想往往以新形式为面具出现,通过形式维度隐蔽自身,很少有落后思想“明目张胆”地以纯粹内容的形式出现。如果说社会学、政治学、哲学都有能力直接从内容上批判民族文艺内容中的糟粕,那么民族文艺评论则尤其要关注民族文艺的形式,特别要警惕“新瓶装旧酒”“穿新鞋走老路”的民族文艺形态。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是民族文艺评论工作者必须重视的,不能以旧形式为由将传统优秀文化拒之门外,更不能让新形式成为落后思想的“通行证”。我们一方面要在传承上大力弘扬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真善美,警惕依附在传统文化身上的假恶丑;另一方面要在创新上发扬新形式的建设和批判力量,警惕寄生于新形式中的旧思想,让文艺评论在内容和形式两个维度上具有批判精神。有些文艺作品即使文笔十分优美,手法十分新颖独到,但如果传播的价值观落后陈旧,这样的作品就绝对称不上好作品。特别是在商业文化逐渐进入民族文艺语境的现阶段,更要看到商业文化一方面可以促进民族文艺的传播与发展,如仓央嘉措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就是借由商业文化进入了广大读者的视野,很多民族题材的影视作品如《都是一家人》《血色湘西》、新形态的民族歌舞如《千手观音》《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等更是借此有了更广阔的展示舞台。特别是像《火红的萨日朗》这样的作品,创作者本人并没有去过草原,他作为一个该民族语境外的作者也把握了其精神内涵,进入了该民族的创作领域,正如沈从文的“湘西”一样,“草原”也逐渐成为很多文艺创作者的精神家园。这些文艺现象都表明商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少数民族文艺因传播闭塞而导致的发展瓶颈。但是另一方面,商业形式也可以让宗教迷信思想、封建等级观念借由各种商业展演传播开来,同时商业文化也会让丰富多彩的民族文艺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趋同,以整齐划一的姿态“千人一面”地追求更广的受众和更大的经济利益。因此,民族文艺评论不仅需要透视文艺作品的美学与艺术特征,更需要历史地辨识存在于作品的美学和艺术特征中的精神实质;既要勇于肯定这些文艺作品表现出的积极的正能量,又要立场鲜明地批判存在于它们身上的某些与时代和民族文艺的健康发展格格不入的落后的元素,发挥好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和审美启迪的作用。
三、以中华美学精神为引导,“向民间文艺要资源”
民族地区一个鲜明的特征是其生活方式的艺术化、审美化,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活的方方面面无处不艺术,这是中华文化最深厚的根基与中华美学精神的活力源泉,并且很多方面已经形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艺资源值得民族文艺评论工作者高度重视,深入发掘其历史文化价值。
这些民间文艺是自然、自发的,化于日常而往往缺少艺术的集中与典型形态,需要民族文艺评论与文艺研究工作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深入人民,用专业的、艺术的慧眼去收集、整理、提炼、升华,这是一个艰苦的披沙拣金的过程。我国自古就有“向民间文艺要资源”的传统,《诗经》这部中国文艺的奠基之作就出自孔子对民间创作的整理、筛选。《诗经》中的“风”就是各地的民俗歌谣,“卫风”“齐风”等“十五国风”构成了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虽然并非孔子所作,但是因为这些作品都是按照特定价值、教化功能等为基础筛选的,所以它实际上是初步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文艺评论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如《乌苏里船歌》《祝酒歌》等作品都来自文艺工作者的民间采风和整理,而改革开放以后《爸爸爸》《马桥词典》等“寻根文学”更是让民间资源进入到民族文艺的话语场中。
但是民族文艺评论与文艺研究工作的重要责任不能止于发现,还要去升华再造,即通过发掘民间文艺资源,推动中华民族文艺的繁荣。换言之,民族文艺评论与文艺研究工作既要打通民族文艺评论的两个子形态,让狭义的民族文艺真正在价值上成为广义的中华民族文艺的一部分;又要进一步打通中华民族文艺和世界民族文艺之间的价值通路,着重发掘我国各民族文艺在人类文艺整体的语境下有何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两个意义上的民族文艺真正的世界价值。这些年,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已经高度重视发掘民族民间文艺资源,但是从更高的文化价值、美学精神层面的阐释提炼还远远不够,可以借助美学、艺术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来开辟新的空间,应该说大有可为。
以有关西藏地区的民间文艺评论为例。一般的藏族群众很少会在平日谈话时引用佛教经典、哲学妙语,他们的历史观、价值观、美学观往往就存在于由一个个神话传说、宗教故事、街谈巷议串在一起的一套表征与评价体系之中。因此,关注藏民族的民间文艺显得尤为重要。比起雅致的文学、音乐、舞蹈、雕塑等艺术,关注民族民间文艺或许更加接近生活的本真面目,评论的社会效益会更加显著。可以说,关注隐藏在服饰、饮食、装饰、建筑、民俗、收藏等日常生活中的生活美学,才能艺术地全面把握广大群众的真实精神世界,并从文艺领域深化关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民族地区的特殊性的认识。譬如藏戏,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在藏族群众中有广泛的受众。藏戏的内容大多是佛经中的神话故事,如何挖掘隐藏其中的中华美学精神,发挥故事中积极上进的内容,同时批判其中消极落后的一面,引领藏戏进行现代化方向的改革,更好地服务于当地人民群众的健康文化风俗建设,是藏戏评论的重要任务。谈论藏族民间文艺,大多时候绕不开宗教的影响,因此,做好藏民族民间文艺的评论和研究工作,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历史观出发,淡化宗教消极影响,显得尤为重要。民族文艺评论要发掘民族民间文艺中的中华民族精神和美学意蕴,使其能够成为团结民众、激励中华各族儿女奋勇前进的精神食粮。
一方面,只有充分发扬民族文艺评论的力量,才能让人民群众更好地认识本地区本民族的文艺传统和文艺资源。从一种辩证的意义上来讲,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不能在其自身内部完成,只有作为被思考、被观察的对象才能被反思、被认知。对于自发性的民族文艺创作而言更是如此,很多山歌、民谣都是口耳相传下来的,这就使得它们在接受的过程中逐渐变得机械而直接,人民群众吟诵它们、体悟它们,却往往不会去深刻领会和反思其内在的精神价值。正如常年居住在风景区的人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家乡风景如画,而对家乡之美的认知往往来自于外乡游客的讲述或当自己走出家乡后的新视角。民族文艺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走出自己的创作语境反观自身,而民族文艺评论正好可以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它为封闭的接受语境带入新质,在一种反思的意义上完成对民族文艺价值的领会、认知与确认。
另一方面,民族文艺评论必须在民间资源中扎牢根基,民族文艺评论对民间文艺资源的重视程度决定了民族文艺评论在人民群众中影响力的强弱。民族文艺评论“向民间文艺要资源”,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价值立场,即尊重与重视民间文艺在构建民族文艺工作中的作用,保护民间文艺的独特性,使之在更广阔的共性下彰显出更鲜亮的艺术光辉。尊重和保护是不能改变的价值立场,这要求我们必须拒绝一些雷同化的普遍主义的评论,因为这些评论实际上是要将民间资源当成“别的东西”来讲,这无疑是打着尊重和保护的旗号取消了民间资源的内在价值。同时还必须拒绝猎奇式的、口号式的评论,因为这些评论要么不加区别地使用民间资源,往往没有立场地一概肯定或否定,要么以一种居高临下式的姿态,把民间资源作为“景观”和“噱头”。
四、以形成文艺高峰为目标,发挥好民族文艺评论的经典建构功能
其一,要认真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艺评论对民族文艺经典建构的过程,反思民族文艺经典化的成绩和经验。改革开放之前,民族文艺评论在民族文艺经典化建构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显著的成绩就是对民间文艺的文人再创作,产生了一批影响至今的经典。例如《百鸟衣》本是壮族的民间传说,后来壮族作家韦其麟依此创作了叙事长诗《百鸟衣》。自叙事长诗《百鸟衣》发表开始,主流民族文艺评论界就迅速跟进,从某种程度上与创作者一起完成了其经典化的过程。新时期以来,商业文化基础上的市场评论、媒介舆论、资本力量等参与了文学经典的建构,主流民族文艺评论的影响被大幅度削弱。在很多民族文艺领域,主流文艺评论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换言之,就是没有把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切实承担起来,而是任由商业市场和民间舆论自发作为。
其四,要重视民族文艺评论与文艺理论的互动。民族性和普遍性不能被拆开来看,而是要让民族文艺的价值经由文艺评论进入理论之中得以凝固塑型,使民族文艺评论的价值指向能够从民族特性升华到全人类的意义上。事实上,很多理论上的前沿问题在我国都与民族文艺的话语资源有非常高的契合度。例如在西方,生态问题往往只能如《沙乡年鉴》那样选取特定地域的视角来切入,但是在我国,民族文艺往往同时伴随着各个民族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追求,这本身就是中国生态文艺理论的宝贵资源,从这一领域出发能够使我国在世界理论之林中占据不可取代的理论立足点。再如西方文艺中的种族理论往往是从边缘话语被压抑的角度去讨论解构主导价值,但是我国的民族文艺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它讲述的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下多种文艺话语共同繁荣的文化现实,民族文艺评论对这种关系的深挖非常有助于在西方的“种族理论”之外形成一种中国特色的“民族文艺理论”。同时,这种“接地气”的中国理论必将带来民族文艺创作中内容和形式方法上的深化与创新发展,把二者连接在一起的任务当仁不让地属于民族文艺评论这一重要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