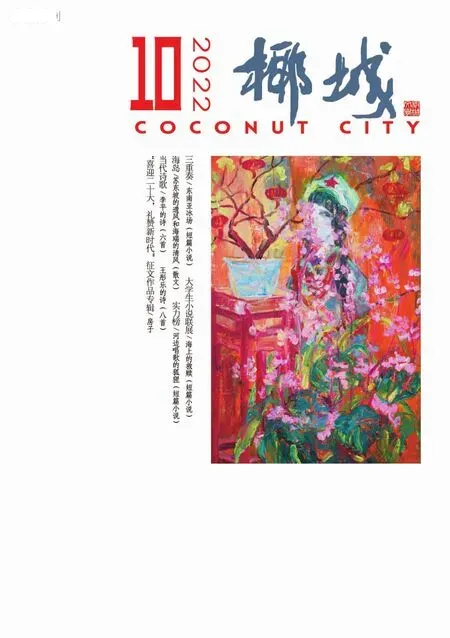房 子
◎毛奎忠
衣食住行,除了一日三餐和保暖遮羞以外,住房便是生活大事了。
过去,豫南农村皆是土坯茅草房,建房只能在秋后。收完稻子,留出一块湿漉漉的稻田,挨着泥土割去稻茬,用石磙碾压两三天,请三五人帮忙挖出一块块土坯。挖土坯是男人的活,五个人一天挖出的土坯够盖三间房使用。女人则将挖出来的新鲜土坯码齐了,在秋阳下晾晒。不用担心家里人手不够,左邻右舍会来帮忙的,女主人只需做一桌可口的饭菜即可。砍几棵树去皮做椽子,再砍一些竹子,整理出一些茅草便可以盖房了。所有用料都是就地取材,自家不够可以向邻居家借,来年还上即可。盖房子的时候更是热闹,请三四个茅匠(会盖土坯房的匠人)和一两个木工师傅,自家人和来帮忙的邻居跑腿打杂做小工,女主人忙活饭菜。上房梁的时候,一挂鞭炮炸响,喜糖撒得满天飞,茅匠师傅再唱上几句顺口溜,妇女孩子们皆疯跑过来抢喜糖、听唱曲儿,全村喜庆。两三天时间,三间新房建成,剩余材料在旁边再建一间厨房,便齐活了。房子里外用黄泥抹平,稍干,屋内糊满报纸,一栋新房全部完工,住进新房的喜悦心情和今天搬新家完全一样。
豫南多雨,茅草屋顶两年就要重盖一次。更可怕的是土坯墙经不起水。春秋季节阴雨连绵,如果下个十几天雨,天空像罩一口铁锅,心里像压一个秤砣,都是沉重的。有时,夜里睡得迷迷糊糊的被大人叫醒,屋里到处放着接水的盆子,叮叮当当的声音敲得心烦。好在每一家院子里都备有一个土堆,万一洪水上来挖开土堆包墙根,全村的大人都会干得热火朝天,孩子们心惊胆战。那时,不怕雨水的砖瓦房对于我们就是一个遥远的传说,遥远到想一想都奢侈,会被骂不切实际的傻子。
准确地说,我大哥是第一个在村里盖砖瓦房的人。虽然只有三间正屋(厨房还是土坯房),却像村东头爬上坡顶的一轮太阳,给全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大哥原是生产队长,土地联产承包以后,人们种自家的田地,生产队长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干脆辞职南下打工。大概两年时间,大哥便回乡盖起了三间砖瓦房。后来大哥说,三间房子花了四千块钱。我们听了咋舌,那是一笔天文数字。
毫无疑问,大哥是村里的富裕户。半年以后,大哥从城里买回一台14吋黑白电视机,无疑又是一个爆炸新闻,小村里有电视了。大哥为此砍秃了院子里一棵树,把一根毛竹用铁丝捆在树上,立起了高高的电视天线,比那三间红墙砖瓦房还高出很多,老远都能看见,招摇过“村”,毫不低调。人们纷纷私下里猜测,不知道我大哥手里到底有多少钱。无论怎么说,电视机对全村人的吸引力是不可小觑的。每天吃过晚饭,大哥便早早地把电视机从砖瓦房里抱出来,放在庭院里的小桌上,让别人盯着电视屏幕,自己反复转动天线调出最佳信号。大哥家的院子里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当时正热播琼瑶的电视连续剧《烟雨蒙蒙》,看得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泪眼蒙胧,唏嘘不已。偶尔碰到下雨天,电视机不能放在院子里,大哥的三间正屋便早早挤满人,来晚的人就在房檐下或站或坐,听声音也可。电视剧揪人心呢,看完一集还相互讨论一番。末了总是说,这看电视咋还上瘾呢?然后暗暗发誓,看完这个电视剧坚决不看了。临了,又总想看看下一个电视剧演什么?再一看,又上瘾了。
村里的第一栋楼房不是我大哥家的,是他的隔墙邻居。邻居家的儿子在外地当兵,三年后复员回到村里。那时我大哥家已经盖了红色砖瓦房,比他家的茅草屋高出一个屋顶,两家房子并排,一高一矮一红一灰极不协调,更映衬我大哥家的房子鹤立鸡群。刚复员那阵子,邻居家的儿子很少在村里露面,也很少下地干活,更不去我大哥家看电视,偶尔见到村里人只点头打个招呼。人们的注意力可能都集中在我大哥家的电视上,没有谁注意他什么时候从村里消失了。后来有人想起问他父母,说是打工去了。很正常,没有更多人在意,就像他当兵没有回来。记不清过了两年还是三年后的一天上午,村外一起开来好几辆拖拉机,车挂斗里装满了砖头,为首一辆拖拉机带驾驶室,那个小伙子坐在副驾上。至此,他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里,而且风风光光。接下来的几天里,整个村子喧闹不止,好几辆拖拉机“突突”地冒着黑烟来回穿梭,村口的一片空地上堆满红砖、沙子、水泥,像小山。看材料,三四间房是用不完的。让人没想到的是最后还拉来一堆楼板,人们方才醒悟,这小伙子有大动作。
小楼落成。两层,比我大哥家的砖瓦房高出一大截。紧接着,一台25吋彩色电视机也搬进小楼,就放在一楼的客厅里,晚饭后也抱出来放在院子饭桌上,虽然都需要转动天线,带色的自然是好看得多。至此,大哥家的电视观众大批量流失,后来简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
这是若干年以前的事了。
如今,村里家家户户早已住上楼房,二层三层不等,大多数人家都是从土坯房直接到楼房。当年的茅草屋已经难觅踪影。如果和现在的孩子们说起过去的茅草屋,就像谈论不可触摸的历史。
不过,大哥仍然为房子发愁。
我们家兄弟姐妹多,年龄差距比较大。细算起来,大哥已年过七十,因为是家里老大,吃苦最多,一生奔波实属不易,虽然身体还算硬朗,毕竟岁数不饶人,真不知此生还能做多少年的兄弟,想起便心里发酸。去年“十一”假期,我带着老婆回老家看望大哥大嫂。
大哥有两儿一女,均在外地打工或经商,其中二儿子已落户天津,多次想接老两口过去,大哥一直不愿意离开,坚守在当年为大儿子建造的三层小楼里。见我们回来,大哥大嫂非常高兴,谈话之间又聊到房子的事。说起当年建造这三层楼房多么不容易,举全家之力,没白天没黑夜地干。如今孩子们都不回来住,若大的房子空荡荡的,即便过年能热闹几天,孙男娣女们也很难聚齐,笑声也填不满这三层小楼。大哥为此心酸不已。
大哥带我在村里转转,偶尔看见三两个人和我们打招呼,那是需要剥离岁月风霜才能找到熟悉的面孔和笑容。大哥摇头说:“这么大的村子,这么多的楼房,只有我们这几个倔强的老家伙守着。”的确,绝大多数楼房都是门上加锁,有些门锁已经生锈,红砖墙皮长满青苔,门口长了一些蒿草,一看就是长期没人居住。大哥叹息说:“可惜呀!”他也许又想起了当年家家户户风风火火建楼房的场景。
回到家里,大嫂已经做好饭,吃饭过程中,大嫂说:“村里能干活的人都外出务工了,年轻的孩子考上大学,毕业以后在大城市工作了,无论租房还是买房,在外地都有了安身的地方,常年不回来。他们有些家庭把老人也接到城里了。”
由此,我想起自己当年考上大学,全村人兴奋,鸡窝里终于飞出了一只金凤凰,后来成为家长教育孩子的榜样。如今,过去的“鸡窝”早已成为“凤凰窝”,一只只“金凤凰”从这里飞出去,飞到城里,飞到天南海北。不再像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过活,他们是为自己找到施展的舞台,为社会做着更大的贡献。
停顿一会儿,大嫂接着说:“你大哥就是倔脾气,不愿意走,还想守着这三层小楼。”
大哥喝完一杯酒,把酒杯往桌上一顿,说:“你懂个啥?当年建这楼房容易吗?累死累活的。现在房子还好好的,就这样扔掉不住了,可惜啊!我们住在这儿,孩子们的家就在这里。”
“你听听,你听听。”大嫂生气地对我说:“你知道的,你二侄儿全家户口多年前就迁到天津了,你大侄儿一家的户口虽然还在这里,但你大侄孙子早已经在县城买房了。年初,你大侄儿又在县城又买了一套房,他们全家也不会再住这里了,回来最多也就是吃一顿饭又走了,看这房子还能守到什么时候?”大嫂说得不无道理,毕竟老两口年龄越来越大,身边需要有人照顾,儿女们也都有自己的孩子和生活,房子不在一起,就不可能随时照应。
正说着,大侄儿打来电话:“爸,我在县城新买的那套房子已经装修好了,说个时间,我回去把您和妈接过来看看。”大侄儿听说我回来了,让我接电话,说:“叔,没想到您回来了,临走之前一定到我这儿看看。条件比不上您们大城市,但房子面积肯定不比您家的小。”听完这话,我不知道如何应答,只有连声说道:“好,好。”
大侄儿又说:“叔,您劝劝我爸,让他和我妈也搬到城里来,我这儿的房子大,和我们一起住,也方便照应。”
我说:“你爸恋旧。”
“是的,”大侄儿说:“老家正进行新农村规划,老房子会拆迁的。我真想不通我爸,现在的生活条件这么好,只要有钱,好房子多的是,怎么就舍不得那栋小楼,真是有福不知道享。”
我听了心里非常高兴,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建设的步伐日益加快,这栋老房子拆迁是早晚的事,大哥大嫂将不会再独守这栋三层小楼了。不过,我也能理解大哥的心情。这三层小楼,当年凝聚了大哥全家的心血,是大哥大嫂和侄儿们辛辛苦苦建起来的,也是大哥大嫂当年的骄傲。如今,房子还好好的,孩子们却像迁徙的鸟儿,不想再回到旧窝。与其说大哥思想守旧,不如说大哥一辈子争强好胜。如今的年轻人生活条件和成就肯定是他当年不可比拟的,虽然老了,却心有不甘。大哥不是不知道享福,是这栋小楼里装满了大哥的记忆,那是他的人生经历和奋斗史,新生活的变化让他想一遍一遍解读自己过去的艰辛。儿女们的成就和生活,同样是他今天的幸福和骄傲,他想用这栋小楼来映照新的生活,从中获取时代变迁带来的美好,咀嚼其中幸福的味道。
假期快结束了,我也该返回自己的城市。临走的时候,大哥大嫂把我们送到路口。车子开出很远,从后视镜里看见大哥大嫂还站在原地,身后那栋三层小楼是他们的背景画。
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和愉悦,仿佛看见了美好的未来,大哥大嫂正被幸福的生活包围着。
车轮滚滚向前驶去,前面的阳光大道迎面而来,身后那栋镌刻着历史印记的老房子越退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