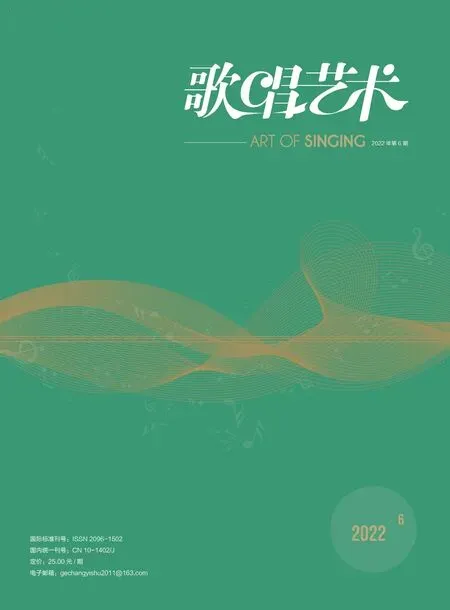激情奔涌唱千歌万曲铸中外名段范本内敛低调倾一腔热血育乐坛教坛精英(下)
—— 弟子忆恩师黎信昌教授
马金泉执笔、整理
胡英华
男中音,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记忆中的黎先生,是一位博学睿智、言语精辟的声乐大师。1991年,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干修班的结业成绩是89分。知道成绩后,我心理不平衡,找到先生问:“能不能再加几分,也算弄个90分以上结业回去?”先生说:“我觉得你现在,离优秀还差一分。”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应该说是给我指明了继续努力的方向。
第一次遇见黎先生时,我还是刚刚留校任教的一个普通教师。1990年秋天,命运让我有机会见到先生并且上了永生难忘的一节课。当时,先生应邀为哈尔滨市歌剧院的歌唱演员们上课,并不是歌剧院歌唱演员的我,通过兄嫂的引荐,也坐在了他们当中,且有幸“蹭”了一节声乐课。前面的人一个一个地唱完,很快就轮到了我。我笔直地站在先生面前,“潇洒”地唱了一首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婚礼》中的咏叹调《你再不要去做情郎》。先生听后,没有给予我任何肯定。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心里多少有点不舒服,心想“俺也是有一定实力的”,不满之意顿时“写”在了脸上。先生依然没说什么,露出浅浅的笑容,不慌不忙地跟我说怎样去调整共鸣位置,开始给我做发声练习。随着位置的调整,我自己明显感觉到了声音的变化。心想,这不就是我一直向往的“音色统一并有较高位置”的声音吗?先生点到之处,简直就是神来之笔,真可谓是一语点醒梦中人!我按照先生的方法继续唱下去,台下掌声不断。这时,先生给了我一些鼓励的眼神。课后,先生又拉着我聊了一会儿,为的是进一步了解我的歌唱经历,最后他亲切地对我说:“你应该出去再学习学习!”天呐!这是给了当时的我方向的指点,姑且也看成对我的认可吧。不过,这也是我跟随先生的学习生涯中受过的唯一一次表扬。对于艺术,先生是严谨而不讲情面的。
先生离开哈尔滨后,我闷头想:先生只是给了我小小的点拨,就能让我进步很多,如果能正式拜在先生门下,我的歌唱一定会有更大的提升。带着这样的想法,刚刚参加工作的我,壮着胆子找到了学院当时的院长汪立三先生,向他提出自己想要去中央音乐学院跟黎先生进修的请求。可能是中央音乐学院和黎先生的知名度,再加上我的诚心实意,汪院长破例同意了我的请求,说“只要你能考得上,我支持你”。没想到这一考,我就成功地拜在了黎先生的门下,正式开始了在中国最高音乐学府的进修学习。

上声乐课之前,每一个进修生都需要先与钢琴伴奏合好要唱的作品。作为当时中央音乐学院声歌系主任的黎先生,给我安排好了钢琴伴奏老师,但我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认识到钢琴伴奏的重要性。在与钢琴伴奏老师合作时,过于自由地加入了自己的想法,还有一些不好的习惯,结果在语言、节奏、强弱、气口、艺术处理等方面都表现不佳。虽然钢琴伴奏老师进行了耐心的纠正、指导,我却满不在乎。两天后的声乐课,钢琴伴奏老师和我一起来到课堂,在课上,黎先生给我指出的问题,跟钢琴伴奏老师说的是一模一样。特别巧合的是,这位钢琴伴奏老师的先生也是搞声乐的,并且是中央歌剧院的职业歌剧演员,跟我同声部(男中音)。所以,我所要唱的作品,钢琴伴奏老师几乎是了如指掌,这时的我才明白黎先生的用意。先生的治学风格真是大家风范,既有宏观的广度,又有微观的细腻。可以说,对于每一个学生的学习安排,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黎先生兢兢业业,循循善诱,真是让我如沐春风,永生铭记。
时光飞逝,记得干修班结业前的一节声乐课,当最后一句唱完,黎先生跟我说:“嗯,还不错,有点意思了。算是‘王八排队,大盖齐’(大概其)吧!”这算是在结业前对我的一次中肯评价。虽然在演唱上仍有不少提升空间,但我跟先生的关系却亲密无间,用东北话说,我俩关系“贼老好”了!
1998年,我参加“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进入复赛以后,抽签抽到了最后一号,便怀着紧张的心情给黎先生打了电话。先生马上跟我说:“挺好啊!不用紧张,最好的都是最后一个出场。”有戏剧色彩的是,进入决赛我抽到的是一号,开场第一个。这次先生对我说:“早些唱完就不紧张了嘛。”先生就是先生,他老人家总是有办法调整学生的状态。正是先生泰然处之的气度,给了我一个平稳又积极的参赛状态。
黎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严师慈父般的人。无论是在江水碧绿的哈尔滨之夏还是在万里雪飘的哈尔滨之冬,我总在等待着黎先生再到我的家乡讲学、做客,哪怕是来了再批评批评我歌唱上的毛病,可您已经离开了我们……
先生,我会记住您的每一句话,您的精神值得我用一生去追随。
曹琳
女高音,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
一场秋雨一场寒,处暑之后的江南显然平添了几缕凉意。夜雨使我回想起第一次在黎先生面前演唱诗词歌曲《思乡》的情景——那是2004年春天,我被南京艺术学院委托培养至中央音乐学院,进入黎信昌先生门下。张佳林教授弹奏的钢琴如雨滴般婉转倾诉,我不禁情动,一曲唱毕,老师沉默半刻说:“不错,很自然,确实有思乡的忧愁。中国歌曲要说着唱,真情实感地去表达”。彼时年少,唱惯外国歌曲的我并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先生要求如此处理?多年后,读朱熹“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才恍然大悟,这是黎先生践行中体西用的经验总结,蕴含中国艺术美学的大智慧。“说着唱,真情实感地去表达”,这句话我始终记着,且贯穿在声乐教学中,这是恩师留给我受用一生的财富。
黎先生爱自己的学生,记忆中他说话总是和风细雨,师母也对我很关怀。江南女孩初到燕京,饮食很不习惯,加上课程紧张,第一学期我就瘦了近十斤。先生知道后,便经常喊我去他家喝广东老火汤,至今每每喝到老火汤,总能想起当年的幸福时光。
毕业我要回金陵,恩师很不舍,于是他请张佳林教授领着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录音棚录制了我的第一张中外作品录音室专辑。恩师叮嘱我:“一是要继续唱,多出作品;二是要继续提高技艺,潜心治学,耐得住寂寞;三是始终要保持独立思考,记得自己是大学专业教师,对世界要保持客观态度。”恩师的期望激励着我不敢懈怠,此后数年,我坚持学习和实践,寒暑假都在国外学习演出,各大剧院和电视台都留下了我的歌声。
2015年,我在“英国爱丁堡国际戏剧节”主演了中国歌剧《秋子》,《中英时报》做了专访。回国后,我把现场视频发给恩师看,恩师很高兴,他说:“声音你这样唱是合适的,唱歌剧对表演要求很高,你演得不错嘛”。至此,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对演唱中国歌剧有了自信。
2019年,我携爱人一起回北京看恩师,霍勇、文刚师兄和我们一道。恩师那天非常开心,席间他想听我唱《威尼斯狂欢节》,唱毕恩师说仿佛又回到当年的美好时光。于是,我又清唱《红梅赞》,恩师很认真地说:“带戏曲风格的行腔这样处理是合适的”。得到了肯定,我信心大增,同年在交响独唱音乐会上演唱了歌剧《江姐》选段。
如今,恩师携师母驾鹤西去,他传授我的专业知识和人生哲学深深影响着我。“商量旧学、培养新知”,如何唱好中国歌曲是恩师留给我的知识财富,如何把中国歌曲、音乐文化介绍给世界?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黎先生对学生们的期待。
男低音,旅欧自由职业歌剧演员
晓良好!大家都知道你现在是活跃在世界各大歌剧院和音乐节的舞台上备受赞誉的男低音歌唱家。曾在“慕尼黑ARD国际音乐大赛”“德国新声音国际声乐比赛”“日本静冈国际歌剧比赛”等重大国际声乐赛事中获奖。记得你当年身为德国汉诺威国家歌剧院和斯图加特国家歌剧院的成员时,几乎演唱了所有歌剧中的男低音角色,2016年被授予斯图加特国家歌剧院“功勋歌唱家”称号,2018年还获得“莫斯科国际专业艺术成就‘Bravo’奖”。应该说,你是黎先生的弟子中在国际声乐舞台上卓有成就的一位。
谢谢师兄!在我的音乐道路上一共有三位老师:启蒙老师是我的父亲;本科前期接受天津音乐学院韩宝林教授的指导;1992年,到中央音乐学院委培,师从黎信昌先生。如果说韩教授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黎先生就是一位带我走向国际舞台、走向职业歌剧演员的导师。我和黎先生的师生情缘,已有29年。
本科毕业后,到底是工作,还是去美国或其他国家留学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虽然那时也有些演出,但机会不是太多。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一天突然接到黎先生的电话,他问我这段时间情况如何,然后说有一个“文化部”主办的选拔赛,希望我能参加。当时我感觉自己是有些没有头绪的忙碌,处在一个不是非常好的状态,心里有点不是很确定自己是否要参加。就在我犹豫的时候,先生说,不管现在状况如何,都希望你一定要参加这个比赛。这是1996年的事情。
这可是一次很好机会啊!
是的。今天看来,先生的这个电话在我的音乐道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后来我决定,不管结果如何,我要在先生的指导下准备这个选拔赛。从那天起,我经常泡在他的课室里,我成了他上完一天课后的另一个学生。我不仅仅是在课室上课,有时候还被先生叫到家里上课,即所谓“开小灶”。先生认真、细致地为我挑选作品、处理作品。经过激烈的选拔,最终文化部决定派我去参加1996年“慕尼黑ARD国际音乐大赛”,这是一项非常有历史的赛事,创办于1952年。这个比赛要求的曲目量非常之大:咏叹调15首咏叹调、艺术歌曲5首,共比赛4轮,每轮要唱最少4首作品。我总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一直跟先生准备这些曲目。其间,我觉得吸收了非常非常多的营养。回首往事,那真是非常有意义的经历。
这种国外的比赛,一般不需要唱中国作品是吧?
师兄,真让你说着了。在准备过程中,一次我跟先生在琴房里商量曲目。他说,晓良,我们唱一首中国的咏叹调吧,杨白劳的咏叹调比较适合你。我忽然有一种感觉,先生是要把我们中国的音乐传播出去,让中国的作品唱响国际舞台。谁承想,这首杨白劳的咏叹调在比赛中反响很大,因为很多外国的评委和音乐家都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中国作品。很多人问我这首咏叹调讲的是什么故事,他们真的非常感兴趣。今天想来,当年先生为了中国声乐艺术的荣誉真是费尽了苦心。
我记得过去跟先生上课,课室总是满满当当的,除了本师门的学生之外,外边来听课的人也很多。
当时,我已经不是学校的学生,老师依然在上完一天课之后帮我处理作品,他真的非常辛苦。正如师兄说的那样,老师的课室里总是有很多的人在旁听,有时到了吃饭时间,课室里依然人多到爆棚。有些事情,时间久了才明白先生的用意。很多学生从外地来就是渴求知识,他们就是想听先生的课;但换个角度看,对于我们来讲,上课时在你面前有“观众”,这无形中也是一个极好的锻炼。这种心理上的锻炼,对我们以后参加赛事、走职业道路都会有很大的益处。
这么多年,去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剧院演出,有些同行就问我是在哪里学的、跟谁学的,我总会非常自豪地说:我是在中国学的,老师是中国人。现在的很多学生选择前往欧美留学,实际上国内就有很多很好的教授,他们的水准也是相当高的。其实,国外也有教授对教学不上心的,如果他们没办法给你很多东西,你也就没办法学到很多东西。
1997年“德国新声音国际声乐比赛”,黎先生是中国参赛队的领队吧?
是的,那次是文化部聘请黎先生带着三位中国选手一起到德国,因为先生早年在德国的“舒曼声乐比赛”中获过奖。他是很早参加国际声乐比赛并获奖的中国歌唱家。他对德国艺术歌曲的研究非常深,包括元音和辅音的关系,以及辅音在德语演唱和说话时有什么区别,怎样做到演唱既有清晰度又不会费嗓子。他还特别强调,在整个句子中,辅音不要破坏句子的连贯性。到了德国比赛,我们和先生经常是一整天都在一起,那真是实打实地言传身教。先生还知晓德国剧院的一些状况,德国文化、生活习惯等。
作为黎先生的弟子,咱们还有一个幸福之处,那就是先生可以唱。当你不明白怎么唱的时候,他立马示范,现身说法。
太对了!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参加国际比赛有师长陪同,那完全是另外一个状态。练唱、合伴奏,先生都在。记得我唱的是《唐卡洛》中菲利普国王的咏叹调,人物的声音、音乐、语言、身份、形体语言等,先生为我讲了很多,这些对我之后的职业道路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先生的声音状态是非常自然、稳健且有说服力的,他绝不属于那种只讲不唱的声乐教授。
那次到德国,你们跟先生还去了哪里?
我们一起去了波恩的中国大使馆。那年正值香港回归,我们在大使馆看了电视直播。到了贝多芬故居,先生讲了很多关于贝多芬的故事。那段时间,对我了解德国、以后在德国发展,先生给了我很多指点和建议。
你走上职业歌剧演员的道路后,一直跟先生保持联系吧?
是的。我们经常会通电话,有时会商量一些角色的事情,包括我是否要唱一些瓦格纳的角色,什么时候唱、大概什么年龄段唱等。每次到北京,我都要跟先生见面,他最喜欢听我说在国外演出的情况。我演出的一些录像、录音,他都特别有兴趣。我总想,如果欧洲到国内不是这么远,我一定接他去看我的演出。当时在北京跟多明戈大师同台演出《纳布科》,我请了先生出席,那天晚上他特别特别开心!在观众席里,很多音乐界的人都祝贺他,很多人过来跟他合影。这就是一位教师看到自己的学生在舞台上有了长足进步,自豪的状态。只要听我的演唱,他都会跟我讲还要注意哪些。后来,我在国家大剧院演唱威尔第《安魂曲》,先生也来了,那天他很激动。
你现在的演出合同很多,很是忙碌。你现在属于哪个剧院?
从斯图加特歌剧院出来后,我现在属于自由职业歌剧演员,在世界各地演出。在欧洲,如果专属一个歌剧院,就只能在这一个歌剧院演出。只有这个剧院的时间空档了,才可以去别的地方演唱。像我现在这样,必须有足够量的歌剧院邀请,才敢选择成为“自由职业歌剧演员”。在欧洲,作为一位自由职业歌唱家,你必须有些名气(这些名气不能是吹出来的,必须是业界和观众的高度认可)才可以,否则会很难生存。
在你的欧洲歌剧舞台职业生涯中,黎先生对你的影响还会有所显现吧?
我觉得对我重大的影响之一就是先生对音乐的严谨。他那种非常干净、非常自然的艺术追求,都体现在了他的发声方法、他对音乐的理解和诠释中。抛弃一切无关紧要的世俗想法,不为虚荣而演唱,不做哗众取宠的表演……都是从先生那里学到的。
我知道,由于国外“疫情”和工作安排,你没能赶到北京参加先生的追悼会,有些遗憾吧……
我跟黎先生如同父子,是家人的感觉,真的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到现在为止,先生离去这件事情,我都难以接受,想起就心痛。大家与先生辞别那天,我在德国面朝北京的方向默哀良久,泪水如泉。我深深地祈盼先生的歌声与精神长存,祈祷先生能在天堂一切无恙!(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