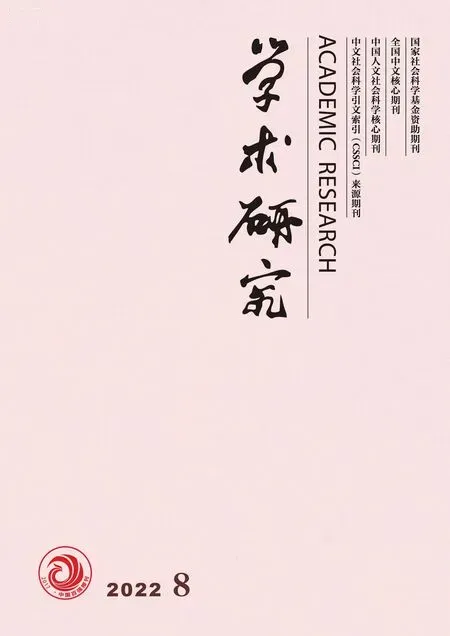汤斌两次入仕辞官考论*
赵秀红
汤斌(1627—1687)是清初顺康年间名臣,著名理学家。他道德纯粹,为政清廉,文章清雅,在哲学、事功等方面都有颇高成就。以汤斌在清初的政治史、理学史地位而言,目前学界的研究难以与其相称;即使对汤斌出仕清廷与其道德人品等基本问题也长期聚讼纷纭,莫衷一是。①有关汤斌的评价有褒贬两种争论。褒者称其为有清一代廉吏、名臣,清代李光地称他为康熙朝“第一流”人物,参见[清]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678页;方苞称其名臣第一,参见[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81页。当代研究成果主要有史革新:《“廉吏”汤斌的理学思想略议》,《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邓学青:《清初名臣汤斌的为官之鉴》,《领导科学》2018年6月(上)。贬者斥其虚伪,为清廷的驯静奴隶,以镇压起义军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都曾从晚清民国政治和文化革新的时代要求出发贬斥汤斌。现代一些文化学者对汤斌评价则往往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如认为汤斌学问低劣,专擅揣摩圣心进行欺骗,参见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198-199页;汤斌是装孙子的宝贝,参见张鸣:《五光十色说历史》,北京:线装书局,2012年,第21页,等等。究其实,这些研究也只是承接了章太炎、梁启超诸公在晚清民国特定时代中对汤斌的看法,并未从学理上推进汤斌的研究。那么,汤斌入仕清廷究竟是否称得上大节有亏?他是否热衷功名利禄一味揣摩圣意,为保乌纱不择手段?若果如此,汤斌为何又能被后世奉为名臣典范而入祀文庙?康熙的评价能否代表士林认同?前贤对这些问题众说纷纭。本文拟就汤斌的仕宦生涯及其立身品性进行专门探讨,同时通过汤斌这一个案窥探清初政治、理学、文化转变背景下汉族士人的生存状态及心路历程。
一、汤斌首次入仕清廷考论
有关汤斌争论的焦点之一是他入仕清廷大节有亏。持此论者往往并未具体考察汤斌首次入仕情况。倘知人论世考察,汤斌大节有亏之论实不能成立。
汤斌生于睢州一个以军功起家的世族门庭,其母赵氏深明礼义,课子甚严。祖先荣光的激励和严格家教让汤斌从小立下追继先贤之愿:“自念世为阀阅旧族,恐贻弓冶羞,遂笃志圣贤之学。”②[清]王廷灿:《年谱初本》,汤斌著,段自成、沈红芳编校:《汤子遗书》卷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8页。
崇祯十五年(1642)汤斌14岁时,李自成军破睢州,其母被害,甚为惨烈:“孺人召集家人,从容慷慨,自以累世高门,今日义无全理,且以姑老不得终事为恨。解衣带自缢,不绝,再投于井,眢井也,家人缒而出之。贼寻至,环以白刃,孺人大骂,贼刃交于胸,噀血不挠。及旬而敛,尸僵如生。”①[清]吴伟业著,李学颖校:《吴梅村全集》(下)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68页。汤斌一度悲痛欲绝,竟至6日水米未进。崇祯十七年,汤斌伯父病死浙江衢州,留下年仅10岁的堂妹。汤斌随父赴衢欲接幼妹回乡,适逢李自成攻破北京,天下板荡,一家人乱离中备尝艰险。直至成年后汤斌对这段经历仍心有余悸:
至壬午,寇陷睢城,家园遂为战场。府君冒险,躬舆大母过河朔,往来曹卫、大名之间。颠沛流离……继有先伯母丧,竭力殡葬。乱离中,真呕尽心血矣。先伯父在浙,依衢州司训孔公。病故,遗女十岁,无所归。府君备历险阻,携回择婿,资奁如礼。时值鼎革,往返六千余里,波涛之汹涌,盗贼之出没,身几危者数矣。不孝斌实从行,至今忆严陵滩、彭蠡湖,犹心悸也。②[清]汤斌著,段自成、沈红芳编校:《汤子遗书》,第329-330页。
短短数年,汤斌连遭6位亲人离世,伯父、叔父留下的年幼儿女,也千里接回抚养。少年时的经历,对汤斌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他于康熙二十三年57岁出任江苏巡抚时依然布衣蔬食,寒素非常。其子汤溥劝他不要太自苦,他的反应是:“色戚然不答。不孝等数数言之。泫然流涕曰:‘吾非欲俭,汝祖母未殉难时,日食粗粝,我未逮养故也。’”③[清]汤溥:《行略》,汤斌著,段自成、沈红芳编校:《汤子遗书》,第19页。
综上,明代带给汤斌的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母亲等6位亲人惨死的血泪记忆和四处避乱的凄怆无助。这也是甲申国变前后整个时代的底色。
由于战乱阻隔,汤斌只得寓居衢州山中读书。国破家亡,前途未卜,深夜虎啸林外,与书声相间。这惨痛的经历和严酷的现实磨砺着还未成年的汤斌的心性,也对塑造其性格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即使在这样动乱的时局下,当听到弘光王朝建立的消息时,汤斌仍携父亲及幼妹千里奔赴南京。
南明弘光朝立国伊始即颁布了《国政二十五款》,诏令各省:大赦天下,优抚南来官吏,减免百姓赋税,寻访山泽贤良,体恤士子生员,显示出一派贤君励精图治的开国气象。其中对各级生员也作了周详安排:“各府州县廪生例得恩贡者,务收真才,以需后用,不拘年序。”④[清]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页。
汤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南京,以流寓生员身份应试:“寻至南京,以流寓应试。”⑤[清]王廷灿:《年谱初本》,汤斌著,段自成、沈红芳编校:《汤子遗书》,第29页。另:关于汤斌以流寓生员身份参加弘光朝考试的情况,只在王廷灿《年谱初本》里有记载;40年后,方苞、杨椿《年谱定本》中已删去该节,这显然是出于维护清廷目的的有意而为。而从这一条文献的删削情况也可证明汤斌最初投奔的乃南明政权而非清廷。可是,虽然弘光朝颁布了优恤生员政策,但权奸掌国,这些政策也多成了空头支票,甚至成为他们借以向生员敛财索要的借口。《小腆纪年附考》记载:“马士英请免童生府州县试,上户银六两,中户四两,下户三两,径送学院收考,其银以充兵部招练军器之用;从之。已而溧阳知县李思谟竟以不令童生纳银,降五级。”⑥[清]徐鼒撰,王崇武点校:《小腆纪年附考》(上)卷8,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267页。弘光批准了童生纳银的建议,且对执行不力的官员实施了惩罚。汤斌正是这批被明令纳银的童生之一。
同时,弘光朝的各种乱象汤斌也有切身体会。《明季南略》记载:“时上深居禁中,惟渔幼女、饮火酒、杂伶官演戏为乐。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大工繁费,宴赏赐皆不以节,国用匮乏。”⑦[清]计六奇:《明季南略》卷2《朝政浊乱》,第104页。弘光朝时局混乱,马世英、阮大铖等权奸掌国,内部纷争严重,史可法也被排挤到了扬州。
汤斌父子及幼妹三人生活无着,在衢州时靠当地山民接济勉强度日,至南京又要纳军需才能参加考试,再耳闻目睹弘光朝的各种乱象,他们对明朝复兴已经绝望:“已而有令,纳军需数两,方许与试。遂弃去。”①[清]王廷灿:《年谱初本》,汤斌著,段自成、沈红芳编校:《汤子遗书》,第29页。弘光元年(1645),汤斌离开南京,回到已被清军占领的家乡睢州。从《年谱初本》这条后来被删削的汤斌赴南京应试的文献可以看出汤斌出仕清廷前的具体情况。
回到睢州后,汤斌于顺治三年参加当地童子试,顺治五年举河南乡试。笔者认为,汤斌选择应试清廷固然由多重因素促成,如有对复明希望的破灭、家计的艰难、传统的荣宗耀祖思想等,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清廷抚恤李自成乱中殉难人员的举措对他心理上的感召。汤斌母亲惨死于李自成兵乱,这段血泪记忆一直是汤斌心底的隐痛。康熙五年,39岁的汤斌拜孙奇逢为师。孙奇逢为汤母所作传云:“后遇忌辰,阴云四合,悲风夜鸣,居人传其期比寒食云。”②[清]孙奇逢著,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77页。孙氏未曾拜谒汤母祠,则其所云汤母忌辰时阴云、悲风等情况当是汤斌在向其讲述时内心情感的感性表述。
清军入关后,一方面以武力镇压各地复明反抗力量,另一方面也实行了一系列优抚政策以招徕汉人。顺治初年即大力表旌因抗击李自成罹难的倪元璐、范景文、刘理顺等故明诸臣。在这种风化下,各地官吏纷纷表奏本地死于李自成乱中的节烈人员:“顺天府府丞张若麒奏:臣父熙骂贼被害,请加恩赐恤。部议应予祭一坛。从之。”③《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6,《清实录》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41页。“河南巡抚罗绣锦疏言,清化镇委署同知史灿麟,同妻高氏拒贼,俱遭惨戮。孟县知县王曰俞骂贼不屈而死。请议恤典。”④《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6,第140页。这种请求表彰死难的奏章在顺治初年非常普遍,而清廷也依例优抚。
对于有着相似经历的汤斌来说,清廷的做法使其从感情上产生认同和慰藉。同时,清廷又借助科举制度大力笼络汉族读书人,从顺治初年即连开科举,破例扩大录取人数,使大批优秀汉族士人脱颖而出,并迅速融入清廷的新政权之中。在清廷的感召下,汤斌遂参加科举考试,并于顺治九年举进士,成为出仕清廷的汉族士人。
汤斌入仕之初即表现出仗义执言、公正严明的为官风范。顺治十一年,汤斌被授国史院检讨。出于史家的责任,他在《敬陈史法疏》里提出请求表彰明亡死难的倪元璐等人之后进一步指出:“更有请者,宋臣欧阳修纂《五代史》,不为韩通立传,后世讥之。《宋史》修于至正三年而不讳文、谢之忠,《元史》修于洪武二年而并列丁、普之义,古今韪之。”⑤[清]汤斌著,段自成、沈红芳编校:《汤子遗书》卷2,第83页。文天祥、谢枋得、丁好礼、普颜不花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不忘故君的义士。汤斌以前朝修史不讳为这些人立传为例,意在劝勉顺治修明史也应表彰意图抗清复明的节烈义士。这一上疏招致满族大臣的不满和忌恨,汤斌处境非常凶险,“遵谕陈言,狂直几得罪”,⑥[清]汤斌著,段自成、沈红芳编校:《汤子遗书》卷6,第330页。幸得顺治宽免,且加以抚慰,于是直声著于朝野。
综观汤斌首次入仕情况可知,汤氏整个家族在明季备遭乱离,明亡时汤斌年仅16岁,无任何功名,危难之中仍投奔南明弘光政权,但鉴于对弘光君臣的彻底绝望,随即做出返回家乡的决定,之后参加清廷科举,为官后不顾自身安危利害,仗义执言。可以说,汤斌选择接受了满清,且在企望国泰民安和延续民族文化中找到了一个汉族士人安心立命的价值。
二、汤斌辞官原因考论
有关汤斌争论的第二个焦点是他热衷功名,不惜以起义军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实际上,汤斌在平定李玉廷叛乱后即坚请辞官,之后长达20年里居,其间两次拒绝朝廷特召。如持汤斌汲汲功名之论,则其壮年辞官、拒绝征召的行为就很难解释,故需对有关问题重新深入考察。
汤斌29岁时由翰林院外转陕西潼关道副使,颇有政绩,3年后升江西岭北道参政。上任后,汤斌立即着手实施一系列行政举措,保民安民,教化一方。如汤斌甫到江西,感于豫章为理学、节义之乡,周敦颐、二程、王阳明皆曾在此讲学,岳飞、文天祥节义彪炳,于是捐俸修复先贤与节烈祠宇,兴书院,崇祀圣学。出于培育根本的教化目的,他力倡社学,设立月课讲学制度,并定期亲赴社学讲学,赣府学风因之丕变:“赣州文教始盛于宋,其地则周子、二程子辙迹之所到也。明王文成继之,我朝汤文正又继之,涵濡于教泽者深,故咸知自奋,所谓得天地阳气之偏者可以理义动也。”⑦[清]魏瀛等修:《(同治十二年)赣州府志》卷23《经政志·学校》,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70年,第438页。
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一年多之后,年富力强、仕途日上的汤斌却以病题请辞官,未获准后,接连又上了三道辞呈,详陈自己的病情,以病恳辞,但是皆未被允准。接着,汤斌又上第五道辞呈,言辞更加恳切,且在反复陈述自己病情之余又增加了父亲病重需回乡奉养之请:
抑本道病源更有实情万难自遣者,本道年十四岁即遭闯寇破城,母仗节骂贼,殉难最惨,本道已抱终天之恨。嗣后流离间关,惟父子相依为命。……临行之时,父执手涕泣,曰:“我病万难支持,你今远去南安四千余里,不知何时得再相见。”本道闻之,心肝裂碎。马首南驰,方寸昏乱。抵任以后,见诸事废弛,竭蹶经营,心血损耗,终日忽忽,若有所失。兼以瘴疠交侵,水土不服,一病遂成沈疴。若溘先朝露为异乡之魂,老父闻知,病必愈加。是本道废弛地方,不可以为臣;病贻亲忧,不可以为子。午夜号泣,中心如刺,情实急切,自非医药所能奏效。⑧[清]汤斌著,段自成、沈红芳编校:《汤子遗书》卷8,第511页。
辞呈列举了诸多于情于理不可不获准的理由,孝亲之情不亚于李密的《陈情表》。清初沿明制,外官告病,一律令休致,不再起用。但是,如果是为父母、祖父母终养,则待其亲病好或为其守丧期满后可复仕。其时,汤斌完全可以以终养为由提请暂时还乡,或者采取其他变通之法。当时的江西巡抚苏宏祖也曾这样建议:“督抚惜之。例:外官予告,非特荐不得起。公故有异母弟,甫六岁。督抚欲令权宜以终养请,公曰:‘奈何以此欺吾君也!且谓无兄弟而归,吾父必不乐。’竟以病告罢,年才三十三云。”⑨[清]徐乾学:《工部尚书汤公神道碑》,钱仪吉:《碑传集》卷16,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53页。汤斌拒绝了苏宏祖的这一好意。他在辞呈里也多次提到告病即等同再无入仕机会的后果:“外官告病,例不起用。本道非情不得已,宁不顾惜功名,自甘废弃?即此可察本道之心矣。”⑩[清]汤斌著,段自成、沈红芳编校:《汤子遗书》卷8,第511页。可见他对以病辞官的后果是非常清楚的。
就目前所见文献分析,汤斌辞官缘由乃自己身染重病难以继续任职。即使有人建议他变通为以终养题请暂归,以为自己日后重入仕途留下希望,但汤斌却不愿如此。则汤斌热衷功名之说似难成立。然而,汤斌历经乱离始艰难一第却于壮岁辞官实不合人之常情,而学界至今无人专门细致考察汤斌辞官之由。笔者通过细索汤斌在江西的100多道公移,结合他生平处世情况,认为以病辞官只是表面理由,李玉廷事件才是汤斌坚请辞官的隐衷。
汤斌刚到任时,故明抗清将领李玉廷聚众山林,汤斌致书劝降。李玉廷虽许投诚,但屡次藉故不出。汤斌连发告谕,希望李玉廷早日出山投诚。恰逢郑成功、张煌言等海上抗清将士联军进兵南京,汤斌料李玉廷必反,反必先攻南安,于是先在南安设防。李玉廷果率军来攻,见有设防,遂退。
在郑成功战败而退,江西叛乱也出现转机时,汤斌以为局势稳定,一切将步入正轨,他立即晓谕百姓:“地方一切利弊,候本道与府厅各官商榷,次第兴除,务令兵火凋敝之区,渐睹生养安全之效。”⑪[清]汤斌著,段自成、沈红芳编校:《汤子遗书》卷8,第451页。在其施政规划中,一切地方利弊将次第革新,而最终目的则在安民保民,化育百姓,一如在潼关时。这也是汤斌出仕的本衷。
但是,盘踞地虽被捣毁,李玉廷却逃入深山。官兵多次出动追剿,因李玉廷及其部下与当地居民多有联络,致使追剿半年毫无结果。汤斌多次告谕招降,甚至以其父为人质招李玉廷出山:“李玉庭依山负嵎,执迷不出,逆顺祸福之机全然不知,可谓愚矣。且伊父见在省城,生杀惟部院之命。彼逡巡狡诈,不念及乃父乎?”⑫[清]汤斌著,段自成、沈红芳编校:《汤子遗书》卷8,第483页。一般情况下,凶残的匪徒为了达成自己的非法目的,往往不惜劫持人质与官府对抗。而在追剿李玉廷的过程中,汤斌不得已采用了以李父为人质的方法逼迫李玉廷。这对于具有儒家仁政理想的汤斌来说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因追缴未果,上司切责,汤斌甚至亲赴李玉廷可能藏匿之处参与探查、搜捕:“今奉严檄,自知惶悚,以巡检、典史不足寄任,欲奋身前往要辖地方以及窝藏处所,设法挨挤,多方搜缉,得其虚实真伪,驰报扑灭,亦见悔悟振刷之意。”①[清]汤斌著,段自成、沈红芳编校:《汤子遗书》卷8,第503页。其间艰难与无奈可想而知。
汤斌志在养民却被动陷入持久的绞杀汉人的军事行动中,亲见甚至参与各种杀戮,心理的创伤更甚于身体的疾病。当李玉廷最终被擒正法后,汤斌即题请辞官,但在辞呈里显然不能提及李玉廷一节,唯加意强调自己病重与孝亲之情。其实,汤斌所渲染的自己诸多严重病症更多的是精神压力带给他的一种心理暗示,这点一方面可从汤斌辞官归里后《年谱》记载探知。从汤斌辞呈描述看,他患病症状颇为严重,但《年谱》详载其归里后一直从事著述活动,赴夏峰拜孙奇逢为师,与张沐、孙博雅等人问学切磋,却无一言记载其身体病痛。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从他直到50多岁时仍对当年戡乱一事耿耿于怀推测李玉廷事件给他造成的心理创伤。其时,汤斌二次入仕,任康熙日讲官,其门人范景侍从时问为政是否当以顺民情为第一义,汤斌开始表示肯定,良久后又说:“也有顺不得的所在。即如我当初在赣州作道时,正值海寇猖獗,忽有贼持伪檄到抚军辕门。抚军传余甚急,食顷三至。余诣抚军所,以此贼付余。……因令押赴市曹,百姓人人震恐,遮道而请曰:‘杀之,则贼众大至,百万生灵不保矣!’……使是时稍顺民情,不断然斩之,奸宄生心,保无意外之变乎?此岂不是顺不得处?非是当初年少气壮,只是明理耳。”②[清]汤斌著,段自成、沈红芳编校:《汤子遗书》卷1,第74页。
“明理”是汤斌基于自己身为戡乱官员的职责所在,但他明白这样做却有不顺民情之意,而不顺民情则违背了做官的初衷。两相挣扎,他最终选择了辞官。这是汤斌辞官深层的不能明言的原因。循此思路,则他在告病居乡的20年里至少两次拒绝征诏入仕的行为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汤斌二次入仕考论
二次入仕成就了汤斌事功的辉煌:总裁《明史》,日侍讲筵,典试浙江,出任江苏巡抚,主导东宫,深得康熙宠信,同时这也为后世评价汤斌热衷功名提供了口实。对此,我们需深入考察,以理清真相。
首先,汤斌乃被举荐博学鸿词,并非主动求取功名。康熙十七年,51岁的汤斌被魏象枢、金等人举荐鸿博。此时的汤斌早已习惯了居乡问学的生活,在潜心理学中找到了生命价值。刘榛《送汤潜庵先生序》中透露了汤斌当时的心态:
檄至有司,趣先生行。先生难之,不得辞,行有日矣。凡知先生者,无亲疏,设供张祖道称觞,且各赋诗以侑之。其诗之义,或以名位为荣,或以得行其志为先生幸,或以先生之用为吾道光。刘榛曰:此非先生意也。先生悬车二十年,羸马敝裘,读书考道,为吾道之光不少矣,岂关用不用哉?先生弱冠掇巍科,入列侍从,出领方面,先帝未尝不用先生。先生之遇,亦非不足以行其志也。而先生毅然致政归,先生又岂以名位为荣者哉!榛故曰非先生意也。③[清]刘榛:《虚直堂文集》,《四库未收书辑刊》7辑第25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刘榛为汤斌同乡,二人性情相投,常以性理切磋,彼此引为至友。刘榛指出,汤斌归里20年,“羸马敝裘,读书考道”,足可为“吾道之光”,绝非因朝廷征召始为“吾道光”。故徐作肃评刘序曰:“先生与山蔚相勗于道者,宜其赠言如此。”④[清]刘榛:《虚直堂文集》,第17页。刘榛、徐作肃可谓深知汤斌者,指出汤斌再举鸿博入仕,实非其本意。汤斌在临别与友人的赠答诗里也流露出不愿出山、盼望早归田园之意:“入朝倘得辞簪绂,春水还期理钓纶。”⑤[清]汤斌著,段自成、沈红芳编校:《汤子遗书》卷10,第624页。他甚至还计划当年年底回乡与老友相聚:“岁暮可能归旧隐,村邻浊酒正堪携。”⑥[清]汤斌著,段自成、沈红芳编校:《汤子遗书》卷10,第624页。
其次,时局变化使汤斌二次入仕达到事功顶峰。上文已经论述,顺治朝杀戮的政治环境与汤斌的儒家政治理想相左是其壮岁辞官的难言之因。因此,考察汤斌的二次入仕,有必要注意时局的变化。
汤斌二次入仕时,三藩之乱平定在即,文治正兴,他认为顺治时期的杀戮已经成为历史。这种政治生态的变化正是汤斌一直希望看到的,也与他仁治天下的政治理念相符。因此,汤斌在二次入仕后的政治生涯中,以儒家的“兼济天下”之心参与朝廷的各项事务,深得康熙宠信。侍讲筵时,康熙曾让日讲官上各自所作诗文,汤斌选了《院中宿值八韵》呈上,其中有“年老才将尽,忧多道转亲”①[清]汤斌著,段自成、沈红芳编校:《汤子遗书》卷10,第617页。句,康熙询问何意,汤斌奏曰:“臣幼遭乱离,半生在忧患中。当随事体认,于道理转觉亲切。”②[清]汤斌著,段自成、沈红芳编校:《汤子遗书》卷3,第170页。康熙甚为叹赏。
从汤斌进呈给康熙的这首诗里,我们不但可以看出他主张践履而非空谈的理学主张与治学方法,同时也能体会到他出仕后心理的变化,即当时势发展与自己的理想一致时,深藏心底的儒家兼济之志让已逾知天命之年的汤斌收起散淡,义无反顾地承担起社会责任与使命。他的这种入仕理念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汤斌身为帝师“君心正而天下治”“格君心于不自知”的济世情怀及自觉担当。康熙出于治国目的,十分热衷学习汉族经典,且经常在讲筵后向讲官们询问理学的有关问题及治国之道。从康熙十年开始,历任讲官熊赐履、孙在丰、陈廷敬、张英、汤斌等人即以正君心而天下治的责任担当,在给康熙讲解儒家经典的过程中,不断灌输正心诚意、躬行实践等理学主张,逐步形成了康熙“以理治国”的政治理念。汤斌在任讲官期间教导门人窦克勤的一段话透露了其中信息:“讲官所职者大,宜从源头上整理。古人正色立朝,其一段至诚感孚处,有格君心于不自知者。君心正而天下治,此犹天之枢纽转运众星而人不之见者也。讲官又是默令枢纽能转运,底是何等关系!”③[清]汤斌著,段自成、沈红芳编校:《汤子遗书》卷1,第72页。汤斌正是希望以经筵日讲的“格君心于不自知”的济世情怀赢得康熙信任,进而通过日讲的潜移默化对其治国理念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从中也实现自己的兼济之愿。二是汤斌在任江苏巡抚期间严格自律的品性与事功的辉煌体现了他儒家的兼济情怀。康熙二十三年,汤斌被特简为江苏巡抚。康熙之所以打破九卿会推惯例而特简汤斌为江苏巡抚,主要在于汤斌身上表现出一种异于常人的清苦耿介的特质。康熙以为这一特质可矫江苏浮华奢靡的人心与风俗之弊。而汤斌也不负康熙所望,在江南巡抚任上以身作则,扶持正学,严禁淫祠小说、杜绝赛会演戏等,使吴地很快“教化大行,民皆悦服”。④赵尔巽:《清史稿》卷265《汤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932页。他后世所获得的入祀贤良祠、赐谥文正、崇祀文庙等尊荣主要基于他在江苏的政绩。
四、汤斌被谗遭斥考论及时代风评
汤斌在江苏巡抚任上仅一年半即于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奉旨内迁,闰四月抵京,任詹事府詹事,直至二十六年十月逝于京城寓所。这一年半时间里汤斌与康熙的关系逐渐恶化,他一生克己践履形成的道德完人形象也遭破坏,并持续不断被康熙口诛。而由于康熙的帝王身份,他的评价影响深远,这是造成历史上对汤斌评价褒贬不一的主要原因。
梳理汤斌被谗遭斥过程可知,汤斌刚进京时,康熙对他十分器重,朝议也多征求其意见。如康熙二十五年,郭琇在考选科道时考了下卷,且有征赋未完等事,但因其乃汤斌举荐,康熙否定了部议不准的决议而特加简用:“二十五年,巡抚汤斌荐琇居心恬淡,莅事精锐,请迁擢。部议以琇征赋未如额,寝其奏,圣祖特许之,行取,授江南道御史。”⑤赵尔巽:《清史稿》卷270《郭琇传》,第10003页。直至该年腊月二十五日,康熙还让汤斌将他在江苏写的十多篇告示呈览,对他在江苏的行政评价颇高。
康熙对汤斌态度转变发生在二十六年,且开始并非单纯针对汤斌。下面按时间顺序仅就《康熙起居注》中该年三月至六月4个月内康熙指责群臣的有关记载略加条举:
三月,京师大旱,康熙借机对官员中逢迎谄媚等陋习严加斥责;
三月二十五日,因议下河事,康熙训诫各官惟利是图;
五月十一日,康熙因怀疑群臣间结党而面试翰詹等满汉官员;
五月十五日,董汉臣上疏言事,有“谕教元良、慎简宰执”等条,康熙责九卿会议具奏;
五月十六日,康熙借祈雨斋戒事斥心不诚者非人类,与禽兽无异;
五月二十五日,康熙借陶式玉题参董汉臣事叱骂言行不一者“非人类,与禽兽何异?”;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631页。
六月初七日,汤斌等三人于畅春园为太子进讲。康熙亲自督导,无端斥责汤斌谗谄面谀,表里不一,并叱责内外不符之人实非人类。
康熙之所以如此激烈斥责群臣,是因为长期以来,尽管出于维护清廷统治目的,康熙一再标榜满汉同体一家,但心里始终固守着满人家法,尤其是三藩之乱后,康熙对汉官已不信任:“(玄烨)心中却始终铭刻着汉官‘背主’‘误国’两大罪。玄烨所见与事实相符若何,为另一问题。但其思想上抱此成见,且一经认定,即终生不改,则可确信无疑。”②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3页。而且,随着他日渐乾纲独揽,更将“伪道学”作为打击汉官的惯用政治手段。他二十六年的“愤怒”用意即在此。而7条材料中前5条皆针对在朝大臣,尤其是汉官集团,后两条才逐渐指向汤斌,因为打击汤斌具有震慑汉官集团的作用。而汤斌政敌明珠一党遂借此机搜集事状对其百般陷谗、弹劾,王鸿绪、翁叔元、佛伦皆与其事:“初,以式玉疏下九卿集议,尚书汤斌谓大臣不言,惭对汉臣。汉臣既黜,鸿绪偕左都御史璙丹、副都御史徐元珙合疏劾斌务名鲜实,并追论江宁巡抚去任时,巧饰文告,以博虚誉。上素重斌清廉,置弗问。”③赵尔巽:《清史稿》卷271《王鸿绪传》,第10012页。康熙虽未处置汤斌,但明珠党的进谗对二人关系的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之效,自此康熙对汤斌再无善言。
汤斌于康熙二十六年十月去世,之后康熙在其30余年的帝王生涯里,始终对汤斌耿耿于怀,时时借机从各方面加以否定、斥责。下面简单条列《康熙起居注》《清实录》里所记汤斌去世后康熙对他的口诛:
(1)康熙二十七年二月,汤斌去世3个月:“朕不以汤斌为人。”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第1724页。
(2)康熙二十七年四月,汤斌去世5个月,康熙借二十六年翰詹考试一事再次对汤斌口诛:“汤斌见德格勒之文大笑,至口鼻涎涕交流,将所持文章坠失于地。……后将伊等所作文章发出乾清门,与众汉官看阅,汤斌闭目不视,且云:适我不得已而笑。”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第1758页。
(3)康熙三十三年,汤斌去世7年,康熙以《理学真伪论》为题考试,又对汤斌再行声讨:“汤斌见德格勒所作之文,不禁大笑,手持文章堕地……既而汤斌出,又向众言:‘我自有生以来,未曾有似此一番造谎者。顷乃不得已而笑也。’”⑥《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63,《清实录》第5册,第785页。
(4)康熙四十九年,汤斌去世23年,康熙否定了先前曾亲口赞誉过的汤斌在江苏居官有声之说:“昔江苏巡抚汤斌好辑书刊刻,其书朕俱见之。当其任巡抚时,未尝能行一事,止奏毁五圣祠,乃彼风采耳。此外竟不能践其书中之言也。”⑦《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42,《清实录》第6册,第404页。
(5)康熙五十四年二月,汤斌去世28年,康熙再次就汤斌为官进行声讨:“汤斌为江宁巡抚时,所出告内云,爱民有心,救民无术。此岂大臣所宜言?”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第2147页。
(6)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康熙对汤斌在苏行政再行痛斥:“曩汤斌在苏州出示,有云爱民有心,救民无术。苏人闻其言咸诟之。”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第2215页。
(7)康熙五十六年,汤斌去世30年,康熙就道学之人为官再次否定其理政能力:“讲道学之人,家中危坐,但可闲谈作文,一有职任,即有所不能。若不用此辈,又以不用士人为怨,朕何必令人怨耶?即如汤斌、耿介与赵申乔辈,朕皆用至大臣。”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第2408页。
上述材料大致可分为两类,对应康熙指斥汤斌的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即(1)(2)(3)条所载内容,从道德上贬斥其虚伪、非人类。为此,康熙不惜在汤斌刚去世3个月、5个月之时两次当众斥责,7年后竟仍能生动复述汤斌当日言行细节。细索这几条文献,疑点实多:其一,有关汤斌在康熙和群臣面前大笑到涎涕交流、文章堕地之丑陋不堪情形,《康熙起居注》与《清实录》均未记载,其他公私文献亦未见片言,只在汤斌死后康熙对他秋后算账时作了生动详细的描述。按:汤斌一生谨小慎微、克己复礼,魏象枢称其为“言笑不苟之端人”,③[清]魏象枢:《寒松堂文集》卷10,故宫珍本丛刊第588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381页。且已年逾花甲,我们很难想象谨严到几乎刻板的他竟能做出如此放肆之举。而联系康熙在打击某一臣子时往往添油加醋甚或无中生有,④如康熙在平定三藩之乱时曾指责汉官中有遣其妻子回原籍的现象,后来竟然变为汉官尽移其妻子回家的指责。类似情形治康熙史者多有阐述。则康熙叙述的真实性值得斟酌。其二,如果朝上情形乃康熙亲见,则他对汤斌在朝外与众人评阅文章时的“闭目不视”及“适我不得已而笑”等言行从何处听得?其真实性如何?因为即使作为官方记载的《康熙起居注》与《清实录》限于体例未载汤斌失仪及朝下私语,而当日与朝官员众多,何以其他公私文献无一言及?其三,按康熙所述,既然汤斌笑乃“不得已”之被动,那么纯粹的演戏又何至不顾一世英名竟失仪至“涎涕交流”?其四,果若当日汤斌如此失仪,康熙为何不当场责难,且还让他与陈廷敬等一起评判3人文章优劣?其五,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太子出阁讲书后,汤斌获罪,康熙谕明珠集群臣讯问汤斌,令其一一据实回奏。汤斌的回奏里历数自己妄荐耿介、妄言董汉臣上书、妄执朱砂及昏盹失仪等事,然未一言提及读卷大笑及背后出言怨怼之罪。⑤参见《汤子遗书》续编卷1《据实回奏疏》《请解任疏》中汤斌自陈及《康熙起居注》里有关记载。《康熙起居注》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记康熙之语:“汤斌三次回奏,方始据实。”然大学士王熙仍认为汤斌未讲明擅执朱笔原因,康熙令再次传问汤斌。初四日,汤斌第四次回奏里言及的失仪罪状乃指太子写字时自己“执书昏倦,以面掩书”,而非康熙在其死后指责他的读卷失仪。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第1652-1653页。明珠条举汤斌罪状亦无此一条。如汤斌果读卷失仪,他于回奏中岂敢不据实回明?明珠等又焉能放过他这一“丑陋至极”之罪过?综之,学界转相征引的汤斌读卷大笑失仪一事史料来源仅出自汤斌去世后康熙的描述,结合当日官员众多,此外无一家文献记载此事等资料,则康熙所述与史实并不相符。
康熙不惜言过其实地声讨汤斌,也并非真的认为汤斌人品道德有多卑劣,而是他一贯善于运用的一种政治权术,其目的是通过对汤斌的打击建立自己绝对一尊的地位,正如姚念慈所说:“他是要将汉人的理学名臣一概打倒,均冠以‘伪理学’之名。只有他自己才是‘以治天下国家之道存于心’。既以真理学自居,则伪理学自然是制服汉人领袖的武器。熊赐履、汤斌、李光地皆不能免。”⑥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第65页。因为汤斌在江苏的治绩与行政举措康熙曾多次嘉赞,并作为典型在全国推广,旋即食言等于否定自己,故康熙一开始先避开对汤斌治政能力的评价,而是抓住他在董汉臣上疏一事朝上与朝下言行不一之举大做文章,斥责他虚伪,判定其为伪理学典型,从汉人立身根本上彻底抽空汤斌;随后,康熙又着手肢解自己亲手树立的汤斌为官天下清廉典范这一形象,⑦汤斌于二十五年闰四月赴京时,康熙于乾清门接见,赞其“汝在江苏能洁己率属,实心任事”,甚为嘉悦,特加超擢。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第1479页。之后康熙也不止一次肯定汤斌在苏治绩。第(4)(5)(6)(7)条即属此类。在这个过程中,康熙对汤斌的斥责是否与事实相符,汤斌是否真的做过此事并不重要。明白此点,则康熙对汤斌态度的不客观与目的的明确性就不言而喻了。
所以,汤斌被斥一方面是明珠一党日积月累的进谗,而根本原因则在于康熙想借对汤斌、魏象枢等汉人精英的打击戕灭整个汉官集团的独立精神和文化优越心理,进而建立起以自己为唯一标准的集治统与道统为一身的绝对统治。汤斌只是汉官集团在当时遭遇的一个缩影和典型。
然而,康熙对汤斌的评价与当时风评却颇有出入。汤斌被明珠、余国柱、翁叔元谗害,可谓天下共愤。李元度认为:“举朝多为不平”。①[清]李元度纂,易孟醇点校:《国朝先正事略》(上)卷5,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133页。当汤斌被明珠一党陷害时,舆情激愤,甚至因翁叔元受明珠指使谗害汤斌,翁叔元的门生何焯竟至要索还门生帖:“叔元疏劾汤斌,焯请削门生籍。”②[清]赵尔巽:《清史稿》卷271《翁叔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011页。士林一时称为快事。另外,类似明珠谗害汤斌的细节屡见于时人文献记述,亦足可证明汤斌见重于士林、朝廷之程度。而究其根源,明珠一党也只是做了康熙的替罪羊。③姚念慈认为时人“将汤斌屈死归于明珠辈,以回护玄烨”。见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第109页。
即使在晚清民国时期,知识界精英对汤斌评价颇有过激之处,但也没有否认汤斌身上的闪光点。邹容称其为“人中之贤者”,就连对汤斌口诛笔伐异常激烈的梁启超也肯定了他的人品道德:“内中如汤斌,如魏裔介,如魏象枢等,风骨尚可钦,但他们都是夏峰门生,半带王学色彩。汤斌并且很受排挤不得志。”④梁启超著,夏晓虹、陆胤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29-130页。排除时代的民族情绪因素,梁氏对汤斌风骨“可钦”的评价,可谓的论。
五、结语
综合考察汤斌两次入仕辞官具体情况可知,他在明亡时年仅16岁,未有功名,算不得贰臣,更无从定为大节有亏;弘光建都时,汤斌曾赴南京以流寓生员应试,绝望后回到家乡,之后参加清廷科考出仕;为官后,汤斌以哲学上的正心诚意严格要求自己,身心纯正,清苦孝友,实心任事,清正廉明。他不愿违背本心上下俯仰,在需要作出选择时能舍弃名利,且能安贫乐道。
汤斌的入仕与辞官,既与其经世致用、躬行实践的理学思想一致,又与其淡泊自励的天性相符,融合于汤斌自幼养成的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观和君子固穷的操守之中。正如冯友兰在论述中国哲学的主题“内圣外王”时所引用的金岳霖的一段话:“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其所以如此,因为道德、政治、反思的思想、知识都统一于一个哲学家之身;知识和德性在他身上统一而不可分。他的哲学需要他生活于其中;他自己以身载道。遵守他的哲学信念而生活,这是他的哲学组成部分。他要做的事就是修养自己,连续地、一贯地保持无私无我的纯粹经验,使他能够与宇宙合一。……对于他,哲学从来就不只是为人类认识摆设的观念模式,而是内在于他的行动的箴言体系;在极端的情况下,他的哲学简直可以说是他的传记。”⑤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简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页。这段话可为汤斌一生哲学思想与行事准则的最好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