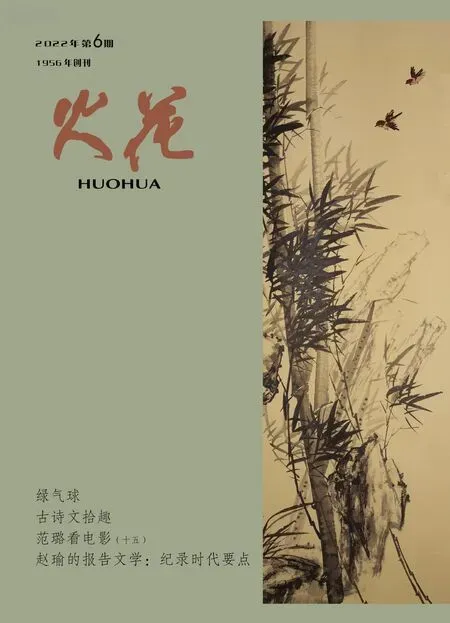归来仍是少年
非珍
“爸,什么时候才能坐火车呀?”
“等你长大了。”
“妈,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很快,就会长大。”
小时候我们带孩子常去屋后的那条铁轨上玩,他在上面欢快地跳来跳去。
周围用铁丝圈起来后,我们仨就站在铁丝外面,踮着脚尖朝里面张望,听着轰隆轰隆的声音从远处传过来,看火车呼啸而过。
接到孩子的电话,是初冬的一个下午。
“爸,我看到咱家后面那条铁道了。”
“妈,我回来了。”
太阳暖烘烘地照进来,我站在阳台上,朝着那条铁轨望去,当年的绿皮火车已经由构造速度更高、设施更先进的空调客车替代,每晚枕着轰隆轰隆声才会安然入睡。在国外,孩子每日坐小火车再转地铁去上学,火车“咔哒咔哒”成了他求学路上不可或缺的旋律。
济南隔离半月回太原,孩子买了Z字头的直达特快列车票,前年,我们送他去北京转乘飞机时,乘着列车离开太原,仿佛是昨天的事。两年后,他坐车返回,路过家门口,儿时玩耍的情景,历历在目就像昨日重现,也因此,萦绕在胸的那份坐火车回乡的情结,便像梦幻一样变得美好起来。
阳台上的暖意让我眼里泛起了潮意,那个决意出国读研的男孩马上要回来了,还是当年那个少年吗?
出国之前,正赶上伏天,外面的太阳像个大火球一样,孩子进了卧室如进了蒸笼,他把凉席铺在地上,然后把电脑、书本搁在上面,他就在凉席上看一会儿书,起来走一走,又坐下看书。晚上的时候,一倒头在席子上睡着了。就像小时候,把所有的拼图一个个拼起来,摆在地上,过一会儿拆开,又拼起来,再拆开,晚上还睡在上面,把卧室搞得像儿童乐园。
孩子忽然出了国,马上就要回来了,我在孩子的卧室这里走走,那里看看,仿佛多年前的情景浮现眼前,孩子一会儿坐在席子上拼拼图,一会儿从这个家跑到那个家,又从那个家跑到这个家。跑来跑去的小身板一点点变大,再变大,大得个头超过了我,超过了先生,卧室一下小起来,那个少年一天天长大了。原来的被子小了,我们给他换了大被子,原来的床短了,我们买了新床,他的衣服、鞋袜与他的个头相比,也必将一点点小去。
于他的成长而言,我们在一天天老去,有一天,先生从沙发上站起,膝盖剧烈疼痛,他缓慢坐下来,不停地揉痛处,嘴里还“嘶嘶嘶”地抽着凉气。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电视时,我按摩着老寒腿,先生不停地揉着膝盖。到了单位,我们除了被腿痛困扰外,只要有人提到谁的小孩毕业了,谁的小孩学成归来,我们极度敏感,瞬间就哑了声,孩子远行就像一个不能触及的痛。同事们开玩笑地说,想孩子想的吧,等孩子回来了,腿疾就不医而愈了,放松,放松。我们就笑了。
回头再看,七百多个日子就像春天的花骨朵一样,“噗”地一下开过去了,但过往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细细拆开铺展,又像翻过的一页页书,它们整齐地摞在书架上,于我们而言就是一种陪伴。六年前孩子像一只挣脱了翅膀的风筝,飞向了一所南方大学,那个以陶瓷闻名于世的城市,再一次上了我的热搜,尽管相隔千里,我们依然会每天通话,尽管会每天通话,我们依然无法排解对孩子的思念,于是那座城市牢牢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那时,正赶上“出国热”,周围朋友纷纷跨国旅游,我们却沿着孩子经过的路线向南出发,而每一次踏足异乡,就会向孩子所在的城市递进,心里就会无限向往。
两年前孩子异国求学,我们突然终止了旅游,所有的风景与孩子比起来都黯然失色。我们常常会想:孩子独自在异国,西餐吃不吃得惯,孩子适不适应当地的作息时间,大雪的冬天是不是格外冷,鼻炎有没有发作过,尤其是疫情突发,国外大街上戴口罩的人寥寥无几,孩子面临的是怎样的危险?但孩子和我们的视频里,表现得风轻云淡,我们很少会在他的脸上找到想要的答案,挂了电话,脑子里忽然蹦出来“善意的谎言”五个字,就会让我们惊悸得一晚上睡不着。第二天,我傻傻地问先生,要不,我们出趟国怎样?先生看看我,没搭理我。看着徘徊在地图前的我,他不知该说什么好。
当地图上的那个点被我抚摸得掉了颜色时,日子在一天天过去,它是那么漫长,让我们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它又是那么短暂,一晃而过。当孩子告诉我们,到了太原,还需隔离七天,我们的相聚又变得漫长了起来。不过,隔离酒店仅需二十分钟即可到达,我们与孩子的距离由数千公里变得越来越近,一想到孩子归来的情景,我们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孩子隔离第三天,一个雪落晴好的日子,天色刚有一些发白,邻家的小狗还没叫起来的时候,我悄悄从床上下了地,一回头,先生也醒了。
匆匆吃过饭,一看时间还早,我一会儿从厨房走到客厅,一会儿从客厅走到阳台,先生也不听早间新闻了,一个人盯着走廊自言自语,穿什么衣服呀?孩子睡醒了吗?孩子吃早饭了吗?如果醒了,在做什么?
我从衣柜里找出一件先生很久不穿的绿色登山服,我则穿了一件红色羽绒服,“红”和“绿”辨识度高,能让孩子从人群里一眼把我们给认出来。出门的时候,先生又折回客厅,走廊上传出剃须刀“哧啦哧啦”的响声,他一边剃须一边闭着眼睛,好像一睁开眼睛孩子就在眼前似的那般陶醉。
几日前孩子还在济南,太原的一场大雪突然而至,在太原久居,如果冬天不下雪,整个冬天好像会过得不舒坦。大雪过去几天了,低洼处的积雪依然还在,暖融融的太阳照上去,我差点被刺眼的光晃花了眼睛。
大雪那天,孩子从视频里让我们看济南的雪,落在地上,薄薄一层。老舍先生《济南的冬天》里这样描述:“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最妙的就是下点小雪呀……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
济南的雪在老舍先生的笔下也温情了起来,它怎能抵得过太原的雪?太原的冬天,在许多人还没准备好的时候捷足先登,有人几天前还穿着半袖,一大早撩开窗帘发现,一场雪浩浩荡荡来了,而且太原的第一场雪一下就是大雪。
瑞雪兆丰年!这预示着幸福吉祥的大雪,飘飘洒洒自天而降!人生中会有无数次大雪来临,在以后的日子里,孩子,你将会和我们一起迎接每场漫天飞舞的雪花。
隔离酒店的底层窗户用厚厚的铁皮包裹着,站在楼下,看不到高层的窗户,我们需要穿过人流到大街对面去。疾步走向人行道,红灯亮了,短短的十多秒却像过了半个世纪。我们站在隔离酒店对面一个超市的门口,就站在那儿猜,就像孩子参加高考时,我们站在考场外猜,孩子会在楼上的哪个窗户下奋笔答卷,此时,孩子又会在哪一个窗户里呢?是左面的窗户,还是右面的窗户?是挂着海蓝色窗帘,还是窗台上放着绿色盆栽的那个?
来之前想,只在远处看看。后来,我们还是拨通了电话,恰在这时,无数个窗户上有人影晃动。我们身后的超市门口,有一个雪人,朝天的萝卜做成的红鼻子,十分可爱。不知是谁堆得像擎天柱似的,雪水淋淋漓漓地往下淌。
“宝贝儿,看到我们了吗?”
“宝贝儿,我们在对面的超市门口。”
“宝贝儿,雪人,看到了吗?我们就在那儿。”
“超市?雪人?”
“看到了,看到了。”
“爸妈,我看到你们了。”
我们循着孩子说的第三个窗户望去,窗户上冒出一双挥动的手。
“孩子,是你吗?”我们盯着那双挥动的手,一会儿又不见了,接着电话里传出叮叮咚咚的响声。
孩子担心我们看不到,拿了一把凳子,踩在凳子上,手里攥着一张报纸,报纸被剧烈地晃动着。那张帅气的脸出现在窗户上时,我们惊喜地站在大街上旁若无人地喊着。
还是那个少年啊!
我们也开始挥手。两年,虽然视频了无数次,当我们相隔五十米的距离看到孩子时,声音还是哽咽起来。
“爸妈等你回家。”当我们离开时,谁都没有回头,只要一回头,就会流下幸福的眼泪。我们知道,身后默默注视我们的孩子也一定会泪流满面,此刻,我们是那么幸福。
其实,一个多月前,得知孩子要回国的那一瞬间,我们脸上就开始洋溢着幸福。当时出国上研,根据课程安排,办了两年签证,课程结束,签证正好到期,而西方国家疫情只增不减,又赶上航班一次又一次熔断。签证到期,回国无望,怎么办?每一个毕业生回国的脚步变得沉重而艰难。再和孩子视频时,屏幕里的孩子躲闪的眼神里,有无尽的不安和忧虑,我们的心时时刻刻悬在空中,每天都在忐忑不安中度过。
欣闻国航针对应届毕业生包机回国,那天晚上先生值夜班,在去单位的路上,脑子里全是孩子回国的喜讯,没成想被脚下的枯树枝绊了一下,摔倒时磕破了下巴。而那晚,同样欣喜过度的我,整个晚上没有一点睡意,站在日历旁细数七百多个日日夜夜发生的点点滴滴,数着数着眼眶就潮湿了起来。
当“咚咚咚”擂鼓似的叩门声把我从梦中惊醒,先生进门的一刹那,下巴处风干的血渍像一个火球一样直击我的眼睛,紧接着前胸两侧鲜血的印迹,像一记重锤敲打在我的脑门上,“嗡”的一声,我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双手软塌塌抬不起来。
“怎……么……了?”此时的我,不会连词成句。
“没,没事。”先生镇定自若地说。
然后,我们拥抱在一起,一点一点笑出了眼泪。
回国需要做一系列的检测,而每一次检测结果,都会让某些回国学生望洋兴叹,符合各项指标的人数逐渐减少。
“孩子,今天是第二次检测,加油!”
“孩子,今天是第三次检测,加油!”
“孩子,今天是第四次检测,加油!”
“孩子,今天是第五次检测,加油!”
一次次做检测,我们都要相互鼓励,之后就是对检测结果的漫长等待。夜色深重,我们坐在沙发上,一边频繁换着电视频道,一边盯着手机。国内外时差五个小时,当那边晚上十一点新冠检测呈阴性的结果出来时,这边已经是北京时间凌晨四点,黎明悄然而至,我们攥着手机,盯着孩子发过来的结果,幸福地进入梦乡。
周日在我们的期盼中马上就到了。周六正好要参加《名家名刊太原作家座谈会》,我如果在家,肯定会坐立不安。早在儿子落地济南时,我们就开始刻意调整生活模式,早回家一点,点外卖少一点。原先两个人的饭菜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馍也不蒸了,面也不擀了,孩子马上回来了,即使工作再忙,也不能再买外面的馍,再去外面的饭馆吃。孩子总是说,回去给你们做炒肉啦,炒菜啦,他在异国总比不上在家,要让孩子回来就有回家的感觉。我们提前把菜买好,把馍蒸好,米面油还买了“大号的”,然后就像孩子每次放假回家一样,把自己挂在窗户上,擦玻璃擦油烟机擦灯,然后钻进厨房,烧肉、炸丸子、绞肉馅。再然后,一趟趟往超市跑,大包小包提回了瓜子花生榛子栗子核桃巧克力大杏仁果脯、苹果香蕉柚子猕猴桃奇异果、鱼虾鸭蟹牛羊猪鸡。
认真听完一天的讲座,散场时天色渐黑,当前脚迈进门槛,孩子电话跟来,所有检测结果一切正常,提前回家!
孩子要提前回家,我问先生,是提前回来吗?真的是提前回来吗?先生点点头说,千真万确。我还没来得及卸下背包,一脚又跨出门潜入夜色,边走边想,还有什么没买的,百密难免一疏。
大步流星走在明亮的街灯里,一辆辆闪着弱灯的小车从我身边擦肩而过,孩子是不是已经出发在路上了?我在车流如海的街上试图找出载着孩子的那辆车。
正是工薪族下班的时间点,水果店、菜市场、超市的人挤来挤去,就像海里奔腾的浪花川流不息。我忽然眼里涌出泪花,在这初冬的晚上,略带寒意的冷风轻轻拂过大地,万家灯火透射出温润的光芒照进我此刻火热激动的心房。
情不自禁推开蛋糕房的玻璃门,有六年了,孩子的生日不是过在异乡就是过在异国。孩子的生日在九月,本以为今年会回家过生日,生日蛋糕提前都看好了,暂时又不回来,只有推后预定了生日蛋糕。服务生看见我在玻璃窗前久久不动,走上前来。我指着一盒蛋糕,心想:这份迟来的生日礼物,孩子一定喜欢,蛋糕表面铺陈了一圈纯巧克力,上面还有蓝莓、芒果小果粒,都是孩子爱吃的,就让服务生包起来。漂亮的服务生很快包起来,递在我手里,我小心装进纸袋,抱着纸袋走出蛋糕房。
这时,电话响了,攥着手机的手“嚯嚯嚯”抖个不停,不敢看手机,更不敢接听,心里涌上一股难以言状的感动,任手机铃声持续响个不停。
原来是先生打过来的:“蛋糕买了吗?”
我说:“买了。”
然后先生一直不挂机,支支吾吾着。
“还有事吗?”我问。
先生一个字一个字说:“以前咱做家长的太专横了,孩子什么都听咱们的,孩子马上要回来了,可不是从前的小孩子了。”
我狠狠点点头,说:“哦。”
两个人想一块了。挂了电话,我加快脚步,一定赶在孩子之前到家,初冬虽有些寒意,我赶回家时,全身汗津津的。
由于修路,疾控中心的专车停在小区北门,先生飞快地下楼。窗外,先生的背影穿过一幢楼,绕过中心广场,走上小台阶,消失在夜色中,我的心开始“咚咚咚”地剧烈跳起来,直到一高一低两个身影出现在小台阶上,一前一后绕过中心广场,没走几步隐入那幢楼里,我不错眼珠地盯着,几秒钟后,一高一低的两个身影,从那幢楼里缓缓走出,向这边走过来。
近了,近了,先生旁边的那不就是孩子?还是那个少年啊!孩子比之前高了瘦了,走在旁边的先生,明显老了矮了驼了。数年前,高大的先生紧紧牵着矮小的孩子走出小区的身影,转眼间,先生的头发秃了,远处看就是一个小老头,而孩子已经长大,是一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
那果真是孩子吗?我的眼睛模糊了。
伴着由远及近拉杆箱哗啦哗啦摩擦地板的声音,我慌乱地跑到走廊,打开门,又折到窗前,透过玻璃窗,一个人傻傻乐着,然后又跑到走廊,楼道里静悄悄的。我又折到窗前,孩子抬头一眼惊喜,他明显看到我了,身子晃动着向我挥手,我隔着窗户,向他们挥手,然后手指着单元门,示意孩子进楼道。我又跑到走廊,担心大门被风关上,一直站在门口,听了听,又听了听,楼道里响起父子俩的说笑声,从底层一层层传上来,此时楼道走廊的声控灯一下全亮了,孩子穿着紫色的帽衫,蓝色裤子,白色高帮鞋,背着背包,提着箱子走上楼,一抬头,笑了。
归来仍是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