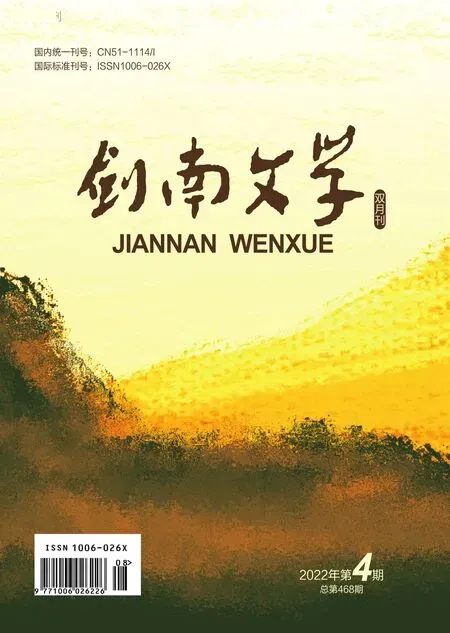霜从天上来
□刘玉明
牛经济韩老五死于霜降的第二天晚上。
在四棵树镇,关于韩老五的死因说法颇多。由此延伸出“今年霜冻大,能冻死人”的说法。韩老五的死便是佐证。躺在热乎乎的被窝里,哪知夜半霜冻的寒冷,只有亲身经历才能知晓。霜降都这么冷,要是入冬那还了得?!说这话的人,大多一副心怀天下的严肃表情,仿佛疼痛浮在面皮上,即便站着,也让人有要疼到腰上的错觉。于是便有争论,有人反驳,其实韩老五并不完全是冻死的,韩老五走村串户,足迹遍布十余个乡镇,壮实得像头牛,怎么会让一场细霜就给冻死了嘛。韩老五好酒,他是喝过头了,醉死过去的。
对于后者,秦大山不以为然,老韩年龄大了谁能保证不出个意外。他环顾了一下周围的人,像是在征询众人的意见。韩老五是秦大山的好朋友,众人不好插话,他便惋惜地摇了摇头,忧伤从额头跑出来,密布在眼角和皱纹里,让人看着都觉得辛酸,免不了说几句安慰的话。
秦大山的情绪好了些,麻利地给人杀鱼、打甲、溜片。末了,大方地送上两根葱一棵芹菜。但众人不走,拎着袋子围在鱼摊子前,继续听秦大山讲韩老五的故事。
镇如其名。四株粗大的黄桷树各踞镇子一角,据说是清嘉庆年间种下的,树干要数人合围才能抱住,枝叶茂密,蓊蓊郁郁,把镇子笼在一片绿荫当中。秦大山没有和村子里的人一道外出打工,家里有个老眼昏花的爹,加上老婆有哮喘,干不得重活,儿子又在外省打工,家里全靠他一人。走得远了,都照顾不上。便承包了村子里七八亩大的水塘,养鱼种藕。逢场时,挑了鱼或是莲藕到黄葛树下卖。水塘里的鱼和莲藕需一年才成,就骑着三轮车到六十多里地的县城进货,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赶回来天才蒙蒙亮。藕鲜鱼活,虽然没有自家养殖的水灵,但镇子里就他一人做这水鲜生意,众人也无法挑肥拣瘦,便结识了韩老五。
韩老五做牛经济,撮合买卖双方交易耕牛。交易成功,从买家卖家两方抽成,日子过得十分滋润,修了楼房,给儿子娶了媳妇儿,看着小两口欢天喜地到外省打工去了,家里就留下他和老伴过日子。韩老五喜欢喝酒,每次交易结束就到酒馆里切一盘卤菜,点上一碟花生米,喝上几杯。自己肚儿饱满了,家里还有一个人呢,韩老五就琢磨给老伴儿带点好吃的回去,割斤把肉,打一两块豆腐,老伴儿也能吃得心满意足。可是不能老是猪肉豆腐啥的,还得买些河鲜,便去秦大山的鱼摊前,拎一尾草鱼,或是鲤鱼或是花鲢。一来二去,秦大山就单给韩老五留一条,等他吃饱喝足后拿给他,两人成了朋友。卖鱼的时候,秦大山抽空儿去酒馆里陪韩老五喝一杯,韩老五来拿鱼的时候,秦大山也不收他的钱。
日子如同镇子下面的白水河,波澜不惊,又在不经意间倏忽流走了。有大半年的时间,秦大山没见到过韩老五的影子。卖鱼闲暇,他总会朝酒馆里望一眼,看韩老五在不在。韩老五最爱坐的那张桌子旁总是有人,也是常来秦大山鱼摊买鱼的人,唯独不见韩老五的身影。有时候,盯着那张桌旁的身影,秦大山感到恍惚:韩老五醉眼朦胧,伸出手向他招呼,让他过去喝一杯。坐在树下,秦大山透过黄葛树密密的枝叶,想韩老五是不是出啥事了?这个念头随着这年秋天的到来,像枝头的黄叶一样不时飘落下来,让他有些犯怔。黄叶掉在水盆里,给韩老五留下的鱼在树叶下游弋,仿佛找到了庇护。终于按捺不住,秦大山去牛市场上寻韩老五。牛市在街尾,地面上干痂的牛粪似乎在诉说市场昔日的繁华。一排拴牛的木桩上,几截短绳在风里摇摆。秦大山站了好一会儿。
以前,韩老五从一个木桩走到另一个木桩,他的身后是一双双紧张的眼睛。韩老五在牛的身遭转悠,让拴在木桩上的牛也紧张起来。牛们等待着这个套着西服、脚蹬胶鞋、面目粗糙的人给出最为精当的评语——那些评语决定了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从事劳动的强度和吃喝的好孬,决定了生活幸福与否的同时,还决定了未来的时光里,有没有机会在山中肆意体验青草和阳光带来的快乐。只有那些不懂事的牛,依仗硕壮的腱子肉,瞪着一双铜铃大的眼睛不屑一顾地扫过韩老五。等待它们的是韩老五钳子般的双手。“老五一出手,便知有没有”,这句话不是大风吹出来。韩老五拎着牛鼻绳,掀开它们的厚嘴唇,伸出两根手指头,在牛舌头和唇腮里摸索,顺带出一股股亮晶晶的涎水。他把粘在手指头上的涎水毫不留情地抹在牛头上、健硕的牛大腿上,一股凉丝丝的感觉瞬间浸透牛的全身,让它们不得不夹紧尾巴,把要冲出来的牛粪和橙黄的尿液憋回肚子里。在这期间,迎接它们的将是主人家的一顿鞭笞,或是一顿咒骂。在数十块钱上下的价格争吵中,那些高傲的牛饱尝了世间的冷暖,它们从内心深处对韩老五生出不满,却不敢表露出来,只是泪眼汪汪地站在一旁,希望获得那个面目可憎的男人一个同情的眼神。在韩老五的最终决断下,一头头牛完成了从一家到另一家的交接,开始了完全一样又截然不同的生活。
牛市空空荡荡,飘落的树叶被风吹卷到干涸的牛脚印里,让秦大山有些失落。一个被尿憋胀的赶集人急匆匆地跑到角落,响亮地放水。赶集人说,老秦,你还准备买牛?秦大山支吾了一句连自己也没有听懂的话。赶集人说,现在都用铁牛了,哪个还买牛嘛!牛,都用来吃肉了。秦大山恍然大悟,他挠了挠脑袋,自己家里不是也用铁牛耕田种地了么!
秦大山想,韩老五许是改行了,开店卖铁牛去了;也许是随儿子进城去了……那鱼,今后还要不要给他留?
霜降的第二天,韩老五突然出现在镇子上。他站在秦大山的鱼摊前,用脚踢了踢水盆,水盆里的鱼受到惊吓,泼喇喇地游动起来,搅得水花四溅。秦大山抹了一把溅在脸上的水珠,仰起头来,见是韩老五便嗔怪道:“老韩,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秦大山的声音如同受惊的鱼,把四面做买卖的人都惊醒过来,大家看见韩老五,热情地打招呼,免不了一番寒暄。秦大山看着眼前的韩老五,有些不认识。韩老五穿着一件灰褐色的呢子大衣,里面西服的领子翻起来一角,但不影响他的精气神。韩老五顿了顿脚上的水珠,一双黑皮鞋立刻亮起来。
秦大山说,老韩,发财了哦。韩老五用两根手指头捋了捋花白的短发——那两根捅了数十年牛口腔、牛屁股的指头已经不利索了。他打了个哈哈,说:“发屁的财哦,就是想兄弟了,过来看看。”他瞅了瞅水盆,说,给我留的鱼呢?秦大山指着盆里的鱼说:“留着呢,鲤鱼,鲤鱼肥,抽筋切块炖着吃,补秋膘最合适不过了。”
“都霜降了,还补秋膘?”韩老五斜着眼珠子看着秦大山,仿佛秦大山就是一头年轻结实的牛犊子,眼光亲切得让秦大山身上一热。
“得补,一年补透透,不如补霜降。”秦大山一本正经。
“快把鱼卖了,我们去好好喝几杯。”韩老五挥了挥手说。
中午,秦大山和韩老五坐在了桌子上。韩老五没有卖铁牛,也没改行当,他还做牛生意。以前做牛经济,现在做肉牛生意。韩老五说,现在都不用牛耕田耕地,只能吃肉了。城里人喜好牛肉,要自然生态的好牛肉。好牛肉在哪里呢,还不是在咱们乡下。咱们乡下没工厂,牛儿们吃的是没有受过污染的青草,喝的是没有受过污染的山泉水,毛顺溜肉结实,哪有不好的?!
韩老五竖着两个指头,秦大山给他拿了一根烟,他用另一只手的两根指头接了。“一头牛毛利润是这个数。”韩老五说。
“两千!” 秦大山差点叫出声来,“我的个乖乖,赚那么多。”秦大山为韩老五感到高兴,老朋友赚大钱了,自己面上也有光彩。一瓶酒喝下肚,秦大山主动让再拿一瓶来。“没那么多,也就五六百。”韩老五大概是不想在老伙计面前显摆,让他生出自己是在炫富的想法来,也有个财不外露的顾虑,卷着舌头说:“今天这顿饭我请,咱们哥俩要好好喝一回。”
酒馆里都是熟人,来给久未谋面的韩老五敬酒,恭维的话说了一箩筐。老板也来凑热闹,捏了捏韩老五的呢子大衣说是真呢子的,怕要好几百。韩老五便把呢子大衣脱下来,放在板凳上。秦大山说:“老哥,气温降得快,冷,还是穿上的好。”韩老五说:“不冷,你说怪不,越喝越热和。见到你,我全身都热和。”秦大山搓了搓手,说:“老哥,你走的时候把鱼给嫂子带回去。”
“对,得对你嫂子好点儿,让她也补补。” 韩老五说,“这辈子就她对我好。我那个败家的儿,就只听他婆娘的话了,这么多年一分钱都没给老子拿过。嘿,老子找得到钱,现在又想老子包包里的了,说是要在城里买房。城里的房得好几千块一平方,是金子银子建成的么?”
韩老五的话题有些沉重,秦大山不好接,只听他絮絮叨叨地说。到天快黑下的时候,秦大山的脸都喝青了,红着眼睛看韩老五。韩老五的脸也青了,眼睛鼓了出来。“下霜了,得穿上厚衣服。”秦大山说。
“热和得很。”韩老五挪着大舌头,问,“霜……是天上下的么?”
秦大山摸了摸后脑勺,霜是咋成的,他不记得了。好多东西在学校学过,都一股脑儿还给了老师。他现在脑子里一团浆糊,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从镇子里出来,两人分了手。韩老五在前面走,秦大山在后面走,枯草夹紧的山路被两人踩歪斜了。一回到家,秦大山便倒在床上。第二天要抠藕,秦大山一早便被老婆叫醒了。秦大山感觉脑袋有点重,晚上梦见好几个人请他喝酒,一个妖娆的女人端着酒杯嗲嗲地说她在村口的桥下等他,她就喜欢大山这样的好男人,实在。秦大山沉浸在梦中,这辈子没有那么妖娆的婆娘跟他说过话,更不用说给他敬酒——这都是前辈子修来的福分。秦大山的老婆是邻村的,打的娃娃亲。小时候觉得没啥,除了被人拿来玩笑害羞外,他都不太在意。读初中的时候,秦大山对同班的一个女同学印象极好,但人家不太理会他。娃娃亲的事情已经闹得全校皆知,似乎一切天注定,不可更改,再有非分之想便是道德缺失,天理不容。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秦大山有些心灰意冷,把青春的冲动掐了,只偷偷在操场上觑将来的另一半,长相周正,挑不出啥毛病,心里也就安稳了。婚后,老婆对他说,大山尊重人,不对她乱看,别人说东道西也不反驳,心眼儿瓷实。更让她感到放心的是,秦大山在学校里没有和其他女生眉来眼去过。都是什么逻辑嘛,一般儿的长相,一般儿的成绩,还倒数着呢,在一起算是凑合了。秦大山没说自己喜欢过其他女生。结婚的时候,他被长辈们灌了好几杯酒,看着眼前的女人,觉得格外亲切,只想困觉。秦大山喜欢喝几杯,特别是儿子出去打工后,下塘捞鱼抠藕的事主要落在他身上,累乏是自然的事情,喝酒便成了一项特权。他不喝,老婆觉得不正常,眼眉儿看他都要乖觉一些。于是,养成了习惯。
秦大山醉了,把和韩老五一起喝酒的事情忘在了梦里。梦里还回到了上学的时候,曾经喜欢过的女孩子对他笑,伸手去拉,人家化作一溜烟。好不容易冒出个说话嗲嗲的女人,女人容貌赛过镇子上的豆腐西施,甚至还要美上几分,劝他喝酒,还说在桥下等他。秦大山耽在梦里,不想出来。但抠藕的事情不能不做,即便他不记得,老婆还记得清楚。
水塘在村头。秦大山挑着箩筐,沿着小路往水塘走去。道路两旁的草叶上,露珠不再晶莹,有些灰白。腰带似的薄雾在山间游动,慢慢延展到水塘里,和升起的雾气融在一起,渐渐弥散开来,盖住了水面、沟壑,低洼的大地变得混沌起来。水塘旁堆扎的稻草垛在乳白色的雾气里黯淡,像一个敦实的小胖子留下的影子。秦大山觉得那影子特别像儿子的背影。送儿子外出打工的时候,也是这个时节,儿子慢慢走进雾气里,把背影留给自己。儿子许是回过头给他说过什么话,但他没有听见。乡村的寂静会让人生出许多幻觉,好像那些熟悉的声音在四处回荡——尽管那些熟悉的人已经陆续离开了村庄,但他们的声音被山间的岩石、路边的树木和草叶收藏起来了,时不时溜出来吼两声,仿佛他们一直都在。
秦大山觉得有必要去看看那个敦实的背影,好像儿子的声音就藏在那个模糊黯淡的影子里。他放下箩筐,点了一支烟,辛辣的烟味从口腔窜上脑门儿,把宿醉冲了个趔趄。一件衣服匍匐在稻草垛子前,像还在瞌睡的人形。秦大山把要吐出去的一口烟吞了回去,喉咙像被人捏了一把,他弓下腰,剧烈的咳嗽把晨雾撕开了一道口子。
秦大山没有看错,睡在地上的那件衣服正是韩老五昨天穿的呢子大衣。
韩老五窝在稻草里,脸上挂着笑,但四肢已经冰凉。秦大山蹲下身子,想要给他揉揉,让他暖和,但韩老五不配合,刚扶正又倒了下去,让秦大山很是为难,把要给他暖和暖和的念头掐灭了。
派出所民警赶到的时候,雾气已经消散。韩老五的尸体依然歪斜地窝在稻草里。周围站满了前来围观的村民,有熟悉韩老五的,也有听过名字没见过真人的,都挤到草垛前,仔细打量这个笑着离开世间的人。场面肃穆而又诡异,大家保持了对逝者的尊重,嘴里发出莫名的叹息或是嘶嘶的声音,仿佛吃了一撮辣椒面。
一个民警开始对韩老五的身体进行检查,翻眼皮,又用带了橡皮手套的手指掰开嘴,嘴里有食物的残渣,混合着酒气和死亡的气息,让民警的眉头皱成一团。整个过程没有大伙儿想象中的复杂。“是醉酒后猝死的”,民警说。
这个论断打散了村民的沉默。大家开始小声讨论,对韩老五的死因进行深入分析,声音渐渐大起来,覆盖在鱼塘的上空。几个民警对村民们的讨论没有兴趣,这类似的情况,没少见过。一个瘦高个的民警大声问:“谁最先发现的?”
秦大山身子抖了一下,像个犯错的小学生一样举起右手,瘦个子民警带他到一旁问话。秦大山心里打鼓:如果韩老五的死和自己有关系,那自己不也就成犯人了?!他战战兢兢地问:“所长,老韩真是猝死的?”
瘦高个的民警对秦大山的态度很满意,特别是称呼他所长,让人听着就很舒服。民警问得很简单,也很关键:时间,地点——地点就不说了,明摆着的;尸体动过没有?秦大山小心回答。民警一一记录在本子上。
秦大山有点恍惚,上学的时候没少犯错,规规矩矩站在讲台前接受老师批评,和眼前的情景一模一样。这让他有些感慨,不由得想起晚上的梦来。兴许那就不是一个好兆头。算命的俆瞎子不是说过,半百发春梦,万事都蹉跎。秦大山觉得蹉跎就是戳脱,没得搞头了。
一场春梦,祸事就落一坨。民警开始询问韩老五和谁喝了酒。怂恿喝酒出了事情是要负责任的。民警这句话把秦大山潜藏在脑子里的一点侥幸给消灭了。他眼神迷茫,已经消失的雾气从山沟沟里飘出来,飘进他的眼睛里,一切都显得混沌模糊。民警又问了他一句,他才从迷雾里醒过来,用蚊子般的声音回答。
民警对秦大山的答案有些诧异,合上本子,咂了咂嘴说:“这下麻烦了。”麻烦的是秦大山。
匆匆赶来的村主任赵军和几个民警嘀咕了好一阵子。他两撇眉毛皱成了川字,一口烟接一口烟,走到秦大山跟前,刀子似的眼光把秦大山从上到下刮了一遍。秦大山后背起了一层毛毛汗,一股凉意凝聚在头盖骨上,让他打了个寒颤。
年龄比秦大山小好几岁的赵军叹了口气,喷出口浓烟,他用看儿子一样的目光盯着秦大山,半晌才说,最好协商解决,不走法院的路子。赵军没少吃秦大山送的鲜鱼和莲藕,一想到那些鱼和藕,他恨不得立马从兜里掏出钱来,把以往的费用给补上。
于事无补。赵军晃了晃脖子,他对秦大山说:“找几个人,把韩老五的尸体先弄回去,给他儿子打电话,回来办丧事。办事的钱你先垫着。”他拍了拍秦大山的肩膀,“多给人家说说贴心窝子的话。”
秦大山咧了咧嘴,表情看起来像哭又像笑,他说:“老韩和我是过命的交情,这钱得出。”
“这不是交情的问题,参与喝酒的有你吧,现在人死了,活着的还不找你扯皮?” 赵军觉得秦大山脑袋转不过弯,萌生出要上前踢他一脚的冲动。
“好些人都跟他喝过。”秦大山嗫嚅着说。
“这——就是过命的交情的事儿了。”赵军说,“你就按我说的办,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说着,转身看几个站在一边抽烟的民警,说,有我们帮衬着,你就不要吝惜那几个钱。
几个村民抬着韩老五回家,秦大山在小卖部给每个人拿了一包烟。家里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的新被单盖在韩老五的身上,粉红的被单上,大红的花儿翠绿的叶儿暗金色的鸳鸯在风中晃晃悠悠。众人看着秦大山一行人走上山坡,消失在青郁郁的树林里。不像死了人,倒是像办喜事。有人说。
丧事办得隆重,按主持丧礼的俆瞎子说的,该有的都有了。韩老五的尸体送回家,老太太当场就哭晕了过去。秦大山给老太太掐人中,老太太醒过来,有些呆滞。韩老五的身子放在院坝里成什么事儿,秦大山让帮忙的人赶紧抬到堂屋里。老太太缓过气来,坐在椅子上,拿手背抹眼泪,问秦大山啥情况。秦大山蹲在韩老五尸体旁,老太太问一句他答一句。喝酒是韩老五请的客这事他没说,该说的都一五一十地给老太太说了。老太太嗓子里抽了抽,跌坐在地面上,掀起被单,看韩老五的脸,眼泪又吧嗒吧嗒落下来。
老太太没少听韩老五说起秦大山,在老伴儿的嘴里,秦大山是个好人,值得交往。老太太相信自己的丈夫,也坚信秦大山是好人。要不,秦大山不会这么热心把老伴儿的尸体送回来。老太太哭了一会儿,挣扎着起来给秦大山煮鸡蛋。秦大山说:“韩老哥是我过命的老哥子,他走得仓促,该办的事儿得办,嫂子你给娃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回来一趟。这办事的钱我来出。”
老太太不哭了,只抹眼泪,眼泡肿得像核桃。她想了想说:“这是老韩的命。”
秦大山悬着的心落回到肚子里。
从外地赶回来的小两口对老人的意外去世有些震惊。灵堂已经搭起来。小两口扔掉手中的东西,扑在韩老五的尸体上嚎啕。那儿媳妇声音尖厉,把喇叭里的丧乐都给压了下去。吃了两天一夜的白事酒,韩老五下了葬。
小两口对爹的去世耿耿于怀,在秦大山再一次的讲述中,时不时插嘴,带着审讯的意味,仿佛要从秦大山的话里抽丝剥茧,找寻些蛛丝马迹出来。几天下来,历经多次问讯的秦大山,应答得已经炉火纯青。他避重就轻,强调自己和韩老五一见相识,从相识到相知,再到忘年之交的过程。话语断断续续,过程却串联得无比通畅。老太太插了话,秦叔叔和你们爹是过命的交情。
小两口不再用带有敌意的眼光看秦大山。秦大山保证,今后韩家有什么事他都会来帮忙。小两口要继续外出打工,老太太喜欢吃的鱼和藕逢场就会送过来,田地里的活路自然也要帮衬……秦大山觉得自己对得起有过命交情的韩老五了。
一场丧事,秦大山花了一万多元。韩家人不提这笔花销,秦大山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吞。赵军说了,喝酒死了人参与的人都得赔偿,主要的人员赔偿更多,少则五六万,多则十几万。里面的人情世故更是掰扯不伸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好。
和韩老五那天一起闹酒的人没一个来。秦大山做了朋友应做的事,是一个重情义的人,赢得了村民的赞誉。坐在市场上卖鱼的时候,他看那些昔日熟悉且主动和韩老五套近乎的人,他们面目和蔼,礼貌周到,对秦大山也恭敬,却没有一个人提起和韩老五喝酒的事。他们本来也该出点钱的,秦大山想。
但他想不明白的是,镇子里的人对韩老五的死因突然热情起来,许是镇子里没啥新闻,缺乏谈资。国家大事不是小镇人操得了心的,欧美大陆距离小镇又显得太远,讨论不出啥结果;探讨探讨土地款补贴,某某人挣了钱衣锦还乡修桥铺路,或是返乡创业种点啥值钱的果树有什么不好?
秦大山对“霜冻大,能冻死人”的说法比较赞同。关于韩老五死于醉酒的说法,他无法反驳,只能保持中立,也封不住别人的嘴,反驳的言辞反倒让自己处于不利的位置。用赵军主任的话说,他负有主要责任,一定要设法脱出身来,哪怕是像酒馆的老板那样,对韩老五喝酒猝死的事情宁肯不说一句话,也照样来找他买鱼买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是传了不晓得好多辈人的至理名言。
秦大山以韩老五老朋友的身份,对那些胡乱猜测的言辞进行委婉的纠正,有点拨乱反正的意思在里头。牛经济韩老五火眼金睛,两根指头定牛之前途;韩老五转行卖牛肉,山间草牛成了城里人桌上的美餐,抖皮鞋穿呢子月进斗金……关于韩老五的诸多故事从秦大山嘴里出来,更具真实性,满足了众人的好奇心。一些熟悉韩老五的人开始回忆和韩老五交往的点点滴滴,回忆起以前饲养的那头耕地草牛,不免唏嘘。
秦大山对自己说出来的话语深信不疑,他很满意这些话,这些话产生的效果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把那些胡乱猜测的言辞带回到了模棱两可的正道上。坐在板凳上,望着离去的人们,他有过惭愧,但那一丝愧疚很快被丝丝缕缕降落的寒意给湮灭了。他想,趁着不赶场,得去把老太太那一亩多地的油菜栽种了。
立冬过后,万物蛰伏,也孕育着新生。秦大山苦苦营造的氛围终究被一个电话打破。关于韩老五是死于和秦大山醉酒后的事情,越过山梁沟壑,隐隐伏伏,兜兜转转,最后溜进了韩老五儿子小韩的耳朵里。
小韩怒不可遏,对秦大山的那一丝微不足道的好感瞬间灰飞烟灭。他在电话里对秦大山说:“姓秦的,亏你还是我爸的好朋友,你是把他往死里弄啊!这事儿没完,咱们法庭上见……”
小韩是真生气,秦大山的电话差点被他吼破。捏着手机,秦大山觉得后脑勺被人用棍子敲了一下,嗡嗡作响。他有些张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了,脱了叶的树枝斜斜地刺向灰白的天空,塘堰里的残荷败枝扭曲,朝淤泥里钻。他站在原地,寒气缕缕从空中降落,他想,狗日的霜肯定也是这样从天上落下来的。
秦大山脸色灰白地回了家,拧开酒瓶狠狠灌了几口,才缓过气来。他捞了两尾肥大的花鲢,提着几截藕往老太太家里去。婆娘在身后喊他加一件衣裳免得受凉,也没听见。缺了门牙的老爹坐在门槛上,看儿子走得歪歪倒倒,对儿媳妇说:“我要吃鱼,要喝酒。”
老太太对秦大山的到来没有显出以往的热情,她说:“大山,我胃口不好得很,不想吃鱼。”秦大山放下鱼和藕:“肠胃不舒服?我去找个医生给你看看。吃不得鱼莫啥,这藕脆生生的,凉拌好吃,炖肉也好吃……”
老太太抹了一把眼睛,拖着哭腔说:“大山啊,一看见藕,我就想起我们家老韩来了,他以前老给我买藕……心里难受,难受得很。”
老太太是真哭了,哭声干瘪,如同颈脖上的皮肤,软塌塌没有水分,让秦大山手脚无措。小韩肯定给老太太也打了电话,看来最后一点转圜的机会也掐断了,他叹了口气。老太太坚持不收他带来的东西,两人在院子里把彼此的坚持粉碎成一堆渣滓,让远远看的人感慨,韩老五这辈子值了,有这么好一个朋友,这份情谊比得上古人。
夜幕降临的时候,秦大山拖着沉重的步子进了村主任赵军的家。赵军说:“老秦,你情绪低落哦。”主任的女人伸手去接秦大山递过来的鱼和藕,赵主任咳嗽了一声,忙缩了回去,仿佛那些东西烫手。赵军吩咐女人,捧点花生出来,和老秦喝两杯。屋子里冷嗖嗖的,秦大山把要说出口的话咽了下去,找了借口放下东西就走。赵军追了出来,把东西重新塞回到秦大山手上,安慰说:“老秦,没有迈不过的坎,该帮衬的我一定会尽力。”
草枯路白,蜿蜒如鳝。狗不吠鸡不叫,万籁俱寂,只有点点灯火在远处闪闪烁烁。秦大山突然有茫茫世间只余自己一人的错觉,他呵呵笑了一声,把提在手里的两尾鱼和几截藕扔了出去。鱼鲜活,藕水灵,在空中划了道弧线,掉进黑暗里。
赵军没有糊弄秦大山,一心一意要闹上法庭的事,在赵军的斡旋下,成了民事调解。按照小韩小两口的意思,秦大山是酒局的组织者,对韩老五的死负有主要责任,怎么也得赔偿个三四十万。韩老五转行做肉牛生意一年收入十来万,前途一片光明,如果打开了局面,那还得了,就是在城里搞几个门面做生意也不成问题。小两口思维活络,也有苦衷——在城里工作多年,朋友多应酬多,挣钱的速度又赶不上房价上涨的步伐,谋划多年的购房计划在父亲醉酒猝死之后,蓦然间柳暗花明。小韩甚至对韩老五的意外去世感到庆幸,这个念头虽然只是在和妻子为购房斗气时突然萌生出来的,但那种如同蚂蚁爬过脑髓的感觉让他记忆深刻。他跑进厕所里狠狠抽了自己两个耳光,满腔义愤地给秦大山下了通牒。
赔偿的过程繁琐而又漫长,缠上官司更会让人筋疲力尽。经过赵军主任等人的斡旋,小韩果断地选择调解。对秦大山,他恨不起来,他需要的是钱。一个在小镇做生意的农民,能有多少积蓄?这也是他担忧的地方。双方在小镇的茶馆里达成协议:秦大山本着老朋友的情分,决定拿出二十万元对韩老五的死亡给予补偿。秦大山本不需要赔偿这么大一笔钱,给韩老五敬酒的人不在少数,熟悉的,凑热闹的,都是街坊邻居,乡里乡亲,生意上的老主顾,谁撕得下这张饱经风霜日渐苍老的面皮,让人家也掉入这纠纷中来?秦大山表示,自己的确拿不出那么多现钱,得分三年才能给清。小韩满脸不乐意,被婆娘在凳子底下掐了一把,想了想便勉为其难地同意了。城里的房子尚且可以按揭,对于做小本生意的秦大山为啥不能宽容呢?小韩对女人的看法深表赞同。兔子急了还咬人,把卖鱼抠藕的秦大山憋急了,出个意外,别说二十万,一分钱都别想拿到手。
摁了手印,小韩把协议对折了两下揣进怀里。秦大山和韩老五结下的情谊在这一刻画上了句号。老太太眼泪花花,她不敢看儿子和儿媳妇儿,直到小两口走出茶馆,才抬起头,泪汪汪地对秦大山说:“大山啊,油菜地里草长得老高了……你还来看看我不……”
秦大山不看老太太,瞥一眼茶馆面前的百年黄葛树,黄叶在空中打着旋飘下来,落在地面上,细风吹卷,缓缓向角落里移动。“冷起来了,明早儿有霜。”他说,“等几天我就过来收拾。”老太太嘤嘤地哭着走了。秦大山双腿发软,他没有送这个孤苦伶仃的老人离开。和老太太一样,他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
坐在茶馆里,秦大山给儿子打了电话,赔偿二十万元这么大的事情得让儿子知晓。秦大山的表述断断续续,仿佛欠了儿子很大一笔账,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儿子竟然出奇地冷静,听完他的讲述后,只淡淡地说:“你也要少喝酒了,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秦大山鼻子有些发酸,儿子在城里跑外卖,辛苦不说,挣的钱不多,自己没能帮贴他,反倒多出些外债来,秦大山觉得对不起儿子。
临近春节,生意愈发好起来。秦大山跑城里的次数多了。早晨,村庄和镇子都还沉浸在梦里,他就骑着三轮摩托出发了。霜凝结在草叶、油菜、青菜上,白晃晃一片,像下了一场小雪。不赶场的时候,秦大山穿着破了洞的皮裤在塘堰里抠藕,寒气刺骨。赵军好几次路过,看见秦大山抠几段藕,又猛喝两口酒来驱赶寒气,突然生出戒酒的想法。不喜欢吃藕的赵军每场必买五斤鲜藕,说是吃藕肠胃好,让婆娘埋怨了好几回。
这天,赵军还在做梦,梦见自己和秦大山一起抠藕。小时候,他跟在秦大山屁股后面,上山掏鸟下河摸鱼。长大后,两人一起上学,虽然不同年级,感情还好,遇到高年级学生欺负他的时候,秦大山第一个站出来维护他。初中毕业后,他外出务工,当了个小包工头,招呼秦大山来挣钱,秦大山要照顾家中老人走不掉。忽忽数年,赵军回来了,创业养猪,又当了村主任。秦大山承包塘堰,他也没少出力。在小镇上卖鱼卖藕的秦大山打心眼里感激赵军。
那晚没收秦大山送来的两尾鱼几截鲜藕,赵军颇有些后悔。好些天,吃饱了藕的赵军就发梦,梦见和秦大山一起在淤泥里抠藕。
电话是秦大山女人打来的。女人哭哭啼啼地说:“大山掉河沟里了,早上进的货也掉河里了,钱都打了水飘……”
赵军问:“人呢?”女人抽泣着说:“他断了条腿,被人送卫生院里去了。”赵军松了口气,安慰女人:“人活着就好,我去医院看看。”披了衣服,骑了摩托车,朝卫生院赶去。
秦大山命大。进货回来的路上,晨雾里依稀看见前面有个人影,车头一打,向着河里栽落。鱼归大流,藕飘河面,秦大山被一截从岩石边伸出来的树枝挂住,他的腿是树枝断了后跌断的。赵军搓着手,连连感叹:“幸好幸好。”
“俆瞎子说我还有好多年的福要享,死不了的。”秦大山拍着赵军的手背说。卫生院里,赶回来的儿子看着父亲。父亲脸更黑了,白头发多了好些,趴在两鬓耀武扬威,不由得鼻子发酸。“不想出去打工了。”儿子说,“我想在镇子里找个门面,专做水鲜生意,除了河鲜还做海鲜。”
秦大山想骂这个儿子,不争气呢,还有几十万块钱的账要还呢。话到嘴边出不了口。他说:“也好。我这腿要好几个月才能好,你韩老爹家的几亩地就靠你了。”给他削苹果的儿子“嗯”了一声,说等几天就去看看老太太。
憋了好久的秦大山忍不住了,他问儿子:“你读的书还没有交还给老师吧,你说说这霜是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
“你说啥就是啥。”儿子把削好的苹果递给他。秦大山啃了一口,瞥了瞥儿子,含混不清地骂了一句:“你个狗日的,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