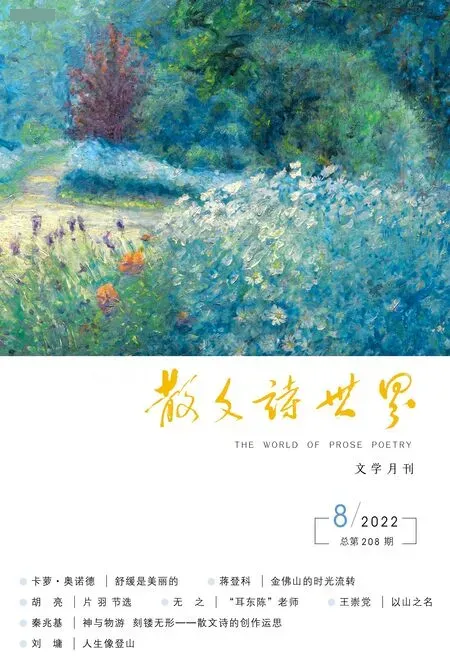楠木遗事录
吴婷婷(云南昭通赤水源高级中学)
“天秋木叶下,月冷莎鸡悲。”半轮秋色照着异乡异客,唯有一片月与故土相近。像糖葫芦一串地穿过记忆,谁都不愿勾了丝的甜,不敢触及心底的渊。无月夜偏说月,您权当是在木叶纷纷下的夜里,月华流照,我为您絮絮叨叨地讲些有关楠木村的旧事罢。
我所在的楠木村并没有楠木,竹子倒是满山遍野,这种矛盾的取名方式有些红楼梦的味道。海棠无香,非要用“红香”来指代,颇具揭短的嫌隙;芭蕉本是草木,可也嫌它上不得台面,非得加上个“玉”字,以“绿玉”来代,方显得它多金贵似的,也不说到底是金玉俗,还是草木之重,难用他物来比拟。
村里人也有他的偏执,楠木贵重,虽无此物,用了这名字,也算是讨了些喜气,到底是好的。
隔着很久一段时间的距离,我回乡里,在镇上的一个街道边,等来接的车。爷爷背着背篓,背佝偻着,像是压弯了,放背篓在旁边等车时,背也是弯着,不像是背背篓的事。背着的那时,像是就放一个东西,立马就会压断了他的背,才是突然感叹到:年轻是真的好啊,任意自然,随心随性,洒脱又有力。
年轻的时候,年轻人总是不注意年轻的好的,更不会顾及。遥想当年,爷爷也是可随意地扛着两三百斤重量的肥料,走过几公里的路,去往快如风。可“老”是时间的利器,手刃年轻里各色的“匆匆”。而这次的旧处新游,负着好几圈的年轮,我亦不再年轻,再次踏上故土,村景呈来,有触及不到的亲近,熟悉又陌生。
流光容易把人抛,颜色纷纷染上树梢。竹林里的樱桃红了一遍又一遍,我是好久的未见花开,未得其果了,甚至其落叶时的衰败也不见得是有注意过多少次的。入林石砌的小路窄了许多,草色的青苔铺着,满处的落叶子,走过去了是一路沙沙的叶碎之声。
土也被各式的草占据,下不去脚,茅草长疯了,在风行过的时当里,一簇簇地高举着身杆,洒着漫天的茅花,没有人迹的参与,显然是有些迷乱了。
家里木质的老房,好些年就已经拆掉,老辈人里认为最好的木头拉出的木板子被用作了柴火,在迸发出最后一朵热烈的落红后,成了灰,化了泥了。空空荡荡,只留着这大块的老屋基,满满当当全被种上了蔬菜,竹条制的篱笆围成的园子,片片青绿。
路旁有处不大不小的芭蕉林,初地里,还是几株小的苗子,不知到底是何时竟成了这片林去了。日影斑驳透过青绿的大叶子,晶绿的光影子映在地面来,是一块块淡淡的清晖。
蹀躞青石上,过去的时光也这样过去,一步一攀越,一步一跫音,都是生命的绝色。听耳畔微语,攥一缕手里的余温,在楠木村这里有回首可触的暖意。浓密的树影子盖上眼眸,每一次的伫立,我与它之间就多了一份缱绻。树叶子正是繁茂,它会把所有村里人的故事都凝成木叶之脉,而总有一片是关于我的。
童年的时光总有些温暖的东西,随着岁月的洪流不知不觉地落在一路孤单的狂沙上,像初夏凉池子里突然冒出的一只青荷,使人心生惊异,有一种清浅的快乐。
后来在无数的波卷浪淘中,再是多不平,我们仍然能从那些浅浅的快乐里得到慰藉,而那些快乐历经长河,无需指挥,也无需特定的曲谱,句句妙音。它紧紧拽着你手里的小轻愁,安抚那些你心底不安的小情绪。
林深处的小户人家,竹子四处地围着,朱红色漆的小木房上是青黛瓦片盖着的屋顶,高远之处,碧海中隐现着缕缕的青烟。东风闲来,院落的桃花枝满,是温润的红艳。新芽添生,以悠然的模样散发着浅淡的温柔香。远处的柳絮是片片碎去的朵朵流云,结着队地要去模拟一场正月初里曼妙飞舞的轻雪,洋洋洒洒,直直入了这处处的木花窗。
莺飞种柳,细草纤纤的绿茵上有些清明时节里的酒意,山花正盛,点点的黄白红紫各处铺陈,一袭清风,花气和应。踏着青石板阶,在门前侧边下的方地,苍苔绿影,清溪缓缓,带着远山一路里的繁花,直扑这溪底的圆石,满处的水珠子溅出,一处处的白净水花响出哗啦啦的音。晨阳斜照,山涧的流云拂过,竹影婆娑,林泉悠悠怡然的闲情样子,向着碧海的林深更远处。
明月光像是霜白的雾样子,轻纱一般盖着木小屋,光在院落里折出一道痕,半是明来,半是“夜”。夏夜时的我们向来是不爱呆在这屋子里的,闷热得紧,大多是敞开着门,一家子抬出小的木凳来坐在院落的葡萄藤架下纳凉,闲谈着有的没的各种趣事。爷爷奶奶最爱手里拿着一把棕榈树叶子缝制的圆扇,红色的边线,挥动着,代了这电动的风扇,驱走吮血的蚊虫。
我们几个孩子有时间就会把自己藏在这两个老年人当中。他们的世界里,有永远都难以想象的丰富。与他们谈着的时间里,有各种的故事——有听来的,亲生经历的,假的与真的,或者是各种的唠叨了。两个老人也喜欢和一帮孩子一起,在孤独者的宣泄里,孩子是最好的听众,谈着的过程也总是开心的,有讲有听,有说有笑,相互配合里相互取暖。
山清风色,月明安宁,天朗气清的光华最是亮白,映在边围的竹叶上,满处如同银光的鳞片。那时候的我们是坐不住的,被这夜里许多的流萤羁绊住,倒是围着这院子疯跑了好几个来回。抓住了它,去放在风干的有着白色纹理的萝卜壳里,做了这天然的萝卜灯笼,便是一片的笑语。
好雨知时,如帘珠般淅淅落下,线似的直,嗒嗒滴在青黑瓦上,顺着房檐低处形成几条细丝雨线,随着高山处里流着的山水涌入江水溪流。大雨嘈嘈,细雨切切,于荷塘,于碧竹林园,于青石板阶,落下后是升起的轻纱雾,长风万里流过的绕指柔,是物华新的仙境地。雨后的花阶,山林清音,竹声细曲,鸟叫虫鸣絮絮而响。下过雨了,隔壁家田里的鱼儿估计也漫出来了,我们拿着渔网是赶快地网鱼去了,若是遇着下太阳雨,这倒是个生菌子的好时候,还得往山林里去,满满的收获,总不会白跑一趟的。
秋霜是叶的春时,叶华如花,它总不是单一的绿调子,树树斑斓如同繁花春时的盛放。农忙收成,乡里的爷爷戴着遮阳的草帽子,竹制的大背篓背着,手里还牵着这陪了好些年的老水牛,步履安然,渴了,饮路边的山泉水,累了,便闲坐于路旁的大树底,山水林音,亦是乐心真意之事。夜幕在黄昏的手中慢慢打捞,天色越来越沉,爷爷回来,他的手里绝不会空着,他一手牵着牛,一手就会有我们感兴趣的鸟蛋或者是小时最爱的野果。
冬时,事最少,闲时颇多,火炉子烧得最旺,方的或是圆的大盘子是统一的火的红色,锅子里扑通地煮着一家子爱吃的火锅菜。雪如盐白,鹅毛般轻盈,仅一夜之间便覆尽了所有的涂色。大冷的天,谁也不爱出门,奶奶便有条有理地说着在冬雪地里能捡到寻食的鸟儿,野兔子遇见了人,是冷得跑不了的,只得把头埋进雪里,任由人如同萝卜一样扯起来。我们几个孩子也信了真,一脸的兴奋在她的带领下出了门。银装素色的片地,老与小的脚印子如同一串串相和的音符,发出步步踏雪的窸窣声,满目的山清林寂,空净自然,自是无所获得,然此安乐则无从附加。
没有手机干涉的童年,我们有太多自己的安排。去山上拾柴,没有蛇虫蚂蚁危险的概念,我与阿妹总要先趴着睡一觉,最后去砍上一捆柴慢悠悠地背回家。在林子里,我们有自己的乐趣,草坡上的草比我们还高,我与她偏要来一场爬坡的比赛,看谁更快些到达顶上,现在再去看幼时那坡草地,我是再不敢进去,更何况是比赛了。
蚂蚱是我们玩弄的重要对象,被抓住后的它将会被拔掉能弹跳的后腿,用树叶裹成婴儿的样子,我与阿妹会在林中用石头围成它的小屋,用叶子铺上一张床,样子简陋,枕头和被子却一样不少。被裹住的蚂蚱,我们会定时给它供给小虫子或是不知名的野草,看见它大口地吃,我们也非常兴奋。这整个过程,我与阿妹取名为“喂猪”,而蚂蚱则被冠以只有我们知道的“猪”名。张口即来的吃食,也没能使蚂蚱的命运变得有多幸运,我与阿妹在喂猪的同时还有其他好玩的东西把时间占去,多久后想起来,此猪早就被雨水冲走或被蚂蚁大军抬走,又得要换个新的了。若它运气好些,恰逢我们来,还能从排着队的蚂蚁手上将它夺回,避免一场“猪入蚁口”的悲剧发生,它的小屋还会重新修缮。
小小的年纪有大大的脑洞,也有坏坏的小心思和莫名其妙的勇气。有次清明节扫墓回来的半路上,我看到一堆稻草扎在一棵榛子树上,好奇心驱使我把手放进去试探,竟然掏出两枚鸡蛋,当时并不知,只知道会孵化出毛茸茸的小动物。拿回家来,我与阿妹把蛋放在肚子处,唯恐蛋变凉,整天在床上趴着,学母鸡的样子进行孵化,期待自己也能拥有一只毛茸茸的鸟宝宝。最后我那颗蛋,因意外而摔碎,而阿妹一人孵蛋也觉得无聊,这一场闹剧才告结束。
一起去山里游玩时,我与阿妹演起了被父母抛弃的戏份。整个下午,都在假装的忧愁里度过,一部姐妹情深,相依为命的大戏在夕阳的打光下慢慢展开,我与她都是最好的演员。
阿妹的脾气从小就有些火爆,鸡枞菌疯长之时,她同我一道去林里察看,许是才受了批评,心中有气,我提醒她路边有蜂窝的事,她也不在意,直直过来,碰到了树枝,更是惊得更多的野蜂朝我们扑来。我按着老辈人所说的经验,蜜蜂看不见趴着的人,于是大叫着:“快趴下!”她也识趣趴下,可有些不情愿的念头,竟忘记屁股还高翘着,被蜜蜂逮了个正着。这时候,她听不见我的劝,气也更大了,索性与这堆野蜂斗到底。她爬起来穿过蜂窝,引得一路野蜂的又一番“追杀”,许是战火太过猛烈,惨叫声传遍了整个山,吓坏了借着放牛的时间在山坡上用青蒿杆子拼刺刀的两个弟弟。
阿妹年纪小,按着大孩子要让着小孩子的理论,我常常要受更多的气,有什么好处也轮不到我,这就滋生了我嫉妒的仇恨之心。农村的孩子很难买一双新鞋子,孩子多的家庭更是如此,在眼睁睁地看着家里人为阿妹新添了一双粉色凉鞋,而又没有我的那份之后,我让她拿着鞋子去房屋后面玩耍。我的凉鞋早就坏掉,围着脚踝处的鞋带子被我割掉成了拖鞋,我穿上它极力炫耀,并且口中还念念叨叨:“我有拖鞋,你有吗?”表情洋洋得意,成功使得她把才买的凉鞋割成了拖鞋。后来等她反应过来,被家里人一通大骂,我在隔壁只听得她哇哇大哭的声音,却有一种大仇得报的畅快。
年纪是个不断向外拉着的线,后来我们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比不得还小的那时了。我们各自揣着手机,放着不是秘密的秘密,藏着掖着,无形中隔出几座孤独的岛。
可我们终究不是单行道,那些我们一起奔赴的日夜,终会化成清淼,流过我们彼此的山川岁月,在我们寂寞的沙洲上迎来历历的晴光春色。
往事回望,谁不是热泪盈眶。
几度叶底藏花,几回梦里踏雪,热闹在岁月中逐渐沉寂,整个村所有的屋舍,木色换了石妆,小木屋流去了记忆奔腾的长河里。村中人也大多去到了外头,热闹重归自然山色。
在楠木村这里,从村头到村尾,一花一树与几人的交集,我仍有未尽的情,未完的话。花声相叠,日星隐耀,生活与周遭的剪影都是童年曼妙的舞姿新色。多年后回过去看,除去双眸里所见的这虚设的富华景象,这一草一木的欢悦,恰需要这样一个难得的太阳。——眼睛看得见万物的悲喜,而阳光照耀一切。
再次回乡,我的那份童年不可避免地化成一声叹息,就算自己死性不认,群树也会起来作证。年纪越大,与村之间的线就被拉得越长,村以薜荔为衣,树越是茂盛,越感觉像都变成了一堵绿墙,加重了我与她之间的隔阂,物非人非。
几个孩子在大门口外的宽亮处嘻耍,小小个的样子,一个个接起来玩着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欢笑着,汗流满面。我从旁而过,看看他们,再看了看自己,不服老是真不行了,年轻到底是十分好的,快乐不过那么些年,过去了,就真的是过去了。
从别后,他乡成同乡,故乡变异乡,更多的时候,不仅是对人,哪怕仅仅是一朵花的影、一片叶的青绿、人潮聚散……这些都落在时光的洪流里,于我千万难。
寥寥秋色,应念故城风,席卷木叶以入怀。牛绳子做的秋千索,把整个关于楠木村的童年梦也翻过去,故事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