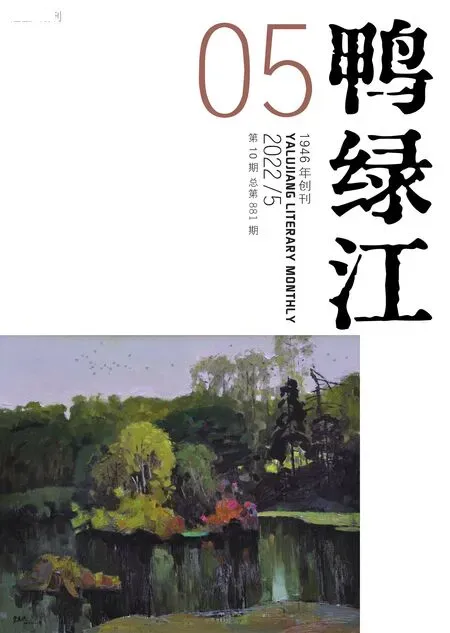崖上的鲸鱼
安昌河
老陈不在家,小耳朵坐在院坝里。老温给老安打电话说,老陈不见了,电话也打不通。老安说,他应该走不远,小耳朵在院坝里,他咋放心呢?老温说,小耳朵跟个菩萨样一动不动,有啥不放心的呢?老安问小耳朵看起来咋样,老温说能咋样呢。老安说,你赶紧给老秦打电话,让他快点过来,我马上也到了。
老温走到小耳朵跟前,手在他眼前挥了挥,小耳朵翻翻眼皮。鲸鱼游到哪里了?是在崖壁上还是在山峁上?小耳朵张张嘴,呜呜啦啦几声。老温叹着气说,你就不能讲清楚点吗?小耳朵又呜呜啦啦两声。老温说,它还在吗?不是每年冬天它都要回大海里去吗?
从小耳朵的表情来看,那头鲸鱼没有离开,可能还在崖壁上。他试图指给老温看,但没有力气抬起手来。起风了,老温要把小耳朵挪进去,小耳朵扯起了哭腔,他不肯离开,他要继续看那头鲸鱼,他慢慢地转动脖子,那头鲸鱼应该正从崖壁那头游过来。
晚霞映照着下面的山谷,映照在对面崖壁上,崖壁和崖壁上的那些树木都闪耀着金光。那些树叶才经了几夜的霜冻,就红彤彤一片,风一过,像蔓延的火焰。老安教过书,眼睛能看见老陈和老温他们看不见的美,心头能触碰到老陈和老温他们够不着的事,所以,他相信小耳朵。在他的劝说下,他们也都相信了小耳朵,相信了在山谷里游来游去的鲸鱼,相信那条巨大的鲸鱼总会在傍晚来到崖上采食那些金色的晚霞。
老温见老安满头大汗,忙上前,要从他手里接过纸箱。老安说后头还有一个箱子,你去接一下。司机气喘吁吁,将箱子递给老温,叮嘱他小心,里头可都是汤汤水水。
老安跟老温讲,吕品成要亲自送的,他不让,人家今天可是新郎官呢。老温打着呵呵说,两个老东西、一对新夫妻,你还跟他们讲究啥呢?老安没理他,径直来到小耳朵跟前,蹲下身子,看着他。
小耳朵脑袋肿得很大,磨芯般细细的脖子完全无力支撑,脑袋就耷拉在椅靠上,原本青灰肿胀的一张脸,此刻竟然有了点颜色,一半是晚霞的辉映,一半是鲸鱼带来的激动。小耳朵能说话的时候就曾经说过,相比海洋,鲸鱼在天空自由得多。水的压力太大,越深压力就越大,它必得使劲游,周身出力,拍动翅膀和尾鳍,一刻不停,才不会被洋流拽入海底。空气就不一样了,只要不是雨天,气流都是向上的,在太阳的照耀下,温暖的大地就总会生长出温暖的气流。这个时候,是鲸鱼在空中最惬意的时光,饱满的氧气通过肺部输送到骨骼和皮肉,浑身洋溢着自由和自在。
小耳朵还说过,离开海洋的鲸鱼,最喜欢在一早一晚采食晨光和晚霞。春天的时候它从遥远的海洋过来,越过平原,栖息在崇山峻岭里,因为这里的晨光和晚霞没有受到雾与霾的污染,它不那么费劲就可以从干净的阳光里采食到喜欢的颜色。春天的时候,它喜欢食用橙色和黄色;夏天它偏爱绿色和青色;秋天它对紫色情有独钟;临近冬天了,它除了火焰般的红色,偶尔也采食一点儿绿色。火焰般的红色会让鲸鱼感觉温暖,绿色会让它想起诞生自己的海洋。它就要离开这里了,回到海洋里去了。小耳朵说,他会随着鲸鱼一同离开,他不会再回来。鲸鱼会。鲸鱼会在春天回到山谷,回到崖上,继续采食晨光和晚霞。这话是他回到秦村那年讲的。三年了,鲸鱼回来又离开,离开又回来,他还留在这里。是鲸鱼不带他走吗?还是鲸鱼觉得没到时候?
老秦到了,老陈却还没有回来。一见老安,老秦就讲,那样的事情我可干不出来!老安瞪着他,啥事呀?啥事你干不出来呀?打电话叫你来,是叫你喝酒的!老秦看着老温,纳闷了,不是你跟我讲,老安的意思是要我来动手的吗?老温叹口气,说,我说是万不得已,现在还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嘛。老秦眼珠子转到老安身上,哎,你总听清楚了吧,这是你的意思吗?老安没有理会他,他小心地打开纸箱,从纸箱里往外取东西。都是打包盒,盒子里头是各色菜肴,保鲜膜一层覆一层封得严严实实的,但还是渗出了汤汁油水。老温和老秦都过来帮忙,却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只晓得把它们一样一样接过来,摆在桌子上,摆得规规整整的。
老安说,你们去拿碗拿盘子来嘛,装塑料盒子里像咋回事呢?不好吃,也不好看!老秦说,他那些碗盘子还没这盒子干净呢。老安说,你就不晓得洗洗吗?
老秦洗碗盘的样子叫老温很看不惯,伸出几根指头,生怕水把手打湿了似的。老温讲了他几句,你是纸做的啊?沾水就要化掉吗?老秦说,我在家从来没洗过锅碗呢。老温说,你家的碗盘子都是狗舔干净的吗?老秦说,你会洗,你来。老温一把推开老秦,碗盘叮当响,水花四溅。老秦后退两步,抖抖身上的水,嘿嘿笑。
菜很丰盛,凉菜,蒸菜,烧菜,还有炒菜。老秦以为都是吃剩下的,凑近了一看,不太像。看到镶碗,还有蒸鲲鸡蒸肘子,老秦啧啧地咋舌,还以为是残汤剩菜,没想到是一桌席呢!哎,咋个不见蒸鱼呢?现在的席桌不是都时兴蒸团鱼吗?
老安懒得理会他,小心翼翼地将打包盒的菜一样一样挪到碗盘里,再精心细致地恢复菜品的原样。
不愧是教书先生呢,做啥都跟绣花样!老秦站在一旁抱着膀子欣赏。老温左一下右一下在身上擦着两手的水,也过来了,要老安讲讲今天都啥状况,都来了哪些客人,秀妈还是那么胖吗?老安说,我这里跟你们讲一遍,等会儿老陈回来,我是不是还要再讲一遍?你们都别稳得跟八哥儿一样,该抹桌子抹桌子,该洗锅烧火就洗锅烧火,该上锅灶蒸一下还是要蒸一下!
老温和老秦在屋里忙着,手上乒乒乓乓,嘴里叽哩呱啦,年轻打捶,老了斗嘴,只要一碰面,他们就不会消停。年轻那会儿是武斗,动刀子动火铳,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老了就文斗,嘴巴上虽然不饶人,但文明多了,尤其是就近这些年,突然晓得彼此珍惜了似的,出口没了脏话,也都不再揭老底,一个人硬,另一个人晓得软。
小耳朵还坐在门口。暮色已经上来了,鲸鱼应该早不见了。小耳朵还是不肯回屋,他要等老陈。老安说上露气了,等等又该你难受了,回屋吧,回屋你爷爷就回来了。小耳朵不让他碰,趔趄着身子。老安摸出电话来打,打不通,不甘心,一遍遍地摁,他担心老陈,他没有理由不担心老陈,特别是今天。
迟迟不见老陈回来,老温和老秦也着急了。背篼挂在墙上,弯刀插在墙缝里,鹤嘴锄靠在门边……他不是去砍柴,也不是去挖药,他去干什么了呢?如果在村里,应该老早就见了他影子。他多半是往山上去了。可是去山上哪里呢?又去干什么呢?老温和老秦问老安,老安只轻轻叹气。老秦和老温知道,老安心头是有数的,老陈和老安讲的话多,他信老安,老安见多识广,心眼儿也算几个人中最好的,经他拿出的主意,一般错不了。
凉菜都端上了桌子,热菜都热进了锅里,酒也斟进了杯子里。酒是定制酒,上头印着大大的“囍”字,还有几行字:“吕品成先生和赵秀芳女士婚宴专用酒”“百年好合”“万事如意”……
老秦捏起几粒酥皮花生,一边嚼着一边感叹,说不及老白做得好,不管是椒盐花生还是鱼皮花生或者是酥皮花生,这方圆十里八乡,老白自领第二,就没人敢称第一。老白做的花生,香是自然,最难得的是化渣。咳,只可惜了那一身好手艺啊,要是还活着,土镇办厂,单卖个油炸花生米,生意肯定盖天地地好!
老温懒得听他嘀咕,出了门,和老安一起站在院坝里,陪在小耳朵身边。一阵窸窸窣窣,老陈回来了,走到他们跟前,摸摸小耳朵。小耳朵在哆嗦,不知道是疼还是冻的。咋不把他弄进屋里呢?老陈搂住小耳朵,小耳朵太长,两脚磕在地上,老安要搭手,老温先伸了手过去,抬住两腿。老陈说,老安你帮把手先把椅子搬进去。
堆在椅子里的棉被半截落在地上,裹住了老安的腿,差点把他绊一跤。椅子搬回到睡屋里,老陈指挥老安把棉被铺好,把小耳朵塞进去。正侍弄着,老陈抽抽鼻子,停下了动作。老安知道,这是小耳朵拉了。他去帮忙打了热水来,又拿了香皂,要继续帮忙,老陈让他们都出去,说你们还是不见的好,免得影响一会儿吃东西。老温觉得多个人帮忙,来得快。老安晓得光景,扯扯他的衣袖。
走到外头,老秦过来问是不是可以开动了,他这就把热菜端上桌。老安让再等等,老陈还在给小耳朵洗屁股。
现在究竟是个啥情况?老温问。老秦也凑过来听。啥情况呀,四个字来形容,惨不忍睹。老安叹息一声,说,后背全是褥疮,屁股上也起了,根本不能挨床,加上肚腹里的问题,只能蜷缩在椅子里。老秦跟着叹气说,前半辈子毁在娃身上,后半辈子毁在孙子身上,这个老陈呀,上辈子做了啥冤孽事呢?
老陈出来了,泼了盆子里的脏水。老秦问要不要给小耳朵整点啥吃的,老陈就像没听见。他当然不可能没听见,他只是懒得回答。老秦问第二遍,老陈才回话,要是吃得进就好喽。老秦还要讲点啥,老安见老陈要去舀冷水洗手,就戳了他一指头,说你去给老陈整点热水,老陈的风湿又犯了。老陈说没关系。老安拉住他说,你又不是缺柴火。热水倒进盆里,老陈两手浸泡了一阵,然后抓了洗衣粉细细地搓洗。
热菜端上来,摆满了一桌子。老陈要去烧开水,要给大家都泡上茶。老安不让,说等会儿再烧水吧,不然菜又凉了。老陈说趁着锅热,也就几把柴的事。
老陈挨个给大家沏好茶,又钻进里屋,好一会儿才出来,手上拎着两瓶“爱城玉液”。这两瓶酒很上了些年头,盒子都发霉了。老秦直搓手,呵呵笑,你是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呢,还是要请我们喝掉它?老陈说,能喝就都喝掉吧。老秦说,哎呀,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老安说,这不有酒嘛,你还是存那里吧。老陈拆了盒子,酒瓶拿到老安跟前,老规矩,还请你提壶。
提壶人,手不软,来,大家都把跟前这杯干了,咱们好喝老陈的好酒。老安先端起杯子,一饮而尽。老陈埋下脑袋,撮着嘴唇,先抿了一口,这才伸手去端杯子。他的手哆嗦得厉害,都快端不稳杯子了。老安看着他,真是替他难受。等大家都干了杯,老安站起身来,拧开盖子,晃晃酒瓶,在大家面前绕了一圈。一缕酒香飘溢而出。老秦抽着鼻子,赞叹道,真香啊,年头也久,怕要值两千一瓶吧,喝了怪可惜啊!老温说,可惜?那你就别喝呀!老秦瞪了他一眼,你才应该别喝,你不是痔疮犯了吗?老温说是呀,我刚给它换了口假牙呢!
值不了两千,人家只肯出四百,老陈说,你二位也别抬杠了,能喝上这酒,还真得感谢老安呢。大家都看着老安,就像是要请他说两句。老安挨个儿给老秦和老温倒上酒,又把自己面前的杯子斟上,他下手很轻,也很稳,酒出一线,凤凰三点头,酒满八分,盖面上一层细密的酒花。我说这么好的酒才给四百一瓶,是嘲笑我们没长嘴吗?可是老陈急着用钱呢,我就凑了一千块钱给他。酒呢,还存这里,等该喝的时候,咱们几个老兄弟也都享受享受。
老秦冲老安跷起大拇指,赞叹他这事儿办得漂亮。
这酒的来历大家都很清楚。这是老陈的儿子第一年参加工作,过年回老家孝敬他的。爱城玉液酒,成都五牛烟,都是老陈见过但没吃过的。老陈有些怄气,跟老安他们在一起私下埋怨,为了他念书,家里穷成啥样他能不知道?与其打肿脸装胖子,还不如给我钱,我好快点把十屁股账还掉九屁股呀!老兄弟们都骂他说,就你养个儿子还有个儿子的样儿,你还不知足?你看我们的那些娃,一年到头,烟屁股还捡不到他一个呢!老陈苦笑说,你们莫要觉得他拿了烟酒给我就多好了,他是逮给我只抱鸡母,转手就要牵头牯牛走!
儿子就要回去上班了,老陈咬咬牙,狠下心肠递给他张纸片,上头记着借贷。儿子搓着手,不肯接。老陈叹着气,你妈害了这么多年病,离不开个药罐子,你补习、考学、学杂费……杂七杂八都写在这里,你看看数目嘛,心头也算有个底呀。儿子也叹气,才工作,工资才起步,领导要孝敬,同事要团结,我这么大岁数了,人家女娃儿喊一起去看场电影我都不敢答应呢。老陈说既然这样,你买那些好烟好酒干啥呢?儿子说,孝敬你的呀,你苦累了大半辈子,总该知道啥子是好酒、好烟啥味道嘛。
酒是可以存放的,越陈越香。烟就不一样了。老陈取了三包,一包塞给老安,感谢他这么些年诸事关照,两包给老兄弟们散了。剩下的,老陈悄悄拿土镇烟酒铺子换了钱。
这年年底,儿子回来没有带烟酒,带的是糖果,因为随他一起回来的姑娘说烟酒不利于健康。老陈仔细看了那些糖果,都很平常。心头难免窃喜,这个姑娘,像个过日子的。姑娘的表现确然不错,糖果平常,可是嘴巴甜,表现既热情又大方。过完年就该回去上班了,临行前夜,那姑娘两句话就将老陈问得浑身冰凉。第一句是他们下半年准备结婚,问老陈有没有意见。第二句是结婚了就要买房就要带娃,问老陈能不能像父母通常都应该做的那样,支持一把。
儿子结婚第二年,老伴就去世了。老陈恍然如梦,走路像踩在棉花上,睡觉似梦似醒,有吃的就伸手,没吃的也不叫饿。做完头七,儿子和儿媳就走了。送他们出村口的时候,遇到人打招呼,老陈还笑。回家就倒下了,眼泪止不住地流,哭声也压不住,干号,哀号。老安他们来劝,老温说,哭哭就行了吧,老秦说,你平常待她又是拳头又是耳光,开口就没一句好的,咋还这么哭?哭给谁看呀?老安捶了老秦一拳头,指着他,让他闭嘴。
老安提酒,一杯敬大家都还健康,一杯敬老陈。老陈说,先别敬我,我们先敬另外一个人。大家都说好啊,你说敬谁就是谁。
老陈说,这杯酒,就敬给我那个死婆娘吧。咳,老秦,你记得她的生日吗?老秦被问住了似的,慌张了一下,讪笑说,我咋个会记她的生日呢?我咋个会记得呢?老陈说,她活着的时候不止一次地跟我讲,如果不是看在儿子的分儿上,早吊喉抹颈了。这世间,除了她的儿子,恐怕只有我这个老冤家还记得她的生日。老秦,你以前没记住,以后可要记住啊!大前天,二十三,就是她的生日!老秦不自在,要回话,被老安捅了一指头。老秦不点头,也不回嘴,作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老陈接着说,我等了一天,以为会等来儿子的什么消息,结果,从早到晚,清风雅静,杳无音信,真是杳无音信啊!老陈不敢一只手端杯子,两只手去捉,结果更抖,只好放下杯子,长长叹一声说,今天相聚,看见这么好的酒菜,临时起意提出这个想法来,就算是给她过个生吧!以后各位老兄弟还能见到我的那个儿子,麻烦告诉他,为了给他攒钱结婚,他妈从他们计划结婚那一天起就再没去看过医生拿过药!
大家都喝了酒,都沉默了。老安等大家都吃了一会儿,这才提第三杯酒。这杯酒是大家聚在一起的主题,上桌子就该说的,老安一直在酝酿说辞。该咋个说呢?早上出门的时候都在想,中午面对一桌子的好酒菜,秀妈也带了她新婚的丈夫和儿女来盛情劝酒,他没敢端杯子,就想保持住清醒,就在想晚上该怎么讲。该怎么讲呢?秀妈说,你就照实跟他讲吧,都到了这份上了,不讲实话又跟他讲什么呢?老安虽然觉得事实确实如此,但还是想先抿上几杯酒,让酒把这些话焐热乎了柔软了,可能更好接受。
秀妈是老安的相好,那会儿老安在土镇教书,秀妈在学校烧饭。秀妈烧饭做菜还真是没得说,一帮老伙计可没少吃,也都真诚地赞叹过。老安退休了,妻子一反常态地安静下来,对他各种好。儿子生了孩子,女儿也出嫁了,没多久也生了孩子……儿女们都眼巴巴地看着他,说咱们一家人好好过不行吗?还办了酒席,把老秦、老温和老陈等一帮子他的老伙计请来,恳请他们都帮忙劝劝。儿子说,年纪这么大了,就清静过点日子吧。女儿说,能不能顾及一下我们的脸面?一帮老伙计也都看着他问,你啥打算。老安说,她天天闹,片刻也不得清静,不离婚又咋办呢?都问,真要离吗?老安苦笑着摊摊手,她现在不闹了呀。独独老陈一个人提到了秀妈,问,你这么整,秀妈咋办?老安纳闷了,啥咋办呀?老陈倒吸口凉气,你就从来没想过和她结婚?老安说,是啊,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讲好的。老陈摔了酒杯,哪里有你这样的人呢,亏得人家对你那么好,良心给狗吃啦?
这场争吵很快就传到了秀妈那里。秀妈原来对老陈的印象并不好,还当面骂过他。现在,她就像遇到了知音。她抹着眼泪跟老陈说,是那样讲过的,我也从来不指望,只是想起来心头还是难受,就像养了十几年的狗,头也不回跟别人去了。
过了些年,孙儿孙女大了,可以脱手了,老安夫妇回了土镇,接着又回到秦村。老安找了秀妈几回,秀妈不见他。老安问老陈咋回事,老陈说秀妈又找了个相好的。好像是个退休干部。老安去打听了,说那个干部不靠谱。没过多久,秀妈就和那个干部分开了,闹得很难听,更难看,秀妈被打得鼻青脸肿,一个月才好。老安带了几个老伙计去给秀妈讨了说法,秀妈摆了酒席感谢大家。老安酒喝得最多,说喝这么多酒的目的,就是想讲句实在话。他跟秀妈说,你别心气太高,不要指望那些教过书的当过官的戴过大檐帽的,老陈不好吗?你就不觉得你和老陈其实是一对?
一瓶爱城玉液见了底,老安不肯再开第二瓶了。他拿起开了瓶的定制酒给大家斟满,端起杯来看着大家,大家都端起杯来看着老陈。老陈也端起杯,他的手已经不那么哆嗦了。
咱们先祝福秀妈吧!
老安干了杯,大家也跟着干杯。老安搁下杯子,看着老陈,说,味道还好吧?秀妈说你吃鱼总是卡刺,酒席就取消了鱼这道菜。老陈说,她晓得我不会去的。老安说,当然,她晓得你走不脱身,她说你被困着了。
是啊,老陈一直都受着困,先是被儿子困着,接着又受孙子的困。最开始的时候儿子的事业发展很顺,吹气一样膨胀,一回秦村不是捐钱给敬老院,就是帮那些上不起学的娃娃交学费。老陈心头隐隐不安,说你别一天到晚想着赚好名声,你要真有善心,给我把房子换了吧。儿子说,你有两个选择,一是跟我进城去住;二是再等等,等我事业再大一点儿,我在秦村修栋大别墅。他似乎真有这个打算,还请了风水先生看遍秦村的选宅基地。没过几年,老陈就听说儿子住院了,挨打,差点被打死。动手的是他的债主。要债的还跑到秦村,说不给钱就掘祖坟。亏得一帮子老伙计,要不保不齐老陈也会被打残。此后儿子就像是人间蒸发。那些年头,老陈真是度日如年,走到哪里都有人指指点点,一出村子就心惊胆战,害怕追债的过来要他子债父还。
三年前,儿子突然回来,推着个轮椅,轮椅里蜷缩个孩子,跟老陈讲,这是他孙子,叫陈东,小名小耳朵。老陈看着儿子,儿子很憔悴,头发全白了,枯瘦得像一阵风就可以吹倒。再看孙子,比着他爹一样瘦,面色煞白,衬得那双眼睛又大又黑。儿子还没开腔,就先哭起来,边哭边讲。老陈打断儿子的哭诉,指着孙子问他,他听得见吗?儿子说目前听力和视力都还没受到影响。老陈有些怄气,你就不知道背臭?
背臭是句秦村的土话,意思是私下讲,避免被人听见。儿子讲的都是小耳朵的病情和他们的境况。小耳朵是五年前害的病,不久他妈妈就离开了,因为他妈妈受不了穷困,更接受不了小耳朵很快就会病死的结果。
整个晚上,老陈都在想怎么办。首先,该怎么把这情况跟秀妈说。他都已经做好了前往土镇居住的准备,秀妈也做好了和他一起生活的准备,租了门店,要开一家小酒馆,老白自告奋勇要来当跑堂倌。那些天里,老陈一直在想酒馆的名字,是“秀妈小酒馆”好呢,还是叫“秦村饭店”?老陈本来说让老安帮忙想一个名,秀妈一句话就把他呛住了,这小酒馆就等于是我们的娃儿,哪有自家的娃儿叫别个起名字的?天亮了,老陈也差不多想好了。只是这个决定太绝情了些,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又怎么开口跟儿子讲呢?
清晨起床,四处不见儿子。孙子小耳朵坐在院坝里,看着对面的崖壁,口中喃喃地讲着什么。老陈问他,你爸爸呢?你爸爸跑哪里去了?小耳朵抬起麻秆一样纤细的手,指着对面的崖壁,快看呀,鲸鱼,鲸鱼啊!
老伙计闻讯而来,都帮忙找。老安说大家就别劳神了,他这一趟回来的目的不就是想当缩头乌龟,想躲得远远的吗?老陈想起昨夜儿子一边跟自己哭诉,一边跪在地上乒乒乓乓磕头的样子,真是哀叹无泪,这个龟儿子啊,咋个跑得比老子还快呀!
秀妈也赶来了,看了小耳朵的光景,问老陈,你是伤心呢,还是着急呢?老陈说我真不知道该拿啥话来回你呀,你看突然闹这么一出,接下来咋整呢?秀妈说,他是你孙子呢,害着病呢,牛不死不断草,人不死不断药,活一天,总得照顾一天呀。你好好照顾着吧,馆子那头也不能耽搁,我照应着,你放心。老陈说,你放心我,可是我不放心你呀!秀妈说,你莫急,他耽搁不了你多长时间。
瞧小耳朵的光景,他的确是活不了多久的样子。也不知是老陈把他照料得太好的缘故,还是说他的病一时半会儿还要不了命,虽然情形越来越糟糕,可是那糟糕的程度却进展缓慢。秀妈再来看老陈的时候,当着一帮子老伙计的面跟他讲,老陈,我不是个大姑娘,也不是小媳妇儿,我真是等不起了啊。大伙都劝秀妈,你再等等吧,你看看那娃儿,眼看就快不行了呀!
老安劝老陈,老伙计,你就放手吧,让他走吧。老陈说,我咋个放手?老安说,你不要给他拣药了。老陈咬咬牙,狠下心肠不给小耳朵拣药。有药没药,小耳朵似乎早已习惯。吃了药,他也是那么疼痛,彻夜呻唤;不吃药,折磨似乎也并不比之前强烈多少。他注定是要受够那么多劫难的。可是,这劫难该是多长的日子呀?啥时候才是个头儿呀?老安说,你别照顾那么细,很快就到头儿了。老陈哆嗦着声音说,他可是人呀,他可是我孙子呀!
老陈将熄火的药罐子又重新烧起来,还让老安给秀妈带话,不用再等他了。从此后,老陈也疏于和大家往来,他开始四处打零工,忙着挣钱,一有闲暇,不是上山给小耳朵挖药,就是陪在小耳朵身边,听他讲那头在崖壁间游来游去的鲸鱼。老伙计们都晓得老陈的日子过得艰难,有点好吃的好喝的,总是会送到他家门口。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免不了也总是谈起他,替他着急,替他难受,替他想办法。老安找来了药,跟老陈讲,几乎没感觉的,而且快。老陈接过药,道了谢,然后一把撒了。老安说,我知道你下不去手,你点个头总行吧!老陈不吱声。老安先是叹气,然后生气,说,你就永远被困在里头吧,你们都永远被困在里头吧!
请帖是秀妈和吕品成亲自送来的。吕品成开着车,他跟老陈讲,车子新买的,婚后他们会去度蜜月,自驾游,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吕品成说,我还去过些地方,秀妈最远就去了成都,她得见见没见过的,尝尝没吃过的,不然这辈子就真是太亏了。老陈说,你们真是好福气呀,秀妈人好,你人也好,我可是衷心地祝福你们呀!秀妈抹了眼泪,跟老陈讲,秦村这些老伙计,她就觉得老安和他人不错,所以,也只请了他们二位。
秀妈早猜到你去不了,所以早就安排了饭店,让打包一桌酒菜,吕品成要亲自送,我觉得不合适,秀妈就安排了辆车子,请我帮忙把这桌酒席带回来,再把这些个老伙计请到一起,陪你喝上几杯。老安说到这里,摸出两个红包,一个薄,一个厚。薄的是老陈请老安带给秀妈的礼金。厚的是秀妈送给老陈的。一点儿心意,要你保重好身体,给小耳朵买点好吃的。老安说,这是秀妈的原话。老温感叹道,真是个有情有义的娘儿们呢!老秦也感叹,老陈,人家可是对得起你了啊!
真是太感谢了啊,不过还要再麻烦你还给她。老陈把红包推到老安跟前,说,那头鲸鱼,我今天终于找到它了!
到底还是把那瓶爱城玉液开了。老安示意老秦和老温都逮着老陈敬,让他多喝点儿,喝醉了,他的计划就可以泡汤了。老陈自然晓得他们的心思,下口都很浅,怎么也不肯干杯。他说,喝这么急干啥呢?喝醉了就不好讲话了。大家都看着他,心情很沉重。老陈反过来敬大家,跟老秦讲,人老了,得有个老人样儿,话说人死如灯灭,可是名声这面旗子却是长久飘舞着呢。又跟老温讲,这顿酒喝了你就戒酒吧,戒一阵子,把你那病好好治治,以后就莫要去乱搞了,该是收心收性的时候了。几个没有来到的老伙计,他也都敬了酒,讲了话,要老安带给他们。
黎明的时候,老陈背着小耳朵出了门。事先讲好的,不准送。所以几个老伙计就坐在桌子前,守着一桌子残汤剩饭,默默地流泪。
太阳出来了,金色的光线透过门缝透进了屋子里。老秦突然挣起身子,侧着耳朵,快听,都听见了吗?老温也侧了耳朵,眉毛一扬,听见了,听见了,是鲸鱼在叫唤吗?老安下了桌,步子太快,差点跌倒。他打开门,阳光涌入屋子,屋子里一切金光灿灿。随着涌入的还有鲸鱼的叫声,啊啊啊,哦哦哦,嗷嗷嗷……高亢,嘹亮,悠长,带着穿透一切的颤音,迎面而来,随之远去。
哪里是叫唤,是歌唱呢,听呀,声调欢乐着呢!老安将剩下的酒斟满所有的酒杯——
来,咱们送送他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