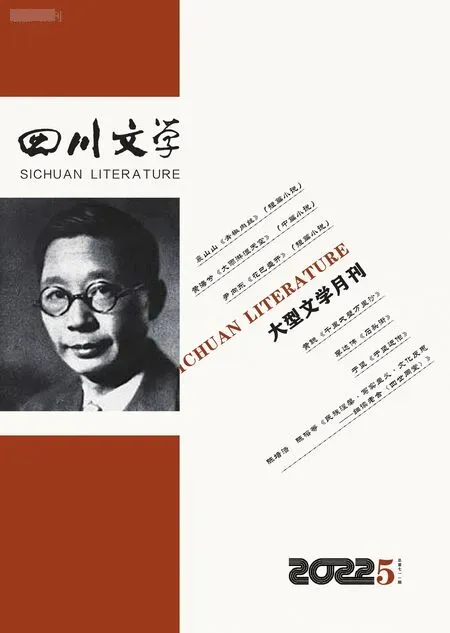短歌行
萤火虫(组诗)
○ 曹僧
在灰坑前
柏木像一根探针读取着风的唱片
透明的缱绻中有一种颤动如鱼的渴
传染着嫩梢,毛线头密叠的鳞叶
还有,一种芳香幽幽地沉落
使清悄像一条耸着鼻子的狗贴地小跑
在人的高度上,树干保持着距离伫立
所有残忍之物也这样,仰望着
久久地就像俯瞰——天空深不见底
云的咏叹中阵阵鲸歌翻越
而骑士携领扈从走上心的泛黄玉阶
令它滑动如琴键,弹奏在必要的休止前:
当闪着黑光的乌鸦翩然、闪亮
亡灵的期会上草铃铛轻晃将空白句读
猫头鹰
远处,工厂的烟囱像巨魔正炊煮
向冥茫问索,层山间的支流枝展如珊瑚
太阳下山后的黄昏,孤悬如桨的鹅掌楸
划转金黄的寂落。草岸像一根排队线
湿鞋的野人要上去,端庄的黑马要下来
在一张猫面具后藏伏,来了它看见
一个入口也是一面墓碑,为狐禅所辨读
腐烂的叶片揉进泥肥,枯枝的裂断
惊骇有如失态。它睁开一只眼而闭上另一只
纳受那些“像而不是”:有什么在呼唤
一条生蛆的健虎,拉动战车驰骋于林植
永生的幽黑缓缓上升、播撒,像浓密的戾语
它的小犹疑,在松针间滴溜溜地转动
一声尖叫,使闯入者的魂灵朝身躯外退却一番
用力从树枝上蹬跳,它击扇合金的硬翅
两只圆大的瞳孔巡视,微弱的隐光因它而洞穿
找
我找它,某处发笑
反射而来的光像钻石一样坚硬
小桥流浪,学小猫拱拱腰
我赶上,薄冰下的鱼鳞
泥塘里醉成圈套的蛇
我不敢喊它,怕
一喊出就会有另一个
舌头撤回来,滑溜溜的酸枣
要的是它,在楼榭的栋梁背面我找
一行小字驮着我像天马——
后来我就把它名字忘掉
去巷战里,乌漆墨黑里找
眼珠大得像黑布林
水牛反刍着缰绳,与它无关
但它把兜兜转转送给我
我去跨水闸,跨过葬礼的现场
尸体欢喜着擦洗
空气中魂魄的味道不新鲜
我说我找它,它说你走吧
在女教师弹性的舞蹈里
她的喇叭裤腿
扇起地上的灰,主席台说好
孩子们的笑都发亮
像一窝雨后被翻出的小树蛙
我想起我,要找
某刻分明叫了,没有冲我
几声掠过闲摆的树梢、屋顶和云
萤火虫
从摊着手掌呆立的泡桐树开始
异常的寂静发动奇袭,像蛇
横穿鹅卵石马路,攀缘上木槿护栏
簇生的扁豆被缓慢地抹去唇边血色
分头行动,一边是菜园内,那里还有
晚餐的蔬食
另一边是走廊,和一把掉漆的空椅子
战斗很快结束
山那边绯红的旗帜拔掉
一天就这样又一次失败了,然后是失聪后长久的嗡鸣
夜露出它的真面目
而他沮丧地躺在一张竹床上,脚朝着大门外——
入睡,就是突围
让残损的心灵小队
潜入造物主用食指戳开的某个黑洞
一条迷瘴般的防线也在四处摸索
思绪的坦克重整,满是伤痕刚发动就熄火于沼泽
单兵纷拥投掷燃烧瓶
一片焦灼中它出现
一闪一闪,像一颗微缩的绿色星球
挣脱了引力掠过红巨星、白矮星或玫瑰星云而来
它在空中定住,接着划出符咒似的不可思议的弧线
延时的光晕,像金石将整个的暗质切割
另一道门打开了,他看见
州河畔,一座城(组诗)
○ 亚男
达巴路口
这是一个很绵长的秋天
成排的梧桐树顶着回忆
南来北往的车辆碾压着
一些颠簸的日子
站得笔直的街灯一句话也不说
落到指路牌上
我清楚在这里停留很有必要
辨认自己去的方向
每一粒尘土都带着故乡的体温
从小巷转移出来
我的脚步比尘埃还要轻
不想惊动赶路的刹车
在通川中路上班那几年
没有少麻烦达巴路口的商店
在几支香烟的支持下
很多夜晚交给了浓度有限的生活
柴市街
可以放纵地,在一块瓷砖上
刻画。就有了商标的精准定位
语言的窈窕伴随着夜色
在灯光的掩护下,无可挑剔地是用来障眼法
款式就是制胜的法宝
新潮的取向,尽量袒露心胸
不用婉转,以川东的泼辣方式
吆喝,就有取之不尽的前途
至于为什么叫柴市街
也许是谐音吧。一溜的商铺
把四月领进冬天的门
夸张的讨价还价以绝对值压低成本
风靡的,不用担心换季
大幅地甩卖也不过是一款价廉物美
赶在新品上市
柴市街人头攒动
夜 市
冷啖杯估算了夜的成本
落下的寂寞和空虚佐以酒的浓度
在街边,呼朋唤友
灯光照得整个街面都是豪爽
夜已经没有多少空地了
对面的灯已关掉,风吹不到
酒气弥漫
女人习惯了这沉浸式的生活
挽着夜市去领悟
不管是天晴,还是雨
夜市不能少了女人的调味
不然夜市就热闹不起来
尤其州河畔,这座城
才有泼辣的味儿
登高凤凰山
元稹在山上化开了
泼墨作诗,语言明亮部分
沿着山径一直向上
到了山顶,城在州河的缠绕下
此起彼伏。延伸到普光气田
火苗越过凤凰山
照亮一座城
山上的文学院正在书写
半亩悠闲。一笔一画雕刻下凤凰的羽翼
满城蜂拥而至
山上元稹两袖清风
拥有一座山,日后每年正月初九
赶往山上叩拜
我在人群中脚力不济
走走停停
把初九的光揽在怀里
便有了元稹的悟性
船行越溪河
○ 陈海龙
这条路太柔软
鱼虾垫底
香樟油润滑的土地
竹节斑斑
山水间盘根错节
拉不住鱼尾
空山不空
满腹的隐私无处发泄
红砂岩腔内
佛在面壁
君临越溪
两岸都是板桥的朋友
千根钓竿
哪一挂是子牙抛出的金钩
我在风险之上
等雨敲门
美女也无法抵挡的诱惑
是越溪那片香樟林
长着一双双爱美的眼睛
看透巴黎街头的风景
脚下的粉红含着生命
你把天地
连接成泼墨的丹青
许多的疑问没有答案
每一根毛细血管
都在吟唱着
落叶无痕
藏在大山深处的部落
谁是你的首领
是越溪的水
还是天边的云
山居(外一首)
○ 游天杰
山居
我爱那破碎的云
和起舞的光
落日
和黄昏的山峦
我爱那种晶莹剔透的蓝
发亮的湖水
蘑菇、雏菊
满天星
黔灵山一日游
有小鹿,有寺庙
有神迹
裙摆在你抛出五月祈祷后
飘飞出柔软的弧度
像父亲,秋阳也要养活一年四季(组诗)
○ 赵琼
春风里的父亲和一群蚂蚁
我坚信,这一场由春风引领的颂唱
一定会让在地下憋屈了
一个冬天的蚂蚁与在家里憋屈了
一个冬天的父亲一样
在嘴里哼出那一句
与新芽和柳絮相关的民歌的同时
心里的幸福与感恩,一定大于
用以表达情绪的表情或肢体
其实,我还坚信他们
悠扬的心情只专注于温暖
至于那句含有柳絮的歌词
只是歌者曲中一个小小的过门
尽管细小,但也不是无关紧要
就像是父亲坐在窑崖门口正在擦拭着
长鞭上的那一簇红缨
就像是母亲正在案板上捏着的
那些雪一样洁白的馒头,以及馒头上
那些有意或无意的欢娱的造型
就像是一个沉默了很久
需要大喊一声的那个人
深深地吸入腹腔的那一口底气
就像是那一次要出远门的夜里
父亲夜半的那一声咳嗽
此刻,柳絮也一定探首于柳枝的最高处
那已显曼妙身姿,与春风一起
招展在窗外蓝天的瞳孔里
门洞里的父亲与地下那些个
贴着草根聆听春风吟唱的蚂蚁
都在渴望着一个节气口令,然后
在一片冒着热气的田野里
以老友重逢的方式
去经营各自一年的收成……
在秋天的一棵果树下,与父亲谈心
秋一天天往深处走,果子的心
就一天天跟着软。
像我那暴躁了大半辈子的父亲
在秋风的凉意中,拂一拂
满头的白发后,学会了轻声说话:
“人生一世事,草木一秋春。
该让人收获的,任你是谁
就是想拦,你也拦不住……”
父亲在秋天里的这段话语
就像是儿时,母亲手里攥着的
一枚红果
总在我将要号啕大哭的当口
恰逢其时地,将我的眼泪
还原为清水
秋阳,就像父亲手中的那把镰刀
有秋叶发黄,无风也落
秋阳,就像一把镰刀
如父亲一般,一门心思
就知道收割
也难怪啊
就像父亲要养活他的一家老小
秋阳也要养活一年四季,以及
这四季里的万物
在寒风中报春(组诗)
○ 李欣蔓
看啊,山坡上那片草随风起舞
正在丰满理想的时候
被村民割断或者连根拔起
我与它们相逢,深一脚、浅一脚
在青草的呼吸里走过生活的荆棘
长成另一棵小草
言语在宽窄的路途走来折回
草一样互相依靠
声音加重了世间的悲伤
冷言冰语滴落在阳光中
绝望,悲凉融化为灰烬
长成生命中重要的刻度
狂风暴雨一层层地覆盖大地
却无法覆盖这样一棵草
在寒风中报春,竖起未来
揭穿时间的秘密
月光下的脸像地上的一片树叶
路过的人们
听到它们在风中发出清脆的声音
我蹦起跳下,蹦起跳下
踩乱了无边的草色
遍地长满虫眼的叶子
一些在我的脚下
蹿上蹿下,嘁嘁嚓嚓
和我捉迷藏
悄悄地化为泥土深处的寂静
一些飘在空中,与我对话
从颓废的枯叶中长出新叶
一下戳穿了时间的秘密
向我问好
白头鹤
一只白头鹤心无旁骛地飞来飞去
那股风对它喊了一辈子
从天真的年少追过来
喜悦像一滴滴晶莹的露珠
时而滴在它的羽毛上
时而在树叶上画图画
香樟、松树、枫树迎风摇曳
长得高大,却有易折之心
我站在一望无际的绿浪里
头上的麦秸草帽被风吹走
噗的一声落在白头鹤的身上
它的眼前一黑,像夕阳躲进草丛
石 榴
风点燃的小灯笼,一排排一坡坡
带你进村,照亮初春大地
修改了一张张被刀斧凿过的脸
压不住的躁动像是从地里冒出来
发射新生的希望
人们以为是春节卖灯笼的墟市
从山地走到山顶
一些迷路的人眼睛亮起来
影子恰似风吹不灭的颗颗石榴
摇曳出村庄红火的日子
与祖国的命运共同起伏悲欢
暮色中的鸦群(外一首)
○ 哑鸣
气温一再下降
每一只飞鸟在日落之时
吞下一块乌黑的炭
体温耗尽之前
集体向北飞
寻找一根点燃身体的火柴
满天的飞鸟卷过天空
满天的炭飞翔在天空
吵吵闹闹
火柴从它们的翅膀下滑落
全部受潮
寒风呼呼的天空
像一个巨大炉口
那些乌鸦
最后就像冰冷的炭渣堆积在黄昏下
虚无的灵魂
阳光热烈地照在草滩上
河流安静地流过
青草从眼前铺到天边
夏天的牧场就像一个热闹的乡间杂耍场
牦牛吃饱喝足之后
躺在草滩上安享着正午的阳光
有两只好斗的家伙
庞然的身躯架在一起犄角顶着犄角
就像雪山上一块陡峭的岩石
两头暴躁的牦牛
在夏天的草场上
重复着冬天的风雪故事
阳光与青草
为它们加油喝彩
不远处毡房里的牧人喝着酥油茶
山后有些雪直到这个夏天结束也不会融化
草滩上的牦牛
在青草的包围中
某个时刻
那些茂盛的青草并不是青草
是昨天的风雪
所有一望无涯的青草都是安静的风雪
盛大的风雪
也有疲惫的时候
也有充满愧疚的时候
也有从一个虚无的灵魂
进入一个真实的灵魂的强烈愿望
把一个身影推下悬崖
是昨天的一念之差
遍地金色的阳光正在帮它们慢慢纠正
读诗记(组诗)
○ 白鹤林
神 奇
我同时读着两位诗人的两本诗集:
一个深邃隐秘,一个明亮如星。
两位诗人来自两个国度:
一位停留加州,一位长眠仙崎。
两本诗集也来路不同:
一本友人馈赠,一本网购快递。
两本诗集拥有两位译者:
一位漂泊湖北,一位幽居山口。
两位诗人也拥有两种人生:
一种痴情放浪,一种童话悲剧。
这些都不神奇,的确:
我喜爱两位诗人,并见过一位译者。
诗与棋
我在读诗。我在下棋。
我在玩玻璃球、花生和小陀螺。
天真是一位初学的魔术师,
如卡通人爱上喜剧。
嗯!“善于在最微小的事物中创造吧。”
俄国人巴尔蒙特说。
我拥有这本《安魂曲》很多年,
却还是第一次读他的诗。
诗歌其实也是粽子
史蒂文斯说,诗歌是金钱。
因为他心中有一杆,
可以称量两个世界的秤。
而我发现,诗歌其实也是粽子。
因为它们都是黏稠的,
包含着我们对世界相同的爱。
当我们在这个节日里,
用一个个虚拟的微信粽子,
来追思缅怀那超级现实主义的诗人——
就像是爱恨交织的你,
也给那逝者如斯的汨罗江水,
发去一封惜墨如金的电函。
悼阿巴斯
夏日暴雨如注,
也为你的忌辰而恸哭?
你只写过几行
短促而隽永的诗句,
恰如我们的生命
隽永而短促。
这一日属于诗歌
这一日属于诗歌,属于你,
属于你曾尝试赞美的这个残缺的世界。
死亡是三月写下又抹掉的一行诗。
这一日属于睡眠,属于失眠,
属于热爱你的诗歌的无限的少数人。
这一日是第二十三个也是第一个诗歌日。
不同语言和肤色的诗人都应该为你代替我们,
去完成了一首最具象征意义的诗,
而吟诵而沉默而恸哭而铭记……
亲爱的扎加耶夫斯基先生!我仿佛看见你,
独自一人在无止境的海上绝望地歌唱:
“游泳一如祈祷”。而天地悲泣无声,
就像你在某年十一月读的那首写于一千年前的,
有关雨、乌篷船和黄昏的中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