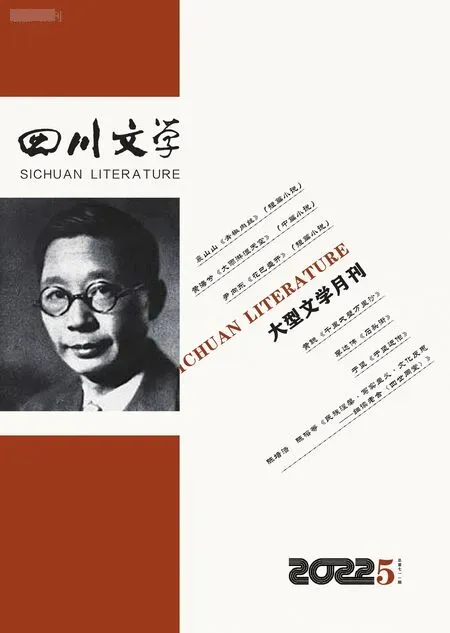大祠堂
□文/巴文燕
奢颇街上的阿纕奶是个奇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从不睡觉。白天睁起一双眼睛,夜晚睁起一双眼睛。很多很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她孙崽起来解手,穿过堂屋时,看到一对亮晶晶的东西,还以为是娘娘山上的狼进屋了,人当时就吓瘫在地。结果是阿纕奶,睁起双眼坐在堂屋的黑杉木椅子上。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奢颇人才晓得,阿纕奶夜晚不睡觉,第二天照样能麻利做活路。
有人问过阿纕奶,您不睡觉困不困?
阿纕奶说,困啊!
那您咋不睡觉嘛?
睡不着。
为啥子睡不着嘛?你问我,我去问哪个?
再后来,阿纕奶就彻底老了,老得都缩成了一团(远看就像个黑色的逗号),老得都快走不动路了,还是睡不着觉,还是天天夜晚坐在堂屋头,睁起双眼,一眨不眨,就像黑夜是个调皮的精灵,被薄脆的玻璃器皿罩着,还搁在逼仄的神龛上,她得好好守着,唯恐眨下眼睛就会摔到地上,死掉。阿纕奶晚上不睡觉,白天就把两片皱巴巴的眼皮垂下来,把眼珠子盖上,闭目养神,看上去就像是睡着了,可但凡有个响动她都晓得。有一次,一只耗子朝她移动,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哪晓得还没挨近,还有半尺光景,阿纕奶一抬脚就把那小畜生给踩死了,再顺势一踢,软趴趴的耗子就到门外了。吃饭她也懒得睁眼,鼻子下一根紫红的肉线,左右拉扯,时不时,暗红的牙床扑腾出来,饭粒溜到下颌,舌头倒是灵巧,一卷,就进嘴巴了。她的曾孙以凝固的姿态,仰望着她,想象一只蚊子飞过来,双眼紧闭的祖奶,倏忽伸出手中的竹筷,一夹,细如游丝的蚊子,就被拦腰截断;薄如蝉翼的黑翅,在半空中翻卷——和武侠片里一模一样。
到了夜里,一切照旧,阿纕奶怎么都闭不上眼睛,眼珠子鼓出来,就像两颗跃出水面的水晶弹子。刚开始人们稀罕,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偶尔有外乡人问起,奢颇人嗑起瓜子点头说,是啊,我们这里是有个老奶不睡觉,再细问,没人搭理了。什么事情都架不住时间的磨砺。
寒露前一天,是个星期四的下午,奢颇贯穿南北的主街上,冒出个瘦高的男人来,那人左手握把米多长的黑伞,右肩搭条布袋,从东头乌东家的小饭馆,走到西头乌泰家铁匠铺,再从铁匠铺走到小饭馆,六百三十米长的街道,移过来移过去,晃人眼睛。起先,没人注意,只是那道幻影闪来闪去的,像一出乏味的独幕剧,那些无精打采的眼睛,才开始向他汇聚。杂货铺老板娘牛彩英,眼珠子跟着那人来回了好几趟,眼睛都要花了,终于忍不住拦住那人,问他走来走去地干什么,是要找人吗?如果找人尽管问她,奢颇街上没有她牛彩英不认识的人。那人没看她,瞄了一眼她身后的杂货铺,摇摇头,继续往前走。牛彩英莫名就有点受伤害的感觉,紧走几步跟上去,噫,你这个人有点怪嘞,咋不理人就走了呢?你说嘛,你找哪个,我给你说。那人低头颔首,说,我不找人。还是继续往前走。牛彩英看着他的背影,发现那人的个子奇高,刚刚跟他说话的时候,仰着脸,都没看清他的五官。其实牛彩英长得不丑,还有点姿色,要不咋能嫁到奢颇来。牛彩英想跟过去,再次拦截,走了两步,算了。平常这种情况,她得跺脚骂人了,这回她蔫蔫地回到杂货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乌二贵捧着和他头一样大的搪瓷碗,正稀里呼噜地吞面。牛彩英还算窈窕的身影盖在他身上,他抬起头来,面红耳赤,额头和两侧太阳穴的汗珠刺眼,手指宽的面条如瀑布般悬挂在嘴和碗之间。
天黑得像一团墨汁的时候,奢颇街上安静下来。天气渐凉,外面阴冷阴冷的,炭火还不打算升,但没事谁也不愿意出门。只有年轻人借着酒意在街面上游荡,昏黄的街灯下,勾肩搭背,大呼小叫。小巷里窜出来一条野狗,被其中一个狠狠踹上一脚,野狗嘶鸣,东倒西歪地逃窜,引来更加猖狂的怪笑。
牛彩英吩咐乌二贵关门,卷闸门拉下来的声音像一把用钝了的刀,在空气的皮肤下搅动,震得整个水泥路面,腾起一层硬生生的白雾来。两个人正准备上床睡觉,门外响起哐哐的敲门声,这么晚,不是买酒就是买烟。但是乌二贵不太习惯这种节奏缓慢的击打,他半撑腰,支棱起耳朵,牛彩花却已经翻过他山包样的身体,说我去。打开门,正是白天那个在街上走来走去的怪人。牛彩花退后两步,想看清他的五官,屋里的灯泡才15瓦,看不清。那人请求在杂货铺借宿,因为看来看去,就你家房子大。确实,奢颇街上都是传统木房,像这种三层楼的砖房,独牛彩花一家。对于这一点,牛彩花甚是得意,于是对怪人说,可以,不过不便宜。对方答,钱不是问题。
第二天,怪人没走,继续跟牛彩花商量,想借住杂货铺一段时间,并声称要在铺外立块牌子。立什么牌子?你要搞哪样?牛彩花问。那人说,我打算在你们这里买一个梦。牛彩花以为自己的耳朵有问题,还有人买梦?梦不是每个人都在做吗?天天做,夜夜做,还需要买?买来有什么用?我只是买,没打算用,怪人说。现在,牛彩花已经能看清怪人的长相了,四十五六岁的样子,五官周正,高鼻梁,有着清爽的额头,一看就不是本地人(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打扮有点怪,披着件卡其色的亚麻长衫,头发却已灰白,如果剃个光头,跟个和尚没两样。
从那天开始,奢颇街上乌家杂货铺外,就立了一块收购梦的牌子,六十公分见方的红纸,写着“购梦”两个大大的正楷黑字。这倒罢了,最让奢颇人惊诧的是,“购梦”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一旦成交,支付十万现金”。牌子一出来,奢颇街上,以及娘娘山附近村寨的人,都来了,把杂货铺围个水泄不通,纷纷向购梦人表示自己的梦有好稀奇,排着队要说自己的梦。有些人还讲了个两三句,大多数人刚一张嘴,就被叫停,有那么一两个人总算是把梦讲完了。遗憾的是,都没有达到购梦人的要求。
自从出现买梦的事情,奢颇人有事没事就往乌家杂货铺跑,他们也想听听其他人的梦是什么样子的。可惜,购梦人听梦的时候,都是关在一间屋子里,门紧闭,窗户不露一丝缝隙,根本就听不见。虽然听不见,他们还是想去凑热闹,想知道究竟会是什么样的梦,能让购梦人拿出十万块钱来买。他们聚拢在杂货铺门外,或站或坐,聊天打牌抽烟摆龙门阵,试图窥探别人的秘密,这让杂货铺的生意格外红火,进货都忙不过来,牛彩花每天笑得合不拢嘴,小心伺候着购梦人,希望他能多待就多待,最好永远不要买到那个梦。
两个月后,一场大雪将奢颇带进纯白的世界,街上铺满亮晶晶的凝冻,灰扑扑的水泥路面隐蔽在冰面下,街两边屋檐上,长短不一的冰锤子像波浪漫延,悬挂在每一个进出屋门的人的头上。孩子们用被大人丢弃的木块制成滑板,寻到一处斜坡,玩溜冰游戏,欢笑声此起彼伏。老人们不太敢出来了,怕摔跤,这样的事情又不是没有发生过。
乌家杂货铺前骤然冷清下来,牛彩英专门烧的一盆炭火,也招不来人了。来说梦的人越来越少,有时一天也没一个人。牛彩英生怕购梦人觉得生意不好,会走人,就让乌二贵去说梦。乌二贵每天睡得跟个死猪样,他说没做梦。牛彩英就说,以前做的也行,他哪知道你是哪天做的?乌二贵说以前的不记得了。牛彩英掐他,尖着嗓子喊,编,编一个总会吧!编,对乌二贵来说也挺难的,但牛彩英的话他又不能不听,那就赶鸭子上架。奇怪的是,无论乌二贵编得多么蹩脚,购梦人都会耐心听,还给他个三五十块。这鼓励了乌二贵,绞尽脑汁,实在编不出来,就跑别人家去问。被问得烦了,别人也给他瞎编,不知不觉就变成了摆龙门阵。既然是摆龙门阵,就引出奢颇许多逸闻趣谈、传说旧事。
别看奢颇如今是个小村庄,却有着五百多年的历史。村庄边上的清水河,可入洞庭湖、湘江,直至长江入海。这里四处都是大山,植被丰饶,森林茂密,因而有着几百年的木柴经营历史,曾经一度是个热闹的商埠、集镇。如果不信,看奢颇街上那些雕龙画凤的木屋,多精细多漂亮;再看娘娘山脚,那幢气宇轩昂的大祠堂,尽管年久失修,露出些许败相,但也是瘦死的骆驼。
乌二贵很是得意,三五十块钱,让他时不时可以溜到乌东家喝上两盅,实在是久违的惬意。自从娶了牛彩花,他的嘴被管着,钱被管着,口袋里一年四季,除了几张废报纸用来解手,什么也没有。但他有点烦乌东,每次喝酒,都要问他什么时候生崽?他和牛彩花结婚十多年了,生不出崽来,全奢颇哪个不晓得,还问哪样!这个也就算了,有次乌东还问他是不是他不行,这就过分了,他当时一口酒下肚,转身就走了,害他油炸花生米都没吃完。不过,没几天,乌二贵又去了,乌东照样问三问四。得了钱不上交,反而偷着去喝酒,这事很快就被牛彩花发现了,揪住他的耳朵问哪来的钱,是不是又偷拿杂货铺的东西去卖了。乌二贵只能老实交代。这倒让牛彩花意外,因为购梦人说过,只要不满意,他是一分钱也不会给的。
第二天,牛彩英去找购梦人,说她也有一个梦。
租给购梦人的这间屋子,就在一楼,也就十几个平方米,以前用来放些杂物。购梦人住进去后,牛彩花这还是第一次来,屋子归置得整洁,她的手脚就有点不知道放哪儿。房间正中有张小方桌,铺了灰白格子的桌布,上面放了几本书,一个比巴掌还要大的棕色笔记本。牛彩花的眼睛四处瞟,嘴里发出啧啧啧的赞叹声,说,你搞得好干净啊,硬是漂亮嘞。
屋里只有一张木椅,购梦人请牛彩花坐下,递给她一瓶矿泉水,他自己坐小方桌对面的床上。
你说吧。
牛彩花的屁股在椅子上,左抬一下,右抬一下,终于安静下来双手握着那瓶矿泉水,开始说她的梦。
我梦见我们奢颇街上,突然冒出密密麻麻的狗来,一眼望过去,白森森的一片。对,都是白色的。刚开始,它们朝我叫,不停地叫,牙齿又弯又长,我吓得全身发抖,就往后退,哪晓得一抬脚,就踩到一条狗身上——我还看见狗毛上我的脚印子,黑黢黢的。那条狗遭我踩到后,转身就跑,往娘娘山跑,然后我看见所有的狗都往娘娘山跑,往大祠堂跑,远远看过去,就像是一堆一堆的棉花,还蛮好看……牛彩英说的这个梦,确实做过,是她刚嫁到奢颇时做的,很多年了,因为太奇怪,所以她一直记得。
后来呢,购梦人问她。
我当时看迷了,忘记趁机跑开,哪晓得那些狗又返回来了,因为狗太多了,一个踩一个,好多狗都被踩死了。没踩死的都朝我压过来,想咬死我。离我最近的那条狗,牙齿好长哦,长得像是一弯月亮,我眼睁睁地看到月亮卡进我的颈子了。哎哟,太吓人了!
购梦人坐在床沿,腰板挺得笔直,平静地注视着牛彩花。
后来我就醒来了。
购梦人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块钱,说,谢谢你。牛彩英晓得自己的梦不会合格,这一百块钱比她想象的要多,相当于杂货铺两天的利润。她接过钱高高兴兴地走了。
尝到甜头的牛彩英,又连续说了半个月的梦,把她以前做过的、有印象,还有别人说给她听的,都一一说给购梦人听。反正,不管怎样,购梦人都会给钱,三十五十。差不多一个月后,牛彩英费尽心机也编不出梦来了,于是和乌二贵分工合作,每天,一个人看店,一个人去找梦。奢颇人以为购梦人是请杂货铺两口子上门服务,乐得在家里摆龙门阵,万一呢!
有天晚上,雪很大,奢颇人躺在屋子里,只要不说话,都能听到雪花落地的声音,沙沙沙,沙沙沙,就像奢颇街上那只流浪猫蹑巧的四足,踏着毛茸茸的夜色,踯躅在时间的沙地上,一直持续到夤夜。
雪停的时候,牛彩英还没睡着。刚上床时,她如往常一样,想着第二天去哪家收梦。最近奢颇人好像听到什么风声,不太愿意给他两口子摆龙门阵了,不得已,说一个,牛彩英给五块钱,这才又激发起大家的热情。但这总不是长久之计,购梦人总是要走的,如果春天以前,她能把那个十万块钱的梦收上来也就罢了(她心里可是有个小九九的),如果没有,天暖了,奢颇人自己上门说梦,甚至其他村寨的人都来说梦,到时候总会有人中彩的,即便没有,购梦人早晚也要离开,那她杂货铺的生意又会回到从前要死不活的样子。想到这些,牛彩英就发愁,抬腿,狠狠踹一脚乌二贵的屁股,男人震天响的呼噜,停了一次,翻过身,继续鼾声雷动。牛彩英躺平身子,把自己的目光挂在空中,她感觉暗夜就像一只硕大的蜘蛛,随时都可能把网织到她的身上。
十八年前,牛彩英嫁进奢颇,住进奢颇街上最气派的房子,原来以为美好的日子就此开始了。哪晓得,乌家接连出事。乌二贵的爹是早死了的,她嫁过来两年,婆婆妈也死了,刚把后事料理停当,刚刚二十岁的乌三贵,在外面打工出车祸死了。乌家还有个老大,据说七八岁的时候就失踪了,她也从未见过。庆幸的是还有个乌二贵,可也不晓得是咋回事,乌二贵越来越笨,结婚前那么精明的一个人,现在跟个傻子似的。最让牛彩花难以接受的是,自己一直未能生育,成为奢颇人的笑柄。她还隐约听到有人嘀咕,说是报应。报应哪样?她牛彩英一不偷人二不害人,报应从何说起。有时她也把委屈说给乌二贵听,让男人去找人理论。可乌二贵软得像他嘴巴里的面条,不是一般的宝器。本来以为,日子就这个鬼样子了,哪晓得冒出个购梦人,牛彩花的生活,如一潭死水,投进一枚有棱有角的大石子,漾起的涟漪,从水面一直深入水底。
牛彩花想累了,慢慢闭上疲乏的眼睛!突然,脑子里灵光乍现,那种力道让她猛地坐起来——是啊,为什么她不能得到这十万块钱呢,为什么只想那些小钱呢?有了这十万块钱,那她牛彩英这辈子还求什么?哪怕没生崽又怎样,奢颇哪个有十万块钱?
天刚亮,牛彩英敲开购梦人的门。进得屋来,牛彩英坐在椅子上,双手在肚腹前揉过来搓过去。
牛彩花抬起头来问:“我就是想来问下,什么样的梦你才肯花十万块钱?”
购梦人想了想说:“就像你之前说过的那个白狗的梦就挺好。”
牛彩英说:“我只做过一次。我也不想再做那种梦了,太怕了。”
购梦人说:“你不说像月亮吗?”
牛彩英说:“那是杀人的月亮。”
购梦人睃她一眼,说:“这句话说得好。”
牛彩英有点疑惑,购梦人说:“那月亮是长在狗嘴里的。”
牛彩英笑了。她笑起来还是好看的,腮上托起两团红晕,说话也温柔了许多,那你说嘛,哪样梦你才买嘛?
1.2设备和试剂运用希森美康公司所制的K-4500型血细胞分析设备、日本进口的奥林巴斯CX21生物显微镜及瑞氏-吉姆萨复合型染色试剂。
购梦人说:“等它出现的时候我自然买。”
这句话等于没说。但就在那一刻,牛彩英想到了阿纕奶,那个从不睡觉的阿纕奶,她曾经听乌二贵的妈说过,说阿纕奶睡不着觉,是因为老梦到死人。也许,她那里有个什么特别的梦,至少也要值两百块钱吧。
这天大清早,雨后的奢颇街上,还是铅灰色的时候,牛彩英家的杂货铺来了个人,那人戴着斗笠,披着棕色蓑衣,脚上蹬着双看不出颜色的胶鞋。杂货铺还没开门,有人看见那个人在杂货铺门口站了足足半个小时,一动也不动,直到卷闸门哗的一声往上拉起,露出乌二贵一张还有些迷糊的脸。猛地见个人杵在眼前,乌二贵吓了一大跳,手一松,卷闸门往下滑了三寸。乌二贵很不高兴,大声问,你是哪个?站我家门口干什么?那人个子不高,满脸乱蓬蓬的胡子,只露出鼻子,眼睛埋在斗笠下。也不看乌二贵,说,我要找那个人。乌二贵当然知道他想找哪个人,上下扫了对方几眼,看不出个所以然,说,你等到。
等那人进了购梦人的房间,牛彩英和乌二贵就坐在柜台后面,盯着那扇小门,满脸狐疑。牛彩英晚了半步,只看见那人的背影,就问乌二贵,你真的没见过?乌二贵说,没有,从来没见过,也看不清。牛彩英又问,是不是我们这里的口音?乌二贵说,好像是。牛彩英踢他一脚,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好像是哪样意思?乌二贵把两只大脚缩进椅子下面说,他只说了几个字,我没听清楚。
半个小时后,门吱嘎一响,斗笠首先从门框里伸出来,接着是棕色的蓑衣,裹在一个瘦削的人形上。脚步倒是矫健,三两步就跨出了杂货铺。牛彩英的头几乎侧弯成九十度,也没看清那人长啥样。牛彩英不甘心,去敲购梦人的门,里面问有事吗?
“煮了米粉,有肉末,你吃不?”
屋里人回:“谢谢,不用了。”
牛彩英又问:“刚才那个人是来说梦的?”
门板里面半天没回音。
牛彩英冲着门做了个鬼脸,咕噜了句:稀罕!然后想,估计又是哪个寨上的人,最近陆陆续续有奢颇外面的人来找购梦人。不过在牛彩英看来,如果连奢颇都没有值十万元的梦,到哪儿都别想有。方圆几百里,明清时就奢颇出过秀才、举人,新中国成立前还出过红军师长,现在虽说不如从前那般气派,但据说省里还有位领导是奢颇人。要不然,她牛彩英为什么非要嫁到奢颇来呢?奢颇一千多户,百分之九十九都姓乌,寥寥的外姓基本上是嫁进来的,她牛彩英就是其中一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奢颇可是方圆百里最大的寨子,以前还是镇政府所在地,娘娘山、清水河两岸,村村寨寨的姑娘,哪个不想嫁进奢颇来,哪个不想在奢颇大祠堂留下一个名字。虽然,如今大祠堂被锁起来了,说是要破除迷信(前几年被还划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大事小情都由村委会、镇政府解决。尽管如此,奢颇人的自豪感,一点也不少于有祠堂的时候。那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牛彩英自嫁进奢颇那一天,就开始有了。
想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牛彩英莫名其妙的就有些着急,她好几次都想去找阿纕奶。阿纕奶差不多有一百岁了吧,肯定有好多好多梦——她晚上不睡,但白天睡啊,闭起眼睛,哪个晓得她不是在睡觉?即便没得梦,也肯定有好多好多龙门阵,奢颇好多人都是听着阿纕奶的龙门阵长大的。而且,阿纕奶讲的龙门阵,都是奢颇人自己的故事。她从来不讲七仙女、葫芦娃、孙悟空那些摸不着边际的传说。
腊月十六那天,天气愈发冷了,娘娘山顶被垂挂的雾霭遮蔽,黛青色的腰肢,在远处若隐若现。奢颇街面上翻卷着白霜似的寒气,像白色的火焰。街上人影寂寂。乌家杂货铺的卷闸门,半开半闭,这使得冷峭更加有机可乘,像把宽大的剑,从敞开的门刺进来,在屋里东砍西削,让人不得安生。牛彩英蜷缩在火厢里,诅咒这鬼天气。乌二贵劝牛彩英还是关门算了,已经连续三天没人上门了。牛彩英说,不来说梦也就罢了,奢颇人不过年了?不准备点年货?乌二贵扫了一眼空荡荡的货架说,这天气,货都进不来。牛彩英瞪他一眼,说,下午你再去车站,要是再没有班车,就租乌东家的面包车……话音未落,一个弯弓形状的暗影,幽灵般飘进门来。牛彩英把“车”字噎回去,倏地挺起腰来,步履颠踬。
看到阿纕奶的一瞬间,牛彩英感觉是自己的意念起了作用——阿纕奶主动找上门来了!随即,又有点惶惑,她差不多有十年没看见阿纕奶了。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阿纕奶不再出门,即便有人特意去看她,她也不见。过年过节也窝在屋头。也就是说,阿纕奶在奢颇的存在,等于一个符号。说句不好听的,她老人家就跟作古了差不多。也正是这个原因,牛彩英迟迟没敢去找阿纕奶,怕别人说她想钱想疯了。
此刻,这么天寒地冻的天气,阿纕奶遽然出现在自家屋门口。
牛彩英抬脚出火厢时差点绊一跤,乌二贵坐在火厢里头,露着两瓣门牙,半天没合上,还是牛彩英喊了他两声,才闭上嘴去扶阿纕奶。牛彩英给乌二贵递眼色,让他快去把村主任喊来。牛彩英很清楚,阿纕奶太老了,整个人就像一个倾斜的三角形,铁质的,灰暗,尖锐,感觉稍不留意,支撑起黑色棉衣的骨架,就会噼里啪啦落一地。
阿纕奶并没有想取暖的意思,杵着根比她还高出两尺的乌木拐杖,说要见那个外乡人。阿纕奶的嘴里只剩赤红的牙床,说起话来像吐鱼泡泡,但牛彩英还是听得明白,听明白的同时,肚子的肠子也瞬间转青,恨自己咋不早一脚去找阿纕奶。
阿纕奶的拐杖在牛彩英的脚前,哚哚哚地响。牛彩英赶紧说,奶,你坐,我去叫他来。阿纕奶不肯,颤着两条玉米秆似的细腿,说要跟她一起。没得法,牛彩英扶过阿纕奶的右手(她感觉双手握住的是一节空空的袖管),准备带她到外乡人的房间。刚转个身,购梦人已经站在她俩面前。牛彩英一个趔趄,猝然后退,那节空空的袖管同时从她的手中滑落。
哎哟,你搞哪样哦,吓死我了!
购梦人没理牛彩英,问阿纕奶:老奶,您是要给我说梦吗?
阿纕奶使劲伸展她曲里麻拐的身子,终究还是失败了,她把她同样是三角形的脑袋,吃力地侧翻过来,眼珠子撑起肉垢般的眼睑,这才勉强窥见购梦人的前胸。还好,购梦人恰到好处地蹲了下来,一张中年男人的脸摆在她昏花的眼雾中。
你就是那个收梦的外乡人?阿纕奶吐着鱼泡泡说。
购梦人用力地点点头。
阿纕奶说:“我给你说个梦,我不要你的钱。”
购梦人说:“该给还是要给的。”
阿纕奶说:“这个梦我做了几十年,只要闭眼睛就做,你想听不?”牛彩英伫立一旁,咬紧下巴骨,两个拳头捏得紧紧的,肚子里的肠子已经变成墨绿色的了。
购梦人说:“奶,到我屋头说。”说着伸手过去,欲搀过阿纕奶,哪知斜刺里飞来一只蛮粗粗的手,拍飞了他的。购梦人一看,是个五十多岁矮矮壮壮的男人,昂起下巴瞪他,浑浊的双眼又大又圆。
哎哟,村主任来了,坐嘛坐嘛。
牛彩花一边拉板凳,一边给跟在村主任后面的乌二贵使眼色。乌二贵不晓得老婆挤眉弄眼是几个意思,站在原地扯面前的衣服,眼睛东瞟西躲。牛彩英急得直跺脚,近前两步去拉村主任。村主任把手一甩,转过身扶起阿纕奶就要走。阿纕奶不肯,轻飘飘的身子像突然装了铁锚,黑黢黢的拐杖像根定海神针,戳在地上,纹丝不动。
奶,我们回家去。村主任的牛眼睛此时变成了眯缝眼,小心翼翼。
一坨空气被阿纕奶吸进嘴巴,干瘪的口腔来回蠕动,村主任说,你从不睡觉哪里有梦嘛。阿纕奶薄皮似的两颊又凹陷两下。村主任说,那你说我是哪个?阿纕奶说,你是打铁的乌泰。村主任大声说,我是你孙崽乌大春!说完蹲下,来,我背你回家。村主任右手往后稍使力,阿纕奶的拐杖就滑到他手里了,牛彩英赶紧上前帮忙。阿纕奶的身子在她的棉衣里,勉强挤挨两下,就乖乖趴在了乌大春身上,嘴里的空气逐渐稀薄、混浊。
购梦人站在旁边,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
村主任把阿纕奶背走了。
牛彩英站在杂货铺门口,两只手揣进棉衣的袖筒里,望着渐渐远去的背影,自言自语:“阿纕奶都认不到人了,幸好我没去找她,不然遭村主任骂死。”人远去,留下空荡荡的路,路面铺着一层薄冰,都能印出两旁木屋的瓦檐、翘角,像一幅抽象的水彩画。女人蹙着眉又嘀咕:脚杆都只剩两根细骨头了,阿纕奶是咋个走过来的呢?站在旁边的乌二贵说,我刚才跑过去的时候都摔了两跤。牛彩英像从梦中醒来,侧头睥睨他一眼,嘴里崩出句:你个宝器!
当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什么事呢?乌小春起夜,经过堂屋时,没看见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多少年了,半夜堂屋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就像神龛上的祖宗牌位,突然消失了,那是比天还大的事情。当下乌小春就吓得半死,尿都没撒,就把村主任叫醒。两个人先是在院子里找,又到奢颇街上找,最后居然在阿纕奶的房间里找到了——老人家睡得香甜,还打着绵软的鼾声。父子俩站在阿纕奶床边,足足伫立了二十分钟。
第二天,家人发现阿纕奶与往日并无异样,乌小春没忍住,问祖奶是不是睡着觉了。阿纕奶说,我终于做了一个清亮的梦。不过好景不长,也就三天,阿纕奶又睡不着了。估计是老了,这回睡不着,阿纕奶没那么淡定,烦躁得很。一遍遍请求孙崽把她放进棺材(棺材都准备三十年了),说是阎王爷来收她了,她也活累了,想死。乌大春肯定不同意啊,哪有人没死就放棺材里的嘛,那不让奢颇人笑掉大牙,以后他这个村主任咋当?乌大春问他奶,有没有别的办法,只要不睡进棺材。阿纕奶就说,你不让我睡棺材也可以,那就让我去见那个外乡人。乌大春思前想后,蹲下身子,把阿纕奶背到了乌家杂货铺。
那天,奢颇街上就像赶集一样,乌家杂货铺更是围得水泄不通,因为阿纕奶说了,要当着奢颇所有的人来讲这个梦,购梦人也答应了。
阿纕奶坐在杂货铺门口,面前一盆炭火,烧得正旺。购梦人穿着亚麻长衫,外面套一件蓝色的羽绒背心,坐在她身侧,乌大春坐在老人的另一侧,生怕有个闪失。奢颇人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几圈,好些个年轻人爬上路边的大榕树——管他听得见听不见,重在参与。
阿纕奶的嘴嗫嚅着,粉色的舌头在嘴的缝隙处时隐时现,像是在活动活动关键部位,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准备。她的眼睛比往日任何时候都亮堂。人们屏息静听。
很多年前,奢颇来了两个外乡人,是一对逃荒的年轻夫妇,还带着个两三岁的娃娃,他们实在走不动了,请求在这里住下来。大家看他们可怜,就同意了,还给了他们一间废弃的土屋。外乡人很勤快,什么活路都做,哪家需要帮忙都伸手,从没有半句埋怨。那时奢颇街上没有商店,夫妻两个就开了间铺子,男的去山外边进货,女的就在家里守店。以前奢颇人都到山外去买东西,这下奢颇有了个铺子,方便得很,都到他家来买东西。生意好,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有一天,那个男的来找我男人,说是想把土屋改造一下,我男人说可以啊,没有问题。原来以为他们开杂货铺挣了点钱,把土屋翻修翻修,哪晓得,夫妻两个把土屋推倒,重新盖了幢三层楼的水泥楼。哎哟,那个气派哦!我们奢颇,住的都是木房子,哪里见过水泥楼房,还那么高。也是怪,外乡人来讨生活的时候,奢颇人可怜他们,可他们日子过好了,奢颇人心里又不是滋味,你们说怪不怪。
原来,废弃的土屋和那块地是没有人要的,可是房子盖起来了,就有人来要了,说是他家祖上的地,要钱。外乡人在奢颇也住了几年,知道那是块无主的地,自然不答应。那家人就找我男人,让我男人出面。老一辈都晓得,我男人那时候管事,就去找外乡人。外乡人记我男人收留他们的情,答应给点,说是盖房子钱都花光了。人家就说没钱就要房子。说来说去,外乡人也答应了,那就给第三层,可那家人贪心哦,硬要第一层,不然就要上面两层。两边都不肯让步,最后只好去大祠堂。那天,人比今天还要多,我男人这边说那边说,口水都说干了,外乡人终于松口了,不过有个条件。我男人问是什么条件?外乡人说,他要看地契,不然,就不给,一层楼也不给,一分钱也不给。我男人问那家人有没有,自然是没有的。那家人是奢颇的老户,一向蛮横,大家也晓得,他们平白无故地要钱,就是欺负外乡人。但我们都是奢颇人,虽然晓得他们欺生,但也不会去帮一个外乡人。原来我男人想,外乡人的好日子奢颇人也有功劳,双方一个让一步,大家好生过日子。哪晓得外乡人较起真来。那家人脾气暴,来硬的,和外乡人打起来了,我们拉都拉不动。混乱当中,奢颇这边不晓得从哪里冒出个钉耙,一钉耙扎进外乡人的脑壳,当场就死了……说到这儿的时候,阿纕奶嘴里的泡泡吐得更密集了,乌小春都来不及擦。阿纕奶脸上的皱褶像冲击在悬崖上的碎浪,一阵又一阵,溅起猩红的血丝。
到处都是血——阿纕奶全身都在抖,握着拐杖的左手,惨白惨白的——外乡人的老婆哭起喊起,拖起娃娃就往外面跑。哪晓得都遭吓倒了,个个往祠堂外面跑,人挤人,人踩人,连根扁担都插不进去。等到终于都挤出去了,大祠堂空了,才发现那个女人,被踩死在门槛上了……
牛彩英双手举在胸口,一直都没有放下来。阿纕奶说的龙门阵,她从来没有听过,但听起那么熟悉,这是说她夫家的事吗?还有那幢她引以为傲的三层楼房。阿纕奶口水滴答吐鱼泡泡的时候,牛彩英感觉到一双双眼睛落到她身上,又倏忽飞走,她脸上的皮肤刺痛刺痛的。她想起奢颇人若有若无的报应一说,她想起那空荡荡的楼房、她自己瘪瘪的肚腹……她的双手悬在脖颈处,像托着自己的心脏,怕一松,就露出某个真相。好几次,牛彩英想跳起来骂人,她甚至想阻止阿纕奶,责怪她乱说,但她没有,她从来没有像此刻这么安静。她闪烁的眼神瞄了几眼乌二贵,乌二贵脸上的表情和所有人一样,专注得有些迷离。
后来呢?打铁的乌泰问。
阿纕奶曲着身坐在那儿,腰以上就直了起来,她微微抬起她的下巴,深陷在肉褶中的眼睛,穿过高高低低的人丛,望向她根本就看不见的娘娘山。
我就说嘛,阿纕奶会摆故事得很。人群中有声音传来,试图缓解陌生的寂静,一些人听了,尝试松开揪起的心,阿纕奶又吐泡泡了,这就是让我睡不着的梦哦!散落在犄角旮旯的心,同时朝一个方向,齐刷刷地放下——原来是梦啊,放心了,放心了!说得我们奢颇人那么小气,怎么可能嘛。奢颇人怎么可能干出那种事情来!不可能,对,就是不可能。
乌小春小声问,祖奶,你说的究竟是梦,还是龙门阵?
阿纕奶的下巴放下来,一双老眼渗出黏稠的液体,对身侧的购梦人说:娃儿,对不起你,我们都是罪人啊!外乡人的双眼赤红,泪水淤积在眼眶里。阿纕奶又说,那天看到你,我的心放下半颗了。今天,心安了,可以睡了,我再也不想醒来了。外乡人颤着声问阿纕奶,老人家,那对夫妇后来……是怎么处理的?
……埋了。
埋哪里了?
阿纕奶指向娘娘山,嘴里吐出最后一个泡泡:大祠堂。
外乡人的十万终究是拿了出来,阿纕奶讲完梦就往生了(这一觉可以睡好长好长)。乌大春却坚持不要。外乡人就说,你们不是一直想修大祠堂吗?就当我捐给奢颇的吧。
这天,是大祠堂修葺一新的日子,奢颇人要给大祠堂披红挂彩,做最热闹的开祠仪式。一大早,牛彩花就起来收拾打扮。她穿了那件准备过年的红色羽绒服,围了根亮黄色的针织围巾,那是她给自己织的,还给乌二贵也织了一条。她让乌二贵也围上。乌二贵拗不过他婆娘——她就盼着这天呢,腆着个肚子,要向所有奢颇人宣布:我牛彩花怀孕了!要生崽了!乌二贵想了,再到乌东的饭馆喝酒,他可以昂起下巴嚼花生米了。
俩人拾掇好,刚出门,见一个人站在外面,听到响动,那人回过身来,冲两口子笑。乌二贵有点懵,恍若在哪儿见过。他想起一年前,就在这里,杂货铺门前,那个穿蓑衣的人,满脸的胡子,只是,眼前这个人胡子刮得干净,衣衫也整洁……倒是牛彩花机灵,看看那人,再看看乌二贵,俩人眉眼八分神似,牛彩花扯了扯老公的衣襟,说,二贵,这不会是大哥吧?顷刻,乌二贵肿胀的眼眶就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