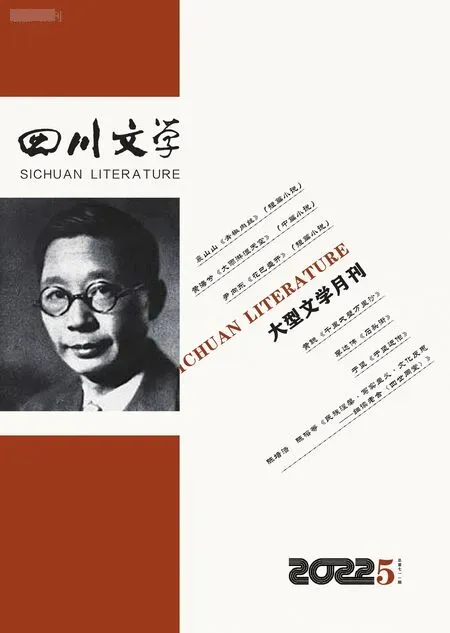琵琶缘
□文/张嘉慧
做梦也没有想到这辈子我会跟琵琶有缘。
1965年的冬天,我们县文工团在一个乡区演出。县文化馆馆长黄忠厚带来一个戴着眼镜的比我年龄大些的姑娘。说是弹琵琶的老师,姓陈。黄馆长介绍后大家立即邀请她弹一首曲子。她没有推辞,从套子里取出琵琶,又要了点开水烫烫手,然后戴上指甲。她说:“我弹一首《彝族舞曲》吧。”她用右手划动了四条琴弦后静坐了片刻,一串清脆、优美的音符有如跳跃的小溪从她手指间流淌出来。
只见她五个指头飞速地转动,“大珠小珠落玉盘”。那音调时而和风细雨般轻柔婉转,时而狂风暴雨般欢快激越。在场的人都听呆了。用“如闻仙乐耳暂明”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曲终了都还没回过神来。
在大家的要求下,她又弹奏了《十面埋伏》。那楚汉相争的古战场上人喊马嘶、铁骑突出、刀枪撞击的声音,把大家听得如痴如醉。
我惊叹她那么文雅、那么瘦弱,怎么会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后来我才知道,她的父亲陈济略老先生是四川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西南琵琶王。他不仅把自己的艺术传授给了女儿,还把她送到上海林石城(著名琵琶演奏大师)老师和其他造诣很深的大师那里去博采。加上她自己的天赋和勤奋,才铸成今日的艺术成果。
说实话,我们这帮十多岁的年轻人,全都是没有经过正规院校和专业表演技能培训过的,只在排演过程中相互学习、自己摸索而逐渐适应工作的。如今来了这么一位老师,还要培养学生,这是一个多么诱人又是多么巨大的喜事啊!
前不久,我们就听说要来一个琵琶老师,也知道她要培养两名学生的消息。谁也没有多大的兴趣与渴望。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琵琶不过就是像二胡一样的民族乐器罢了。二胡,几乎人人都会杀鸡杀鸭(形容拉得难听)地弄几下。那时要求一专多能,除了担任演员角色,还要学乐器。二胡便宜又便于携带,绝大多数人都在学。所以认为,学不学琵琶都无所谓。
听了陈老师的演奏,才觉得这才叫音乐、这才叫艺术。而这艺术将在我们女生中的两个人身上播种,不知这天大的幸运会降临到谁的头上。大家都期盼着。
团长好像是故意吊大家的胃口,压根儿不提这事。我们干着急也无法。
那阵我们工作、生活的条件是相当艰苦的。县上成立这么一个专业文艺团体,是为了开展农村文化活动的需要。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上山下乡为贫下中农送戏上门和辅导农村业余文艺表演。那时的交通条件不像现在这么好,从县城到乡下全是烂泥路,从乡上到各生产队的路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得背着被盖和演出用的服装、道具、煤气灯等步行到目的地。大家考虑到陈老师刚来,想要照顾她,争着帮她拿东西,但她却不让,坚持和我们一道背东西、拉铁丝、装台、挂幕布。有一次安排女生住宿,团长要把她安排到一个条件相对好点的农民家,她说啥也不答应,硬是搬了出来跟我们一起睡在猪圈上面。团长还在会上表扬她说:人家陈奉从大城市来,一点儿也没有资产阶级娇小姐的味道。
选择学生的时刻,终于来到了。那天下午,团长把全部女生喊到一起,让陈老师一一看手(学琵琶要手指长)。那天晚上,我没有睡着,估计所有的女生都没睡着。好容易盼到天明。盼来了团长让我和另一个女生到陈老帅那里去。
成了。我放下手里的饭碗就跑。没被选上的当然不好受,有位女同胞竟在夜里把我琵琶上的四根弦全部扯断,以泄心中的气愤。
这发泄可真是情有可原,那时学习乐器,教的人不成问题,也有在专业团体呆过拉得较好的,拉得好的教不会的。而乐器却都是自己买,我们学员每月工资15元,不但要供自己,还要供养家庭。要拿出几元钱买二胡,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们学琵琶,老师是请专业的,琴是团里买的,弦也是团里买的。这么多的好处全被我们占了,人家心理平衡吗?所以,我没有把这事汇报给团长。只说是我自己不小心弄的。如果实说了,那位同事不但要被重重批评,还要赔买弦的钱。
陈奉老师教学非常认真,特别是对基本功,弹、挑、轮、滚、按弦、换把的姿势,要求非常严格。她为我们定下每一个音符上的指法、指序、把位符号,一个也不能错。如果一点不正确,她会让你重来无数遍,直到对了为止。
她的语音很轻很柔,听她说话也有一种美的感觉。有时候我会故意出点错,听她用那温柔、优美的声音表达她的意思。
当我们会弹几首简单的乐曲时,团长要求上琵琶弹唱。陈老师为我们编选了两首弹唱歌曲,一首叫《学习焦裕禄》,一首叫《送公粮》。《学习焦裕禄》内容大致是这样:拨动琴弦高声唱,焦裕禄是咱的好榜样,毛泽东思想红灯高高举呀,照得革命的道路亮堂堂……《送公粮》里有一处撑音“得儿”就像四川清音里的颤舌音。要转很多弯,有八拍之长,陈老师一遍又一遍地示范,学得我们舌头发麻,最后好歹“得儿”圆了。陈老师高兴得像孩子一样。
不久,有人悄悄问我:“陈奉老师琵琶弹得那么好,按理说到中央、省歌舞团都行,为啥到我们这个县班子来?”我回答说:“是黄馆长请来的,黄馆长认识她父亲。”她说:“才不是呢。她父亲有历史问题。”我当时一惊,觉得这的确是一个事。是什么事,自己也说不清楚。那个时候已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已经浓浓了。
没过两天那位同事又对我说:“陈奉来绵竹前曾在部队文工团,还随团到广州参加中南区会演,一曲《彝族舞曲》征服了所有观众。可惜不久因查出她父亲有历史问题把她退回了成都。”
紧接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演出停止了。再来后,我们都回家去了,陈奉老师一个人住在公园里一间又黑又湿的小房子里。作为她的学生,而家又在绵竹的我,却没有常去看看她。
和她再次相见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了。在长长的三十年中,我们没有任何联系,为了生存各自忙碌。1973年文工团恢复时,她没有回来,那时她已成了家,有了孩子。
在这三十年中发生了很多事,明白了很多事,理清很多情感,虽然我们没有联系上,但在心中却实实在在地为对方留下了一个位置。
我知道她在这长长的三十年中,为了生计东奔西走,做过街道工厂的手工产品,经历过不敢想象的艰辛、磨难,最后,她终于成为四川音乐学院正式教职工队伍中的一员。但却不是以琵琶演奏家或民乐系教授的身份。这,绝不仅是她个人的失落与悲哀。
但她并没有与琵琶绝缘。如今,她的女儿弹得一手好琵琶;还有我这个已为人师的学生。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你们老师的老师叫陈奉,她曾弹得一手比你们老师不知好多少的琵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