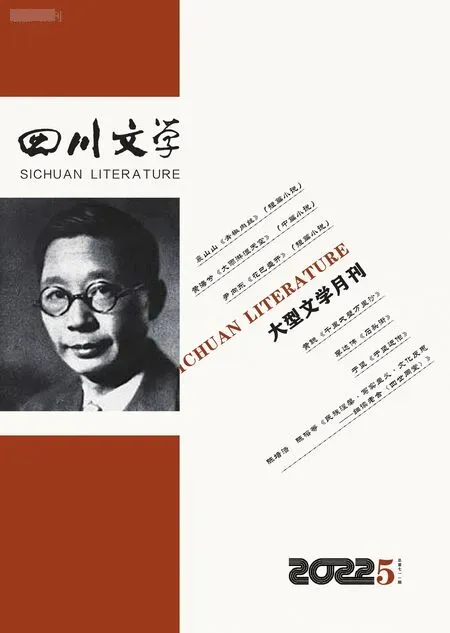某年某夏
□文/朱夏楠
某年某夏,去京城为叶同学饯行。
毕业回到自己的故乡后,我有意无意地避开着关于这座城市的话题,既然离开了,那里的一切便都与我再不相干了。可事实并非如此。过往的回忆层层叠叠,熟悉的人与事,一直徘徊在那里。只是现在回去,需要一个理由,不能显得太刻意。
没想到,为叶同学饯行成了一个恰好的理由。
叶同学博士毕业,正预备去香港浸会大学做博士后。聊起此事的时候,竟有天涯苍茫之感。此前,尽管我们两个一南一北,中间隔着长江与黄河,也不觉得什么。仿佛只要同在这块陆地,那么,始终就是连着的、可控的,虽说数年间再未相见,但似乎说见便可见。而去了香港,未来就变成了孤悬在外的不可知。
这不可知需要一份郑重的仪式感来冲淡。
1
列车一路向北,从白昼开入暮色,漫长的路途骤然止步于灯光灼灼的北京南站。光鲜亮丽,只是有些陌生。从前的往返,多在北京站,灰色的建筑,空旷的广场,熙熙攘攘背负着繁重行李的人群,喧哗又默然。
新鲜的疏离感扑面而来,我迅速进入了游客的角色。这些因机缘四方而聚合的散沙,随时预备流向四方。我从南站流向了双井,才九十点钟,巷子已经暗了,灯光在远处,人罩在影子里。影子里走出来的是莎莎,一脸灿然。
老同学,多久没见了呢?我们不约而同地想要把时间线拼凑起来。哦,最后一次,是一起在未名湖边过了一个大雨滂沱的中秋。那是五六年前,她还在北大读书,而我在五道口混迹于文青之中。现在,我们被时间推着踏上了新的旅程。
她接过行李,引我去了住处。房子是合租的老小区,刚用粗糙的水泥刷了新,裸着灰色的颗粒。屋内摆设陈旧,浴室门都是折叠式的玻璃材质,晕着彩光。发黄的四方餐桌贴着墙角,为厨房腾出一些空间。她熟练地开火、放水、下面,还打了一个鸡蛋。旅途劳顿消退后的饥饿感涌了上来,被温暖市井气包裹了。
卧室不大,床挨着窗,窗沿上放着一盆半开的茉莉。探头望去,底下低矮的一爿屋脊黯如丘壑,唯有朗月当空,剪出茉莉的影子。这样寂寥的京城,是我未曾见过的。
莎莎侧身用毛巾擦拭着湿漉漉的发丝,氤氲的水汽,像是回到了本科的时光,两个南方姑娘挎着篮子结伴去澡堂,羞怯,又强自装作不在乎,目不斜视地穿过长长的人群。高大的白杨树上,筑着很多硕大的鸟巢,不时有黑色的鸟群飞过。
北大读完硕士后,她入职了唐山一家钢铁企业,并很快以所在企业的优惠价购置了房子,还将远在四川老家的母亲接去同住了。她在电话里和我说起这些的时候,我不由得称赞她能干,仅凭着自己,就能在一座城市中安身立命。她却没有岁月静好的安稳,相反,充斥着显而易见的不安。
那座重工业城市,充斥着机械与笨重、重复与单调。她无所适从的焦灼顺着电话线从唐山传递到了我所在的江南。年轻的我们对这个世界其实所知甚少,除了家乡,便是负笈求学的京城了。没有人可以引导我们。是无知,也是心怀侥幸,以为另一个城市不过是稍微逊色而已,不至于相差太大吧?可她终究还是无法忍受,随即辞职,回到京城,一切重新开始。
是彻底的重新开始。她放下了本科就读的新闻学、硕士就读的语言学,扎进了保险这个陌生的行业。这比跨越城市的选择,更令我错愕。在我的偏见里,这个与推销勾连的名词多少沾染了些市侩气,劳碌而廉价。然而莎莎是认真的。为此,她特意攻读了经济学学位,业余时间里在网上听各种名师讲课,并认真地做着笔记。这座城市给了她再次选择的机会。
新的事业也让她找回了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她如数家珍般向我介绍着保险的种类、意义与发展前景,说了很多很多,具体的内容,我已全然忘了。对不感兴趣的事物我的记性总是很差。我不关心这个行业,只是看到莎莎那骄傲的模样,我相信她的选择是对的。她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没有什么比当下的充实更重要。
她略微带着些歉意道,周末我要回唐山陪母亲,怕是不能带你逛了。或者你再多住几天,等下周?
我忙婉拒。此行是来看看旧时的朋友,见见面,聊聊天,已然足够。而且,也和其他同学约好了见面。
住哪里呢?
朋友那,或者是酒店,都行。反正我行李少,可以说走就走。
你还是和原来一样。她露出了熟悉的笑容。
第二天,莎莎换上了职业套装,步行前往国贸,笑容一如名片上的干练精神。白天的这条街道撕去了寂寥的包装,阳光穿过纤细的枝叶疏疏落落地洒在她肩头,照耀着她的未来。
2
我向东而行,去见琼女。我读研时的舍友,一个美丽的四川姑娘。
琼女在欢乐谷附近租了民宅,租金少而空间宽敞,唯一的不足是交通不便,地铁无法直达。不过对她这个不上班的人而言,也无关紧要。
她回来一年多了,她的回来出乎所有朋友意料。这座城市里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她过得并不快乐。几年前的毕业季,她甚至是以厌弃的决绝姿态逃离的。
在望京的研究生院入学半年后,我们很快就被发配去了良乡的新校区。没过几天,她说我晚上常常说梦话。有时英语,有时家乡方言,而她只依稀记得普通话版本:
“这里什么都没有,到处都是光秃秃的。”
彼此相视大笑。是的,我们落脚后,草木才随之栽培,随之茂盛。我说,我们是拓荒者,也是小白鼠。先看看我们能否活下来,再让花花草草迁居于此。不过我很快就适应了。一所学校所应有的,这里也都有,就够了。外面的世界再精彩,日后总会见识到的。而琼女则不然,她几乎要抑郁了。
在她那个重男轻女、重商轻教育的家庭里,她的堂姐或表妹们,都仰仗着出众的基因早早结婚过上了富足的日子。只有她,跟随着稍有见识的爷爷长大,才在求学上花了心思。多读了些书,那样的日子她便不愿意屈从了,所以决定考研。原想读古代文学,觉得太难,又改选了现当代诗歌。然而参加了几次诗人活动,其装腔作势之态令她深觉腐朽酸臭,又失去了兴趣。
写诗歌就不能正常些吗?现在东西不怎么样,人先端起来了?她皱着眉头。
大概是写作水平的提升终归不是件容易的事,而臆想中的清高之举反倒是容易模仿的。模仿久了,也就骗过了自己,当真把自己当作了不得的诗人了。我推想着。而后来当上了编辑的我,体会到了琼女当日的痛苦。
只是她当日的痛苦迷茫无可排遣。最初是为了什么要来这里的呢,能获得什么呢?这样的三年时光,找个好人家嫁了像她姊妹那样过日子不好吗?她甚至觉得,她父亲的读书无用论或许是对的,困守于这个穷乡僻壤之中,不过是徒劳地浪费着美好的青春。这个地方多么土气,身边的同学多么土气,只有她还保持着与生俱来的美丽。如果身边的一切都是美美的就好了,这是琼女的愿望。她有时也忍不住敲打我,希望我作为她的舍友能打扮得漂亮一点,用她的卷发棒,用她的眉笔和指甲油。然而指甲油的味道散着刺鼻的化学药水味,试了一次我就放弃了。想到每天晚上要将一早精心描绘于脸上的颜色拆卸下来,我更觉得无趣。她笑着说,你简直不像个女孩子。
可这个美丽的女孩子,遭到了北京的亏待。到了没多久她就皮肤过敏了,不能晒太阳,一晒就长疹子。这对爱美的她来说,无疑是场酷刑。后来,又因为赶论文而伤了眼睛,遂一毕业,就以最快的速度逃往了家乡。
毕业的那个夏天,她对我的忧伤嗤之以鼻。她只想着逃离,去投身于社会的风浪中,去施展一番拳脚。彼时新校区的荒草已经长成了规整的模样,大片的树荫是我们留给后来者的礼物。
后来的日子我们天各一方,偶有联系,只听得生活并未能如她所愿。因眼睛不能看电脑,没办法找个适合的工作,她干脆四处游走。在丽江的青旅她做了一年的柜台,接待形形色色的游客;她还在束河边,和一个退伍的兵哥哥学散打,说自己体质太差了,该好好锻炼,不然无法应对这个粗糙的社会。最后,回了四川老家,想着还是结婚吧,像她家人期待的那样。但是事情走向了另一个方向。每次提起此事,我们都禁不住爆笑。不知是不是介绍人有意隐瞒,相亲的男生在见面的时候才得知她是硕士生毕业。男生错愕,继而光速离席,仿佛对面坐的是一头怪兽。
“有这么可怕吗?”琼女几乎快笑出了泪花。
不可思议,魔幻,太过戏剧化。后来想想,那只是我们的认知而已,我们都生活在各自的偏见里,这是无可奈何的事。琼女终于认清,家乡也许并不适合她。
这是一段阴郁的日子,意外地闯入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读研时一个隔壁班的男同学。他热烈地追求着她,从西安飞往成都,为她捎去各种礼物,以及各种笨拙的甜言蜜语。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琼女想,要不就是他了吧。男生热情,却并不自信,她决定做些努力。像他们约定的那样,她去了西安,表示愿意放弃从前浪迹天涯的生活,愿意洗手做羹汤做个贤妻。可这却成了她的一厢情愿。男生的家人以传统自居,他们无法忍受,也不愿信任这样一个散漫的、没有正经工作的结婚对象。
“是我配不上你。”男生低下了头。他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尽管,也曾渴望着借由耀眼的火焰挣脱束缚,但终究还是认清了,自己并不是那样的人。
琼女带着一身伤回到了北京。是自我放逐,也是想要找寻出路。自己怎么会落到这般狼狈的地步呢?她不明白。她想既然到了北方,索性再去见见师友吧,或者找个工作也好,先养活自己。工作找得并不顺利,反而遇上了从前暗恋她的学长。兜兜转转了一圈,好像只是为了他们相遇。
这次见到琼女,她还是一样的漂亮。我甚至怀疑此前她说自己遭受的那些痛苦与折磨都是夸大其词。她笑我天真,生活哪有那么简单啊,看自己现在不是又陷入了难题么,一个似曾相识的难题。
学长的母亲强硬地要求他们分手,她心目中的儿媳妇应该是个家境优渥的北京姑娘,而不是琼女这种外地的小康家庭。这样的婚姻无助于他们家族地位的提升。琼女累了。她早已从爱情的幻梦里清醒过来。西安之行,不过是无望的生活中自以为的救赎,她并没有那么喜欢那个男生。她只是,给自己空虚的人生找了一点寄托,却误将之美化成了爱情。男生是对的,他们确实不合适。现在的她,对爱情,并没有抱过多的期望。她只想好好地爱自己,做回最初自在的自己。
她提出了分手,但是学长不让,宁可与家庭决裂。平息所有争议的,是新生命的到来。琼女意外怀孕了。她不忍心打掉孩子,由此不得不打乱了他们最初丁克的计划,而这也意味着他们必须得郑重地开始考虑未来了。结婚、买房,随之像逃难一样仓促地被提上了日程。但矛盾依然在。她未来的婆婆依然不满意,甚至在两家父母见面时,还在为当初棒打鸳鸯的失败而耿耿于怀。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变成了被生活推着往前走。她苦笑着,说,有时候想,真的还不如单身呢,不用去应酬那些不相干的人,也不必让自己的父母跟着受罪。
反正是你们两个人过日子,学长靠谱就行了。我的安慰苍白无力。凡是选择,都有放弃,放弃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热爱自由的灵魂,对尘网的束缚更为敏感;而自由本身,又何尝不需要付出代价?
好久没出去见人了,都忘了怎么打扮自己了。她打开衣柜,拎出一件件衣服在镜子前比画着。
3
次日一早,我们从东边往西北而行去北大见叶同学。另一个同学非雨,则从四号线的新宫站上车,将与我们在同一个目的地会合。
正好,我也要还书给叶同学呢,趁他现在还没离校。非雨的公司就在中关村,想看书又找不到的时候,就会拜托叶同学在学校里帮她借。她幽幽地道,以后怕是不行了。
非雨是语言学专业的,和我们不是同一个所。语言学其实偏向理工科了,她曾经正儿八经地和我科普。我听她讲实验讲数据,渐渐地,觉得语言学都该从中文系中脱离出来自成一派了。
她的宿舍和我们的挨着,时常串门,又常一起玩游戏,关系自然就密切了。那时班长大人定期会组织玩桌游,三国杀、仙剑奇侠传、小白世纪等等。只要和非雨搭档,几乎都是稳赢。她有着极强的计算能力与逻辑推理能力,甚至能够记下牌面。每次打出制胜的一招时,都能听见对面的男生在战栗。
非雨长相温婉,笑起来有浅浅的梨涡,谁能想到梨涡下藏着的是一个霸气的御姐。其实这样不好。她掩口而笑,该装的时候还是要装,满足下男生的虚荣心。自然,很多时候她是不屑于装的。她沉浸在美好的二次元世界里,还有天涯四美中的某个角色,为此还写起了各式各样的同人文。与之相比,现实世界简直无趣至极,不过是为了供养肉身而存在。
有段时间,她被拉入了粉圈,但很快就退了,此后也对这个圈子避之不及。她微微蹙着眉,说那里乌烟瘴气。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欢的只是某个角色,而后捎带着喜欢某个演员而已。喜欢是很私人化的事,自己的喜欢并不意味着那个演员当真有多优秀。因为当她在粉圈里听到种种溢美之词时,一层层厌恶感从心底涌起。再看那个演员、那个角色,哪里配得上这些吹捧?心思就这么淡了,她愤然道,再在那里待下去,她就要转路人黑了。
当然有些朱砂痣,一直都在。在2016年夏天,在日子拮据的时候,她突然飞往英国,去见了她喜欢了好久的一个演员,《邪恶力量》中的男主角Dean。漫长的旅途,漫长的白昼与黑夜,去见一个人。
我只是觉得,需要给自己的喜欢一个完结的仪式。她说。当她意识到自己对他的喜欢在淡去时,有种无能为力的惊恐。明明还是喜欢的啊,所以她想做点什么。当她得知这个美国男演员将在英国出席活动时,她义无反顾地买了机票。
他有看到你吗?
没有吧。不过这不重要,我见到他了就好。真人也很好。他的妻子也很好。
一切都很好,所以她选择了适合的时机,让这段喜欢有了圆满的落幕。
那一年,她在新东方管着一堆负责网络运营的程序员,充分发挥着自己的统筹特长。唯一的不足是,北京的房租太贵了。住在天宫院,每次要花上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能抵达位于中关村的公司。为了能在地铁上找个座位,她有时候先多等几列车,让前面排队的人被消化得差不多了,才上车。然后找个座位,睡上一路。
压力最大的那段时间,她甚至要想过调去杭州的分公司,但最后还是选择留下来。这也是大多数北方同学的选择。他们习惯了这里的水土与人情。意识到自己大概不会离开北京后,非雨迅速对自己的人生做了规划,最重要最现实的,就是买房。
凭自己有限的收入自然是无法在北京买下房子的,所以她早早就跑去河北查看,最后看中了张家口这个地段。通过精密而烦琐的计算,她认为尚能够负担得起,于是迅速地用尽各种方式攒首付,工资、信用卡套现、亲友借贷……零零碎碎地,居然凑成了。
就在这段紧张的日子里,她去英国见了年少时的偶像,像是对过往青春的一场告别。一场独属于她的告别。然后,投入现实的零碎苟且与剑拔弩张之中。
京张高铁开通后,到北京就很方便了。想到即将交付的房子,非雨满怀信心。她说有了房子心里都安定了,以后就算嫁不出去,也算是个归宿。我们说起了晚年,仿佛近在咫尺。像应对一场战斗,我们需要靠自己囤积粮食与装备。
可是有些人总归是要离开的,比如叶同学。到了北大,他正在校门口迎接我们,人群中一眼就能够认出。
这年夏天,毕业数年后,我们终于重聚了,以饯行的名义。
4
校园似乎有让时光停滞的功能,叶同学的身上看不出任何变化。还是那个,在暗夜里骑着自行车去地铁站接我们的,叶同学。
在良乡读书时,校区离最近的地铁站还有段荒僻的路。旁边是农田,车子少,路灯也是暗暗的,还不时会窜出野狗。记得当时为了防身,我还加入了学校的武术协会,学一些诸如金丝缠腕的简单技巧。但是会长直白地说,碰上力气大的,一切都是花架子。心理上的安慰,无法抵挡对暗夜里那段路途的恐惧。因此班上的女生回去晚了,男生们常常自发骑着自行车来接。叶同学也是其中的一员。
当时房山线与九号线还未接通。某个夏日的晚上,我打的从空白的这端驰往那端,出租车师傅说可能赶不上地铁的末班车了。下了车,我急着奔赴房山线,脚下不稳,狠狠摔了一跤。进了站,检票的工作人员见我裤子破了,膝盖处血肉模糊,脸上又挂着泪,吓了一跳,对着随后跟来的司机怒目而斥。我又痛,又因误信了司机的话而深觉屈辱,只是含混不清地解释道,司机不是坏人,只是以为末班车要没了。工作人员温柔地安慰着我,说时间充裕的。司机也连连道歉。
那天来接的叶同学也吓坏了,但是校医院已经关门了,他只能帮我简单地处理了一下。第二日陪我去敷了药,伤口灼烧着。他帮我轻轻吹了吹,说没事的,这点小伤,不会留疤的。他见我紧张,觉得好笑,说自己所见过的伤情比这个可怕多了,最后也都好了,不会留疤的。又说那个司机肯定是想骗你一路打车到这里,要是我,肯定就戳穿他了。他絮絮叨叨地说着,我哭笑不得,只能感谢他的好意。
叶同学的耿直可爱常让我们哑然。某年暑假过后,他从家乡带来虾干送给我和琼女,认真地说,这是自己家晒的,每天只能吃三个噢。
一脸郑重的模样,仿佛是在开医嘱。我们面面相觑。琼女是内地妹子,不解有什么讲究。而我的家乡在海边,对虾干并不陌生,却也不懂何故,就追问着。
他迟疑了一下,憨笑着说,反正,多吃就是不好的啦。
到底有什么不好,最后都没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我们捧着着珍贵的远道而来的礼物,最初两天还依言奉行,而后完全将之抛诸脑后,大快朵颐。似乎身体也没什么异样。
叶同学很像个书呆子。就一个话题争论的时候,他答不上来了,就喜欢掉书袋,说,我觉得你可以先去看看某某书,那个时候我们再讨论。书我们自然是不会去看的,讨论也不了了之。后来我遇见有人说我书呆子的时候,我就想起叶同学。我明明还不够资格。
对这个班上唯一的文学系男生,我们总是心存爱护的,也一致认为他适合读博。毕竟他的心地纯粹,除了学术似乎别无所好。所以当他终于如愿以偿考上心中的理想学府北大时,所有人都为他高兴。这几年里,非雨不时地去找他借书,琼女回到北京后,三人也偶有小聚。而我和他虽然数年未见,彼此间也不觉得陌生。
北大的校园似乎还是那个样子,只是夏天的太阳照下来,晃得人看不清,只觉得白白的一片,所有人都面目模糊。
叶同学说不用去外面吃了吧,食堂里什么都有。用罢午饭,四人又去旁边的咖啡厅小坐。闲谈了几句近况,话题自然地拉到了毕业的事宜上。他有些后怕地说,这届的中文系博士通过率不到三分之二,很多都延期了。
延期,我们想起了金师兄。金师兄是文学系的博士,与我们都不是同一个导师,只是我们都习惯这么称呼他。他是个韩国人,据说服兵役时还在总统府站过岗。因为喜欢中国,来了好些年。我们读硕时,他正在写关于李白的博士毕业论文。他一本正经地说自己梦见过李白,李白鼓励他好好学习,不要懈怠。他相信自己与李白在冥冥之中是有关联的,因着这股子力量,他奋笔撰写博士论文。可惜论文没有完成,只能延期。
当时他的心态还不错,打算用两个月的时间,去走李白当年走过的路,也为自己整理思路。他去当涂县祭拜了李白,而后去西安见识盛唐。但是旅途很快夭折了,在西安,他遭遇了骗子与小偷,心灰意冷下提前回了北京。第二年,导师不忍见他这般辛苦,同意只要他完成论文就让他毕业。却没想到金师兄选择了不辞而别,切断了所有的联系方式。
记得他在西安时,还特意来电说,不能来宁波看我了,那些连环套的骗局让他对很多事情包括对自己产生了深切的怀疑。笑话,全都是笑话。这是我与他的最后一次通话。一些美的想象破碎了、消解了,我想对于一个心地澄明的人来说,这个打击远比论文的失败要沉重。
现在远在韩国的他,还在读李白吗?我们不得而知。
金师兄真是个很认真的人哪。叶同学慨叹着。
叶同学选择了浸会大学,是因为香港这个城市。他想去接触下不同的文化,见识更广阔的天地;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那里离他的家乡潮州不远。家乡离开再远,都是特殊的存在。
有一天,我也会离开的。琼女说。她依然不喜欢这里,也没想过要长住。有了宝宝后这个想法更坚定了。这里的房价之高、教育资源竞争之激烈都不是她所能承受的。她还是适合天府之国那种安逸的日子。
那我下次再来北京,没几个朋友可以聚了。我莫名有些伤感了。
反正我应该是赖在这里了,哪里都不会去。非笑道。
去香港找我也可以啊,我们那里聚。山河万里,都在他眼底涌起。
那你千万不要被资本主义世界的糖衣炮弹给腐蚀了啊。我敲打着他。
四人都笑了起来。那些鸡零狗碎的现实琐事暂时放过了我们。咖啡厅内空气凉凉的,透过并立的落地玻璃窗,外面是满地绿荫。阳光已经冷了下来,这个夏天似乎没有预料中的燥热。行人来来往往,就像这个城市,有人逃离,有人回来,也有人以一个游客的身份,远远观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