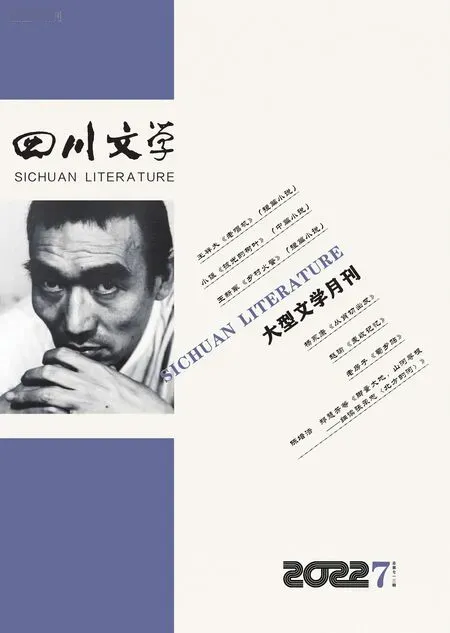纤夫的救与赎
□文/梁芳
太阳砸到山头,鲜血喷涌,天空泼满了血。金沙江映在血光里,它咆哮得更欢腾,噬血的兴奋,狂奔、怒吼。
同样怒吼的,还有这群纤夫。
(领)喔喔,吆不嗬
(和)嗨嗨
(领)吆喽咦喽吆,吆喽咦喽吆,喂喽嗨喽吆
(和)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今天这滩,挣不上去。纤夫与金沙江,拼命了,号声更急,鼓起的胸肌积蓄力量,逼出的汗滴撞击乱石。17岁的江大满脸通红,肩背忘记了痛,匍匐,用力,脚蹬着石头。他听到旁边陈二吼号子的声音,稚气,嘶哑,他还是个孩子,比江大小半岁。江大吼不出号子,用领头号子师傅的话说,江大的嗓门还没有开。突然,陈二急速往后仰,手在空中捞了一下,似乎要抓住江大。砰,一声巨响。是人与石头撞击的声音。江大停下了,救人,是他本能的反应。“走”,旁边吴大叔一声大吼,江大来不及思考,再次用力蹬石,前进,石头,吞着泪与汗。这个时候不能松劲,松劲会有更多的伤亡。号声更有力了,渗着悲,渗着痛。
黑,蚕食着天空的血,当天边还有几缕红色的时候,船,终于挣上了滩。水,平静了。“靠岸吧!他还小,不能丢下”,领头纤夫说。“纤夫,死了没人埋”,这是俗语,因为,伤亡随时有。江大跑得最快,陈二与他一起来当船工的,两家是邻居,开裆裤的朋友,江大是家里老大,兄妹6个,他得挣钱养家,船工,可以实现养家目的。听说江大去当船工,陈二也闹着去,他家相对宽裕,不需要他养家,父母不同意,船工,苦,危险,他们不舍,陈二执意要去,他要跟着江大,他们是朋友。陈二已经没有了气息,头,撞到了石头,江大在一个石缝间看到了脑花,白嫩嫩的,像猪脑水。江大胸口堵着一团悲痛,发不出,按不住。他颤抖着摘下白头巾,把脑花包起来。纤夫们都取下白头巾,把陈二的尸体慢慢裹着,像是裹着他们后面的人生。他们求着船老大,“把他带回去吧!他父母想见儿子。”
一段时间,江大神情木讷,痴痴说一句话,“我可以抓住他的,我可以抓住他的。”船,还是照样行驶,纤夫照样吼着号子。江大比以前更拼命了,堵在心里的那团悲痛像长了结,拔也拔不出来,那白嫩嫩的脑花常在眼前、在梦里。他想喊,他想吼,却发不了声,堵,逼着他迸发,他想抓住什么东西,一种救赎他灵魂的东西。
甲板上,江大吹着风,船靠岸了,今晚,要在船上过夜。洗漱完的纤夫早早爬到了床上。上下床,十几个人一间。想家的纤夫无法入眠,吼起了号子,声音在黑夜中来回穿梭。江大听着号子,一种力量牵引着他,他开始揣摩号子的旋律。这夜,月黑风高,他跳下甲板,站在大石头上,这是陈二去世的地方,江水带着黑夜咆哮。江大大吼一声,嗓门一下开了,他对着黑夜,对着滔滔江水,声嘶力竭吼着,吼声拍打着野兽般的江面,拍打着悬崖峭壁,他思索着号子的旋律,吼出的声音渐渐变得婉转而雄厚,这是号子!他,终于吼了出来。
(领)吆……嗬喽嗬
(领)吆……喽咦哈
(领)手巴鹅石脚蹬沙,啦呀联手
(领)找点钱来盘冤家哦
(领)二四八月凉风天,拉呀哥呀
(领)哥哥走路妹来牵哦
江大心中的结,被号声带进茫茫的黑夜,卷入滔滔江水,化解,远去,再远去,心中豁然开朗,他开始搜索记忆中的词,他开始编造生活中的词,一遍又一遍,他用力吼着,声音穿透夜空。船舱里的人震撼了,领头纤夫说,明天,他来领吼。
水,船,纤夫。
从宜宾到雷波,一百多里。金沙江水,金黄,像千军万马咆哮。船,或沉或浮,或上或下,它是旁观者,更是始作俑者,任由水与人斗。纤夫,一个标签,成为水与船的附属品。他们忘记了“人”这个称谓,至少,在沙与石、水与船间,“人”,渐行渐远。他们背着晨曦匍匐前进,把它背到山巅,汗水与鹅卵石撞击,鹅卵石尝到了苦涩。他们不读夸父追日,每个脚印理性而踏实。
一百多里,水,是最先号叫的,它怒吼,它咆哮。唐古拉山的冰雪是它的号角,它是狂奔的骏马,脱缰,那是自由的狂野。纤夫也想自由,老母妻儿编织的缰绳让他们套上这根纤绳。纤夫不走,走,也要带着纤绳,哪怕,不堪重负。他们也想怒吼,就像金江水的咆哮,力量,压着的肩背,太阳,烘烤的古铜,心中的火在燃烧。压吧!力量,到极限,就会迸发。江大胸腔一股热流,涌动,积聚,挤压,喷发。上下快速蠕动的喉头按捺不住了。破口而出,声嘶力竭,响彻云霄。
(领)吆喽……吆喽嗬
(和)喔……喔
江大成了领唱,从宜宾到雷波,每一个脚印踏着一声号子,这一吼,他成了号子大王,这一吼,就是37年。
号子救赎了江大,号子救赎了纤夫,宜宾到雷波不变的是石头、沙滩、江水、船。变化的,是号子,他们可以随意编造,心里所想,便是号声所在,纤夫心里跳跃着火焰,他们燃烧着生命,他们知道,号声,在诉说着人生,这时候,他们感觉到自己作为“人”的存在。
江大,在号声中成长,在号声中得到救赎,他说,陈二,一定能在天上听到他的号声。而他,会在生命中懂得号子,号子让他看到了生命,他也更加珍惜每一个生命。
那天中午,阳光刺人,船顺水而行,纤夫都在船上。这个时候,纤夫是最享受的,他们可以慵懒一会儿。船过了小城,要经过一段暗礁,今天的船,超载。暗礁与船碰撞,翻船就在这不经意间发生了,船员和纤夫们都是上好水手,这是他们生存的本事,水与他们是一体的,与水斗,也是生存的一环。俗话说,“金沙江上险滩多,不是行人安乐窝”,在金沙江上行船,翻船、死人是常事。江大遇到翻船也不是一次两次,他们都没有惊慌,凭着上好的水性游到了河岸,各自散了。江大想在江边休息一会儿,他望着翻过来的船,在江中起起伏伏,船底若隐若现。突然,他大叫一声,“不好,乌家两口子还在船舱”,他一头扎进江水,快速向船游去,他依稀记得乌家两口子的船舱,因为他去拿过衣服,还同他们说过两句话,他们是搭乘顺风船到宜宾看儿子的。他敲着船舱,里面有了回应,江大换了口气,摸索着进去,还好,船舱里还有点空间,他拉着乌家男人的手,把他拉了出来。乌家男人顺利被救。江大把他送上岸边后,再次跳入水中,同样的办法,他去拉乌家女人,江大突然觉得拉不动,女人胖,被船窗卡住了。江大用力掰船窗,无用,咋办?舍弃吗?不行,江大觉得,眼前的生命,他要挽留,陈二看着呢?他冷静了一下,工具在另一个船舱,工具舱已经被水全淹没了,江大深吸一口气,钻下去,摸索着,终于摸到了锤子,他快速游到女人船舱,用锤子敲窗,水中操作很困难,眼看水在慢慢往上涨,江大默念着,“一定要把人救出去,一定要把人救出去”。他更加用力了,终于,窗敲开了,女人得救了。回到岸边的江大一下瘫倒在河沙上,睁开眼睛的时候,太阳还是很刺眼,他清了清嗓子,吼起了号子。
(领)喽咦喽吆,吆喽咦嗨喽嗨嗨
(领)山有高,路有窄,歪着金莲走不得,吆喽咦喽吆
(领)年轻不妖,老来妖,老来看你咋开交,吆喽咦喽吆
这是愉悦的号子,江大觉得有种快感,一种救人的快感,号子在江边跳动,江水也变得欢畅,他仿佛看见了陈二的微笑。
江大来自小城,这个小城是金沙江航道必经之路,小城在山下,狭窄而修长,像一条横卧的鱼。小城的人们每天都听着号子,这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依赖,更是一种承诺。
江大与号子浑然一体,号子与金沙江浑然一体,金沙江与小城浑然一体。号子像一道划痕,每天从小城掠过,小城便与号子结成联盟,一种灵与魂的联盟。
峭壁静默,顽石孤寂,金江轻喘,挤压在山脚的小城酣睡。
吆咦喽吆……吆喽咦喽吆……喂喽嗨喽吆……
远方,缥缈的旋律从江面跳动而来,在平静的江面轻溅起浪花,圆的、滑的、柔的,如一缕冉冉升起的青烟,飘在若有若无的心底,如一缕清风拂过少女的情怀,桃花般染红了羞涩的笑脸,如几颗闪亮的流星划过,湛蓝的天空燃起爱的火花。酣睡的小城听到远方的召唤,“该醒了”,它梦呓般说道。
号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震撼,小城躁动起来了,江边的洗衣女,手随号声舞动,号声击拍着她肩背,燃烧着她炽热的心;挑沙工肩头的扁担随号声起伏,音符挂在了扁担两头;大婶的勺子随着号声节奏翻炒;农夫的锄头,一下,一下,跟随着号子的旋律。孩童停止了打闹,欢呼着奔向江边……一切都凝聚了、躁动了、亢奋了;红的、白的、黄的、蓝的,大的、小的、少的;恬静的、开朗的、郁闷的,全动起来了,小城翻卷着、沸腾着、欢悦着,弥漫的号声渗透在每个角落、每个毛孔、每个细胞。
一群赤条条的纤夫,几十根颤抖的纤绳,系着最原始的力量、最原始的魅力、最原始的纯粹。他们裸露的躯体展示着天地间最淳朴的情怀,他们是一群完美生命的结合体,只有凝聚,才能生存,只有凝聚,才能完成任务,也只有凝聚才能迸发出这样的号子。厚重的,圆润的,洪亮的,铿锵的,高昂的,辽远的。号声萦绕在河谷中,翻滚,升腾,他们攀峭岩、过险滩、劈恶浪、斗暗礁,每一个脚印都烙着血汗,每一个脚印都写着艰辛,每一个脚印都留着酸楚,每一个脚印都刻着疼痛,每一个脚印都重复着昨天的故事。他们是用汗、用血、用生命书写着纤夫的歌,每一次迸发都是心底最易触动的情愫,痛苦、艰辛、难过、孤寂、思念融进号子中迸发了、释放了、宣泄了、沉淀了、豁然开朗了,他们把月亮变成了太阳,把萧萧的落叶变成了明朗的春天,明天鲜活的血液又将重新沸腾。
纤夫的故事系在纤绳上,流淌着、流淌着……
这一流淌就是千年,金沙江下游自古通航,据《三国志》和《南中志》记载,公元225年春,蜀相诸葛亮率军南征,走的就是这条水道。唐宋年间,金沙江下游浮木塞江,水运景况繁华。据《绥江县志》记载:“宋代已有舟楫横渡航行”。
1969年绥江县第一艘机动船下水后,木船逐渐被取缔。号子也逐渐消失。江大他们不得不离开船,小城,再也没有了纤夫。“我们可以离开船,但小城离不开号子”,江大说。江大做起了小生意,卖猪饲料谋生。小城的人们到江大的小店,不买饲料,听号子,来的人,江大都吼一段,人们满足了,喝一盅老茶,离开。江大自己也吼号子,不是在家,他必须到江边,仿佛那里,才有仪式感。
在“金江号子”传承基地,我见到了江大,基地不大,只有20平方米,是他自己出资成立的,他说,有地儿了,才有人愿意来听听、学学。我环视了一下,基地墙壁上,挂着纤绳、白头巾、草鞋等物件,还有一些船上的摆件。桌上,有一叠江大手写的号子歌单,江老告诉我,很多人都想把它谱曲出来,我也找了好些人,但都没有成功。你想,咋能谱曲出来呢?都是我们自编自唱的,我编的唱词就有四五百首,曲调几十种,谁能谱得出曲来?我望着眼前这个清瘦的八旬老人,黝黑而精神抖擞,这是金沙江染的色,这是号子传的神。“你看看我的肩膀。”他拉下右膀的衣服,不规则的疤像地形图。我想,这地形图也测量出了他人生的深度吧!他说,我是船工,就是你们说的纤夫,专以纤绳帮人拉船为生的人,也是金沙江船工号子喊号领头人。
我对号子充满好奇,想在老人的眼里,找到号子的魂,他的眼睛浑浊、暗黄,却有一股力量、一种坚韧。我看到了他眼中的金沙江,正在奔腾、咆哮。
江大说,这几十年,号子在救我。家庭、生活的重压,我能坚持,是号子给了我力量,吼着号子,会把生活的不幸吼出去。
号子,我不知道还是个好东西,也不知道真有人把它当成宝贝。江大回忆说,那是1970年初春,歌唱家李双江找到我,李双江,你知道,唱歌的,著名歌唱家,他唱歌,好听,如果他当船工,吼号子,一定是领唱。李双江老师很随和,我给他讲了金沙江、纤夫、船和号子的故事,他非常高兴,偶尔,打断我说,等等,再重复一遍,我还没有记下来。听我唱了金沙江下游船工号子《二度梅》后。你知道吗?李双江老师高兴得直拍手,连说几声“好,好,好”。还当即回唱了一曲《巴山草鞋》,李双江老师的声音,“啧!啧!”那才是真的好听。后来,我才知道,李双江老师是专门来收集民歌素材的,他的那首《船工号子》,唱响了全国各地。
船没了,不能没有了号子,号子救了我,救了纤夫,也救了小城,怎么说呢?金沙江号子,就是让我们活了过来。我得要救号子。说这话的时候,江大很坚定。
这30年,江大在拯救号子,到全国各地演出,把舞台上的金沙江下游船工号子唱到了北京、深圳、上海。他与日本、印度、埃及等国交流河流号子经验。金沙江下游船工号子表演获得了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等几十项殊荣。
这30年,江大把寻找热爱号子的人,当成生命的意义,学生、教师、公务员、工人,只要爱好的,他都教。
这30年,他成立了金沙江下游船工号子传承基地。
这30年,金沙江下游船工号子成为省级非物资文化遗产,他成了金沙江下游船工号子非遗传承人。
一度辉煌的号子渐渐冷了下来,没有了纤夫,金沙江下游船工号子没有了根。江大忧伤地说,我努力了,我救不了号子,我的徒弟,越来越少。他们只是一时兴起,学生更是一时新鲜,隔夜就忘了。想学的人,没有当过纤夫,唱不了那个味。号子,是与金沙江、船、纤夫共存的,但我会坚持唱,到死。我默默望着老人,一个被号子救赎的老人,一个用尽毕生精力传承号子的人。他浑浊的眼中有泪。
江大救不了号子,号子救了江大。
金江号子下游船工号子是纤帆木船在金沙江航行时使用的劳动号子,流传地域在四川省新市镇至长江上游的重庆市之间。金沙江是长江上游最险要的河段,从绥江到宜宾145公里航程,有大小险滩45个,水流十分湍急,表面最大流速达4-6米/秒,江面狭窄,弯急浪恶,号子随水势不同变化多端。有招架号子、五板号子、四平腔、搬滩号子、抛河号子、下滩号子和抽桅子号子等七大类,船经过险滩时使用的“扳滩号子”便具有急促激昂、节奏紧凑、铿锵有力的特点。每一类号子中又分为若干种唱法,按曲调区分,计有17种。金江号子的唱词古书续唱,即兴发挥,自编自唱。2007年3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把金沙江船工号子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江津乐和师弟甘大林也成为金江号子的传承人。
——以乌江流域船工饮食文化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