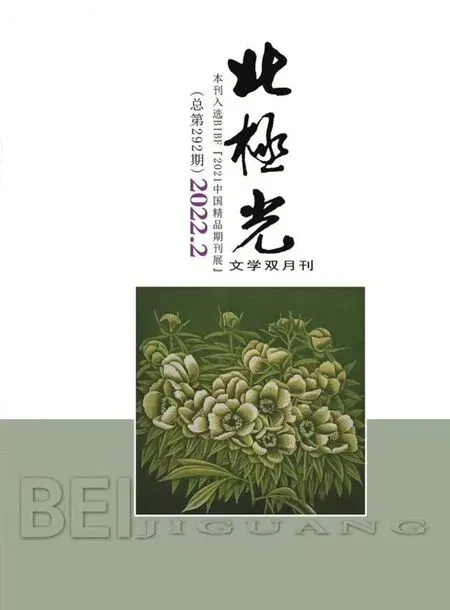想念老屋
□邢秀芳
家乡就像一根风筝的线,当你飞的越远这根线就系的越紧,牵着我的心,使我的思绪常常顺着这根线飘动,常常想起在故乡老屋时的件件往事……
离开家乡,想家成了我生命中永恒的主题。父母老了,搬到我在县里置办的房子,老屋便由弟弟一家住。前几年,弟弟嫌老屋太老不保暖,格局不新潮,便扒掉老屋盖了时尚新房。新房盖好后,我趁休假陪伴父亲一起回去住了一晚,夜里辗转反侧,到天亮也没睡着,新屋虽然时尚亮堂,却没了老屋的归属感,没了老屋的气息,感觉这里不是家了。
老屋是我们还小时父母一筐土一锨泥一点点垒起来的,墙体里面的是泥土和谷草搅拌脱坯砌墙,外面贴的红砖保暖,房脊是木头,房顶开始是茅草,后来换的红瓦。那时家里非常贫困,盖老屋的物料也是几年一点点积攒后盖起来的。老屋盖好后,父亲在房后栽种了一圈杨树和榆树,我离家时这些树木早已枝繁叶茂长成大树。夏天园子里种着黄瓜子等时令蔬菜,还有我特爱吃的东北特有甜杆儿。房前菜园子的边角栽种的是本地樱桃、沙果和李子树,春天果树开花,满园芬芳。进入暑假,樱桃最先熟了,一颗颗像红珍珠样果子挂满枝头,鲜艳欲滴。然后是李子、沙果渐次成熟,院子里从春到秋飘满果香,这花香和果香是我远在千里思乡的常客。农村孩子皮实,我记得我是10岁吧,拎着镰刀去砍甜杆儿,可能嘴馋急切,不知怎么就被地垄拌倒摔了一跤,自己一轱辘爬起来,也没觉得疼,血却顺着眼角淌下来,吓得都不知道哭的找我妈去了,我至今清楚记得也没去医院,就把去痛片擀碎了,敷到伤口上,用不知道哪儿找的白棉布包上就不管了,多长时间好的我也不记得了,眼角额眉处留下一条清晰的疤痕,那时年龄小,疤痕没长开,怕被人笑话,留了很多年刘海儿遮挡。现在每次洗脸梳头看见这条已经淡了的疤,都忘不了吃甜杆儿的甜蜜。我儿子两周岁,带他回去看看妈妈生活的地方,在楼房里出生长大的儿子一回到老家,在老家院子里房前屋后钻来钻去探险,当躺在热乎乎大炕上睡午觉时,他觉得床这么大还全都是热的很是新奇,一会起来摸摸,看看我后躺下,一会儿又骨碌起来,仿佛奇怪这床怎么和家里的不一样,闹得那天午觉都没睡。那个秋天儿子白天基本长在园子里了,揪黄瓜摘柿子的,回来时行李里装了一大半李子沙果。那个秋天在儿子的童年时光里也是美好的吧,他上大学时钱包里带走的就有那年在园子里怀里捧着沙果李子的照片。
曾经的老屋,承载着我所有亲情的偎依,美好的田园生活,家家户户都饲养鸡鸭鹅狗,晨起的鸡鸣是起炕上学的钟声。厨房里油灯昏暗的光影下有母亲熬粥做饭的身影,炕上一排睡着我们兄弟姐妹。那时的物质是真的匮乏,每天两顿饭,早饭基本都是大碴子水饭,咸菜大酱。晚饭是大碴子粥,菜类不是酸菜就是土豆,还有大酱缸里腌的咸菜。晚上,父母忙活完一天的活计,坐在炕上计划着往后生活,我们兄妹在煤油灯下写作业。尤记得春天刚刚到来乍暖还寒时候,阳光明媚,春风吹在脸上温暖又不晒,乡土生发的气息非常好闻。中午放学回家饥肠辘辘,一到家门口就能闻到煮大碴粥和炖土豆酱的香味,小燕子在院子晾衣绳上欢唱,园子里蔬菜刚露出地面,母亲还满头黑发,那时的一切都生机盎然。
80年代末,我从当时贫瘠的小村考上中专,在当时看似乎鱼跃龙门,从此改变了生来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我高兴的离开故乡,坐汽车到哈尔滨,不认得学校的路,只记得随着通知书一起的入学须知里写着火车站有校车接站,问了又问客车司机下车怎么去火车站,到了火车站,果然有大大的牌子写着某某校接站,我出示通知书上车等候,心才算踏实下来。从此也开启了我离乡思乡的记忆,多年过去,当年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真应了那句“少年不知曲中意,听懂已是曲中人。”故乡,雀跃着离开,想念时已是泪湿枕畔。
随着我们长大,像蒲公英一样各奔东西,落地安家,只是父母还守着老屋等待异乡的我们,老屋也因风吹雨淋而老旧。十年前我们兄妹在老屋送别母亲,母亲去了后,父亲的精气神大不如以前,怕父亲在老屋一个人伤神,也为了生活方便,父亲捧着母亲的遗像一起住到了楼房里。楼房里是窗明几净,吃住方便了,但我再回家时却找不到在老屋生活的感觉,漂泊的心似乎没了依靠,所以我每次回家都走遍城里的大街小巷,记住城里的气息,希望记忆里印下如老屋般的痕迹。十多年过去,想起老家,依旧是老屋被雨水冲刷得斑驳的窗棂,被苔藓腐蚀的房瓦,想念园子里的果树,甚至房后那棵高大的杨树和那棵歪脖子老榆树。
想家,想念那老屋,想念家乡的一草一木……所有的想念,都是家乡的气息。那根风筝线深深地系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