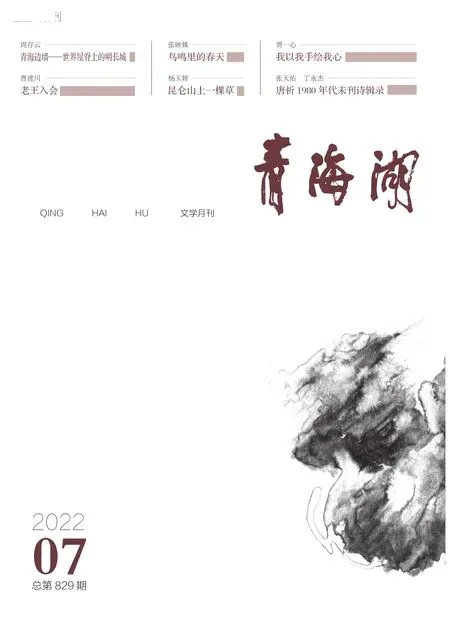浪山笔记二则
马有福
夜宿大梁且怀古
时序之变,令人心惊。生活之规,早已叛道。
二十多年前,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大致都还按照春夏秋冬一茬庄稼的周期安排和规划起止作息,工作周期。买卖人都看农家的脸,是农村和农民引领岁月前行的。在这样的时序周期中,腊月则更是岁月枝头的鲜果,那么泾渭分明地规约和统一着全民乃至一国的心理节奏。
而如今,虽然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一年二十四节气没变,但人的心理节奏却悄悄地变了。细数数,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都不约而同跟着学校的脚步和心跳而安排和规划整个社会生活的脉动。高考三日,全社会更是如履薄冰、屏声静气,学校周围的建筑工地无一例外都歇工放假,不言不争,顺天应命。
就这样,不经意间,我们把中国农业曾经之重转移到了初升的太阳教育上了。从“以粮为纲”到“以学为天”,价值指挥棒变了: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我们不加思考地跟着潮流转,就自觉不自觉地加入揠苗助长的大军中,绑架孩子,剥夺童趣,反正做了不少亏心事。更为奇怪的是,作为正儿八经的肆虐狂,我们自己从中并没有由此获取哪怕丝毫的轻松。反而,就像进入了一个不见天日的隧道般陪着孩子受压抑,虽一去几十年,早都无怨无悔了。骂谁呢?鲁迅一句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警句,早就让我们释然。
既然悟透,就得行动。所以,一俟孙子们放假,我常常有一种开车出了隧道般的轻松与敞亮,也早做了出行浪山的准备。这不,才七月十日,我们与几家亲戚就相约从西宁出发,各自带着自己的孙子向祁连山深处出发。
去哪儿呢?
与相约的亲戚们在高速路口碰头商量一番,就随心决定:这一次,翻越达坂山,挺进祁连山。具体地点就看这一行我们与哪一段山川更有缘了。
于是,从西宁出发,沿宁张公路向西北行,随着海拔在攀升。先是大通宝库的黑泉水库,再是达坂山口。一路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没有找到心仪的驻足地。走到门源马场附近时,孩子们就开始闹着要吃东西喝水了。我们不好在大路边上停车,就一直贼溜溜瞅着岔道,看哪一方远离道路的草地更适合停车,这就不经意间来到了著名的西北金场——大梁。
好,就是大梁了!
在原大梁桥右侧,一条坑坑洼洼的砂石路把我们引向高出路面的草地一隅。草地被一条由东向西的河流从中间切开,切出了一条弯弯曲曲的河谷地带。我们就选择了在小河南岸未被铁丝网圈住的一隅。时,太阳偏西,天朗气清,山风习习,蜜蜂嚷嚷,景色如画。
不到半小时,我们就把自己顺利安顿下来。三座帐篷,三辆汽车,一袭炊烟,十来个叽叽喳喳的孩子,空山一时迎来了人气和饭香。在我们下榻草地的周围,一边是一条弯弯绕绕通向河边的羊肠小道,一边是无限延展直通公路边的、刚刚栽上了松苗的石子滩,有橡皮管弯弯绕绕直向远方。
我们烧了茯茶,趁着天气,把各自带着的布单和毯子拼凑着铺在一起,摆上牛肉、馍饼,席地围了一圈,各端茶碗,打起尖来。也怪,为什么把路头上的这种吃饭叫做打尖呢?我们一边嚼着已经进嘴的饭食,来不及咽下去,就开始了讨论。我说,这不仅是青海人的说法,京津一带以及古代文学作品中都把路途中的吃便饭叫做“打尖”。
这,不可能吧?有人反对,有人拿起手机开始百度。但这里却早没了信号,电话都打不出去,与外界的联络就此中断了。一切都得靠自己的判断。这才叫做有意思,这才是对自身的一次轻松打开,人有一种回归了常识,远离了万般遮蔽的感觉。
就这样,打完尖之后,我们起身四散开来,端详着周围的山形,心思沉淀在金场曾经的辉煌,就一边散步,一边说起自己曾经在这里的细碎记忆。而孩子们则彻底疯了,不是追着蝴蝶跑,就是箭一般涌向了涛声张扬的河边。他们这一疯,原本半躺着伸开腿在草地上全然放松身心而晒着太阳的女人们就一个个不安分了。一时之间,她们起身追逐,喊着骂着,宛然到了自家的村巷。而这时,我们几个男人则就像看笑话一样看着她们骨子里的精心和责任,理都不理地走向半山腰。在一片视野逐渐开阔起来的平台上,在一丛接一丛的金露梅之间,我们依旧说不罢大梁和金场。
曾几何时,这是青海东部农业区最为牢靠的钱袋子和人生靠山,堪比内地中原文化链之中举之路。就像内地人一个个培养书生指望中举一样,青海农人希望的天空中,在过去,大梁确曾是最亮的一颗星。除了种地,多少人家的一时、一年或一世辉煌几乎都来自大梁。不知是从何时起,农民们种了庄稼,到了闲月,哪怕是寒冬腊月,仍一心向往大梁。还有,那些债台高筑、走投无路之人,所剩下的路,最后投靠的,也无非大梁。所以,一年四季,大梁就像热闹的街市,从来都是熙熙攘攘的金客。
犹记得,改革开放之初,东部农业区放开了手脚的人们一夜间都像长了翅膀一样地飞到了大梁。帐篷扎满河岸、半坡,筛床支满了河谷地带,金窝子则更像马蹄窝一样撒落在宁张公路两边,让没有见过这阵势的汽车司机和旅客们停车观看,在这里往往要逗留很久很久。1998 年夏天,我一介书生在大梁卧牛河一带也设下窝子揭草淘沙,这时,大梁吸引着的人群不止农人了。在机关单位找不到体面生存时,我亦把发财的希望一度寄予了大梁。
大梁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我想,这一方面是交通沿线,离东部农业区乡村最近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大梁金场的个性使然。大梁金场很少有块金,矿脉四散,金沙覆盖面很大,无论是在河谷地带,还是在河岸的草皮上,随便在那儿挖下去,也无论是在地面的哪一层,都会有麸皮般的金粒。这使那些有本钱的金客不看好大梁的前景,而把大梁留给了千千万万的穷人。所以,有人把大梁又叫做穷人的金场。穷人们只要舍得时间投入,没多有少,在这里总有所获。尤为奇怪的是,大梁河谷地带早就是翻了多少遍的砂层,用金客的话说是不知多少代人的熟窝了。但翻来翻去,谁都发不了财,谁都不会空着金盆回家。直至20 世纪80 年代,在河谷地带不怀多大希望的金客们每天还都能获得个分照人儿的收入。这是金客的行话,意思就是,每人每天都能得到一分金子。这是多大的收入呢?我请教过老人,他们掐指计算,说:十分一钱,十钱一两,那是当时超过一个干部月工资收入水平的。
哦!
当然也有例外。在大梁的狮子口一带,如果从河岸打洞进入草皮底下的地层,撵上或者碰到一点点生茬,冻沙里偶尔就会出现小麦、豌豆那么大的金粒。但这样的机会和概率却很小很小,这就像传说中的那个刚到金场蹲地上方便,眼前一黄,就是一块黄金的故事主人公一样一直在传,却从不知其姓甚名谁。
但我知道的是,我的好多初中同学几乎都曾在这里窝冬穿洞,多少年,试探和触碰过这样的运气,但他们谁都不曾一夜暴富,进入神话。相反,做冬工,那是一个比夏天淘金更加艰辛的尝试。他们之中,两个人曾因遭遇山洞塌陷而身死大梁,一人曾因搬运洞里搭架的木头而滑倒在冰面上,木头砸中太阳穴,并由此殒命。说来,都是心酸啊。
就从这一点看,大梁何尝不是青海东部农业区各族农人的一部伤心史。我不止一次跟老人们请教过他们旧社会在大梁的经历和个人记忆。他们说,那时,日月寒难,脚步狭窄。走来走去,谁都一腔子眼泪。他们从来是一步一步背着盘缠远投大梁的。在大通人的记忆里,从家到达坂山下是一站,翻越达坂山走到青石嘴是一站,从青石嘴到盘坡是一站,再从盘坡到大梁又是一站。这一路,不仅得背着行李和锅碗瓢盆,还得要背着熟食面粉,简直是背着一座山。这门是随便出不起的。而最最不堪一说的是,这一路上还不少土匪,他们一声吼,窜出占着、守着的空山险地,让帮口小的金客连身上一件御寒的衣服都是保不住的。为此,农民们不得不结伙出门,豁出老命。
改革开放之后,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甚至绝迹了。交通之便,让人们坐车一觉睡到大梁,淘金工具和生活资源也不再像过去那么金贵奇缺了。可大梁一时遭遇的问题却是狼多肉少,纠纷频发。这,就招来了金管站。金管站工作人员都是带枪穿警服的,哪能只维持公平而忘了自己发财?这就发生了很多公私兼顾的故事,腐败现象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好在2000年之后,青海果断踩下那一脚刹车,叫停各地金场,这就救下了不少人啊。
我们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说着大梁,忘了时间。看山影重重,时间不早了,我们就急急赶回帐篷跟前,开始忙着和面洗菜,捡柴点火,把一缕炊烟就像风筝一样放到了晴空。孩子们没有见过这场面,就一个个围在三块石头支起来的铁锅周围,瞪大了眼睛。这不是很好的视野拓展和别样的体验?
无言之教就这样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吃了晚饭,在河边按部就班刷洗完锅碗瓢盆之后,我们各自为阵,就不约而同,纷纷从车里取下被褥铺在各自的帐篷里,准备夜宿。山风袭来,浑身冰凉,温度一下子降了下来,谁都不由自主吸着冷气。早该钻进被窝了。但睡意不知跑哪了,我们都不想睡,孩子们则还在兴奋地跑来跑去。于是,给他们加了棉衣,带着他们在星光下的草地上随意走去。一开始,他们都还自由散漫,追追打打,不觉恐惧。可一道鞭子般甩下来的闪电让他们一时慌了手脚,纷纷跑回来把手伸向自己的大人。看雨点渗漏,等我们转身往帐篷里回去时,不知是在哪儿安身的猫头鹰就重一声、轻一声地在耳畔吼叫开来,让这浓云下的深山夜空显得更加冰凉如水。不,这简直一把无形的杵子,每一声都像直接杵在帐篷顶头的雨点,在孩子们的记忆里就像省略号一样一直延伸到了他们这一天的梦境之中。
晚上,睡在帐篷里,听着噼噼啪啪的雨点时紧时松地敲打,忍受着一阵又一阵狂风对帐篷的不时撕扯,我失眠了。我想,我们这不把自己投入了一个万丈深渊?自从金场关闭,二十多年了,这里是野兽的领地,也是山风和阵雨不时侵袭之地,我们却如此贸然踏脚侵入,会不会冒犯诸多野兽和幽魂?我说幽魂是因为,这里曾经不仅是古金场,也是丝路大动脉,古今中外,多少人曾经从这里经过,在这里留下了他们不绝如缕的脚步,也曾鬼哭狼嚎中意外牺牲在这里,留下过一缕幽魂。金客就不说了,生生世世,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不足为怪。想到这里,倒吸了一口冷气,我紧一紧被子,在两个外孙的鼻息中又一一盘算起来:清代,左宗棠追杀着的回民老小在白彦虎的带领下,就从这里走向河西走廊,翻越天山,逃难到如今的哈萨克斯坦等国的;民国年间,起事西宁、河州,直逼河西走廊,最终远去新疆的尕司令马仲英也是取道这里,一步步唱着河湟小调走向扁都口的;1937 年,兵败祁连山的几千名西路军战士被俘之后,也是从这里被押解到西宁以及河湟各地,从而流落民间的;解放那年,王震将军率领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新疆的大部队也是从这里走向星星峡,军歌一度震醒了栖息在山崖上的猫头鹰。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我知道的,不知道的,很多很多。
河水哗哗,涛声依旧。
夜幕沉沉,山风时起。
大概早过了午夜,阵雨过去后,星光洒落到了帐篷的天窗。在这没有睡意的夜晚,不知咋回事,还有那么多飞机飞过大梁,回声就像四散开来的涟漪,一次次穿心而过,又一次次渐渐远逝。
就这么翻来覆去中,借着手机,我及时写下了感受:
天黑星诡风近帐,耳边犹闻夜鹰唱。裹被欲远山溪凉,机声隆隆却断肠。自知身处古大梁,莫非今日是战场?听涛想家思无量,劝君慢说英雄腔。
这一天是2021 年7 月10 日。在我写下这样的文字时,三顶帐篷里熟睡着把自己全然交给了大梁的孩子们将来将会写下怎样的感受呢?
我可以断定,肯定是最贴近自己的一页。
浪不完的循化
每年夏天的浪山,总绕不开循化这一站。循化早已成为我心中不可或缺的风景了。套用青海花儿一句歌词:不浪,由不得个家(自己)。这使我们一家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翻越青沙山,穿云破雾,就像一朵雨中浪花般驱车腾挪跌宕于前往循化的山路之上,总不忘汇入循化,看一眼黄河。
在循化,那么桀骜不驯、生龙活虎的黄河则就像一个贤淑雅致、隐身村巷的撒拉艳姑,一下子变得无声无息、温柔娴静了。每每站在河岸上,看着不声不响的河面,我就想起八十多岁的撒拉族藏客韩哈乃斐一番解读:这黄河就像一匹烈马,你压得住它,它就是你屁股底下的一阵风,任你使唤,柔若柳枝;你压不住它,它就是翻江倒海的火山熔岩,瞬间会把你烧成一堆灰。
哦,还有这样比喻的!我心中一惊。
在接下来的交往中,我才明白:原来,韩哈乃斐老人自小生活在藏区,他对藏族民俗和语言的精到到了藏族都阿啦啦赞叹不止的水平。再加上撒拉话、汉话这样两种语言的参照,他的出语惊人早就闻名于循化和青海藏区。为此,我暗暗庆幸,这是难得的请教机会。这就接着问:那么,是谁压服了这一段黄河?
他说,还不是这火焰般隆起在两岸的大山吗?无论出了公伯峡之后那团团红色的火焰,还是出了清水湾,然后一直延伸到孟达峡的那铁色的火焰,它们均是大自然点燃起来之后一时凝固了的火把,曾经照亮过当年尕勒莽、阿合莽寻找骆驼的黑夜,也曾照亮了黄河的容颜。所以,到了这里,黄河就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它桀骜不驯的头,并让撒拉族成为黄河浪尖上的筏子客。
我知道,筏子客曾经是一种职业。在没有桥的时代,他们把充了气的山羊皮绑扎在一起,以此渡人、运货,方便了藏客,麦客,金客们的出行。靠着在黄河浪尖上练就的硬本领,后来,筏子客通过黄河,把青海的羊毛等畜产品运往内蒙古、天津一带。如今,交通发达,架桥技术超群,时代淘汰了筏子客。但每年夏天,作为非物质为文化遗产,筏子客们依旧还要在黄河里表演一番他们曾经的身手,这是难得一见的循化风物。
就这样,多少次,相会街子,坐绿荫下的茶园,我与韩哈乃斐老人谈天说地,成为朋友。我因此了解到他是藏客,是往来于藏区的文明使者。他把农业区的特产带到藏区,然后把藏族的特产带到循化。来来去去,这不仅搞活了经济,还促使了藏族和撒拉族之间的相互了解。所以,他在藏话、撒拉话、汉话等语言的波峰浪谷间自由飞翔,随意转换,其流畅就像是瓦罐里倒核桃,一点都不打折扣的。曾经,我就问他的上学情况,他“嗯哼”一声摇着头说,一天都没有上过学,但现在都能看汉语的报纸。在他丰富的地方和民族知识面前,我无非依旧一个小学生。所以,看着他,我否定了自己久蹲书斋的生活,而不止一次地说服自己走向了大山。
最难忘,他跟我开玩笑的一句话:撒拉走天下,全靠胆子大。所以,来到循化,每每告别了韩哈乃斐,我犹逡巡街子村巷,想起撒拉历史一页,有一种穿行在时光隧道中的感觉。
那是八百多年前的光阴里了。一头白驼,几十个大胡子、深眼窝、棱鼻子的男人,从中亚撒马尔罕出发,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中国,穿山越岭,不知何止。忽然,有一天,在循化的奥突斯山下,黄河岸边,这骆驼便一卧不起了。怎么办?他们中的首领说,天意在此,何不止步?就从那时开始,撒拉族在循化落脚诞生。从此之后,他们以街子为中心,四散开来,并结亲藏族,开垦土地,安家落户,繁衍生息。如今,洋洋十万多人,一个民族。在西部,难道还有比这更生动的身边传奇?
在街子,尕勒莽、阿合莽的墓地犹在。古老的《古兰经》犹在。驮经的骆驼早就玉化成石,映在泉水之中,续上了传说的历史。器宇轩昂的木头大房,门前屋后的魅力花园,还那么明显地延续着先辈记忆,在整个东部农业区有点另类。
景点含着人文。
远方就在身边!
就这么吟咏着,走遍循化,我不止一次地坐在黄河岸边的茶园里享受了一种淡淡的中亚民风和河湟民风交织在一起的循化风味,还无一例外地买了核桃、辣椒、花椒等循化特产。一年四季,靠着这些特产和旅行中的记忆,我们与循化始终保持着藕断丝连的联系。
有意思吧!
在西宁,我还没有说完这一切,几个小外孙就嚷嚷着还要去循化。她们说,不骑骡子不算到了循化。这是因为,多少次去循化,在清水黄河岸的波光中从容刮着碗子休闲还不尽兴时,我们总驱车孟达峡,弯弯绕绕,游一番孟达天池。都说孟达天池是青海的西双版纳,西部的动植物宝库,其生态种类之全,在全国都是屈指可数的。但我那几个淘气外孙,哪里听得进这些话。她们一心向往骑骡子,每次去孟达,还不等我停车稳妥,犹独自跑到山脚下,一个个已经骑到骡背上的鞍心里了。到达天池,还不等我拍照休息,从容绕一圈天池,喘几口粗气,她们则飞一样跑出木头栈道,又一个个被扶上了骡背。这使我老伴总在提心吊胆,嘱托连连,甚至被吓得蒙上了眼睛。但她们依旧不管不顾,故作潇洒,还唱将起来。
就这样,孟达,骡子,踏沙坡,古老清真寺,犹自循化历史一端,常常把我们带出惯常,带出城市,带到书本之外,不断拓展着我们一家大人和小孩的视野,弥补着我们在知识储备上的各种先天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