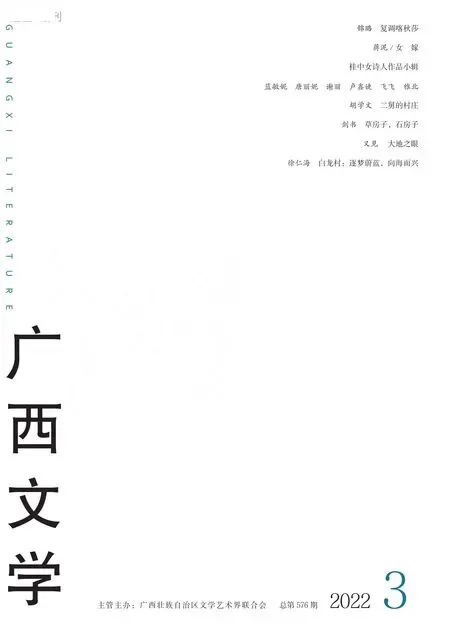九面埋伏(组诗)
蓝敏妮
青衣戏
青衣到了青衣江,一场戏才算完
只有到了江水边,他才恢复了男儿身
青衣江几无泥沙,所以沉默
所以把说话的时间都让给他
水袖汇入江水,他轻轻一摇
水听他说话,鱼也游上来,听他说话
他说秘密或悲喜
鱼都一动不动,都只吐泡泡
他说那么多,江水都只往前流
无岸无涯里,那么多人忙着改嘴色
他是在一步一步卸妆
柔媚之下,都是或凸或凹的骨头
没有生育过的女子不配比作月亮
白练一样的月光挂在梧桐树上
年近秋分的女子在斟茶
她们在老月光里不服老,聊新意:比如学琴
司鼓,走棋,还可以学猫步,穿破洞的牛仔服
“我们都是月光里的仙子”
“没错!服侍丈夫儿女公公婆婆……”
“从此我们改做一回自己”
环佩叮当声越来越响,玉友会名不虚设
有一个嗓音吊到眉梢,又尖又细
她这样讲:
没有生育过的女子不配比作月亮
有几条搁浅的鱼站立不动,只饮水
又饮水,饮水凉成雪
她们在白月光下继续讲:
绝对自私!不配当个女人
不配当个人!
没有玉德!
那种女人,买再好的翡翠传给谁?
九面埋伏
盯着一辆木板车看了好久
盯着一只脏兮兮的小野猫看了好久
它们都一动不动
这真是太要命了,一辆有轮子的车
一只有野性的猫,都一动不动地
还定定看着我
我深陷于这种相峙或相疑
车会突然朝小猫轧过来?
猫会突然朝我抓上来?
我会突然朝小猫扑上去?
猫会突然朝车子冲过去?
这是深冬,屋角投下滴寒的暗影
木板车露出一个角,白猫露出一个头
我有崭新的鞋尖
其余的都模糊在逆光里
多面埋伏中,某些念头一触即发
大 戏
在南锣鼓巷
黄皮肤白皮肤黑皮肤的人在走着
红脸黑脸白脸在跟着
青花天蓝粉青在橱窗里看着
千年的窑火扑腾想飞着
圆的方的瓷片困在细细的链子中
是耳钉、项链、环扣的臣民
阳光在镜子中起身
有人啜饮,有人对白
有人描眉,有人涂着油彩
都在去往戏台的途中
我狠狠踩了人一脚
心里咕咚一荡
那人回头,端一脸歉意:
慢了,走慢了
不许拍照!
鼓点响起,人潮异动
不知是谁突然把自己的面皮剥下
啪地钉在树上,鸟兽飞散四下无人
我听闻三声唱,随后一声叹
树上两张京剧脸谱似笑非笑着
一张说——我是“男”
一张对——我叫“女”
橘 种
有人在海这边种橘,疏剪,抹芽
天比水蓝
有人在海那边研究萌发率、促生短枝、
诱导成花
不苟言笑的女精英跨洋去求学,炼心
被男色勾引,赠她接骨木,喂她迷魂汤
她从暗里一点一点探出指尖
先是业务文件,再是涉密资料
种橘人在树下喷农药,诱杀害虫
蝶翼翩翩飞过沧海,搬去小小剂量的毒
捕机密文件四份、秘密文件十份……
春风吹啊吹,海的两边都在成花坐果
一枚叫橘,一枚叫枳
三人行
三弦声起,那英雄甩袖提刀
越过门廊一路直行
烛火微动,那美人在夜光里弹古琴
一声断一声续
“又大又甜的橘子,快来买”
这是第三人的声音,在戏外
那个“买”字拖长了发音,拐着调调
转了多个弯,终于抵达了甜
第一人和第二人听到了
他们学不来那样的声腔与音调
那是经历择土移植、抹芽放梢、摘心疏剪、
陷落又抬起的动静
他们沉溺在戏中
“那英雄啊他们是错了一路”
“美人啊你是一路的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