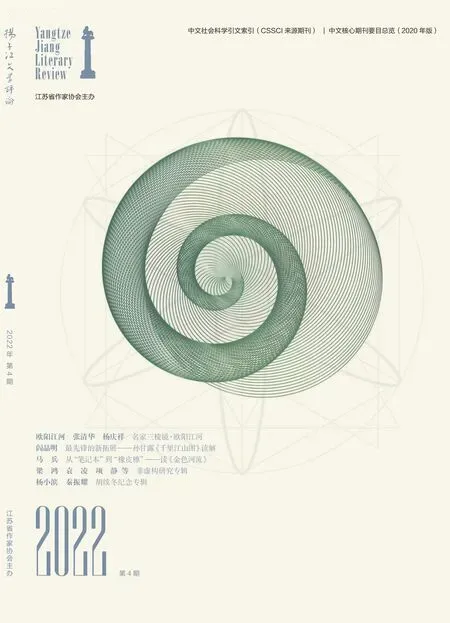文本 策略 语境
——格非“江南三部曲”时空演变叙事艺术论
陈 粲
格非“江南三部曲”的叙事结构既包含着深厚的诗学蕴涵,又具有鲜明的时空演变特色。丁帆认为三部曲“的确是作者精心构思出来的一部叙事结构非常精致的杰作”。格非亦自谦“时空问题在《江南三部曲》里边有一些思考”。就叙事结构而言,时空演变委实是“江南三部曲”小说世界建构的一项重要因素:它既为小说提供了虚拟却可信的空间场域,从而使小说叙事具备有效而完整的空间系统构造;也在小说空间系统建构的同时,赋予空间场景以共时性并置和圆环式循环结构,赋予时、空意象以象征性,从而完成小说叙事空间形式和时间蕴涵的双重建构。
一、时空演变叙事文本
时间和空间是小说创作的两个重要维度,格非对此的理解是:“空间和时间是互相包孕的两个概念,每一个空间都沉积了巨大的历史内涵,而反过来说,时间的线性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认识理论上的假象,实际上它也蕴藏着丰富的空间性细节。”“江南三部曲”中,小说的时空关系主要呈现为重叠、封闭与穿越的状态。格非在小说中塑造的“江南”是线性时间线上的空间重叠状态的典型。它不仅是小说的虚拟地理空间,更是作者结合自身对于“江南”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想象而形成的具有时空双重性质的“江南”世界。小说叙事文本以“孤岛”和“阁楼”为封闭空间的代表,与日常生活形成隔绝,呈现个体命运的局促与逼仄。三部小说穿越时空的“花家舍”意象则是一体两面,表现为异位的空间具象,不仅指向乌托邦世界,更展现出与之相互背离的镜像世界。
(一)“江南”:重叠时空
综观格非的小说,其叙事一直有自觉求“变”的实验,在先锋技巧之外逐步汲取传统小说叙事方法,现实世界的日常生活书写在小说中的比重亦不断增加。与莫言的高密、苏童的苏州相似,“江南”是格非小说的主要创作背景。“江南三部曲”中,“江南”呈现出两种性质,一是基于对现实生活中的“江南”的记忆塑就的虚拟地志空间; 二是基于“江南”所蕴含的“历史和文化概念”而构建的“江南”时空意象。
格非出生于江苏丹徒,童年阶段都是在“江南”岸边的一个小村庄度过,因此“江南”作为他的记忆“贮存器”,为其小说提供了地理空间背景。“江南三部曲”中的“江南”空间,在格非笔下由小到大逐步扩散。从《人面桃花》中的普济、夏庄、长洲等村镇,到《山河入梦》中的梅城,再到《春尽江南》中的鹤浦市及其附属行政区域,“江南”空间在格非的小说叙事中不断地生发。“江南”世界是“三部曲”的地理背景,更是蕴涵诗意想象的时空意象。格非化“雨”“植物”等物象为装置,并充分赋以古典意象,为“三部曲”文本增添了诗意的文化内涵。“雨”的意象在小说文本中,尤其得到了充分诠释。它不仅是“江南”常见的一种气候现象,也是小说人物命运变数的征兆。《人面桃花》中陆侃失踪前对秀米说:“普济马上就要下雨”;《山河入梦》中谭功达与姚佩佩在雨夜的暧昧对话;谭功达修建水库的梦想在一场大雨中的彻底破灭;《春尽江南》中庞家玉去世之际鹤浦市的“等待已久的一场大雨”。伴随着“雨”的出现,带来了小说文本中已发生、正发生、或即将发生重大变故。“雨”作为传统文学中极为重要的意象之一,有机穿插于叙事之间,在预示人物命运的同时,也承载着独特的情感内涵,包含诸多的精神内涵。“三部曲”中的“江南”世界,“雨”的意象作为人物情绪的外延,孕育着小说叙事的诗意氛围。
同样,“三部曲”中植物类意象在充实 “江南”诗意叙事的同时,又隐喻着小说叙事的时空变迁。夏天满园的荼蘼花、满山的紫云英、招隐寺池塘里的睡莲,又或是荼蘼架下一年四季不同的鲜花:春天的海棠、芍药,夏天的芙蓉、石榴,秋天的兰蕙和凤仙。这些植物意象营造出独特的“江南”景观,展现出浪漫唯美的“江南”文化特征。这些植物意象不仅显示出“江南”的美丽风光,更多地是以花事暗示人物的命运变迁。《人面桃花》中,陆侃下楼时,花败叶茂的西府海棠隐喻着陆侃“桃源梦”的破灭。《春尽江南》中,慕田峪山头那段倾颓的长城城墙下迟开的野桃花,既为庞家玉“又活了一次”做了铺垫,又指涉一种逃离现实追求理想的无果尝试。
格非笔下的雨和植物类的意象不仅丰富了“江南”的自然环境,为小说增添了诗意,也承载着“江南”的历史文化想象,从而使“江南”世界在时空维度上更为立体化。他不仅在小说中重现“江南”的景象,而且立足现代,重新审视其内在精神,完成了传统与现代的互文对话。
(二)“阁楼”:封闭时空
阁楼本是空间概念,在格非的笔下却成了时间的“贮存器”。如果说“江南”代表的是一种地理和文化层面的外部开放空间,那陆家宅院的“阁楼”则是偏安于“江南”一隅的封闭空间,可将叙事视角转向人物的内心世界。开放空间与封闭空间的并置,构成了“江南三部曲”立体的文本空间。
三部曲的开篇第一句话是:“父亲从楼上下来了。”但直至陆秀米经历一系列事件、最终获释从梅城监狱返回老宅后,叙事视点才正式进入“阁楼”。这个角落曾经是父亲陆侃独居的封闭式空间,张季元曾短暂逗留过,陆秀米从日本返回后也居住在此,但直至秀米密谋攻打梅城失败被捕三年后返回,叙事视角才真正进入“阁楼”。加斯东·巴什拉对“阁楼”做出过解释,他指出:“在一日梦想之中,对于狭窄、简陋而局促的独处空间的回忆,就是我们关于给人安慰的空间的经验,这种空间不需要扩大,但它特别需要被占有。”换而言之,作为封闭空间存在的“阁楼”,为个体进行回忆、幻想提供了场所。“阁楼”是“发疯”之后的陆侃臆想“桃源梦”的封闭空间。直到某一天,这个封闭的空间被打破了,疯子陆侃从楼上走了下来,并且很快就不知去向,与他一同消失的还有他的“桃源梦”。“阁楼”的存在象征着一个自我意识庇护所,处在阴暗的角落里,成为小说叙事容纳回忆的时空贮存器。
作为一个封闭的空间,“阁楼”的内部时间流动陷入了某种奇异的悬置,但是这种悬置并非全然地静止不动,而是一种依赖自我感觉的细微流动。在陆秀米搬进“阁楼”之后,她发现了陆侃制作的墙影与季节、时序相关联的对照列表,也理解了父亲对于时间的深刻感知。时间的悬置与空间的封闭在此统一,形成一个精神世界庇护所,成为进入“阁楼”者的藏身处,将人从现实当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够重新体验自我封存的回忆。陆秀米在从梅城监狱里回到普济老宅后,像她的父亲一样走入“阁楼”。此时的“阁楼”再次将陆秀米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使她得以通过禁语惩罚和自我折磨来获得精神慰藉。“阁楼”就像一座“孤岛”,在将现实空间进行隔离的同时,也将人的精神世界与外在的物质世界剥离开来。正如格非借王观澄鬼魂和韩六之口所说:“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小岛,被水围困,与世隔绝。”而谭功达被贬到花家舍时也深深体会到母亲陆秀米当年的心境:“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被围困的岛屿,孤立无援。”在这样的封闭空间中,格非将人物的自我意识剥离出来,放置于封闭的精神“孤岛”,从而展现出在社会时代变迁下个体命运的无奈以及精神世界的逼仄。
(三)“花家舍”:穿越时空
格非采取“叙事错综”方法,使这种圆环式循环结构更具内在逻辑性,从而使读者产生认同感。具体体现则是在“江南三部曲”中,人物对于自己所处的空间环境有一种“穿越时空的追忆”——对未曾见过的事物或场景,感到似曾相识。
《人面桃花》中,陆秀米被土匪绑架到孤岛,韩六取水刷锅时木勺敲到水缸缸壁发出的嗡嗡声,使得陆秀米想起听到张季元敲击瓦釜发出的金石之声时,感觉身体如同一片羽毛随风飘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原来竟是这儿……”《山河入梦》中,姚佩佩在第一次看见谭功达老宅的“阁楼”时,也有这样类似的描述,“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可怎么看都觉得十分眼熟。”《春尽江南》中,庞家玉梦见自己出生在江南一个没落的高门望族里,父亲出走后,家里来了一个革命党人,而这正是陆秀米的生活经历。格非通过时空穿越的追忆手法,让人物通过追忆的过程寻找整体的记忆,使人物与人物之间产生某种联系和共鸣,形成特殊而牢固的认同感,从而能温和地隐匿现实时间,淡化文本叙事的线性时间。
“三部曲”中穿越时空现象尤为显著者,非“花家舍”莫属。《人面桃花》中的花家舍修建在一个平缓的土坡的小村庄里。这里的屋舍都整齐划一,都是一样的粉墙黛瓦、木门花窗,有一条风雨长廊将散落在各处的屋舍连接起来,一直通往田里。看似一个世外桃源,有着桑竹美池之属,但其实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土匪窝。花家舍的男人平时替人干活,收人工费,但是实际上是为了摸清人家的家底,以此搜寻绑架的对象。在绑走陆秀米以后,花家舍发生内讧,最终沦为一片废墟。花家舍的“异位空间”性质正是借助这一片废墟呈现出来,展示了人性中的欲望、权力、恐惧,彼此交织。
《山河入梦》将时间从晚清时期瞬间拉至20世纪50-60年代。梅城县长谭功达在“大跃进精神”的号召下,陷入构建理想社会的狂热幻想中。而他在遭遇挫折、失去权力之后,与郭从年在后者建成的花家舍人民公社相遇。在这里,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一个界限,不可以有丝毫的违背。而为了使得每个人自觉地遵守这一界限,郭从年在花家舍设置随处可见的信箱,使得花家舍的每一个人互相监督,彼此检举。花家舍的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都处在被时刻监视的状态,这使得花家舍里的人都极度紧张,一旦触碰到这个被监视着的界限,就会如小韶的哥哥那样导致自我彻底崩溃,陷入疯狂。花家舍人民公社集权中心对于个体的严密监控以及人性的缺失,使得乌托邦走向异托邦。
而在《春尽江南》中,花家舍不再具有曾经的乌托邦与异托邦共存的性质,而是彻底沦为一个异托邦。理想世界的追求者王元庆拜倒在利益至上者张有德的手下,曾经作为乌托邦世界的花家舍沦为现代社会的温柔富贵乡——酒吧、别墅、色情场所。它容纳的不再是对个体幸福生活的追求,而是纯粹的物质享受。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里,花家舍失去了过往的质朴与诗意。
二、时空演变叙事策略
通过对格非“江南三部曲”的梳理,可以发现小说叙事虽然整体依然呈现线性叙事,但共时性并置叙事俯拾皆是,且共时性叙事都被巧妙地融入整体线性叙事结构中。这种时空演变叙事策略主要体现为共时性空间并置和圆环式循环结构两个方面。首先,不同时间/空间发生的事件的并置,使得小说不同时代的场景、意象可以统一在同一时空整体中,使共置文本产生互文效果,使小说产生复调效果;其次,圆环式时空循环使得小说叙事呈现出复现与循环的倾向,故事的起点和终点被刻意模糊,使整体叙事生出开放时空的效果。
(一)共时性空间并置
西方小说中的“共时性”叙事,往往是通过人物的意识流将过去、现在和将来强行拉到一起,具体表现为将时间空间化。在故事发展的过程中的某个情节的不同层次之间, 通过来回切断, 取消了时间顺序,从而将不同空间、不同时间发生的事件并置一起,使得“注意力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被固定在诸种联系的交互作用之中。这些联系游离叙述之外而被并置着;该场景的全部意味都仅仅由各个意义单位之间的反应并赋予”。换而言之,就是将场景与场景、意象与意象等统一在空间关系中,以此展现出文本叙述的情感倾向,从而揭示出时空叙事内在的深层意蕴。格非意识到,“西方小说中的‘共时性’叙事,往往是通过人物的意识流将过去、现在和将来人为地强拉到一起,时空错杂紊乱,给读者阅读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可以明显看出格非在“三部曲”中的并置手段较之本人先前作品,有着明显的调和色彩。有通过对话得出,有通过注释得出,而最显著的方法便是通过物象装置,有机联系不同时空场景,赋予物象以时空贮存器的意象。
在《人面桃花》中,张季元的日记本是将两个不同叙事空间并置的一种装置。张季元之死虽然使得陆秀米与其天人相隔,但陆秀米在其曾经栖居的“阁楼”中找到的日记本,又把死去的张季元的生活与记忆拉回到陆秀米的生活之中。格非将日记这一装置意象化,不仅将过去时间中的空间场景引出,形成过去时态与现在时态的并置,而且特定物理空间中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也得以厘清。通过张季元日记的插入,格非不仅在文本中建构了一个代表着过去时间的叙事空间,即张季元在普济的生活,并且,小说就此将陆秀米现时的生活空间与张季元过去的生活空间,这两种不同时空的场景并置,在文本中交替出现,为小说的叙事发展提供了新的时空建构,从而使读者得以出入于不同的时空之中。张季元的日记本被赋予意象,不仅“瞬时复活全部的历史记忆”,而且极为巧妙地“擦去时间全部的线性痕迹”。
“主题并置叙事”是“江南三部曲”所采用的并置叙事策略的细分。弗兰克所归纳的并置叙事是场景与场景、意象与意象的并置,这种并置的前提条件是文本内部存在一条清晰的叙事线索。而格非的“主题并置叙事”策略是:“不同的叙事时间围绕着某一个主题而并列呈现”,尝试从各异的时间/空间发生的事件中找到共通性。
主题并置叙事在三部小说中都有体现,而尤以《春尽江南》为著。《春尽江南》以一个共同主题“孤独”为中心,通过空间并置的叙事策略向前推进,以此完成整体的叙事。书中讲述了庞家玉、谭端午、王元庆、绿珠、陈守仁等人在内的诸多故事,各人境遇各不相同。资本侵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留不下任何供人休憩的诗意空间。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关系,被物质利益所取代后导致的现实人际关系的冷漠与自身的孤独,由此引发的更为宏观的主题——现代社会下人际关系的功利化追求,带来的理想世界的崩灭。在每一位人物故事背后,不难发现,其中所呈现的是他们自身对于理想世界追求破灭后的恐惧与绝望,其命运共同指向了同一个主题:孤独。小说在打破传统的线性叙事的同时,丰富了空间叙事的层次感。

(二)圆环式时空结构

就“三部曲”叙事中的物理空间而言,以一个初始空间为叙事原点,或出于自觉或由于被迫,故事人物尝试逃离,但最终都宿命般回归叙事起点,形成了若干“离去-回归”的圆环结构。《人面桃花》中,叙事发轫于陆家宅院。陆秀米对父亲陆侃的桃源梦不甚明了,却接触到了张季元追求的革命梦想。在张季元死后经历了出嫁路上被绑、花家舍内斗。至此格非略去陆秀米及花家舍与蜩蛄会众人攻打梅城失败后东渡日本的情节,之后仍是回到普济,至此形成一个离去-回归的圆环。陆秀米借办学校为名参与革命,遭龙庆棠设计被捕入狱等一系列事件,之后从梅城监狱被释放后又回到了陆家宅院,最终戏剧般地去世。这又是一个归去来兮圆环,且两个圆环呈现出完全对称的叙事结构。翠莲从普济随龙庆棠去了梅城,遭遗弃后乞讨为生,却怎么都是围绕着普济打转。《山河入梦》中,这种圆环式叙事空间体现得更加明显:姚佩佩在用石头砸死金玉后被迫逃离梅城,但却阴差阳错地只是绕着高邮湖跑了一圈,最终仍是回到了自己的梅城。
《春尽江南》的结尾处则为“三部曲”设置了一个更大的、头尾相接的叙事圆环,使得三部小说有机形成了一个自洽的圆环式时空循环结构,完成了三“部”一体的更高层次超越。庞家玉自缢于成都一家名为“普济”的医院里,而谭端午为了纪念她,开始写一部小说,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定在一个叫作“普济”的“江南”小村。这个“普济”既是“春尽江南”故事的终结处,又遥指三部曲《人面桃花》中的“普济”乡村。两个不同时空的“普济”相互呼应,模糊了故事线性时间上开始与结束的节点,使得从晚清到现代社会一百年的历史成为一个圆环式的循环时空结构——过去可以延伸到现在,也能成为未来,三部曲文本的百年江南时空也因此得以拓宽,呈现出开放时空的复义文本效果。

三、时空演变叙事语境
在讨论格非叙事方法的演变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即理解“格非的面孔”。在文学方面,格非至少有两副面孔:作家和学者。作家的面孔加深了他对世界或存在本身的了解,并保持着敏锐而锋利的感觉;而学者的面孔则使他在教书过程中能够大量阅读中西文学作品和文论,并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从中发掘实践范例,将其提升为理论并从中汲取养料,最终反馈于创作。格非的两副面孔,是读者感受和体验“三部曲”的时空演变叙事结构形成语境的先决条件。作家的作品实践与学者的理论探索相辅相成,汲古融西的理论与求新求精的作品对举映衬,在格非建构自身特有诗学的探索道路上又是一种玄妙的“并置”和“圆的循环”。
(一)实验与探索
在初期的创作过程中,社会经济和时代思潮发生巨变。格非作为一名有着敏锐感受力的作家,自然对此现象反应强烈。他一方面想要表现自己矛盾、迷惘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又想要表现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现代人精神上的混乱和危机。而格非不满足于传统意义上的理性、逻辑的秩序和线性发展的叙事结构,于是将注意力转到对文体的实验与探索之上,现代主义小说的先锋叙事便成为格非从1985到2000年不愿轻易割舍的技巧。

(二)守望与求变



与之前的作品,尤其是与长篇《敌人》和《边缘》相比,《欲望的旗帜》叙事的“和解”首先体现为采用了“提前叙事”:提前告知章节情节梗概与走向,以期吸引住读者。在文体上,具体呈现为故事尚未展开,先有了“导读”性质的内容预告:在每一章进入叙事之前,都会有一段凝练本章故事的“序”;在情节上,更是如此:如曾山半夜被电话惊醒却未来得及接听,对来电者身份的猜测,又如张末进入大学报到时与正在接待处的曾山交臂而过。
除了文体和情节上的预告之外,“和解”还以一个相对明亮的小说结尾呈现:



(三)融合与内化
格非具有极高的理论素养,自觉的诗学追求与执着的创作实践。他在中西文学艺术资源的反复比较、估价的基础上,探索自己深刻认同的诗学目标并持续地实践,以求完美地实现。《塞壬的歌声》 《卡夫卡的钟摆》是其大量阅读的感悟;而其技巧的圆熟则和《小说艺术面面观》 《小说叙事研究》的撰著与课堂讲授的课程有关,《文学的邀约》更是熔铸中西、贯通古今的诗学理论著作。
在文学无法与电视、电影等现代文化传媒产业抗衡的“势”下,格非在叙事上一直进行执着的实验,具体方法便是在作品中剔除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慢节奏、全知叙事和线性叙事,在现代主义小说的底蕴之上融合其他传统叙事技巧,试图探索出一条“兼而有之”的、属于自己的道路。从“不轻易放纵读者”的《褐色鸟群》 《迷舟》,到故事核心信息日渐丰富的《傻瓜的诗篇》 《湮灭》,到利用传统典故、线性叙事的《推背图》,再到尝试与读者“和解”的《欲望的旗帜》,都有着小说叙事的守望、思索和探索。如《欲望的旗帜》此类迎合读者和市场的作品,是作者格非所能写的,却不是学者格非所想要写的,因为作品的叙事中过多闪现着诸多西方现代小说大师的身影,这不是他自己认同的诗学目标;学者格非想要的,从来都是属于自身特有的“不朽的作品”和“经典”。

格非审视着世界文学中的古今资源,又向中国古代文学汲取生命力,诗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对举映衬。他结合自身从20世纪90年代伊始对于小说诗学的持续思索和实践,在“江南三部曲”中以“共时性空间并置”和“圆环式时空建构”策略呈现时空演变叙事,拓展了小说的叙事模式,实现并践行了自身深刻认同的诗学目标,赋予了文本超越时空的内涵。
【注释】
①丁帆:《在“变”与“不变”之间——以格非小说为蓝本剖析“先锋派”的沉浮》,《小说评论》2021年第4期。
②张小琴、江舒远主编:《守望与思索——人文清华讲坛实录2016》,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5页。
③格非:《中国小说的两个传统》,《博尔赫斯的面孔》,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页。
④⑥⑩⑫⑭⑰㉖格非:《人面桃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5页、3页、1页、115页、105页、323页。

⑦⑧⑮⑱⑳格非:《山河入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页、189-193页、292页、133页、287页。

⑬[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
㉑[美]约瑟夫·弗兰克等:《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秦林芳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㉒格非:《物象中的时间》,《博尔赫斯的面孔》,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98页。
㉓格非:《废名小说的时间与空间》,《卡夫卡的钟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页。
㉔格非:《短文十篇》,《博尔赫斯的面孔》,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㉕[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阿莱夫》,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93-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