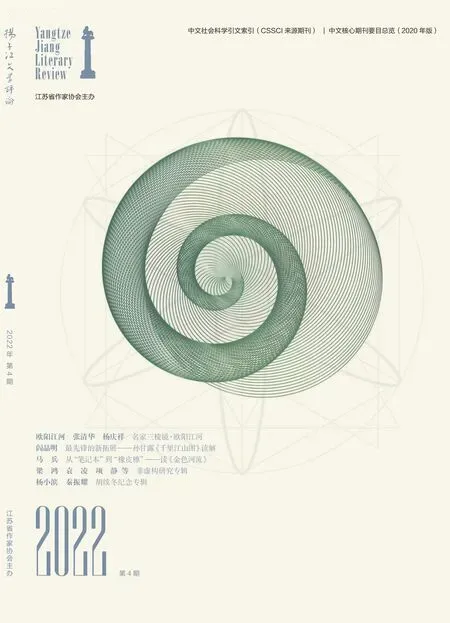“非虚构文学”亟需面世
袁 凌
我是一个长期的非虚构写作者,同时也一直写作非虚构类的小说,另外也涉足严格来说不属于非虚构领域的散文和诗歌。从个人的写作经历出发,对于国内非虚构写作的源流、现状和前景,非虚构与虚构的关系,非虚构对于文学的意义,有一些自己的体会和思考。
一、我的非虚构写作经历
我最初一本严格意义上的非虚构作品是《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初稿写作年代是在2002年左右,到了2014年出版,其间经历了多次修改。写作初稿的时候,我并没有听过非虚构写作的概念。当时我在一家地方报纸《重庆晚报》周末部工作,实际上已经开始写作特写、特稿一类的新闻长报道,但囿于视野,我也没有听说过特稿的概念。当时“特稿”的概念刚刚在《南方周末》萌芽,第一篇标志性特稿《举重冠军之死》 (李海鹏)也还没有诞生。
在写作《我的九十九次死亡》时,我想找到一种真实地把家乡人物的生死记录下来,既不同于虚构的小说,又与散文有所区别的写法,主要是叙事上要更节制、简练,增加语言的表现力度,尽量排除抒情,传达生死本身的重量和实质。就这样,我的写作自发地暗合了非虚构的要领,尽管对于国外的非虚构写作潮流和方法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这三个字。初稿写好以后,因为体裁上的不符常规难以定义,它一直躺在电脑中得不到发表的机会,直到2010年代以后,非虚构和新媒体平台一同兴起,它首先得到了在网易非虚构类公号“真话”连载的机会,其后被理想国编辑罗丹妮注意到,迎来了以“非虚构”名义出版的机会。到这个时候,《中国在梁庄》已经出版,非虚构迎来热潮,我的非虚构写作也很自然地由自发进入自觉阶段。实际上在将近2010年的时候,我的另外一本自传性质的作品《从出生地开始》也已完成,体裁是长散文,这在当时也是我的一种自发探索,当迎来出版时,它不由分说地也被纳入了非虚构写作的范畴。
与此大体同时,我的职业写作也由调查报道转为特稿。这一方面是考虑到媒体调查报道式微的大势,一方面也有我的自觉在内。我的第一篇特稿《血煤上的青苔》发表于2013年,仍然选择了我最熟悉的家乡题材,关心的是在矿难中瘫痪或者残废的矿工此后的人生,以后渐渐拓展到其他地域和阶层、群体的人们。
回头来看,我的非虚构写作无形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征:关心个体和群体的人本身,而不聚焦于某种社会现象或提供典型样本。体现在作品形态上,往往会是系列人物故事的集合,或是生活现场的白描式传达,作品的社会意义是经由人物故事和生活现场传达自然获致的,是存在式而非主题式的写作。这在我随后出版的几本非虚构类作品中也看得很明显:《青苔不会消失》是各类底层边缘人群和生活场景的集合,《寂静的孩子》是留守和流动儿童的系列故事集合,《生死课》作为《我的九十九次死亡》续集依旧是普通人生死的故事系列,而今年准备出版的《汉水的身世》虽然不再是故事集合,却仍旧是以一条河和它的子民为书写对象,是生命、存在而非样本、主题式的写作。
这种写作方式自有其利弊。弊端在于不能借助样本和典型的放大效应,难以引起集中的关注和讨论;但利处在于它符合我心目中文学的本质:关心人,以及其他类型的生命。
同时,我也一直在写小说,两者的共性是都在传达人类的存在经验。多年的跨界探索中,我逐渐形成了对二者的划界:非虚构不允许情节和细节虚构,小说允许情节虚构和穿插组合,但细节上同样需要具备真实性,使人感到一种非虚构的质地。从这个意义上说,“非虚构小说”在我这里是成立的,意即拥有非虚构质地的小说。
二、“非虚构写作”概念失效
非虚构从西方引入本土发展到现在,经历的时间和走过的路途并不长,局面却已十分驳杂繁复。原因在于其外延十分宽泛,而内核尚未真正成型。
“非虚构写作”这一通用语,直观地表达了这一现状。以“写作”名之,似乎具有一些创作的意味,但并没有与实用性写作和学术性写作拉开间距,尤其是为后者进入非虚构场域敞开了大门,客观上导致了带有田野调查性质的学术性著作大量进入非虚构领域,甚至成为主流,前提是添加上一定的文学手法。如果说《中国在梁庄》是一部主动添加了学术性外衣的文学作品,这些著作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学术著作添加了文学性外衣,两者产生了相向而行的趋势。
近年来从社会学、人类学领域进入非虚构写作的代表性著作,大致有《三和青年调查》 《我的凉山兄弟》 《崖边报告》 《袍哥》等,他们具有前述的共同特征,即田野调查式的学术著作对于文学手法的借用,或者说对于文学性的跨界。从好处说,是兼收了学术与文学之效,有助于人们对原本复杂的社会理论和社会问题有所认识,并唤起读者对田野调查这一写作形态的重视,也在传播上带来了杠杆效应,容易形成热点话题,是谓兼得;从风险说,则是在向文学移位的过程中,有可能导致学术性失落,而并未获致真正的文学性,从而两失。决定其成色的根基,是田野调查的扎实度。
而作为非虚构写作另一大门类的特稿,也是由新闻进入文学,从新闻性的本质出发并借助了文学性。好处同样是可兼得,比起调查报道的笨功夫,可以形成更具风格的文本,流传更远;从我自己的写作历程来看,十多年中出产的调查报道并无多少被人记住,反而是采访艰苦程度上次之的特稿更易流传下来。一大批特稿就是这样同时进入了文学界和公众视野,包括《大兴安岭杀人事件》和《太平洋大逃杀》先后获得各种重要奖项或卖出电影版权;但风险也同样在于两失,过于追求文学性,导致稿件真实度的重要性逐渐降低,在年轻一代特稿写作者中,深描人性、追求文笔而淡化采访调查已经成为某种风气;但由于新闻的时效和热点本性,受制于编辑部选题机制和发稿周期限制,产生的文本仍然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而是某个社会热点的报道,并且力图提供某种传播力更强的社会样本,有时候是直接的社会议题、情绪的样本,譬如外卖小哥受困系统;有时是隐喻、象征式的样本,譬如白银杀人事件、庞麦郎或是太平洋渔船上的囚徒困境。
从社会学、人类学、新闻出发对于文学性的借用,固然可造就一时的繁荣,但从长远来看,也使非虚构写作面临局面涣散的困惑。一方面,“非虚构”似乎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篮子,什么样的文本都可以往里装;另一方面,非虚构的核心定义模糊,无法摆脱社会性价值而具有独立文学意义,经典的非虚构作品因此产出寥寥,“非虚构写作”的意义正在耗散,面临概念失效的局面。
这和当初人们提出“非虚构”时寄予的期待拉开了视距。西方的非虚构写作产生于新新闻主义,对文学的使命感不强;中国的非虚构写作则由《人民文学》等权威杂志和文学批评家首创其端,一开始就具有疗救文学积弊的使命,它的意义首先是文学而非新闻或者社会学的,其宗旨在于为过于虚化的当代文学重塑现实根基,使其获得某种真实性。但或许受制于小说为主流的强大文学传统,人们提出的是“非虚构写作”而非“非虚构文学”的概念。这为非虚构在文学上的意义拓展埋下了先天不足的隐患。
如前所述,十几年间在非虚构写作的概念下富集的,主体是以社会学、人类学、新闻学为核心的文本写作,文学性只是社会性或新闻性的附庸和缘饰,或者混合,并无独立性,这在多数非虚构代表文本中体现得很明显。评论界和读者对一部非虚构文本的评价,也首先是着眼于其社会性、概念性,比如反映了什么样重要的社会现实,提供了怎样典型的社会样本,可以提取怎样的社会概念,来帮助我们认识和思考社会;在此前提下,以某种程度的文学性作为包装,而并非该文本提供了怎样的非虚构文体下的文学性,对人的存在和人性的开掘到了何种深度,拥有怎样的丰富性,在语言和叙事上达到了何种成就。纵观近几年来各大文学非虚构类奖项以及文学排行榜的评选,这种取向也很明显,很多时候授予了社会学和人类学者的学术研究作品,这些作品只是略微吸纳了文学性。
与此同时,非虚构写作还受到来自报告文学的掣肘。“非虚构”只能名之为“写作”,“报告”却可称为“文学”,并且垄断官方的文学奖评定体系,这在客观上说明了非虚构在中国的夹缝之境。当然,“非虚构写作”还时常被普通读者还原为“纪实文学”,从而由严肃文学的场域悄然滑落。
种种困难说明,“非虚构写作”的概念过于宽泛,已经不足以面对今天混杂的现实,在外延不断膨胀和内涵日渐模糊的双重趋势下,正在日益走向意义耗散和失效的境地,任此发展,不出多久,非虚构在中国将失去意义。为使当初提出非虚构的初衷不致完全失落,有必要提出“非虚构文学”这一界限更清晰、内涵更明确的概念,来保存和拓展非虚构的核心意义。
三、非虚构的文学性从何而来
和诞生于国外的非虚构写作不同,“非虚构文学”是一个新概念。但它已在一些非虚构作家的言论和文字中出现。这是必然的趋势。冯骥才、梁鸿都曾在相关访谈中谈到他们对非虚构文学的理解,其中冯骥才着重强调了非虚构文学的思想价值和语言价值,梁鸿则谈到了“合理化想象”,以及非虚构文学对于表达人类精神的某种幽微之境的价值。
“非虚构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它何以区别于虚构文学,或者说是小说?
“非虚构文学”与小说获致文学性的路径不同。小说借重想象与化合,来重组生活经验与人性体验,从而获致表达的自由性与意义的丰富性,为人类提供审美自由;非虚构文学同样能够提供审美自由,但它不是借助于想象,而是通过对有限经验、细节的深入理解、感受与表达,来开掘事物内部的丰富性,由此打开自由的空间。同时,在对周遭世界的把握、传达和思考方面,又具有更大的视野格局、更强的精神穿透性,这就使它在内外两方面弥补了想象力的缺陷,带来了创造性和自由度。
冯骥才针对《一百个人的十年》的创作谈到,虚构依靠想象力和创造力,非虚构首先来自对生活的认知和忠实表达。在技术性的层面,他谈到了细节对于非虚构文学和小说的同等重要性。
细节并不天然地等同于文学性,它包含着一个有待打开的空间,开掘的钥匙是作者的感受力和理解力。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处处的生活细节上体会到人类生活的内涵,以及人性的深浅,我们就能发现表面单调琐碎的日常生活的丰富与繁复,无须借助离开生活现实的想象也能获得感受的丰富性和自由度。而这正是非虚构文学性的立足根基,在受限的前提下去获得类似想象力的自由。
至于梁鸿在《梁庄十年》的访谈中说到的非虚构的“合理想象”,并没有脱离开真实生活细节,而是由此出发进行的感受拓展,和小说中的虚构是有很大差别的。
正如冯骥才所说,相比小说的不受限制、任意发挥,非虚构的有限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力量。“作家愈恪守它的真实,它就愈有说服力,这是虚构文学无法达到的。”
现实也正是如此。看起来拥有无限文学自由度的小说,在一味标榜“想象”和“虚构”的口号下却面临想象力衰退、表达力枯萎的困境,只能在常年形成的文学范式里实行套路增殖,面对现实失去了感受和开掘的能力。多数长篇小说都在写演义式的家族传奇,短篇小说则流于情节迷宫、情绪虚浮或人性猎奇,用一位小说家的话来说是“需要对人性的开掘越来越阴暗才能进行下去”,脱离了日常生活场域,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赝品之感,不像是从生活经验中生长出来之物。按一位茅奖得主的说法,是“不停地打滑”。
“非虚构文学”由于忠实于有限性,植根于生活的现实场域,能够保持文学质地的真实性;又具备精神、知识领域的探索能力,能够给文学带来人文性。真实本身是最为丰富的,因此对生活场域的忠实开掘和感受,以及对知识、精神领域潮流的在场性传达,反而在自由和丰富性上超越了看似自由的想象和虚构。后者已经逐渐接近空中楼阁的自我增殖,无法翻空出奇,只能走到穿越、修仙、科幻的类型道路上去。即使作家的心理化合能力再强大,如果长期忽视生活真实,投入的经验之物是虚假的材料,也难以化合出质地可靠的作品来,这就好比烧制瓷器,固然需要经过高温熔炼下的化学作用,但如果用于烧制的窑土不是来自自然的高岭土,而是三合土之类,就注定烧不出地道精美的瓷器来。
另外,疏离于人类存在经验却沉迷于人性迷宫或故事传奇,也会使小说越写越小,失去知识、精神上的意义,人文性阙失,带给读者的除了一种类似“故事会”的心理满足和某种情绪替代,没有心理学层面上更高的东西,更不论精神上的陶冶和终极意义的寻求。小说失去人文性甚至排斥人文性,丧失和拒绝思考功能,也使得小说远离了一般希望对社会有所关注和思考的读者,日渐小众、圈子化,如果不是作协体制支撑,局面难以维持;从长远来看,小说家和读者长期在人类低层面的心理需求上相互迎合,一路走低,则有沦为俗文学之忧。
从文学史上看,很多文学大师都具有非虚构精神,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多长篇小说题材脱胎于当时的新闻报道,又以他坚实的底层生活经验和丰富感受为底子,加上情节的丰富想象和穿插构成《罪与罚》 《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长篇巨著,对于当时各阶层的社会现实、知识状况与精神状态都有很直接切实的传达,并不仅仅是底层传奇或者人性穷究,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可以很自如日常地探讨当时的重要社会话题;金宇澄的《繁花》也具有强烈的非虚构精神,人物的活动场域可以还原到真实的街弄,细节和情节大多从市井口传和生活经验中得来,还涉及当代地下党和“托派”等历史,写法也并非猎奇式的渲染而是情境还原。即使是在石黑一雄这样以艺术性见长的小说家那里,人物也会很自然地进行日常社会思潮的对话讨论,这在中国的家族传奇或者底层传说、残酷青春、文青旧梦式的长篇小说中是看不到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来,非虚构文学对于小说亦有重要的疗救之效。为主流文学打造真实性的地基,恢复小说质地上的可靠性,开辟另一种审美自由;为沉迷于幽暗人性和曲折情节的小说打开人文空间,引入精神性和人文性的表达,使小说成为“大文章”,避免越写越小、越圈子化的窘境,这是非虚构文学进一步的使命。当然在眼下,最重要的课题是正式提出“非虚构文学”这一概念,确立和尊重非虚构的文学性,而不是任其在“非虚构写作”的漫无边际之中耗散和消退。
提出“非虚构文学”,并非要取代虚构文学,二者是互补共生的关系;也不是要淘汰“非虚构写作”的概念,二者是同心圆式的存在,“非虚构写作”可以包容更大范围的、带有文学性的文本创作活动,譬如从学术、行走等出发吸纳文学性的创作,其价值主要在于社会意义;“非虚构文学”是一个更核心、边界更确定的存在,它必须是以写人(或其他生灵)、写人的生活为根本目的,不排除由文学出发吸纳学术性或其他,但其意义主要是文学本身,价值天平的砝码不能置放在社会意义一端。
如此,眼下非虚构“热热闹闹的僵局”才有破局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