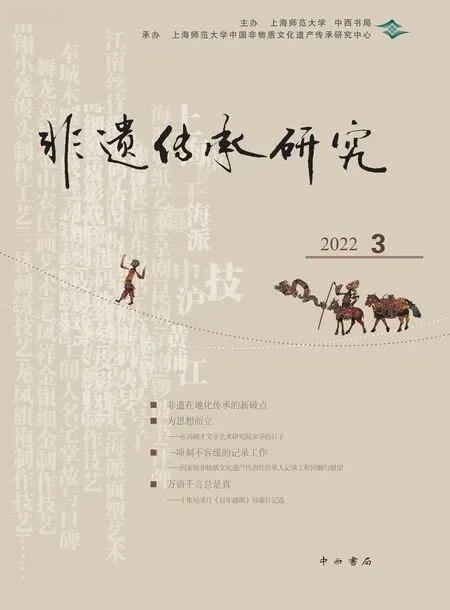传承人记录工作的现状与未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反思
李东晔
自200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公布《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后更名《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特别是中国的昆曲位列其中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也逐渐走进了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相关领域。二十多年来,从国家到地方各级都建立起了相应的工作机构,完善了相应的工作机制,普查、记录与保存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并且,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传承人技艺的有效继承是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关键。传承人记录工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影像及多媒体设备与技术的发展,并且日益广泛地应用在传承人记录工作中,使得具有“活态”属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加有效地记录、保存、呈现与传播。然而,我们的传承人记录工作到底应该记录什么,为什么记录以及怎么记录等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其代表性传承人保护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一、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
“非物质文化”是相对于“物质文化”而出现的一个概念,虽然其所指目前尚不能完全统一,但非物质文化依托于人及人类社会而存在并发展的特点是得到广泛共识的。与非物质文化密切关联的一个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源于2003 年10 月17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 届大会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民族(社区或社群)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
广义而言,我们所有人都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继者,即传承人。但事实上,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不仅有其地域、国家、族群等归属,还有相应的代表性传承人。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其传承人的实践活动为主要载体的“活态”的文化,所以,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所规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重要原则之一,并且与之相配套建立了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等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代表着其所处社区或社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能力的最高水平,并通过不断融入其个性的文化实践活动延续着那些宝贵的文化传统,为确保人类文脉的持久传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保护代表性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
2007 年、2008 年、2009 年、2012 年、2018 年,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先后命名了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总数达三千余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于2019 年11 月12日经文化和旅游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0年3 月1 日起施行。
二、传承人记录工作的思路、规范与指南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代表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与传承的最高水平。但是,正如当下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项目的境遇那样,广大非遗传承人的生存与传承状况并不乐观。普查与记录工作是识别与保护文化遗产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以人为载体的活态属性,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工作势必要以传承人的记录工作为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于2013 年开始试点,并于2015 年全面启动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2018 年更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
此项记录工作尝试依托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相关的多领域及学科的理论、方法与专业人员,充分利用现代影像技术,对各省(区/市)遴选出的非遗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非遗实践活动进行全方位的搜集、记录与整理。自2013 年开始,受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的委托,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以下简称“中心”)陆续编写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规范(试行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操作指南(试行本)》(以下简称《操作指南》),举办了面向各记录工作实施单位、执行团队和验收专家的各类培训。
《操作指南》对记录工作中最为核心的部分“资源建设”工作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包括记录准备、文献收集、影像采集及整理编辑。其中,准备工作基本上借用了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专业田野工作的模式,从组建团队到记录工作需要的知识储备和设备准备等逐项提出了标准与建议。文献收集工作需要基于对相应的非遗项目与传承人的深入了解,需要相应的工作人员具备文史专业的学习与工作背景,以及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影像采集工作则需要建立在扎实的基础文献阅读与相当长时间的田野经验基础上。我们特意设计的“项目实践”“口述史采访”及“教学传承”三个工作环节,针对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口传心授的特点和许多身怀“绝技”的传承人年事高,已经不在自己艺术高峰的实际情况,最终以三个文献片的形式呈现。这三个影像采集环节环环相扣,既相互独立,又互为补充。传承人如果不能或不能够很好地直接进行非遗实践,我们就请他用口述历史来弥补;如果有些技艺的细节与“门道”不能够借助口述让广大观众或读者了解,那么就再通过教学传承来展现。总之,我们就是想通过采集工作尽可能完整地记录并呈现出传承人的技艺特点与风采。
最后的整理编辑工作不仅需要担当此任的人员具有相应的文字与影像整理编辑能力,责任心更是考量该环节完成好坏的重要标尺。我们通常所说的“综述片”就是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呈现出的记录工作成果之一。
《操作指南》的第二部分评估与验收,对上述几个工作环节提出了更加具体的工作要求与量化指标,为工作团队提供了参照,以便更好地完成工作。《操作指南》的最后对记录工作成果的后续利用提出了建议。
总体而言,记录工作的思路、规范与指南都是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要求,在学术界与非遗保护等工作领域已经达成共识的原则基础上搭建起来的,将数字化影像与多媒体技术应用在覆盖全国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中。
三、工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截至2021 年,中央财政已对全国约1600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进行了记录工作的财政支持,记录工作成果包括文献片、综述片、收集文献、口述文字稿及工作流程文件等。记录项目的成片时长平均为25 小时,数字化后的收集文献约为100—300 件,口述史文字稿平均字数为10 万字。每个项目最终提交的资源量平均为300GB(素材资源量平均为1200GB)。截至目前,2015—2018 年国家支持的四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项目中,已有872 个项目通过专家评审,完成了最终验收。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与探索,记录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工作思路与模式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工作中存在的不少问题。
1.被记录传承人的主体性
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哪些主体参与了非遗产的生产与再生产?哪些主体参与了非遗的管理与消费?传承人的主体性体现在哪里?这些问题一直以来都为学术界以及参与保护实践工作的各界人士密切关注与积极探讨。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下各种类型的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有关的工作中,传承人的主体性都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甚至完全消失,他们只是这些工作中的一个客体,一个研究对象,一个拍摄或记录的目标。这种现象在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中依然存在,在各省区(直辖市)提交的项目中,被记录传承人主体性缺失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究其原因,自2001 年“昆曲”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来,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受到了全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但依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工作模式。从国家到地方,从保护到宣传都是如此。包括本文讨论的传承人记录工作,从立项、管理到具体实施,传承人只能在配合或拒绝两个维度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也就是说,在整个记录工作中,传承人的主体性评价往往被简化为记录工作配合度的好与坏。对于个别主体意识比较强的传承人,由于他们“配合度很好”,所以在记录工作过程中能够比较顺畅,并且在最后提交的成果中能够呈现出一个相对好的效果。在历年来提交的成果中,诸如辽宁省“古渔雁民间故事”项目传承人刘则亭、河南省“四大怀药种植与炮制技术”项目传承人李成杰、江苏省“常州吟诵调”项目传承人秦德祥等,他们多年来自觉地对自己所传承的项目做了包括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在内的大量工作,并且也相应地获得了各级保护机构的认可,获得了一定的社会知名度。他们非常乐于配合这种由国家或政府牵头的记录工作,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且发挥出了自己的主体性。但我们的记录工作不能仰仗这些个别传承人自觉或自发式的主体性所发挥的有限作用而实现希望达成的结果。
在我们目前看到的大部分项目中,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传承人的主体性几乎都是被忽略的。此外,该记录工作是有国家经费支持的。而我国目前大部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经济状况都不是很好,亦不稳定,且很多人还面临年老多病的现实情况。虽然我们在《操作指南》上给出了类似支付“劳务费”或“经济补偿”的建议,但由于传承人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参与其中,他们能够看到的只是记录工作的人员、设备等经费支出,与其自身经济情况存在的较大反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传承人心理上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因此,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有必要提出这个问题,至少应该让传承人作为记录工作项目的主动参与者,在申报、立项、方案设计以及成果呈现等诸多环节参与进来,而不是目前这种仅仅作为记录的对象或客体,或者以自己的技艺和时间做一次展演,换取少量劳务费。
2.文献收集与整理
可以说,文献与整理工作是历年完成项目中比较薄弱的环节。由于不同于社科基金等学术研究性项目的申报,传承人记录工作的项目申报与遴选是各省(区/市)以项目招投标形式分包给各个“项目团队”的。这些项目团队大多以导演或团队的拍摄与后期制作能力为主导,也就是说,项目团队是一个拍摄团队。团队的研究与学术能力相对薄弱,并且,对于作为项目支撑的学术基础的重视程度也较差,他们往往将前期的文献收集与整理工作作为拍摄工作的一个简单的素材准备,而忽略了文献工作本身就是记录工作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因此,记录工作中的文献收集与整理工作往往流于形式,不仅该环节工作往往完成质量较差,且经常导致整个记录工作质量不佳,最终只是呈现出一种无本之木或无源之水的样貌。未来可能还应该在项目申报与审批机制上进行优化,在项目团队的遴选与管理上也需要加以规范和完善。
3.学术专员的遴选与职责
学术专员应当是记录工作团队中的核心。综观历年来完成的记录工作,尽管在《操作指南》当中明确提出了学术专员的重要性以及应该承担的职责,但是在项目的实际开展当中,不仅学术专员的水平参差不齐,且发挥的作用也是非常不同的,更有甚者,工作团队中的“学术专员”只是徒有虚名。与传承人主体性缺失不同,学术专员的优劣决定了一项记录工作是否“跑偏”,是否真正记录到了有价值的内容。
之前提到过辽宁省记录工作团队对于“古渔雁民间故事”项目传承人刘则亭的记录工作。该团队拥有包括已故民俗学专家乌丙安先生在内的一个强大的学术团队,学术专员全程参与工作,拍摄记录注重故事讲述,并与其特有文化及自然环境相配合,共记录13 个实践过程,提交传承人讲述的294 个故事,内容涉及神话、祖先、生活故事、生产生活、地理环境、动植物热爱等。还有辽宁省的“医巫闾山剪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汪秀霞的记录工作,该工作团队学术专员王光作为辽宁省锦州市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主席、研究员,从1983 年就开始调查、搜集民间剪纸艺人汪秀霞的资料,基于对项目及传承人长期深入地了解与研究,使整个记录工作呈现出了其应有的样貌与价值。
4.为何以及如何做传承人口述史
《操作指南》中建议记录工作中的口述史采访与整理工作最好由学术专员负责完成。但在实际的操作中,真正意义上由学术专员完成的口述采访与文字稿极少,这也是造成大多数项目的口述采访与文字稿质量都不佳的重要原因。
传承人口述史采访成败的关键在于采访者本身是否具有相应的专业素养与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我们记录工作中的口述史采访对象,即传承人,都是明确的、具有指定性的,也就是说不能选择采访对象,由于我们不能期待每一位传承人都善言辞、易配合,所以认真细致且具有针对性的准备工作是必须的。开始正式的口述采访之前的准备工作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知识性的准备、编写采访提纲、前期沟通与适应。
知识性的准备是指那些有别于法律文书、文件以及技术性的准备。具体包括:相应的社会历史沿革、人文常识及习俗等;传承人所属项目的源流及现状;相关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传承人个人的情况——不仅要了解其工作和生活经历,还要熟悉传承人的生活习惯、个人好恶、人际往来及语言习惯等多侧面各层次的情况。知识性准备工作做得越充分越有助于后续工作的开展。
访谈提纲的编写是在充分做好知识性准备基础上才得以完成的,是一对一的,也就是需要为每一位传承人量身订制专门的提纲。我们要借助于对代表性传承人的采访,了解非遗中所强调的那些“非物质”的内容,以及这些“非物质”的内容是如何通过一个具体的传承人继承下来、传递下去的。如果不是经验极其老到且对项目和传承人情况了然于心的采访者,在正式开始采访之前编写访谈提纲的工作就非常重要且必要了。提纲不是让采访者在现场照着念的,因此还有一个口语转换的环节。
与受访人多沟通与相互适应很重要,大致包含以下几层含义:首先是工作上的沟通,要明确告知采访的目的、内容及形式;其次是情感上的沟通,通过营造一个正面的、利他的、去行政命令化的团队与采访者形象,建立起一个相互信任的工作关系;与此同时,熟悉和适应对方的语言与交流习惯;最后,需要就采访的具体方式做进一步的沟通,选择合适的拍摄地点与环境,让接受采访的传承人适应镜头与环境。
访谈自然是整个口述史采访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检验或考验采访者能力与各项准备工作是否到位的环节。第一,自始至终都需要恪守知情同意的原则、不伤害的原则、有利的原则。第二,始终要尊重被采访传承人的主体性。尽管采访者有很好的专业素养,并且已经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熟悉并了解项目及被采访的传承人,但并不能够替代传承人发言,只有传承人才是那个“非物质”的承载者、实践者与传递者。采访者不仅不能够自认为懂得比被采访人还多、更具权威与发言权,而且始终都要怀有一颗探索真相的好奇心。
5.记录工作的管理与可持续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属性决定了其保护模式必须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是要采取确保其“生命力”可持续的保护措施,影像记录手段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我们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作一种传统,但事实上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当代的,它们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其所谓“活态”亦是永远变动不居的“动态”,只要某个社区或社群中的非物质文化实践活动依然存在,记录工作就应该继续。因此,不仅在某一次记录工作过程中的需要专业性与系统性的管理,而且在单个记录工作完成之后,其档案的存档、保存、研究、传播以及传承等接续工作都需要专业化、系统化的管理。
反观我们目前的记录工作,由于现行的工作机制,基本上都是按照单一的项目申报与管理加以实施的,换句话说,基本上都是一次性的,不仅在单次项目的管理上存在诸多环节上的缺失,很难照顾到后续工作的有机衔接,更不用提及记录工作的可持续性了。因此,如何能够使我们的记录工作不断地继续下去,就是我们在未来工作中需要思考与实施的重要内容了。
四、传承人记录工作的未来
自2013 年受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委托,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开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以来,中心不仅完成了上文提及的几项工作,还围绕记录工作出版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十讲》,组织实施了5 批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的验收,并且每年举办“年华易老,技·忆永存”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展映和主题展览、“他们鉴证了文明”非遗影像公开课等活动。
这项工作目前的意义不仅在于记录和保存一套我国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影音图文多媒体资料,还尝试通过多种途径向社会公众推广这些记录成果,提高传承人和非遗项目在全社会的关注度,吸引更多社会机构和普通公众关注他们,为非遗保护创造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并且,作为国家总书库,国家图书馆也希望这些记录成果能够成功入藏国家图书馆永久保存,为更广大的读者或观众呈现并传播这些宝贵的人类遗产。
然而,正如本文所提出的这项记录工作目前存在的问题,面向我们人类自身的未来,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工作的任重道远,在记录技术手段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不仅要思考如何系统、准确地记录,更要思考记录工作的可持续性与可传承性。
就记录的方式或手段而言,在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组织翻译出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记录与呈现:欧洲的经验》的概述中指出:“文章的作者们一致同意:电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和呈现的最合适、最优质的媒介。他们将影片作为收集收集素材、创造知识、获得认同感、形成持续性和留存记忆的一种研究方法;将影片作为遗产抢救、保护、保存和复兴的一种方式,增强对遗产的重要性和知识保护的意识;也将影片作为向他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传播非遗文化的方式。”
就传承人而言,尽管我们的非遗传承人通常都精通当地文化,且在技艺方面具有特殊的、深厚的造诣,但在记录工作中是不是应该避免一刀切的工作方式?“譬如说,探讨传承谱系和文化继承性,就应当选择那些传承谱系较为清楚的传承人群体,而且应当在几代传承人中都有关键报道人,才能够通过相互补充,了解到文化的传与承、技艺的教与学的全过程;想要讨论文化传承与性别问题,当然需要考虑传承人的性别;如果想要研究不同流派的传承人在技艺上的差异,则需要选择不同流派当地人公认具有代表性的传承人进行调查。在选择关键报道人时,也要考虑传承人是否愿意合作、善于表达、擅长进行细腻的描述和解释、能够明白调查研究的意图,以及能够抽出一定的空闲时间来配合调查。”
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自觉担负起记录、保存、传承、传播文化遗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