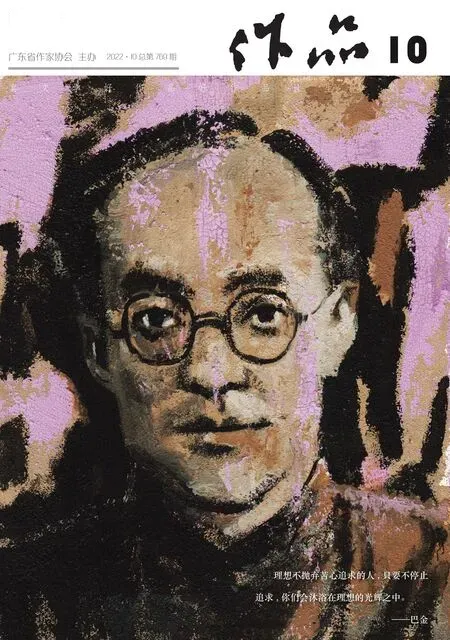在迷雾那边(短篇小说)
韩傲霜(北京林业大学)
杨海峰(内蒙古农业大学)
小说应是生活的真相。《在迷雾那边》接受了这个使命,它在帮助我们到达一个清晰的世界(实际上这个世界子虚乌有、支离易碎)上做过努力,至于成效如何需要读者去评判。从题目上看,我很容易想到普鲁斯特的《在斯万家这边》,而从内容上,我想到的则是卡夫卡,在卡夫卡的《城堡》里有这样的一段描述:K从早晨出门,大约只过了一两个钟头,夜幕就降临了。当然,我更想谈及作品本身,而不是其与他人作品的相关性。
故事发生在一个叫作吉格斯太的地方,这里终日浓雾(或者我们的生活就是大雾天),他与朋友来这里旅行,住酒店,去酒吧喝酒,做(记)梦,与富有传奇性的女人相遇。当然,我觉得还应该提及的是,一个城市的雾天与吸烟有关。直至吉格斯太多云,主人公和朋友去参加晚会庆祝雾霾消退,寻找梦中的那个女人。直至主人公退房,他被前台告知在孤身旅行。他从家里醒来,头痛欲裂(因为梦境?或许这场旅行根本不存在?),以上便是这个短篇的内容。
我们得到的远比小说本身给予的要多。当我们将自己所想的去呈现,就像是小说中所说的“行为才是思想的第一体现,而不是语言”,那么,存在一种可能,我们能到达思想的未及之处。
吉格斯太浓雾,第七天,卡特酒店负一楼似是酒吧。
时间的概念不太明晰了,楼上前台处的摆钟会在正午十二点敲响,不过早敲一会儿或晚敲一会儿也不会有人知道。那么,他们会打乱时间敲钟吗?我们没办法用太阳的方位判断时间,窗外的景致在早上八点和晚上五点也不会有什么区别。我的生物钟向来紊乱不堪,一时想不到其他计算时间的方法,就偷懒认定钟声代表最为准确的时间。雾霾还是没有散,天空是被各种颜色污染弄脏过后的白颜料,白天从卧室外的草坪延伸往远处看过去,视线到五米之外的草坪边缘的马路牙子上就停滞下来。如果是晚上,在到来的第一天还可以看到对面楼里闪耀的灯火,那些一点点摊开的光晕,跟高度近视的人没戴眼镜走在布满霓虹的路上看到的街景如出一辙。现在也与白天混为一团了。连续几天都没办法开窗子通风,饶是如此,窗缝里还是渗进来一股比老地主家的旱烟还要冲的焦油味,还带着些灰扑扑的辣腥味,一齐糊在人的嗓子眼上,上不去也下不来。
我还是把嘴里那口老掉的烤肉就着蔫了吧唧的生菜吞了下去。
当地的餐饮没有一点特色也就罢了,一些全国连锁的餐饮店开到这个地方,沾了吉格斯太人的手加工制作,也成了被剥了皮的洋葱,褪了一层颜色,也差了一层味道。菜单上得有一半实际从没有给客人上过的菜品,烤过头的鸡翅中,肉串中间硕大的肥肉,还有这里的啤酒,寡淡得像小孩子喝的橘子汽水去掉了白砂糖,还没有那么足的气泡。“哈,真让人火大。”身边都是一群大男人的时候,我就不在乎自己的教养问题,好像没穿衣服在床上咒骂的妓女,大声说着对这个地方的厌恶。其实我知道比起其他在晚上八点钟就打烊的小店,还有那些只存在着牌匾却从没营业过的店面,这已经是吉格斯太最有契约精神的小店,二十四小时营业,因此它拥有小镇上所有黑夜的灵魂,角落里总有一些没办法在卡特酒店下榻的外来肉体,他们甚至可以一星期只点一杯廉价啤酒。过了七点钟,这里就不会再有女人,女人们在深夜总是各有去处而不必流落在此。如果这里的浓雾不散,我们会被一直困着没办法离开。赵润泽一年一度的假期要陪我尽数消磨在这里,甚至会耽误下一个工作周期的开始,我是个自由职业者,我不在乎这些,但他不行。浓雾如果一直不散,总有一天,我们也会因为没有办法支付卡特酒店的房费要住在这个小店的角落里了,“节约是有必要的了。”我说。
“及时行乐嘛,已经出来了,在哪里都是休息。”他自顾自地又倒了一杯啤酒,气泡顶满了杯子马上就溢出来但又恰到好处地缩了回去。赵润泽让我把背包递给他,“又来。”我直接掏出血压计给他递了过去,“达成默契了啊。”我把吧台上的两个酒杯拿在手上,腾出地方给他放血压计,看他缠上袖带,袖带慢慢变紧,然后松下来。“150/75,高压是低压的两倍,还算正常,还可以再喝一杯。”“嗯,只有你不看数值看比例。”忘记是哪次一起喝酒,他开始自带血压计,说单位体检查出他的血压有些偏高,医生下了禁酒令。得听医生话不是?所以他之后每次喝酒的时候,喝几杯就量一量血压。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形是在饭店,服务员上菜时刚好看到这一幕直接被惊住了。太丢脸了,我知道制止他在大庭广众之下闹笑话是没有效果的,竟然也想给自己测测血压,反正脸已经丢尽了,结果我自己也爱上了量血压。血压袖带紧绷起来时给肌肉带来的压迫感,能带给我瞬间的平静,奢侈一点可以持续大几秒。我知道自己需要这几秒,也许在未来某一天,一个血压袖带会成为我的精神食粮,超过酒精,也超过爱情。酒精让他的话变得多了起来,“两年前的冬天我出差,到了一座海滨城市,工作完沿着海岸线散步,夏天人满为患的海水浴场啊,那时候没什么人,除了我。也是这么一片白茫茫的海雾,让海风吹着上岸。真高兴啊。现在,那种感觉又重现了。可你老这样闷着自己,岂不是看什么都没趣了?”
的确啊,吉格斯太的雾霾一点也不可爱,不性感。“我想并不存在什么有趣的东西了。我感受到自己的想象力在枯竭,又或许它从来在我这里就不存在,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啊。”这里有许多的好景色应当被看到,我说的不只是蓝天和白云。
你还是太过于任性,不过不能归咎于天气,也不能归咎于想象力,你以为这些不可控,其实这些都是可控的,你所谓的想象力、激情、才华这些具体的东西,还有像天气这种虚幻的事物。其实行为才是思想的第一体现,而不是语言。你把语言看得太重要啦,多去做一些事情吧。别说了别说了,安静下来吧……我好像听他说他想要救赎我,也许是我央求他帮帮我,或许我们都没有说这些,这不像是赵润泽的话,更像梦里奇怪的人告诉我的言论……
吉格斯太浓雾,第八天,卡特酒店三楼房间内。
昨晚好像喝得并不多,再清醒过来却是回了卡特酒店三楼的房间。我全身上下连底裤都没有了,左脚还留了一只袜子,手旁边放了一只青苹果,我丝毫不记得它的来历了,想必是昨晚在酒吧带回来的。酒吧带苹果回来也很奇怪吧,在我手里的当然是我的。已经一周没有碰过水果了,但我还是忍住没有吃下它,它太好看了,绿得让人赏心悦目。没有花的日子里,闻点果香也是很好的。两片窗帘中间透着一拃的空隙,就是那一拃之景,望过去跟把全部拉开看到的景象也是毫无差别的,满天的浓白泛着一些灰色的雾霾。我起身过去把这一拃全部拉住,点开了灯,似乎这只灯泡能冒充太阳,发挥一点阳光的功用。赵润泽不见了,没有消息也没留字条,除了去向大堂经理讨要午晚餐我想不到他还有什么别的事情要做了,因为这里的午餐总是在晚餐时分才送到各个房间,我们一向称这顿饭为午晚餐。肚子开始叫了,但我对赵润泽寄予厚望,他总是能在我需要的时候变出一些食物出来,有两次我在工作室饿到低血糖,躺在地上,都是他过来解救了我。这种依赖是有些过分,但我想到昨晚一定是没有狠下心撇下赵润泽一个人回来,倒让他把我灌醉了,这时负罪感就被抛到九霄之外了。我想起自己叮嘱过他,我的午睡会持续到太阳落山,那是我在睡梦中最清醒的时间,这段时间的梦境总是很管用,我会在醒来后把它们编织成故事,几乎是我所有灵感的源泉,他吵到我的午睡会比偷走我的钱更可恨。有可能他不是去找午晚餐,而是把房间腾出来不打扰我午睡。我发了讯息给他,让他带吃的回来。我拧开矿泉水一口气喝了半瓶,越来越饿了,这样看来屯零食真的是一个绝佳的习惯。
我不应该想这些毫无用处的东西,当我再打开电脑回忆梦境的时候,除了重复通过一座摇晃的窄桥已经想不到其他的内容了。谁让我上的窄桥,要去哪里,过桥做什么,拼命地回忆也没有用,我知道今天的记录已经废掉了,醒来应该先记梦的,之前也不止一次吃过这样的亏了,可就是不长记性。打开没写完的一篇杂文,思路一样很杂,我干脆合上电脑。
空荡的房间让人不知道做些什么,桌子上放着一本《2666》,只有蠢货才会在出行时选这么一块大砖头。我从枕头下找到右脚的袜子套上,事实上,穿着袜子赤身裸体会比什么都不穿时更裸露,而我没有手淫也不打算手淫,而是把书拿过来放在膝盖上,书的第四部分在讲述各种罪行,差天气也会是罪恶流淌的源头之一吧。静心阅读变得困难。我伸手抓起了遥控器,书还在膝上搁着。事实上我已经记不清上次看电视是在什么时候了。我几乎不看电视连续剧,甚至看电影也很难集中时间,有些感兴趣的片段,我会用平板反复播放,这样看完一整遍以后,这个电影就会被我删除。而我的记忆越来越差,我想不起最近看过的一本书的名字,也想不起我看过的那些电影的名字,最严重的时候,我看着赵润泽,忘记了他的全名。我把它们归结为长期酗酒的后遗症。
上一个住客最后看的频道是吉格斯太当地的卫视,一打开就在播放着关于天气的新闻。天气预报就像快要过期的感冒药,没有完全失效,但不会对我的喉咙有半点帮助,在我们到达的第三天就说浓雾即将退散,这个即将仍然是现在进行时,我也不想听到任何报道。直接调进电影频道,这时上映着《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正好是那段我为之神魂颠倒的点烟画面。我闻到楼道传来一阵香烟的味道,随之想到自己由于鼻炎过于灵敏的鼻子,可能只是闻到了外面的雾霾引起的烟尘气味。不,不是,雾霾的味道会带些灰扑扑的辣味,而烟草不会有这种灰扑扑的味道,是香烟里焦油的气味。赵润泽也抽烟,我把他过滤掉了,我想到那个姑娘,是不是她在吸女士香烟?如果是的话,她吸香烟时的眼神必然不会像玛琳娜一样风情万种又令人心碎。不,她清纯而不妩媚,我想到了,她会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歌手易知难,我愿意去给她接烟灰;如果可以,我会抢过她的烟,给自己同样点上一根。那张照片,一种来自纸片独有的宁静,我没有办法把那张脸立体起来,那双眼睛好像下一秒就会留下泪水,宁静的泪水。是不是曾经有一次,她吹完头发,也这样凝望过一个地方?电视上的画面转到玛琳娜被西西里的女人羞辱的桥段,我关上了电视,我信奉一点:当我不去看时,一些事情就没有发生,是假的。有些时候,我希望这是真的。
他回来了,这时我已经不饿了,可能是刚刚的半瓶水起了作用。今天盒饭的分量看着多了些,还是趁热吧。我拆着一次性饭盒,一些汤汁弄到手上,没有纸巾了,只能去洗漱间洗手。赵润泽已经打开盒饭开始吃了。“一如既往的难吃。”他都这样评价,我更不愿意去吃了。“是啊,鸡肉炖得太软太烂了,这不就是养老院没牙的老婆婆专属套餐嘛?”我又想去酒吧点餐了,我后悔昨天提出的节俭倡议了,说出去的话也不好自己打脸。“咱们这一层除了我跟你,是不是还有一个每天去楼道吹头发的姑娘?她吹头发的样子很粗鲁,好像在赶时间要马上吹干,但她又有浓密的黑发,所以可以满不在乎地把打结的几根头发一把扯掉。”我问他有没有见过这个人。“被困在这里的人做出什么事都不会让我奇怪。”赵润泽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饭上,扒了几口饭后突然想到卡特酒店的每间房都配备独立卫浴,问我确定真的看见姑娘跑到楼道里吹头发吗?他又想了想,“好像是有点印象,不过那姑娘只有在撩起头发的时候还算清秀,吹头发时非常没有女人味。是不是你自己头发快秃了,羡慕起别人的发量来了?你晚上早点睡就好了。”
“我去向前台要纸巾。”
“你可以在屋里给前台打电话,我兜里还有几张,有点皱。哦哦哦,你去吧。”
啪,我带上了门。
我顺着烟味来到安全通道的隔间,数得过来的几次下楼我都是乘电梯,所以才发现这儿还有这样宽敞的地方,十个人在这里跳绳都没问题。拿烟的是一个年老的清洁工,那是一根还没有点燃的完完整整的香烟,他见我来急忙塞进兜里,又试探地递了过来,问我要不要来一根,他头上顶了一个有禁止吸烟的标志,大概离他的头顶二十厘米,一行小字大概是说违者罚款之类的话,没有眼镜我看不清楚。那个姑娘不在这里,邂逅失败让人有些丧气,我告诉他我就是出来走走,他要是想抽就在这里抽吧。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举报他。
“以前还有一个吸烟区,自从雾霾开始,吸烟区也封了改成杂物间了。可这雾霾也不是靠吸烟吸出来的。你看现在酒馆照常营业,喝酒是不限量了,可香烟买不到。我囤了一些,你要是有朋友有需求,可以来找我。”敷衍了他一句我就走开了。关上房门的时候,突然想到香烟贩子应该会记得是不是有一个女孩来他这里买过香烟。等我再走过去,隔间里面已经没有人了,我爬上一层楼梯,只听到了自己的喘息声,再听不到别的声音。电梯已经下到了负一楼,健身房已经没有人光顾了,茶餐厅和酒吧还人满为患,在这些地方找到一个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失去了找这个人的兴致,我甚至都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属于这家酒店。线索的每一环都很荒唐,我得等明天的那个时机才对。
回到房间赵润泽没有问我纸巾的事,我有些累了,一头扎在床上,睡了过去。
睡眠的时间越来越长了,也就是说,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了。
吉格斯太浓雾,第八天夜里或第九天凌晨,卡特酒店三楼房间内。
可能是那一束刺眼的光,照在桌上零散地摆放着的一些易拉罐上,也许是先听见的卡车哼哼的汽笛声,总之我醒了,赤脚下床时踩到了掉下床的被子,好在没有被绊倒。走到窗边,拉开厚重的窗帘,还有它最外面的一层纱。我确信那个移动的东西是卡车,我看见车灯照射出来的光了。我兴奋了起来,想把赵润泽弄醒,告诉他。那辆卡车可能是我们的转机,最差的话也会是补给。我发现他的右眼半睁着,我说你也醒了啊。他不答话,发出了一声轻酣,我这才意识到他还在熟睡中,于是绕过床,把被子捡起来,又躺在床上睡了。
是吉格斯太的主街,我只走过一次的街道。街道两边的商铺都熄了灯,光顾者最多的供销社也不例外,寂静的黑雾盖下来,月亮下是黑色的云彩。大约快要晴了,晨光熹微,我脚踩自行车走在这条街道上。不一会商铺没有了,街道两边的房子也没有了,一条路上只有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云彩彻底遮住了月亮,我的眼睛一点作用也不起了,完全看不清脚下的路,但我没有下车,凭感觉掌控着自行车的前行。
凌晨五点钟。我判定是这个时间,毫无理由。做梦的时间紊乱了,以前我不在夜间做梦的。这样的梦在下午发生我是不觉得奇怪的,我几乎每个下午都会遇见这样奇怪的梦境,有时是美梦,比如满树挂的冰糖葫芦,比如乡间土道上爸爸骑着二八自行车驮着我,车筐里是爸爸买给妈妈的点心。记起这些东西,我有一种满足感,我并不是什么都会遗忘,最大的帮助在于我当时第一时间把那些场景用文字描述了出来,像今天做的一样。我想到昨天深夜的事情,问赵润泽的眼睛怎么回事。
“基本上是天生的,你看到的已经是改良后的3.0版本了呢。我做了两次手术才能闭到这个程度。睡觉戴眼罩也不是因为怕光,只是担心眼睛里面进灰尘或者细菌。昨天不知道怎么眼罩松了。”
“影响生活吗?”我知道没什么影响,这几天我们每天都呆在一起,如果不是昨晚看的那一眼,我根本不会知道这个事,但我还是问了,等他给我想要的答案。“你不介意我把你眼睛的事情写进去吧,可能是个会通灵的人物。”“荣幸啊,我要个好结局。”“那你有没有听到卡车的声音?五感是通的,你是不是眼睛不好,耳朵就会特别好用?”我明明知道他昨晚根本没醒,我太渴望有个人跟我斗斗嘴皮子啦。“你说的那是瞎子,我还没到那种程度。”今天反倒是他的兴致不高。
我还没有整理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思路,该午睡了,当我意识到自己该做什么的时候总是不做什么。于是我打开门,留出一条缝,坐在门口的地毯上,我要见那个姑娘,走上前去跟她说点什么。形象可能会幻灭,不管是我对她的还是对自己的,这让我感到紧张。她出来了,我的心脏开始怦怦乱跳,喝醉酒、写试卷对答案,瞒着妈妈偷偷在秸秆垛点火这些事都让我心跳加速过,我深知这不是动情的表现,只是说明我现在有干坏事的紧张,有点想呕吐,我得先去个洗手间。每次我一紧张身体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应,除了剧烈的心跳,有时是呕吐,有时是止不住地咳嗽,查体没有什么问题,或许是心理问题。我还是抵触心理咨询师,我该自己看一点心理方面的书的。现在大把的空余时间,刚好可以用来做这个了。可我没想干什么坏事啊,我只是想说个话而已,我为什么要这样侮辱自己?我趴在洗手盆上把水龙头拧到冷水一侧,洗了脸。要命,我怎么想这些问题,当务之急不应该是我该怎么搭讪吗?
幸运的是,即使她那样不耐心地对待自己的头发,也还没有吹完。我开始放热水,热水出水比冷水慢,等不及了,我放开冷水,一头扎进去,把自己的头发浸湿,一股冷气直冲脑门,比炎夏时喝冰镇饮品的感受还要强烈一些。我要跑到外面,她的面前。走到一半我想起自己忘记擦干了,水珠流下来,准确地说是流淌在衬衫上还有走廊的地毯上,但她已经注意到我了。因为她把自己的吹风机关掉了,加上外面的迷雾,颇有寂静岭的味道。我想她要张口跟我讲话。
我还是没有看清她的脸,我的目光没有停滞在她的胸脯上,也不是后翘的臀部,我看到她的肚子隆起着,很大,像一个横放着的热气球,没有下坠的迹象,而是稳稳地悬浮在身体的正前方。不对,我不确定它很稳,仿佛下一秒就要坠着她到第二层楼去。她已为人妇了吗?为什么一直是孤身一人?我之前一点都没有注意过她的肚子,除了有这样一个孕肚,周身又全然是少女的体态和作风。她更令我惊异了,仿佛肚子里不是孩子,而是一些别的难以名状的物质,也许不是物质,只是某种气韵、某种才华,是我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它激起了我的渴望和野心。这让我变得暴躁。
“你这肚子里面是什么?”我叫道。
我被自己的叫声吵醒,伸手去够卫生纸。不过在梦里,她要跟我讲什么?我记不起是从什么时候睡着的了。还有刚刚的场景里,赵润泽在哪里?现在我还是看不见赵润泽,我决定等他再回来时,不让他在我睡午觉的时候躲出去了。我需要他,我想在醒来时一眼看见他。
吉格斯太多云,第十天,卡特酒店负一楼酒吧内。
酒店在酒吧做了晚会,庆祝雾霾天的结束。没有中间过渡的雨天,雾霾说没有就没有了。实际上我更想去晒太阳而不是参加除雾庆祝会,我太久没有晒过太阳了。但我听说整个酒店的人都会去,那她可能会去。过了今晚大家不出意外都会离开,我意识到这是自己最后的机会,所以我现在在这里。这些前情都无关紧要。人头攒动,我应该尽快找到她。人太多了,女人太多了,化妆的女人也太多了。我不确定她化妆以后我还认不认得出来,最让人生气的是他妈的我忘记她的样子了。我做梦都梦见的一个女孩,而现在我忘了她的样子了。不过如果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应该可以认出来。还有,我可以靠身形分辨,还有黑色的长头发。但随即我发现这里的女人大都体态纤细高挑,这招不行。她们都不染头发的吗,怎么都是黑的?我叫赵润泽跟我一起找她,赵润泽说自己还记得她的样子,向我描述起来,我听了这些描述还是记不起来,这让我有些嫉妒,即使他在帮我时我也难掩嫉妒的心。动起来,绕着整个场地不知道走了多少圈,我已经满脸的汗了。
“这一共也就一百来个人,女人不比男人多,一共三四十个吧,没看见有长得像的。”他像汇报工作一样给我统计这些。我也在找,还遭了几个女孩的白眼。她们年轻漂亮,长得不一样,穿的也不一样,可我就觉得她们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没有像赵润泽那样统计过呆在房间里的人,但也一无所获,可能她确实没有来吧。
认识她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又害怕她像那些我抓不住的梦一样溜走。实际上就会是这样的,最后一面已经用完了。我是不是拿了骑自行车小男孩的剧本?如果是的话,就此杀青吧。那么我该留下一些话,又觉得实在没什么好说的。黑暗一样的静默。
又睡着了。睡梦中我再一次遇见了她,她的肚子瘪了下去,修身的裙子勾勒出了细细的腰线,我知道我早晚会在某一部小说中把她的形象钩沉出来,又跟所有的少女形象有别。那么,可以道个别吗,即使是在梦里?
退房时,我问前台有没有见到我的朋友。他们脸色没有一丝异样,沉静地告诉我,我订了一间标间,但从始至终只有我一个人住,走廊里也没有能吹头发的梳妆台。我来到这座城市的五天里,从来没有出过这间旅店。不过我也不用去看医生,吉格斯太的大雾有致幻的功用,不要紧,即使是当地的有敏感体质的人也会产生幻觉的。清洁阿姨已经进我的房间,告诉前台屋子里其中一张床上放着许多腐烂的苹果,霉菌在被子上一簇一簇地生长,要我支付清洗和更换床单被褥的费用。
从家里的床上醒来,我头痛欲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