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命运共同体”:全球海洋治理的价值向度
魏建勋
(外交学院 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北京 100037)
2019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集体会见出席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外方代表团团长时指出:“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529页。2021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指出,“积极发展蓝色伙伴关系,深度参与国际海洋治理机制和相关规则制定与实施,推动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海洋秩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13页。。至此,“海洋命运共同体”真正走入大众视野。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提出的全球海洋治理理念。该理念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对于推进全球海洋治理的进程意义重大。自该理念提出以来,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部分学者从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来源进行研究,认为其源于“天人合一”的思想,“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上合于道,下合于身’,‘知天、知人、成己、成物’,才能知行合一、知行并举,具有高道德标准”(3)吴士存:《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意蕴与中国使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4期;翟崑:《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需知行合一》,《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1期。;认为其源于马克思主义中的海洋思想和共同体思想、唯物史观(4)李国选:《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成逻辑》,《邓小平研究》,2020年第6期;陈娜、陈明富:《习近平关于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与时代意义》,《邓小平研究》,2019年第5期。、“自由人联合体”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思想(5)刘巍:《海洋命运共同体: 新时代全球海洋治理的中国方案》,《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4期。。另有部分学者从议题细分的角度对其具体内涵进行研究,认为海洋命运共同体包括海洋地区共同体(南海命运共同体、北极命运共同体等)、海洋功能共同体(海洋生物资源共同体、海洋环境保护共同体等)、海洋专业共同体(海洋政治共同体、海洋经济共同体等)(6)金永明:《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系》,《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海洋安全、利益、生态、和平与和谐共同体(7)姚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意涵:理念创新与制度构建》,《当代法学》,2019年第5期。;海洋安全、发展、责任共同体(8)卢静:《全球海洋治理与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还有部分学者从理念创新的角度研究“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其拓展了海洋政治的研究维度,革新了全球海洋治理理念和安全治理理念,为新型海洋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有助于构建新型海洋规则和新型海洋秩序(9)张景全:《“海洋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海洋政治研究》,《人民论坛》,2019年第S1期; 朱锋:《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到“海洋命运共同体”——推进全球海洋治理与合作的理念和路径》,《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4期;陈秀武:《“海洋命运共同体”:国际关系的新基点与构建新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1期;马金星:《全球海洋治理视域下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意涵及路径》,《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9期; 薛桂芳:《“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共识性话语到制度性安排——以BBNJ协定的磋商为契机》,《法学杂志》,2021年第9期;杨剑:《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知识、制度和行动》,《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1期;朱芹、高兰:《去霸权化:海洋命运共同体叙事下新型海权的时代趋势》,《东北亚论坛》,2021年第2期。。
现有研究有助于增进学界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了解和认识,但也存在需要补充完善之处。就“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来源而言,当前研究主要是从传统哲学的角度展开。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曾提出了诸多全球海洋治理的理念,这些理念也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来源。就“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而言,当前研究的探讨较为宏观,如果从价值尺度的视角入手,则有助于细化“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研究,进而探讨其对全球海洋治理的启示。
一、中国全球海洋治理理念的发展
全球海洋治理理念是指对全球海洋相关议题治理的认知,涉及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海洋安全、海洋合作等多个层面。由于全球海洋治理是国际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联合国是应对国际事务的最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因此,中国全球海洋治理理念可以追溯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之时。
从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开始,中国就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全球海洋治理理念。1972年3月,安致远代表在海底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应该成为解决海洋权问题上各国共同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各国领海和管辖权范围以外的海洋及海底资源,原则上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共有。”(10)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研室:《安致远代表在海底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言阐明我国政府关于海洋权问题的原则立场》,《海洋法资料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7页。1982年3月8日,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十一期会议上,梁于潘团长在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目前公约草案所确认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原则以及有关海底开发制度的基本结构,是不容许改变的。否则就会打破公约的宗旨和原则,打破整个公约草案的一揽子平衡。”(11)《梁于潘团长在全会上的发言》,《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文件集(1982.1—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79页。1982年3月19日,沈韦良在二委非正式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第七十六条实际上是一项有关大陆架定义和概念的一般性规定,它应包含一定的灵活性,以便适用于世界上各地具有不同情况和特点的大陆架。”(12)《沈韦良副团长在二委非正式会议上的发言》,《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文件集(1982.1—6)》,第84页。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指出可以采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应对钓鱼岛问题、南沙群岛问题:“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13)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7页。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认为“海洋安全不仅仅是指传统安全问题如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还包括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海洋经济安全、海洋文化安全、海洋科技安全和海洋生态安全”(14)徐萍:《新时代中国海洋维权理念与实践》,《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6期。。1996年11月,第24届世界海洋和平大会(Pacem in Maribus Conferences)在北京召开,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会见代表时的讲话中指出:“海洋是资源库;海洋是调节器;海洋是联结带。海洋的自然特性决定了海洋事业是一项国际性非常强的事业,决定了所有海洋问题都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才能解决。”(15)魏红涛:《谱写人类海洋和平的新篇章——第24届人类世界海洋和平大会侧记》,《海洋开发与管理》,1997年第1期。
2004年12月,胡锦涛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海洋是国际交往的大通道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宝库。”(16)胡锦涛:《我军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胡锦涛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59页。2009年4月,胡锦涛会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60周年庆典活动的29国海军代表团团长时指出:“推动建设和谐海洋,是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和共同追求。加强各国海军之间的交流,开展国际海上安全合作,对建设和谐海洋具有重要意义。”(17)王建民、曹国强、曹智:《胡锦涛会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60周年庆典活动的29国海军代表团团长》,《人民日报》,2009年4月24日,第1版。2009年7月,胡锦涛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正确把握维权和维稳之间的关系,稳妥处理我国同周边国家海洋权益、领土、跨界河流争端。”(18)胡锦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高对外工作能力水平》,《胡锦涛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0页。2010年9月,第33届世界海洋和平大会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桑国卫在开幕式上再次提出了“和谐海洋”(19)《第33届世界海洋和平大会开幕式》(2021年9月20日),http://www.scio.gov.cn/xwfbh/qyxwfbh/Document/755085/755085.htm。的理念主张,各国应加强在全球海洋议题中的合作,努力营造和谐的海洋秩序。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习近平:《共同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习近平谈“一带一路”》,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1页。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增进地区各国乃至全球各国在海洋事务中的合作。2015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指出:“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21)《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4页。2017年6月,中国政府发布的《“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指出:“建立紧密的蓝色伙伴关系是推动海上合作的有效渠道。加强战略对接与对话磋商,深化合作共识,增进政治互信,建立双多边合作机制,共同参与海洋治理,为深化海上合作提供制度性保障。”(22)《“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2021年9月23日),http://www.gov.cn/xinwen/2017-11/17/5240325/files/13f35a0e00a845a2b8c5655eb0e95df5.pdf。2019年4月,习近平主席正式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
综上所述,“共享海洋资源”“灵活应对海洋问题”“增进海洋合作”“构建稳定海洋秩序”等都是中国提出的全球海洋治理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理念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础。“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多维度的价值内涵,对于构建稳定有序的海洋环境,实现海洋的善治意义重大。
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多维度价值内涵
“价值尺度”是经济学中常用的术语,指以货币为载体去衡量物品的价值。从政治学研究的视角出发,可把“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视为衡量全球海洋治理成效的载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规范价值、行为价值、系统价值、动力价值,具体体现为化解当前全球海洋治理中的二元利益悖论、凝聚全球海洋治理的合力、推进海洋综合治理、推动海洋的可持续性发展。
(一)规范价值:化解二元利益悖论
规范是指导事物运行和发展的行为标准。依性质划分,规范分为调控性规范、评价性规范、说明性规范(23)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8,vol.52,no.4.。调控性规范即规定行动的可为与不可为;评价性规范即按照既定的标准去评价事务的功能、性质、特点等;说明性规范即事务实操的标准。进化和路径依赖是世界政治中常见的规范运动形式(24)Amitav Acharya,How Ideas Spread: Whose Norms Matter? 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2004,vol.58,no.2.。因路径依赖的存在,环境的变化并不必然导致规范的变化。规范进化是国际社会长期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规范能否进化取决于原有规范的合理性和新规范的生长力及两者间的兼容或冲突(25)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当前的全球海洋治理中存在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二元悖论(26)卢静:《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即全球利益的实现要以牺牲相关国家利益为代价,这影响治理规范的建构和进化。“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社会中各类行为体应对全球海洋问题提供了新工具、新方法、新思路,化解了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悖论,促进海洋治理规范的进化。
部分国家过分关注自身国家利益,无法在全球海洋治理的具体方案上达成协议,即便是达成了协议,也难以推进协议的执行,这样就导致海洋治理的低效能,全球利益的实现大打折扣。以当前的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为例,“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是各主权国家均存在独立的权力体系,因而治理机制和规则的设计往往受到强权国家的力量影响”(27)金永波:《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区域化演进与对策》,《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5期。。“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一种超越了对国家狭隘海洋利益的关切,体现了在海洋事务治理中对全球海洋利益的关切,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与对整个人类关切的情怀。”(28)孙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及其实现途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6月13日,第5版。
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出发,就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两者的关系而言,两者是互相促进的。国家海洋利益的实现有助于推动全球海洋利益的实现,全球海洋利益的实现能为国家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海洋环境,从而也能推动国家海洋利益的实现。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通过“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全球利益逐渐得以实现,而全球利益关乎国际社会中的每一成员国、每一成员国的居民,因此,地区、国家、次国家甚至社区层面的利益需求都将逐渐得到满足。“海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秉持全人类共同发展原则,不以私利为先。”(29)张卫彬、朱永倩:《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构》,《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5期。
(二)行为价值:凝聚全球海洋治理的合力
行为是指主体对客体的反应。受制于知识背景(在实践中形成、显现、反过来引导实践的知识)(30)秦亚青:《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国际观察》,2020年第2期。和成长经验的不同,不同主体的认知可能有所差异,其对同一客体的反应可能不一。行为受到结果性逻辑(利益决定行动)、适当性逻辑(规范塑造行动)、实践性逻辑(实践引导行动)的影响(31)秦亚青:《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全球海洋治理行为是治理主体对治理客体的反应,即制定一套公平、高效的海洋使用和资源分配的海洋规则,提供解决争端和享受海洋利益的方法(32)Robert L. Friedheim, Ocean Governance at the Millennium: Where We Have Been—Where We Should Go,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1999,vol.42, no.9.。“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行为价值体现为:推进各类治理主体的认知趋同,使各类主体对海洋治理客体做出趋同反应,从而凝聚全球海洋治理的合力。
当前的全球海洋治理存在明显的集体行动力不足的问题,目前就有关海洋治理的基本宣言和程序达成全球协议的难度越来越大(33)Lori Ridgeway, Global Level Institutions and Processes: Assessment of Critical Roles, Foundations of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Integrated Marine Governance, in Governance of Marine Fisheries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Interaction and Coevolution,Serge M. Garcia, Jake Rice and Anthony Charles (eds.), Hoboken: Wiley-Blackwell, 2014, p.161.。这具体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国家行动力不足,主要体现为部分国家行为体行动迟缓,甚至阻碍海洋治理进程,且国家间的合作不足。二是非国家行为体行动力不足,这主要是由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对非国家行为体重视不足,非国家行为体的能力无法得以充分发挥。三是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间的合作不足,各类行为体就某一特定海洋议题难以统一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物种、治理海洋生态、预防海洋灾害,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是人类的共同责任,需要海洋利益相关方共同应对海洋利益分配与海洋安全的复杂局面。”(34)刘长明、周明珠:《海洋命运共同体何以可能——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的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各类行为体与海洋命运与共,各类行为体所拥有的治理资源是维护海洋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间应加大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合作,促进各类互补性资源的整合,形成全球海洋治理的合力。国家行为体应积极承担全球海洋治理的责任,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进程;应充分激发非国家行为体的潜能,充分给予其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合法性,使其在全球海洋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系统价值:推进海洋综合治理
系统是指各类要素有机结合在一起。组成系统的各类要素有特性,也有共性。特性与共性的动态平衡形成稳定的结构,这是系统存在的基础。各类要素互相作用和影响,在系统中形成不同的节点。节点在种类、性质、数量、功能、规模等层面有差异(35)包广将:《多节点结构: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与“轴辐体系”的困境》,《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2期。。节点互相连接和作用,形成了系统结构。系统时常表现出非线性关系,其结果不是各类要素及相互间关系的简单叠加(36)Robert Jervis,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p.6.。全球海洋治理系统包括主体、客体、工具等各类要素,也包括各类要素互相作用形成的多类别多层级的治理机制。“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系统价值体现为:综合考虑参与海洋治理的各类要素及其交互性影响,推进海洋综合治理。
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全球海洋治理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客体,这包括海洋争端、海洋划界、海洋环境保护、海洋资源开发、极地海洋治理、蓝碳资源开发等。从目前的实践看,全球海洋治理客体,尤其是新兴海洋客体缺乏相应的治理机制。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缺乏有效管理海洋、监督和执行管理措施的机制(37)Stelios Katsanevakis, Vanessa Stelzenmüller, etc, Ecosystem-Based Marine Spatial Management: Review of Concepts, Policies, Tools, and Critical Issues,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2011,vol.54, no.11.。由于海洋本身的流动性和交互性,针对单一海洋客体的治理方案取得的成果有限,且存在单一客体治理成果以牺牲其他客体治理成效为代价的现象,“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以整体思维解决日益复杂的全球性海洋问题”(38)马金星:《全球海洋治理视域下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意涵及路径》,《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9期。。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进海洋综合治理。通过加强专门机制、协调机制和反馈机制的建设,海洋治理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得以在整个系统内流通。根据反馈机制的结果与治理客体的变化,不断调整治理方案,从而提升海洋治理的整体效能。“‘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参与,构建海洋领域的规则与秩序,在全球海洋治理领域提供系统的公共产品,并进一步推动世界各国在平等参与条件下实现对世界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海上通道安全和海上防灾减灾等诸多议题下的全球海洋治理机制与规则的进步和升级。”(39)朱锋:《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到“海洋命运共同体”——推进全球海洋治理与合作的理念和路径》,《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4期。
(四)动力价值:推动海洋可持续性发展
动力是指促进事务发展的积极要素。事务发展是一个持续性的进程,如果没有动力存在,事务将不复存在。动力分为主体层面的动力和体系层面的动力。主体层面的动力源于参与事物进程的各类行为体,体系层面的动力源于行为体建构形成的系统,后者是不能还原到任何具体的个体行为体的(40)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全球海洋治理的动力源于各类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及当下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导人类更加深入地思考自身同海洋的共生关系,促进人类超越传统的民族及其国家一体化形式,而达到更高级的一体化形式(41)庞中英:《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欧洲》,1999年第2期。,从而提升人类参与海洋治理的积极性,建构出更加合理和科学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并使之持续性地提供体系动力,从而推动海洋可持续性发展。
海洋生态环境退化、海洋生物多样性缺失、海水酸化、海洋垃圾增多和化学物质泄漏等各类海洋问题对海洋的可持续性发展造成了严峻挑战,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影响。“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把人类的命运同海洋的未来联系起来,未来海洋环境的好坏直接关乎人类的兴衰,这样就为人类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永续的动力。
“海洋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理应由全体人类共同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和保证资源可持续利用,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是当前的一项全球要务”(42)吴蔚:《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法治路径》,《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2期。,这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体现。该理念“旨在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唤醒各国良知,促进彼此合作,通过海洋法治,逐渐建立公平、公正、合理、普惠的海洋新秩序,推动人类海洋事业的共同发展”(43)冯梁:《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理论价值与实践行动》,《学海》,2020年第5期。。人类意识的觉醒有助于提升自身保护海洋环境的积极性,推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全球海洋治理进程中去;有助于在国际社会建构起人海和谐共生的文化,聚合全球海洋治理的各类要素;有助于推动海洋治理机制的完善创新,使之适应海洋治理客体发展的需要;有助于系统有效地开展海洋治理活动,提升全球海洋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推动海洋的可持续性发展。
三、“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化解当前全球海洋治理困境的启示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多维度的价值,对于化解当前全球海洋治理的主体困境、机制困境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应当从治理主体、机制、理念、行动等层面着手,提升全球海洋治理的效能。
(一)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面临的主要困境
国际社会达成了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石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该体系在各类海洋议题的应对中发挥着一定作用。但当前的全球海洋治理仍面临不少困境,主要表现在部分治理主体发挥的效能有限、治理机制难以回应治理客体的需求两个层面。
1.部分治理主体发挥的效能有限
全球海洋治理的主体可分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受制于历史因素的制约,发展中国家、非国家行为体难以充分发挥自身效能。克里斯汀·韦斯(Kristen Weiss)等指出,“在海洋治理体系中,部分行为体拥有的知识量和取得的决策权是不成正比的”(44)Kristen Weiss, Mark Hamann, etc.,Knowledge Exchange and Policy Influence in a Marine Resource Governance Network,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2012,vol.22,no.1.。
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者而言,发展中国家发挥的效能有限。发达国家凭借其现代化先发优势,掌控了国际机制和规则的制定权。在全球海洋治理领域,发达国家凭借其拥有的资金、技术等优势,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起步较早,且在治理机构的设置、治理议题的选定、治理标准的制定等层面发挥主导作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机制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则较为有限。发达国家通过建立全球海洋治理标准并削弱发展中国家权威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权力主张(45)Lisa M. Campbell, Noella J. Gray, Global Oceans Governance: New and Emerging Issues,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2016,vol.41.,“发达国家和大国集团在全球海洋事务的治理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和议程设置权,使得国际海洋秩序总是为强国所操控”(46)王琪、崔野:《将全球治理引入海洋领域——论全球海洋治理的基本问题与我国的应对策略》,《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6期。。
就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而言,非国家行为体发挥的效能有限。当前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是以主权国家为主导建立起来的,主权国家主导着全球海洋治理合作的谈判进程,达成了诸多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核心的海洋治理合作文件,建立了国际海事组织、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等诸多海洋治理机构。因此,当下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主要是国家行为体意志的体现。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组织、多国公司、跨国社会网络等非国家行为体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力(47)秦亚青:《全球治理趋向扁平》,《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5期。。非国家行为体凭借其拥有的资金、技术、行动力等优势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但在全球海洋治理领域,非国家行为体发挥作用的基础仍依赖于国际体系主要大国的支持(48)吴士存:《全球海洋治理的未来及中国的选择》,《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5期。。民间社会行为体在海洋治理价值观和环境的塑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海洋治理的决策中作用有限(49)Elizabeth A. Kirk, Marine Governance, Adaptation, and Legitimacy,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2011,vol.22,no.1.,国家层面的决策不容易纳入沿海利益相关者(50)Louisa S. Evans, Ecological Knowledge Interactions in Marine Governance in Kenya,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2010,vol.53, no.4.,科学家与决策者在知识交流领域存在障碍(51)C. Cvitanovic, A.J. Hobday, etc, Improving Knowledge Exchange Among Scientists and Decision- Makers to Facilitate the Adaptive Governance of Marine Resources: A Review of Knowledge and Research Needs,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2015,vol.112.。
2.治理机制难以回应治理客体的需求
随着海洋开发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延伸,全球海洋治理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客体。海洋生态环境、海洋经济、海上航行等传统的海洋议题仍然在当前的海洋政治版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且随着国际政治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与此同时,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蓝碳、海洋新疆域等新兴海洋议题也变得越来越凸显。传统海洋问题的新发展与新兴海洋议题的出现对全球海洋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当下的全球海洋治理机制难以回应上述客体的需求。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海洋治理机制建设不够精细;海洋治理机制间缺乏整合。
从当前全球海洋治理的机制发展来看,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共同开发与合作、海洋污染防控等多领域都建立起内容丰富的治理规则和机制,这些治理规制存在笼统、模糊等问题。“当代全球海洋治理体系诸多规则的主要载体是造法性条约,相关规定一般比较原则、笼统,容易导致较大争议。”(52)杨泽伟:《新时代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变革:理念与路径》,《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大多数的国际规制只是在宏观上规定了一些治理的原则、方法和程序,缺少具体而全面的条款。”(53)王琪、崔野:《将全球治理引入海洋领域——论全球海洋治理的基本问题与我国的应对策略》,《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6期。以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为例,生物多样性的治理存在一系列法律、体制和监管差距,缺乏总体治理原则,缺乏建立或管理海洋保护区的全球框架(54)Robert Blasiak, Carole Durussel, etc.,The role of NGOs in Negotiating the Use of Biodiversity in Marine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Marine Policy,2017,vol.81.。与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有关的问题没有系统地纳入部门协议,有关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协议几乎没有监管权力(55)Jeff Ardron, Elisabeth Druel, etc,Advancing Governance of the High Seas,IASS Policy Brief 1,2013,p.5.。再以渔业机制为例,目前的渔业治理制度,如个人可转让配额不足以防止破坏性捕鱼方法的使用(56)Stefan Gelcich, Francisca Reyes-Mendy,Early Assessments of Marine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s: Insight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Implementing New Fisheries Management Regimes,Ecology and Society,2019,vol.24, no.2.,“《挂旗协定》代表性不足,《鱼类种群协定》的权利义务规定不明确,《行为规则》、IPOA-IUU的拘束力不足,目前海洋渔业资源养护的治理体系仍乏强有力的执行机制”(57)魏德红:《海洋渔业资源养护国际治理体系问题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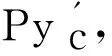
(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启示
为提升全球海洋治理的效能,应调动各类治理主体的积极性,系统治理各类全球性海洋议题,推进治理理念、机制、行动的创新,激活和充分发挥各类治理要素的力量。
1.调动各类治理主体的积极性
调动各类主体的积极性应当从两个层面入手。一是国家行为体层面,推进主权国家全球海洋治理中话语权趋于平等。二是非国家行为体层面,鼓励各类学术团体、智库、基金会、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充分参与到全球海洋治理的进程中。
推进主权国家全球海洋治理中话语权趋于平等。从当前全球海洋治理的实践看,发展中国家发挥的作用有限,这体现在议题设置、规章设定、机制建设等诸多层面。冷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中有自身独到的经验,同时不断积累全球治理的知识和技术。通过推进话语权平等建设,当前存在的话语霸权、议程控制权的现状得到改善,各国都可以自主地为全球海洋治理贡献自己的智慧,把各自拥有的差异性优势运用于全球海洋治理的进程中,调动自身一切积极要素促进全球海洋治理成果的达成,从而为全人类的生存营造良好的海洋环境。
鼓励非国家行为体充分参与到全球海洋治理进程中。首先,从非国家行为体自身的特点而言,多类非国家行为体有先进的知识、成熟的技术、强大的动员力,可从治理议程的设定、治理活动的实践、治理成效的评估等层面,提升全球海洋治理的科学化水平与效率。其次,非国家行为体易结成全球海洋治理网络,这恰恰是全球海洋问题应对所需要的。全球海洋问题波及的范围广,会产生诸多层面的影响,网络化的合作是全面有效应对全球海洋问题的工具。针对特定海洋问题,不同国家和地区会出现不同的非国家行为体,而这些非国家行为体有着共同的目标——推动特定全球海洋问题的解决。在合作与实践的过程中,非国家行为体间建立了网络化的合作机制,通过网络化的合作,凝聚治理的共识,发挥治理的合力,提升治理的效能。
2.系统治理各类全球性海洋议题
全球海洋治理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议题的选定、机制的建设、成效的评估都是全球海洋治理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系统工程推进过程中,海洋知识、海洋技术、资金、人力资源等各类要素,各种有关海洋治理的手段和方法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从系统性的思维出发,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海洋污染治理、海上科学研究、海洋资源开发、南北极治理等各类海洋问题都应当成为全球海洋治理的议题。同时,要根据不同海洋问题的特点制定全球、地区、国家、地方政府等各层级的海洋治理机制,确保各类行为体通过各层级的海洋治理机制做到协调统一。要对各层级的治理成效进行有效性评估,总结治理成果和经验,同时针对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将某一治理进程中的有益做法推广到整个全球海洋治理的系统中。
从激活人力和物力要素的视角出发,要充分发挥国家和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作用,充分运用各类行为体所拥有的资源。考虑到当前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中发挥的作用有限,要为非国家行为体设置更多的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平台和机制,使非国家行为体的资金、技术、知识等要素得以运用和发挥。同时,也要增加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沟通渠道。受制于低阶和高阶等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国家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中占有的决策权的比重较大,而非国家行为体对全球海洋治理体系产生的影响较小。通过增进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间的交流,使得国家对非国家行为体拥有的先进治理理念和经验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促进国家在决策时把非国家行为体的意志考虑在内,从而弥补结构性因素对非国家行为体能动性的制约,增强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影响力。
从手段和方法的视角出发,全球海洋治理的各个环节都应当充分利用现有的手段和方法,提升治理的效率和科学化水平。海洋治理议题的选择要建立在预评估的基础之上,即要通过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对当前的全球海洋问题的发展现状进行评估,从而确定海洋问题治理的优先等级排序,根据不同海洋问题的特点,提出相应的治理工具。要把前沿的海洋治理方法和手段运用于海洋治理机制的建设中,在提升治理机制专业化水平的同时,又要做到机制间的相互协调,同时确保机制的切实可行性,为机制的运营提供配套工具。在海洋治理成效的评估层面,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将有助于全面系统地评估国家、地区、全球等各个层面的全球海洋治理效果,并在此基础之上及时改进海洋治理系统中的不足之处,同时将某一议题上的有益做法推广到整个系统中。
3.推进治理理念、机制、行动的创新
就治理理念而言,全球海洋治理理念需更具创新性和包容性。未来的全球海洋治理理念需充分考虑海洋与陆地的关系、海洋与人类的关系、海洋各领域的内部关系,充分考虑单位层次和体系层次的各类因素,以整体性和尊重个性的思维推动自身创新。另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一切有助于解决全球海洋问题、推动海洋发展的理念都应当被纳入全球海洋治理理念的范畴。
就机制建设而言,首先,要针对传统海洋议题的新特点更新现有治理机制,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运用到传统海洋议题的应对中去。其次,要针对新兴海洋议题设立新的治理机制。就新兴海洋议题而言,由于规则制定相较于现实发展的滞后性,当前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中不存在专门应对新兴海洋议题的公约、规章等法律性文件,也不存在推进新兴议题治理的实施机制,因此,为了应对新兴海洋议题,要根据新兴议题的特点制定相应的规约,设立多层级的实践机制和反馈机制。考虑到针对新兴议题治理的先前经验不足的问题,要设立针对新兴议题治理成效的动态评估机制,以及时有效地调整治理路径和方法,提升针对新兴议题的治理效能。再次,要注重各类治理机制间的协调网络建设。通过加大协调网络的建设,提升治理资源的利用效率,有助于把有效的治理方案在治理系统中推展开来,提升全球海洋治理的整体效能。
就治理行动层面而言,国际社会、地区、国家、地方政府、社区等各个层级的行为体都应当积极参与到全球海洋治理的进程中。国际社会应当加大类似于“深海管理倡议”“地区海项目”等全球性倡议和行动的推出力度,增进地球居民对海洋问题的认知,促进国家对全球利益的再认知。地区层面,域内各国有相似的海洋文化背景,有着共同的海洋利益诉求,应当联合起来公共应对海洋问题,促进地区海洋环境和全球海洋环境的稳定。国家层面,政府应当充分认识到海洋对国家生存、国民的生产和生活的重大意义,应当充分调动资源有效应对海洋问题。地方政府层面,各地方政府应当根据各自发展的特点,出台有关海洋发展和保护的地方性政策,规范海事行为,让海洋为当地造福。社区层面,居民应当在平时的生产生活中注重对海洋的合理利用,注意保护海洋的生态环境。
四、结 语
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实践的进程中,中国曾提出了“共享海洋资源”“灵活应对海洋问题”“增进海洋合作”“构建稳定海洋秩序”等理念,这些理念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础。“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从价值尺度的视角出发,其有规范价值,能够化解全球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悖论;其有行动价值,能够凝聚全球海洋治理合力,呼吁各类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到全球海洋治理中去;其有系统价值,推进海洋综合治理,应对各类海洋问题;其有动力价值,推动海洋可持续性发展,使海洋长期造福于人类。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于化解当前全球海洋治理的困境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未来的全球海洋治理应调动各类主体的积极性;系统治理各类全球性海洋议题;推进治理理念、机制、行动的创新。通过上述做法,充分发挥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作用,整合全球海洋治理的资源,制定符合各治理客体的特点的海洋治理机制,并推动海洋治理机制间的整合,使先进的经验和做法适用于各类海洋议题中,提升海洋治理的整体性和连贯性,提升全球海洋治理的效能,从而为国家间的相处、各国人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国际社会的安全平稳运行营造良好的海洋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如何高效科学地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使其在全球海洋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需更进一步的探讨。其一,增进认知。作为一种新理念,“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知和国际共识不足,要增进国际社会对该理念的认知,促进各类行为体就该理念达成共识。其二,细化理念。“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个宏观的命题,而全球海洋治理包括海洋环境、海洋经济、蓝碳、生物多样性等多种议题。应根据各类议题的特点细化“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其三,优化责任配置。在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实践的进程中,各类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面临着责任分担的问题,要根据各类治理主体的特点,配以适当的责任,优化责任配置结构,提升各类治理主体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