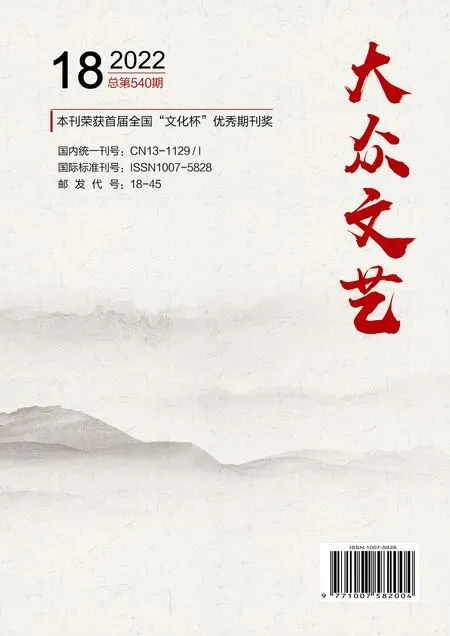叶志诜与陈介祺的金石鉴藏事略
闻 博
(汉江师范学院,湖北十堰 442000)
一、道光间为金石之交
叶志诜(1779-1863),字仲寅,号东卿,晚自号遂翁,湖北汉阳人,斋号“平安馆”,“叶开泰”第六代传人。嘉庆九年入翰林,后官至国子监典簿、兵部武选司郎中。叶志诜早年活动于京师的金石收藏圈。道光二十八年(1842)夏,叶志诜致仕就养于粤东署节,其金石碑帖摹刻于与书籍刊行,大多在此时期。陈介祺(1813—1884),清代晚期重要金石学家和收藏家,字寿卿,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齐东匋父,最著名的是他集毕生所藏编成的《十钟山房印举》,为后世篆刻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陈介祺父陈官俊与叶志诜同朝为官,其岳父与叶志诜亦是金石之交。叶志诜年长陈介祺34岁,陈介祺常以“世兄”或“世尊兄”来称呼叶志诜。二人早期的交往,主要是在“文字之交”方面,陈介祺在《簠斋玉印合编序》中回忆说:“而余在昔文字之交,如仪征相国阮文达、东武李方赤外舅方伯、刘燕庭方伯、汉阳叶东卿笃部……俯仰人间,感叹不能自已,因笔以志之。”此时二人皆活动于京师时期。

叶志诜在印章方面也有收藏。清代学者严可均在《铁桥漫稿》中《洗桐楼集古印章序》 回忆自己曾打算与叶志诜编印谱而未遂一事,“余好收汉章,随聚随散。而孙伯渊氏得百余纽、阮芸薹得两百余纽、叶东卿氏得七八百纽、歙汪氏吴桥某氏各得二千余纽,余与叶东卿欲汇诸家所藏为印集一书因循未卒业。”序言作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可见此前叶志诜藏汉印章的数量在这之前就达到了“七八百余纽”,足见其规模之大。
叶志诜与陈介祺在京师的金石交流过程中,印章是二人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陈介祺曾至手札给叶志诜:“秦印私印九十方,斗检封一先缴上(印内六方待考,余具精妙绝伦,昨晨祥阅一过),匆匆惜不能留一稿本,异日大发尊藏,当效编次之职。官印七方疑存,乞将官印检全(勿疑精者)并付,欲印寄叔均,叙入木夫先生印考之后。铜鼓书堂谱乞留意为幸。谨颂东卿世尊兄太老先生寿祉。祺顿首,七月八日。”可见,陈介祺通过叶志诜观摩到一些秦汉印章,并且因为不能留印存印稿而惋惜过,异日若“尊藏”,簠斋愿意为叶志诜这位叔父辈的金石好友“效编次之职”。叶志诜作为陈介祺的“世兄”,曾与一些当时金石名流一起在经济上支持陈介祺编订印谱,陈介祺日后在《十钟山房印举》(癸未本)自序中忆到:“余自应试至莱,秋试至歷……辛亥读京礼第。东卿、子苾、刘燕庭、吕尧仙、朱筱讴、先怡堂十二叔父同醵资陈粟园畯,成《簠斋印集》十部”。簠斋十九岁开始收集古印,道光末作《簠斋印集》。咸丰元年(1851)六月末陈粟园钤拓事毕。咸丰三年立秋前三日陈介祺作《簠斋印集》自序,此时叶志诜、吴世芬、刘喜海等十二叔父各出十金,共六十金,为购纸镌版,制作印泥之用。这本陈介祺最初制作的印集共钤十部,叶志诜等叔父每人分得一部。簠斋自留二部,其一光绪间赠吴大澂。叶志诜等十二叔父醵资陈介祺所制的《簠斋印集》,可以说是陈介祺最早制作的印谱,簠斋印学思想初见于此。原制十部,百四十年后,尚存其五,亦云幸矣。
陈介祺是叶志诜的晚辈,他通过叶志诜观获到许多金石古物,这影响到了簠斋初期的金石实践活动和思想的形成。而叶志诜作为叔父辈醵资簠斋作印集,一方面是对陈介祺这位晚辈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弥补了他最初“欲汇诸家所藏为印集”的“未卒业”。二人同在京师居住时,是金石文字之交。所以,簠斋后人陈继揆先生说“道光间簠斋与东卿为至好”。
三、陈介祺对叶志诜所藏金石的辨伪
叶志诜和陈介祺都是清代晚期的金石收藏家,而二人金石鉴藏活动有所区别:叶氏多集中在对金石的传播,陈氏集中在考释、辩伪。《簠斋研究》一书中说:“陈氏之传拓、弆藏、辩伪都应作为学术的重要内容,而这也正是其最有影响之处,较其在考释等方面的成绩而言对金石学的贡献更大。”叶志诜作为“叶开泰”的掌门人,财力、物力造就其收藏之丰富,但其所藏最终通过簠斋这位晚辈来辩伪。
清代晚期,金石学家对青铜器的目光都在先秦的器物,尤其是带有文字之器物。所以古董商为谋取利润,制造伪器或在真器上增刻伪铭。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月,叶志诜购得周朝《遂启諆鼎》。事后,陈介祺就看出了这个鼎上的铭文为伪刻,据他在《东武刘氏款识册目》中回忆当时的场景:“東卿言余以爲,余實無是言”。叶氏不信,并编《遂鼎圖題款识》一册,考释数百字。一起作诗歌的有当时金石名流王筠、张廷济、许瀚等四十多人。
鲍康、王懿荣曾题跋《遂启諆鼎》全形拓,鲍康跋文:“是鼎乃道光末年秦中出土,余目击时尚折一足未补完,中有文二行曰:‘遂启諆作广叔宝尊彝’,广字泐遂改作庙字,苏氏得之,属凤眼张者,杂取虢盘诸文前后添刻一百二十余字,以三百金售之叶文东卿,然刘丈燕庭与余均有当日原拓,稍辨其赝,东卿不怿,爰舁送金山寺。此尚是平安馆昔年旧拓,虽出烬馀却完好,试取绎之文义,神致不逮诸巨器远甚,识者谅自有定评也。子年记。”从这段跋文可以得知,《周遂启諆鼎》原来断了一足后经补上,原有铭文两行九字:“遂启諆作广叔宝尊彝”,“广”字因泐而下面加入“朝”而改作“庙”字。该鼎被一苏氏人所得,之后又传到了“凤眼张”的手上并被其加刻西周《虢季子白盘》铭文的一百二十多字。叶志诜通过看到鲍康和刘燕庭的原拓九字拓片,才相信陈介祺当时认定该鼎铭文为出土后增刻。
陈介祺以古传志,提出“传古首在别伪”,他把自己的体会和观点不断地函告金石之友们。叶氏虽嗜金石,而不慎重于学,以至于后来藏器赝品甚多,却自以为是,对此簠斋多有微辞。陈介祺常用以叶志诜对文字考释不足来劝诫金石友,至友人尺牍中还以叶志诜的事情提防古董商的造伪售欺,“昔苏六以古归叶几无一真,云有真则伪自败,可谓有诡识推之用人何莫不肰,惟不反求斯得售欺岂存彼乎。”这里的“苏六”即道光年间卖半真半假的《周遂啓諆鼎》的古董商。而同治年间簠斋从昔日出售增伪刻铭文的苏氏古董商手上花千金购得铭文之多的毛公鼎,足以见陈氏辩伪的能力和信心。
时人对叶志诜金石鉴藏活动的评价有三类。第一类为过于褒,如:张廷济的“汉阳嗜古古成癖,集录直过欧阳剧”、赵之谦的“嘉道间海内所屈指”等;第二类为过于贬,如:吴大澂的“平安馆鉴赏,近时最不可恃”等;第三类较为适中,如:陈介祺认为“东卿收藏前人旧存者俱可观,晚年既收伪刻又毁于羊城,平安馆劫遗至今亦良可慨”。陈介祺对平安馆金石鉴藏活动的评价最为客观。陈氏重金石器物上古文字的考释“以字订之”并且“字大者为佳”,叶氏重金石器物“与其韫而藏之”不如“使之灿着焉”以“不致湮没而不彰也”。也因此陈氏的辩伪能力是当时金石家中的佼佼者,叶氏是“道咸时期北京金石书画群体中的中坚”。陈介祺作为叶志诜的晚辈,早年通过叶志诜等人观摩到金石器物,影响到其早期金石思想的形成。但叶志诜不慎重于学又“嗜古成癖”,而收到了伪物。所以,陈介祺给出了“旧存者俱可”但“晚年收伪刻”,总之“劫遗至今亦良可慨”的客观评价。
四、陈介祺保存平安馆余烬印章
叶志诜六十岁致仕,道光二十八年(1848)夏来到粤东,晚年就养于粤东署节,陈介祺咸丰四年(1854)四十二岁时辞官归里,归里前期深居简出,青灯黄卷,五十九岁同治十年(1871)复出广交金石友,次年至其卒年(1884)是簠斋金石活动最鼎盛的时期,《十钟山房印举》《簠斋吉金录》《封泥考略》等诸多著作皆出于此一时期。
咸丰八年(1858)鸦片战争败后,叶志诜仓惶逃回汉阳,平安馆所藏金石器物大多毁于火中,余烬所存器物被人抢空,或流落琉璃厂。鲍氏在《观古阁从稿中》记载,昔日叶志诜藏翁方纲摹《化度寺碑铭》“惜出自烬余,已非完本,而精光不掩、古趣弥增”陈寅生将其“拾残补缀重装,以还旧观”。《丛稿》中还提道了叶志诜在京师虎桥坊居住时,尚留“五楹藏古器书画几满,封鐍极严”由于“前一日忽不戒于火,率付灰烬”,而“惜烧损仅泉文尚可辨”,泉落于市上,被陈寅生购得。从鲍康和陈寅生对余烬所存故物的购买和整理中可以看出,平安馆无论在京师时期还是粤东时期,其金石拓片收藏规模之大,数量之多。而叶志诜平安馆所收藏印章,后来通过陈介祺而得以幸存。
陈继揆在《万印楼印话》中一书说,簠斋原以为平安馆古器物尽毁于火,簠斋原以为无所遗,岂知故铜印部分为人抢出,叶志诜和潘仕成共2700方印在高要何昆玉的手上。同治十一年(1872)秋,陈介祺致信同乡广东巡抚张兆栋,嘱其代为协商收购何昆玉藏印。故何昆玉携其所藏古玺印来潍坊,归于簠斋。簠斋为何昆玉设榻,留于簠斋,嘱其与次儿陈厚滋始钤拓《十钟山房印举》。癸未本《十钟山房印举》陈敬第作序:“同治壬申,高要何昆玉伯瑜携其吉金斋所藏,又以潘氏看篆楼、叶氏平安馆粤署烬余各印,约二千七百余事来归簠斋,即主其家……”。簠斋在清点初审时,分别以木籤注明“潘”“叶”。而陈介祺在尺牍里面说何氏所携印章“千余纽”,如同治十二年致鲍康尺牍中说:“……秦汉旧印两千,归里后所得又几一千,今又得潘氏看篆楼、东翁署节烬余刻,甫作校名曰‘十钟山房印举’……”陆明君先生认为,或所携潍者簠斋有所选择,未尽归簠斋。
根据《簠斋尺牍》中陈介祺与友人来往的尺牍来看,陈氏所得平安馆余烬印章进行了辩伪和考释的整理。如致鲍康尺牍“近收叶氏物拓,印惟‘强弩都尉章’可疑,石範者殊佳,千斤鉤亦可,古币似古之锯,非币也,鉤印廉生疑之甚是”“记新得叶氏西夏印,不可识而甚古厚”。簠斋还用平安馆旧藏印来考释其他印章,如致王懿荣尺牍中“汉‘巨张千万张’方印一乞,存此种前人多不以为汉印,今证,以叶东卿旧藏‘大司徒’‘大司成’‘公孙匋’等印于公孙印纽之上见有敲击痕,始之此皆施于金银鉼錠者,如今之元宝上字出火尚輭时印之也坿。” 从《簠斋尺牍》中,还可以得知除印章之外的“陈曼簠”“龙节余符”“吴方尊”等平安馆旧藏归簠斋所有,并被陈氏考释与辩伪。此外,平安馆余烬所出并非全部归簠斋,同治十二年八月陈介祺尺致吴云尺牍中提道“叶东翁今有六面朱文秦印今在羊城”,并问:“叶氏印曾得的全帙否?尚有余烬数百在羊城也。吾兄见闻广博,望一一告我,幸甚!幸甚!”
此外,还有《集古印隽》这部印集中,也收录了潘氏看篆楼、叶氏平安馆旧藏印。簠斋集其旧藏印章、潘与叶二家旧藏印章后,又向其金石友惠借所藏古玺汉印,钤拓成《十钟山房印举》这部著作。簠斋在制作《十钟山房印举》过程中的一得力助手王石经,“兹以《印举》所得,与海内大雅吴子苾、李方赤、叶东卿、刘燕庭,今鲍子年、李竹朋、潘伯寅、吴退楼所藏,选为此册”,编《集古印隽》一部。由陈介祺为其作序。
叶志诜为湖广地域金石收藏的第一人,也是金石向两湖传播的先驱,但平生所藏都毁于兵燹。而许多余烬所出旧藏金石器物,尤其是印章,通过陈介祺而得以幸存。陈介祺与何昆玉、王石经等得力助手通过大力搜集,一方面是让叶氏旧藏器物得以幸存。另一方面,簠斋的整理、考释、辩伪等活动,也是对平安馆金石文化的幸存与传播,实现了叶志诜“与其韫而藏之,孰若使之灿着焉?”而“不致散脱而浸失也”“以垂久远”的金石收藏的情怀。
结语
叶志诜与陈介祺同为清代晚期的金石收藏家,整个清代晚期的金石活动都有二人的参与。道光间叶志诜作为陈介祺的长叔父辈,陈介祺早年的金石活动与思想受到了叶志诜的影响。而叶志诜在金石传播上的贡献大于辩伪和考释,陈介祺又弥补了其不足。清代晚期许多金石家的器物大多毁于兵燹,簠斋又让平安馆旧藏器物与金石文化得以幸存与传播。二人在金石文化精神上的追求,都推动了中国金石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