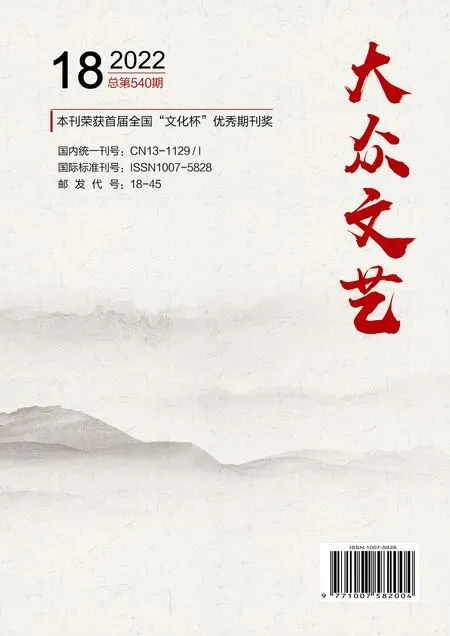迟子建的生态凝视
——以《白雪乌鸦》为例
廖梦绮 胡辰欣 张海昕
(兰州大学,甘肃兰州 730000)
由生态危机的现实指向性,生态伦理思想与疫病叙事相结合,负载着人与自然逻辑的生态批评表征在文学作品中,在近距离审视疫病与社会的互动中刻画出一个时代背景下的伦理阐释。《白雪乌鸦》作为回顾百年前东北鼠疫的经典之作,在新冠肆虐下更具现实意义和生态研究价值。迟子建深沉凝视着混沌诡异的哈尔滨傅家甸,于焚尸化为的层层灰烬中抽拨出生命的希望。疫灾中的人被迫脱下现代生活一般范式的外衣后,展现的是人类社会、疫难及大自然的关系,构筑起人与大自然的主体间性和生命救赎。从疫难的灾祸世态中提取生态启示的黄金,迟子建的生态话语是隐藏在疫难下的积极精神启示。由此加深对中西方疫病书写中更深层次生态价值观的解读,促进后疫情时代的文学创作,唤醒个体心中的自然意识和生态道德。
一、疫难物象与生态视野
(一)生态与自然物象
从“出青”到“回春”,“白雪”与“乌鸦”一白一黑,苍凉荒芜之感表征着生与死,生命形式与自然意象串联相融。在“谨慎的拟人化”笔法下,乌鸦性情刚烈、坚毅正义,它和遭遇鼠疫的人们一道,见证人们从生到死的新生和向死而生的顽强。始于腊月二十三的一场夹杂着寒风的冬雪,鼠疫索求傅家甸人的生命魂灵,由此牵涉的各色人物生活状态能窥见自然万物在疫难书写中的警示作用。“人类身体和环境构成了一个彼此关联的场域……在身体和其他有机体之间,交互作用编织出支撑个体生命的网络。”迟子建用白雪隐喻死亡,感官上是陌生化的冲击,视觉上是置身鲜明的冷色调的咫尺之距,仿佛眼前就能目睹大雪纷飞中垂死挣扎的人们。白雪乌鸦一白一黑,但这里黑不指生命的终结,白也不指圣洁、相反隐喻生命的残缺。
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论主张动物与人一道有知觉和情感,它们的痛苦和死亡与人类具有同源性,人要“道义关怀动物”,帮助它们脱离苦痛。“乌鸦”与的人联系密切,除了翟纪夫妇对待乌鸦截然不同的态度最终阴阳两隔,还有多次在人的生死之际提道乌鸦,比如老鸦炖汤给于秀晴带来丰盈母乳哺育大胖小子、焚尸切断传染源时“坟场守灵人”为逝者送行……乌鸦生生不息地盘旋在傅家甸的天空,和人们一道抗击鼠疫,走过严冬待春来。迟氏笔法下的人与动物,是对人与自然关系期望的一种隐喻,从生物学上看,二者亦完全平等,人类中心主义应该被生态整体主义取而代之。人与动物相互关照,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体现为一种生态平衡的思想。
饱受摧残的青楼女子翟芳桂钟爱乌鸦,时常偷着撒谷物给它们吃。她与晨鸦每天问候早安,何其谐美!她认为黑色是最纯净的颜色,乌鸦不会带来厄运,它们只是与她类似的生灵。但纪永和深深憎恨乌鸦,对其辱骂驱赶、掏蛋毁巢,甚至将粮栈生意差怪罪于乌鸦。看见妻子用粮栈里牟利的粮食喂养乌鸦便怒火攻心,唾骂痛打她,最终作孽投毒。恶性终偿,他染疾而死;善心终报,她迎来曙光;一善一恶的对比冲突中以生死之别收场。
万物有灵,且为超验的灵气,“灶神、烧锅”成了迟氏笔法中的文化符号。“所有符号都有意义,而文化是一个社会所有意义活动的总集合。”从迟氏符号的文化记忆探寻傅家甸鼠疫之下的生态叙事启示,体悟其中神化信仰超验的自然力量。良心和善心可被自然感知,对于深层生命意识,自然回馈的是正向魔法力量。而人的信仰缺失、肆意破坏,浑浊与污淀则会受到自然的摒弃,终食恶果。迟子建在人与自然的仪式中,歌颂生命、尊崇自然。
(二)生态与社会图景
由自在自然到人化自然,人作为依附于自然的存在物,与自然辩证统一,投射于现实危机中的疫难书写,将个体生存意识、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纳入作家的伦理叙事之中。当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被强制中断后,其精神生态在异化中产生的二次危机便真切展现出来。比如乡民占卜拜仙、急于求医问药、疏远戒备病患,化为狐仙“过阴”作法以襄灾的周于氏,竞相采买寿衣棺材的村民等。人类常视疫难为大自然之过或为天灾,这无疑是人类中心的生态观和自然观。除了生命的劫难,更有人心畸变和世态扭曲的呈现。封城之下物资紧缺,粮栈商人纪永和停止售粮、囤积居奇;白脸太监翟役生希望傅家甸的鼠疫永远得不到控制,盘算着靠倒卖棺材发财;周耀庭私藏烟土,中饱私囊……地域的寒冬中孕育着东北独特文化习俗,诸如入土为安的殉葬风俗、纪永和典妻、周于氏过阴,腊月二十三祭灶神、小年换洗扫尘,用黏豆包、猪血糕祭灶等,或积极或消极,都成为这副图景的别样素材。
迟子建在其中用悲悯情怀拥抱伤者,深层次思考人与天道、自然间的关系。尸横遍野、黑脸离世的恐怖众生相带来沉沉死气,巴音、吴芬、金兰、纪永和、谢尼科娃相继陨落。人们起初行为慌乱,放血、刮痧、针灸、找周于氏“过阴”,但迟式笔法无意刻意渲染疫难的惨烈和悲痛,因此笔下人物习惯于这种死寂后便恢复往日做派,寿衣样式、入土方式被聚众探讨,人们别无选择地与疫难共存了,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人类社会的各种灾难是由于人类思想世界的紊乱造成”。踱步于疫难困境中的人心中向往的是破除困境,走到光明处去。
恒常生活的延续弥补鼠疫造成的断裂,在对痛苦的治愈和人性的疗救中驱散阴霾,生命的活力由此在灰暗的疫难底色上泛起光来。隐含的作者地貌感指引从个人反抗到集体反抗的经历再现,从“个体”到“社群”思维视角的演变和升华,礼赞了小人物群体的抗争奉献。富商百川舍利取义,熬制中药无偿提供给百姓们,用家族生产线制作口罩、降价抵制涨价风潮,无一不现重义轻利精神;年迈移民周济,在火车上隔离点的人们面临食物困境时,带领全家老小制作饭食并送到隔离点,这是对傅家甸深沉的爱;客栈老板王春申用他心爱的黑马加入了运尸队,冒着被感染的风险运送死者到坟场,奔走在抗疫一线。渺小的个人无法力挽狂澜,但群体的团结必不可少。
在疫难话语体系中,迟子建始终怀揣着微光暖流,以纯真的生态信仰,建构消解人们伤痛与苦难的一方世界,在文明受冲击的现代性社会拓土于自然的原野,于人文关怀中反思现代文明对个体精神的遮蔽。透过“死亡的层层白骨”,迟子建将众生置于大自然的生命循环和宏伟环境,接受苦难,战胜不利因素,个体生命因此获得超越和重构的可能。
二、疫病符号与生态灵魂
(一)生态与女性身份
“女人是更契合大地、更为植物性的生物,一切体验都更为统一”舍勒对女性的自然表征意义进行了陈述和肯定。人类与自然水乳共生,尤其是女性,这是从女娲造人的神话起源开始就具有的生命联系。传统上看,处于男性霸权压制之下,女性肉体往往悲哀地遭受压迫和欺凌。迟子建基于女性与自然“生理相似、命运想近”的共同性,以一个女性特有感受,基于自然、故乡的深厚积淀,赋予笔下女性人物爱和生命的力量,表现追求自由与生命意义。她以纯真的生态信仰进行生命描述时,使其烙印在东北土地中,亲密地疏离披露出个体的“孤独”。
婚姻爱情原是人类最柔软的情感,而在傅家甸却处于割裂、不幸的尴尬境遇。迟子建用她女性独特的心灵,以疏离的亲密,展现人类的“孤独”。于晴秀和傅百川各有家庭,只能将对彼此的倾慕埋藏,于晴秀喜欢醉后一个人在街上和人搭话,傅百川每日打发伙计去点心铺子并送去乌鸦解决其育乳问题。王春申撞破妻子吴芬和马贩子的私情,嫌恶金兰丑陋的容貌和其情人翟役生,神往美丽的谢尼科娃和她动人的歌喉,却只能在她不幸离世后到钟表店从坏掉的时间中再见她青春的脸。然而这些精神创伤也能带来转机——于晴秀的大胖小子接替喜岁迎来新生,翟芳桂拥有了糖果铺、爱情和儿子陈水,苏秀兰以怀孕弥补了已故“傅春”的缺憾。
在底层群体众生相中,构建具有包容性的多元文化价值体系,表达了弱势群体在经历危机过程中的迫切希望。此外她用社会语境的话语对女性身体进行编码,纪永和灌注于翟芳桂身上的人性反生态书写更将男性主导的罪恶行径表现出来。随之披露的还有男性对女性的主导和征服,翟芳桂每次被作为赚钱的工具利用完毕后,还要再次遭受丈夫的报复性性行为。将性别立场延展至自然领域,环境破坏和生态恶化威胁到人的身体性发展,实际上人类社会的病症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的破坏性意识和行为买单。这种笔法隐含了一种内在化境,使各个物象灵化,在人的感性认知中搭建一个自然生存场。迟子建似乎无意将男性霸权主义文化与生态女性主义置于完全对立面,她以女性观点、母性情怀凝视着自然万物、人类世界。性别与空间叙事交错,人物与事件、灾难与拯救、生与死在想象的空间中酝酿和碰撞,重构了疫难遭遇者的心理认知、生命意识,包蕴着对个体存在和集体发展的沉思与探索。
(二)生态与生命救赎
傅家甸人对待外界自然的功利主义态度和旺盛的工具理性倾向,支撑其自以为是的人类中心主义地位。迟子建介入历史,凸显疫情书写独特的文化功能并由此凝视人性,展示出潜藏深处的恶性畸变,“像任何一种极端的处境一样,令人恐怖的疾病也把人的好品性和坏品性统统暴露出来。然而,对流行病常见的描述,则侧重于疾病对人格的毁灭性影响。”鼠疫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具有不同于战争等人祸的“不可言说性”。
面对疫难,各种各样光怪陆离的事件背后是真切的人性。不管是忠厚淡然的王春申、大义细腻的傅百川、勇担重任的伍连德、清冷孤傲的陈雪卿,还是秀外慧中的于晴秀、坚柔并存的翟芳桂等,隐秘却最真实的欲望在人性深处抗衡和较量,他们的生死交相辉映,他们都是鲜活的生命存在。迟子建通过书写普通小人物在生死存亡间展现出来的活力、温暖与爱,书写对普通人对生命伦理的真情、与疫难背后的自然进行的抗争与达成的和解,构成一个宏大的、鲜活的“生”的主题。
傅家甸的每一个人都是生态共同体里的平等一员,即使是小人物们也具备大地伦理,弱小的生命如何得到救赎?迟子建通过这场鼠疫赋予了他们自然生命的平等与救赎,尤其是后半部分从性别视角介入,衔接疫情和生育,凝视生与死,探究黑土地上丰盈旺盛、遏而不止的生命活力与本质。鼠疫沉重打击了温暖善良的女子于晴秀,其丈夫、儿子、公婆俱亡,然而危难过后是生命废墟上一颗生命种子萌芽于腹中,母性以单纯而强有力的方式成为生存的精神支撑。
生命形态的无限性突破了傅家甸的地域界限,人类与物质环境的互依性认同是一个核心因素,除了在意识形态上折射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危害和的困境,疫难更有价值意义的在于把人类面临的风险中心化和情境化了。从生态批评视角重审其“造成人与周围自然界、自我与他人、心灵与身体间的破坏性断裂”的现代世界观的反生态本质。
三、叙事启示与生态寓言
“几乎所有现代性的解释者都强调个人主义的中心地位。”在鼠疫中,出于自我考量,人们意图建构一个自我生存世界,将自我与外界隔离开来。这个世界内是安全健康、秩序文明,这个世界外是危险混乱、末日混沌。在风险情境中把自己与外界隔离,个人主体为征服大自然而主客体对抗,构造出灾难不断的典型现代性叙事。
面对疫难的生死大考,死亡是贯穿始终的行为动作,似乎我们总是在为生命送葬,而迟子建惯于找寻生的希望,并从生命厚度去重新审视。好人一定能幸免于难、而坏人必会遭到报应吗?答案是否定的,从巴音的暴毙街头到周济祖孙三代一夜离世,再到末篇活人去坟场祭奠死人。鼠疫之下,生死并非两重相隔,而是生命厚度与向度的延伸。透过无数的死亡,是生命的坚守与朝气,在其中蕴含的爱护一花一草、一石一鸟的生态美学始终具有丰富的生态意义。迟子建于灾难中还原普通人的爱与温暖,凸显生命的可贵。
文学在疫难的极端境遇里,深入人的精神世界,去探寻人类如何从单个遭受不幸的个体,饱含强烈的人性之光凝聚起来共抗灾难,举长明火把,迎崭新黎明。结合当前的新冠疫情,与自然的怒气相抗争的我们不得不反思现代文明形态的“杀生之过”,因为人对自然的每一次攫取,它将或小或大地回以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与自然共生,救治地球共同体遭受的疾病。
时光洪流中,人对自然从敬畏、征服到和谐,单纯的自然界没有价值,而人作为价值主体,必须在关爱和保护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再生产。现代社会运行在法制轨道上,生态律令却往往被忽视于索取予求的既得利益中,现实则以更严厉的反响敲响生态启示的警钟。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生态道德应该被贯彻,二者生命共同体的关系应被纳入伦理考量。
在新环境史观视阈下,生态道德是一个核心因素,开展生态文学研究,注重文史互动,挖掘生态文学作品中深刻的政治历史内涵。我们在研究中亦可以借鉴中国本土生态美学理论中曾繁仁先生主张的“生生美学”,融合东西方资源以建构中国生态话语,探讨生态批评对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意义,丰富人类社会的生态道德建设。
结语
物质文化高度发达,人类社会的精神范式在一定程度上被利益石化,所幸文学领域内的生态道德意识指引人类事业渐趋生态文明化。我所理解的文学艺术“生态”创作是一种复归自然、非人类主体化等的一种信仰,将视野落定到疫难文学中,则是将人与自然置于激烈矛盾和冲突的对立面,深刻反映个体及群体在与疫难进行抗争后,双方达成的妥协与和解,由此传达给人类社会警醒与思考。按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文学作品指向未来,按可然律和必然律讲述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新冠从庚子年初蔓延至今,《白雪乌鸦》的帧帧疫难情节倒映于现实,生态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批评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使肩负人类生存责任的我们在批评实践中贯彻生态道德,指导生态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