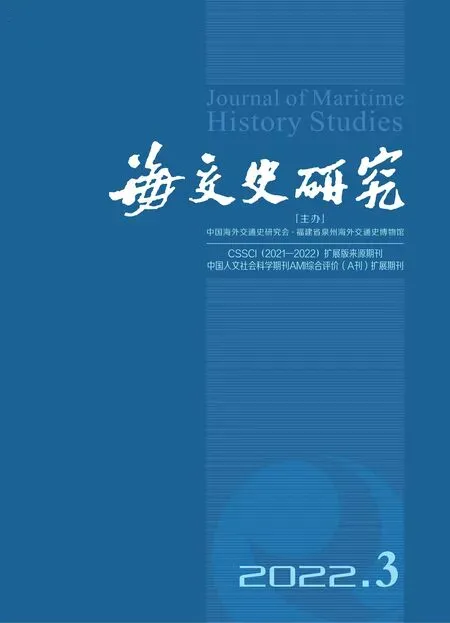海洋观、海洋性与早期海路
——读王子今《上古海洋意识与早期海上丝绸之路》
吴春明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王子今教授的新书《上古海洋意识与早期海上丝绸之路》即将付梓,子老命我作序,我得以先睹为快,认真学习了一遍新书全稿,受益匪浅。子今教授是人杰地灵的考古学重镇西北大学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毕业生,又是著名历史学家中不多的考古出身者,我们相识并不早,但却一见如故。他在考古专业学成后,师承重量级的秦汉史名家林剑鸣教授,以《论秦汉陆路交通》获硕士学位。他几十年来辛勤耕耘的学术领域,都可以看到早年的考古学、秦汉史这两段科班训练的精致锻造痕迹。他已经出版的五十余本史学著作中,近三分之一都是包括海洋在内的交通史考察,分别涉及古道网络、津桥驿站、仓储体系、舟车建造、陆海并进、中外交通等全方位研究,其余的也多是与交通史直接或间接关联的区域治理、边疆行政、民族关系、生态环境、文化景观等。我的学问距离子老还很远,出道晚他半辈,在东南一隅的考古、历史研究中,也主要是从秦汉时代的东、南两越入手,对他据王朝视野下的疆域拓展、郡县推进、区域治理等宏观历史建构颇多认同。加之,我自入门水下考古以来,多关注东南沿海的海洋遗产与考古,子老近年更在陆海交通统筹研究中,相继推出一系列海洋经济文化史的论述,都赐我学习,既有“四海意识”等宏观理论建构,高屋建瓴、气势恢弘,也有“东方海王”一类的区域海洋开发史的梳理,或“海人”“海枣”与“海中星占”等具体海洋要素的微观探求,细腻深刻,让我深受启发。因此,我从他的研究中学习了很多,以至形成了很多共同的涉海语言。本书所涉我国史前、上古海洋意识、海洋文化与早期航海、航路的历史,更是我们多年共同感兴趣的课题。
海洋文化史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研究,是一个复杂和困难的学术课题,学者间在很多重要问题上还有不小的分歧。比如,古代中国是太平洋西岸的一个沿海国家,但中国古代文明的主体是建立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为中心的大陆性农耕社会文化基础上的,正如本书第一章有关“天下”“中国”与远方“四海”的论述所示,海洋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中国早期文明的辐射薄弱的“远方”。对待这样一个远在文明中心之外起源发展的海洋社会文化体系,学界先后有过跨界的、文化相对论的“亚洲东南海洋地带”“亚洲地中海”“环中国海”以及“东亚海洋”的讨论,但更多的是便利地选择“中国史”框架论述“中国(或中华)海洋文化”。又如,古代文明的中心边缘与陆海格局,更使得以中原(早期中国)华夏、汉人历史为主线的中国古代史尤其是上古史,对远方海洋历史的认知很少、记载极少且语焉不详,模糊缺漏,甚至陆、海文化立场的差异常带来不同的认知与描述,因此完全站在传统文献史学、甚至正史立场的涉海历史研究,要获得客观、全面的海洋史论述,难度很大,需要多学科资料与方法的整合。
本书聚焦上古海洋历史,更是海洋史研究中难度最大的篇章。汉文史籍涉海记载的碎片化、模糊化,考古资料尤其是海洋考古资料也零星、残失,使得大部分学者都选择绕开这段朦胧的历史而不愿涉足。子今教授毕业于考古学科班,又受承史学名家的衣钵,在古代史研究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上古史、海洋史研究上优势更加明显。他几乎穷尽了这一主题所有的传世与出土文献、考古出土文物资料,并以他多年来与这一主题有关的诸多专题论文、区域海洋史研究论著为基础,完成了这本约33万字、内容详实的中国上古海洋史专著,在学界恐无第二人能够胜任。
全书的六章分别从上古海洋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角度展开,既考虑历史过程的先后,更关照海洋文化不同要素在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制约、因果关系,既有宏观理论视野,又有微观历史透析。按我的理解,这六章内容虽大致以史前与夏商周、齐国、秦、汉的历史进程为轴,但各章的论述又各有侧重,形成三大块不同的主题,即第一章聚焦上古“海洋观”的建构,第二、三、四章以东周、秦、汉断代史的“海洋文化”为主轴,第四、五章为东洋、南洋的分域“航路史”即“海上丝绸之路”早期历史的钩沉。从海洋观入手,铺陈海洋文化,再梳理古代航路,逻辑清晰、结构合理,我在学习之后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与思考。
第一,从上古华夏海洋意识、海洋观入手,探索先秦两汉时期海洋开发与航海实践的内在动力与文化源泉,赋予海洋史、海丝历史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切入点,使得本书具有一般海洋史限于事像描述、考证所达不到的理论特色与深度。第一章的“上古华夏人的海洋观与最初的海洋探索”,关于早期海洋活动的事像着墨不多,焦点与精华是有关中原华夏“四海”观念的分析。“四海”实际上是作者站在中国早期文明史的全局看海洋的图景,区分了以“中国”“中土”为中心的“天下”“海内”所代表的古代文明、国家的主体空间,以“海外有截”区分的“四海”“海外”所构成的模糊、“昏暗”的远方空间,由此看到了华夏“中国”理想中的内、外地理分野,这是一种基于陆海关系的、“中心—边缘”政治秩序的特殊重建。这一“中国”“四方”“四海”依次构成的华夏文明政治地理秩序,某种程度上也是源于东亚自然地理的客观情势与华夏认知、理想的统一,体现了人文、政治、民族地理观组成的华夏天下观、世界观总成,是解开包括海洋史、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在内的中国交通史诸多重要问题的一把钥匙。中国文明史、中国的海洋史,正是在这样的天下观、宇宙观下形成与发展的。因此我们要认识、复原这段历史,就离不开主导历史的华夏人的这部分主观与精神世界。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对于‘中原’与‘四海’‘天下’与‘四海’,以及‘海内’与‘海外’诸意识的学术考察,有益于深化对中国早期海洋观和海洋探索理念,以及海洋开发实践的认识和理解。”“也有益于推进中国古代交通史的研究”(第一章第五、六节)。
这一以中原华夏为中心的早期文明史框架内的边缘、“海外”“四海”的海洋观,深刻地制约着海洋社会文化史的进程。中原华夏人对海内、外的差异化认知与理解,导致了对“海”的知识缺乏和汉文史籍对夏商时期海洋世界记载的几乎阙如。秦、汉王朝在统一历史进程中,分别在北方对东方“海王之国”、南方东南两越濒海土著王国的最后征服,恐怕也与陆、海关系中海洋社会不同于内陆农耕王国的特殊性与海洋王国的顽强生命力有关。秦、汉王朝先后通过不断的东巡海上、南登琅琊、议于海上、削之会稽、建设东海武库、前所未有的此起彼伏的南北向的海上征服等,不断加强对滨海地带、海洋世界控制,强化海洋在早期帝国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体系中的地位,既与海洋文化、海洋世界在国家文明体系中潜在的相对独立性与离心力有关,也与秦、汉王朝统一“海内”“天下”后,要突破“海外有截”、追求从陆到海、海上扩张的理想所构成的新海洋意识有关。第三、四章分别论述秦、汉两代的海洋文化时,强调了秦汉时期积极向上的海洋意识及其在秦汉时期海洋社会文化实践中的引领作用,把秦皇汉武流连忘返于海上的一系列行为,视为“面对陆上已知世界和海上未知世界,陆上已征服世界和海上未征服世界所发表的政治文化宣言”,这与先秦时期陆、海区隔的海洋观相比有显著进步。不过,先秦华夏“四海”海洋观的基础地位,对秦汉以后不同历史时期的王朝海洋政策、陆海互动模式,仍有不同程度的深远影响,王朝政治站在华夏中心立场,间或对海上倭人(寇)、岛夷、胡番等海洋社会的排他、抵触或海禁,也就是“海外有截”、内陆海外的上古海洋观根深蒂固的沉渣泛起。
第二,从理论上说,大陆性农耕文化特征的中土华夏并不代表中华文明内涵的全部,思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大陆性与海洋性文化的共存、融合,是海洋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又一重要课题与视角。林惠祥在《福建武平的新石器遗址》中就提出我国东南区及相邻的东南亚古文化所构成的“亚洲东南海洋地带”不同于华北内陆中心地带(1937年新加坡“第三届远东史前学家大会”论文)。凌纯声在《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中,同样把以中国古代文化划分成西部华夏农业民族的“大陆文化”,与东部沿海蛮夷渔猎族群“海洋文化”,并分别冠以“珠贝、舟楫、文身”为特征的“亚洲地中海文化圈”和以“金玉、车马、衣冠”为特征的华夏文化圈(台湾《海外杂志》1954年3期第7—10页)。苏秉琦先生也明确将我国宏观历史地理“分为两大部分——面向海洋的东南部地区和面向亚洲大陆腹地的西北部地区”,前者“从山东到广东即差不多我国整个东南沿海地区”(《文物》1978年3期第40—42页)。在此基础上,媒体和社会还常理想化地以“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来描述中国文化的陆海二元构成。
再从世界史的宏观角度看,陆、海二元的文化结构也是人类社会多数古代文明的共性。但因陆海宏观地理格局与文化传统的不同,最后整合形成了东、西方文明之海洋文化发展的巨大差异。在西方古典文明形成与成长的中心地中海,在亚非欧三大洲陆地拥抱、汇聚海洋的地理背景下,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与古希腊等多元文化相继汇聚、融合于海中。地中海扮演了旧大陆多元文明汇聚、扩散并形成西方文明基础的古希腊、古罗马成长的舞台中央角色,海洋文化、航海传统始终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基因。“地中海是旧世界的心脏,没有地中海、没有海洋,西方历史便无从设想了。”(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93页)然而,以古代中国为中心或所代表的东方文明的陆海格局恰好相反,无论是华夏理想中的中土中国、海内天下、海外四海格局,还是现实中如苏秉琦先生所概括的分别面向西北和面向东南的陆、海两大块,古代文明的成长、多元文化汇聚的舞台中央位于陆地中原,面向内陆、“逐鹿中原”的大陆性农耕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几乎是一元独大的。没有中土华夏,中国古代文明同样无从设想。而从中原遥望远方,海洋文化的发展从总体上是局域的、边缘的和非主导的,难有像西方古典文明史进程中海洋文化的作用,更无核心地位,而且在秦汉帝国灭东、南夷、越两方土著“海王”后,海洋文化实践在中华文明史的进程中相对独立性进一步削弱,海洋社会长期蛰伏于国家社会的边缘与基层。
本书第一至四章的海洋文化以断代史为主线的论述,客观地展示了中华早期文明史上陆、海二元文化的发展与消融,也可以看到主要基于华夏汉文史籍建构的中原中心、王朝主导的鲜明的陆海统筹观,海洋文化被客观地视作华夏文明的一个“因素”。比如,第一章除了重点阐述海内、海外“有截”的华夏早期海洋观外,也简要涉及沿海考古发现的史前及夏商时期的贝丘遗址、史前舟楫、海贝流通、有段石锛等海洋文化发展的信息,这一时空遗产正是陆、海二元论者建构夷、越土著的“亚洲东南海洋地带”或“亚洲地中海文化圈”的中心内容,作者发现并开宗明义地主张,作为华夏文明的海洋因素,“滨海居民与中原基本区并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异”。第二章全面论述了“海物惟错”“海王之国”的东夷齐国海洋文化发展进程,我可以体会到其在华夏农耕文化体系外相对独立发展的鲜明特征,这又是理解中华文明史进程中陆、海二元结构与海洋性文化相对独立形态的典型标本。类似的海洋文化形态,应该还有东南沿海的吴、越或百越各“海王”社会,这方面还有进一步拓展的学术潜力。第三、四章的秦、汉海洋文化,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成的背景下,从帝国看海疆、从陆地征服海上,完全回归了华夏中心的立场与观察维度,这也符合这一大变革的历史阶段华夏大陆性文化向海扩张的客观事实,无论是王朝的海上控制与扩张,还是夷、越的“鱼盐之利”等海洋经济的融入,不难体会到中土华夏一统之下海洋社会文化相对独立性的削弱与彻底的边缘化。从先秦时期“海外有截”的陆、海二元格局,到秦汉帝国下华夏中心的大陆性文化独大,海洋文化的隐性化与边缘化,这一新的态势及其对中华海洋文化进程的深远影响,很值得海洋史学者进一步探索、总结与思考。
第三,作者把“海上丝绸之路”置于中华海洋文化史的整体框架中,从以华夏为中心的早期中国人的“四海”开发,到秦皇汉武东进、南征的持续海洋探索中,寻找中华先民早期对外航路的内在格局与“海上丝绸之路”真实的起源,这是对传统“海丝”论述的一个重要创新。
“海丝”的原意是“陆丝”的延伸,是西方学者基于东西交通整体史的立场,将“海道”作为“丝路”语境下中西交通史的派生与发展,实际上是把东方海洋文明史置于“印度洋中心论”下的海洋史话语体系,即“通印度诸港之海道”(沙畹《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2004年新1版第208页),中外学者大致都在此语义下,进一步构建“丝路”,从陆路到海路的“延伸”以及所谓陆丝“衰落”“堵塞”后的地理“转移”(斯文赫定《丝绸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4页;布尔努瓦《丝绸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57页;陈高华、吴太、郭松义《海上丝绸之路》“前言”,海洋出版社1991年)。这一传统意义上的“海丝”,就是汉唐文献相继提到的以“徐闻、合浦南海道”“广州通海夷道”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西(南)洋”航路,只是中华海洋史自身体系中分域航路发展的一个环节,把它切割出来去“附和”中西交通整体史与以印度洋中心的中西海道史的论述,忽视了“四海”视野下中华海洋文化自身多元发展的内在逻辑。
我发现,本书第五、六章分述的秦汉时期的“东洋”“南洋”航运,已是“海丝”历史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换位思考,从西人的印度洋中心论“拨乱反正”到环中国海海洋文化史自身的理论建设。其中,“东洋”航运在秦皇汉武的海洋开拓实践中实际上占据了首要位置,更可溯源到先秦时期的燕人、齐人的海洋实践及“海王之国”的深厚积淀,显然与陆、海“丝路”的所谓空间转移无关,也远远早于“丝路”发展史上以“印度诸港”兴起为标志的陆、海转移史。“南洋”航运的发展,也离不开既有的“南海海洋文化与世界海洋文化发生联系”(第六章开篇),在该航路上不排除所谓“陆丝”“衰落”后,穿越南海、印度洋“海丝”航路承载更多的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功能与角色,但南洋航路兴起无疑也是奠基于南海先民的史前、先秦海洋文化发展基础之上的。作者在阐述了大量上古南洋航路上的考古发现,实证地再现了南洋航路发展及其与“海丝”的关系,年代更早的有关南海北岸史前贝丘、越南沿岸与两广先秦青铜文化的统一性,以及环南海区域史前以来的树皮布、双肩大石铲、突纽形玉玦为代表的玉器文化等考古发现,对于研究南海早期海洋文化与南洋航路的起源,同样值得重视。我注意到,作者在该章中分析《汉书·地理志》有关“徐闻、合浦南海道”的“蛮夷贾船”的主体身份时,据相关文献提出了“西来贾船”“安息西界船人”“中国商人与南洋航海家的组合”等相关可能性,后者在民族考古学上是有重要的学术潜力可以挖掘的,价值不能低估。可见,中华海洋文化史体系内“四海”航运史的源远流长,丰富多彩,不是所谓“丝路”陆、海转移的传统“海丝”单线历史所能概括的,本书在秦、汉“东洋”“南洋”航路研究上的创新开篇,对于中国航海史后续历史的建构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深化研究是有重要启发的。
子今教授凭借独到的智慧与超人的勤奋,在交通史、海洋史长期研究与积累的基础上,通过文献与考古资料的整合,旁征博引,完成了这本理论深度、历史透视、学术创新俱佳的海洋文化史著作,啃下了一块硬骨头,是对中国海洋史、航海史研究的重要贡献。我在初略学习后的一点心得与体会,夹杂了不少自己不成熟的思考,甚至有对原著忽略与误解之处,都请子老和新书的读者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