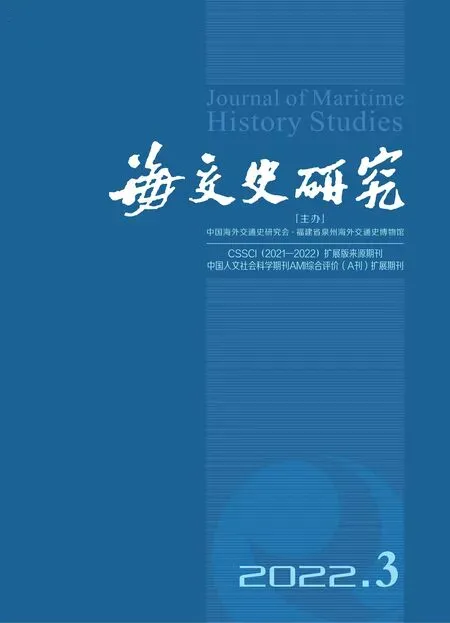也谈明代的“报水”问题
戴佳辉
《海交史研究》2020年第4期登载了刘璐璐博士《明代海洋社会中的“报水”研究》一文(以下简称“刘文”),其中对涉及“报水”的相关问题有着较为全面的梳理与分析,并且也提出了一些新见解。(1)刘璐璐:《明代海洋社会中的“报水”研究》,载《海交史研究》2020年第4期,第68—83页。“刘文”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对嘉万时期闽粤海寇勒索“报水”的梳理、明末郑芝龙收取“报水”行为的分析等两个方面。同样地,作为文章的立论基础与核心论点,“刘文”对“报水”的源起以及“报水”与“引税”的关系也提出了新看法,以下是“刘文”对这两个问题的主要结论:
其一,“刘文”首先认为“海洋社会的‘报水’或‘买水’行为,确切可追溯到正德、嘉靖年间广州实行的‘抽分制’”,并在后续的补充论述中得出“‘报水’的起源正是正德年间官方的‘抽分’”以及“‘报水’起源于官府对非朝贡番舶征收进口税的俗称”这一结论。从史料运用和论证逻辑来看,“刘文”将“报水”与抽分制的实施相关联,同时将“报水”的产生基础归之于抽分制推行后,官方对非朝贡番舶的征税行为。倘若“刘文”的观点成立,那么“报水”也就只能上溯至正德四年(1509)明确实行的抽分制,进一步来说“报水”是明廷海禁政策松弛中海洋税制建构的产物,是官方合法征收的进口税。
其二,“刘文”还认为“作为合法的行为,‘引税’等是在‘报水’基础上演变而成的更为严密完善的纳税方式,体现了官方对海洋社会具备掌控能力”。“刘文”的论证逻辑是,随着海洋秩序治或乱的变化,海洋征税权也在官方与海寇之间发生转移。当官方得以掌控海洋秩序时,开洋政策中的海洋税由官方征收,并以规范的“引税”等名称取代俗称的“报水”;反之,当海洋秩序失控时,海禁政策中的“报水”则出现由公到私的转变,也即海寇通过掌控海域来实现对海洋税收的分割。正是基于此,“刘文”得出“引税”是由“报水”演变而成的结论。然而,“刘文”的这一论点却没有相应的史料来作支撑。
概而言之,尽管“刘文”推动了对明代中后期官商共谋海洋利益等问题研究的新进展,但是“刘文”对“报水”的起源及其与“引税”关系的论证却失之过简、语焉不详,因而所得出的结论也并不准确,笔者认为对此还有商榷的余地。
一、“报水”的起源时间与产生基础
为探讨“报水”的起源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以下认识:明代法律文献中的“报水”指受贿的钱财,对海防武职官员收受“报水”行为的正式罪名为“买港”,也就是将海防武职受贿纵容中外商船进出港口交易的行为,加以明确量刑与定罪惩处。从动机、行为与结果来看,市舶太监或海防官员收受中外海商财物后,准许其在沿海非法贸易的行为,也类似于收取“报水”的“买港”行为,二者具有高度相似性。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将展开对“报水”的溯源。
“报水”产生于海洋贸易之中,因此有必要先对明代的市舶制度进行简要考察。《明史》载:“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2)《明史》卷81,《食货五·市舶》,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80页。明代市舶制度中的互市贸易针对的是朝贡使团及随之而来的番舶,凡是朝贡国均可依照制度规定来华互市。《筹海图编》记载:
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在广东者专为占城、暹罗诸番而设;在福建者专为琉球而设;在浙江者专为日本而设。其来也,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明矣。……贡舶者王法之所许,市舶之所司,乃贸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许,市舶之所不经,乃贸易之私也。(3)[明]胡宗宪:《筹海图编》卷12,《经略二·开互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98—399页。
何乔远也说:“元亦通诸番互市,其法大概如宋,皇朝禁海舶,不通诸番。”(4)[明]何乔远:《闽书》卷39,《版籍志·右杂征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745页。与宋元两代准许海商出洋贸易的市舶制度相比较,明代的市舶制度转向收缩,也即只准许朝贡使团的互市贸易,不允许海商出洋贸易。隆庆开海以前,朝贡使团来华互市成为明代中国与海外国家进行贸易的主要途径之一,而且明廷对远人示以怀柔并不征税,至正德四年才开始实行抽分制征收货物税。正德四年以前,明廷没有对参与互市贸易的番舶征税,抽分制实施后实际上默许了部分非朝贡番舶前来广州互市。
“报水”可能源于历来互市贸易中广东地方官对番舶索取的“例钱”,其时间似乎不迟于成化时期(1465—1487)。约成化九年至十一年(1473—1475),陈燮任广东按察司佥事。据弘治十六年(1503)刻本《大明兴化府志》载:“陈燮,字廷辅……迁广东按察司佥事,宪度益谨。广东地濒海,每互市番舶至,诸司皆有例钱,谓之报水钱,燮独不受,广人至今称之,未三载,卒于官。”(5)参见万历《广东通志》卷10,《藩省志十·秩官·按察佥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7册,第259页;弘治《大明兴化府志》卷42,《礼纪二十八·列传九·宦业下·仙游县·陈燮传》,天一阁博物馆编:《天一阁藏历代方志汇刊》第563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197—199页。此外,国家图书馆也藏有弘治刻本《大明兴化府志》,仅存4册共19卷,可惜其中没有第42卷。另查,弘治《大明兴化府志》尚有天一阁藏清抄本和清同治十年重刊本(弘治《大明兴化府志》卷42,《礼纪·人物·宦业下·仙游县·陈燮传》,清抄本,天一阁藏本,第27a页;[明]周瑛、黄仲昭修纂,蔡金耀点校:《重刊兴化府志》卷42,《礼纪二十八·人物列传九·宦业下·仙游县·陈燮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88—1089页)。嘉靖三十四年(1555)刻本《未轩公文集》的《补遗》卷也收录有相同的文本内容,(6)[明]黄仲昭:《未轩公文集》,《补遗》卷上,《郡志新增列传·广东按察司佥事陈燮列传》,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55册,合肥:黄山书社,2015年,第205页。《补遗》卷是将黄仲昭散见于各处的文章辑录汇编,其中《陈燮传》就是来自“郡志新增列传”,也即黄仲昭参与编纂的弘治《大明兴化府志》。(7)[明]黄仲昭:《未轩公文集》,《补遗》卷上,《兴化府志后序》《人物志引》,《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55册,第200—202页。从黄仲昭的视角来看,迟至弘治十六年,明朝官员已经将历来广东互市贸易中的“例钱”称作“报水钱”。而嘉靖十七年(1538)序刊本《仙游县志》却记载为:“迁广东佥事,宪度益谨。广东地濒海,番舶互市,诸司皆有例钱,燮独不受,未三载,卒于官。”(8)嘉靖《仙游县志》卷4,《人物类·陈燮传》,《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30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37页。万历四十一年(1613)刻本《兴化府志》则简化为:“迁广东按察司佥事。濒海,番船互市,有例入,燮峻拒之,未几,卒于官。”(9)万历《兴化府志》卷42,《人物志六·清修传·陈燮传》,明万历四十一年序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本,第10b页。二者并未将“例钱”解释为“报水钱”。从史源学角度来看,嘉靖《仙游县志》、万历《兴化府志》中的《陈燮传》文本显然是自弘治《大明兴化府志》简化而来。细微变化中可见,福建地方官绅可能已经将“例钱”等同于“报水钱”,但却以“例钱”名目载于地方志。然而,即便是在抽分制推行以后,广东地方官对番舶索取类似钱财的行为依然存在。隆庆元年(1567),周行任香山知县,“时彝商丽处澳门,番舶至,奉檄盘验,有例金,峻拒不纳,惟禁水陆私贩,及诱卖子女等弊而已”。(10)乾隆《香山县志》卷4,《职官·列传(知县)·周行传》,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初编》第11辑,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第444页。明代广东地方官收受“例钱”或“例金”的最早时间、具体情形等尚待考证,目前可以明确的是互市贸易中的“例钱”“例金”显然属于灰色收入,对此品节正直、为官清廉的陈燮和周行都坚拒不受。从黄仲昭的视角来考察,“例钱”“例金”也就是“报水钱”。这类名目的钱财,自成化以至隆庆可能一直延续存在,与抽分制是否实施并无关联。然而,“报水”一词始见于何时、何处尚不明确,目前仅能追溯至弘治十六年。
接着从相关事例来看,中外海商通过贿赂市舶太监换取非法贸易的机会,也类似于海防官员收受“报水”后纵容商船进出港口交易的行为。
何乔新,成化四年三月至九年正月(1468—1473),任福建按察司副使。(11)《明宪宗实录》卷52,成化四年三月壬申;卷112,成化九年正月癸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1055、2175页。史载:“典番舶中官死,镇守太监分其余财,遗三司,先生力辞不得,乃受而输之库。”(12)[明]蔡清:《椒丘先生传》,载何乔新:《椒丘文集》,《外集》,《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50册,第552页。朱英,成化五年六月至七年十一月(1469—1471),任福建右布政使。(13)《明宪宗实录》卷68,成化五年六月己巳,第1356页;卷98,成化七年十一月庚戌,第1865页。史载:“提督市舶中官死,镇守太监分其余赀,遗藩臬,公力辞不能却,乃受而输于官。”(14)[明]何乔新:《椒丘文集》卷29,《神道碑·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赠荣禄大夫太子太保朱公神道碑》,《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50册,第480—481页。福建的市舶司专为琉球来华朝贡而设,市舶太监的余财可能部分来自与琉球互市贸易中的灰色收入。尽管成化时期明廷并不对互市贸易征税,但是地方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已经存在非法索取某种钱财的情形,对此朱英、何乔新的拒收举动也被视作清廉高洁的例证。
陈选,自成化十八年(1482)七月起任广东右布政使,二十年(1484)正月升左布政使。(15)《明宪宗实录》卷229,成化十八年七月丙戌,第3928页;卷248,成化二十年正月己酉,第4202页。二十一年(1485)五月,“番人马力麻与海商通贩,诡称苏门答剌国使臣,眷受其贿,不问,选发其伪。”(16)万历《广东通志》卷13,《藩省志十三·名宦·陈选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7册,第336页。番商马力麻假冒朝贡使臣,通过贿赂市舶太监韦眷从而非法与海商贸易,结果遭到陈选揭发。十一月十四日,陈选又奏曰:“据番禺县呈,鞫犯人黄肆招称,县民王凯父子招集各处客商,交结太监韦眷,私出海洋通番交易,谋财杀人,惊扰乡村,至今屯聚未散。”(17)《明宪宗实录》卷272,成化二十一年十一月辛酉,第4590—4591页。由此可知,地方商人通过向韦眷行贿来非法组织海外贸易,而且在韦眷的贪腐纵容下还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同时走私海商的不法行为也成为地方社会的安全隐患之一。
刘缨,弘治四年至六年(1491—1493),任巡按广东监察御史。(18)[明]雷礼辑:《国朝列卿纪》卷52,《刘缨传》(《续修四库全书》第5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4页)载,“辛亥出按广东,癸丑还朝”,可知刘缨任巡按广东监察御史的时间为弘治四年至六年。史载:“辛亥再奉命按广东,广南并海有列岛曰澳,番舶交易之地……豪民张政者,先窜名番舶,商海外诸国致货,直数十万,夤结中人监舶者,假以公牒,得捕盗海上,凭藉声势张甚。”(19)[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86,《刑部三·刘缨传》,《续修四库全书》第1170册,第64页。最终,刘缨将张政绳之以法。由此可知,张政能够冒名番商前往海外贸易也应该是贿赂市舶太监的结果。
盛洪,自弘治十五年(1502)起任广东按察副使(海道副使)。(20)万历《广东通志》卷10,《藩省志十·秩官·按察副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7册,第256页。为官期间“厘宿弊,严条约。先是通番买港之徒,夤缘假藉骚扰驿传,至是屏绝。市舶中官利通私货,以黄金百斤暮夜馈之,坚拒不纳……尝斩捕海贼千人,又上章论通番奸弊及保安事宜,悉见嘉纳。遇例裁革,归。寻以海道旧事,檄召赴广,卒于道。超擢山东按察使,已不及矣”。(21)[明]方鹏:《昆山人物志》卷4,《盛洪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93册,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第553页。又据《明武宗实录》载:正德四年闰九月戊辰(初九),“升广东按察司副使盛洪为山东按察使”。(22)《明武宗实录》卷55,正德四年闰九月戊辰,第1233—1234页。从中可以得出,盛洪约在弘治十五年至正德四年任广东按察副使,在职期间严禁“通番买港之徒”的不法行为,而受贿纵容商人“买港”的正是市舶太监。
从以上列举陈燮、陈选、刘缨、盛洪、周行等人的事例可以得出,成弘时期广东市舶司管辖的互市贸易中,既存在索取“例钱”“报水钱”等名目钱财的行为,也有受贿后令中外海商非法交易的情况,而背后主要的受贿纵容者正是提督市舶太监,至隆庆时期“例金”也依然存在。再从朱英、何乔新的事例来看,成化时期福建可能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只不过具体细节尚待考证。
嘉靖时期此类行为仍然屡有发生,例如,葡萄牙海商载货前往广东沿海,通过贿赂海防官员从而获得交易的地点。“嘉靖三十二年,舶夷趋濠镜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暂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栢徇贿许之。”(23)万历《广东通志》卷69,《外志四·番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8册,第700页。暂借土地晾晒贡物是虚言,其真实意图是通过行贿,借此获得商品交易地点或贸易中转站。约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八月,“时佛朗机夷违禁潜住南澳,海道副使汪栢受重赂纵臾之,以忠曰:‘此必为东粤它日忧’,力争弗得,寻擢右布政使。”(24)万历《广东通志》卷13,《藩省志十三·名宦·丁以忠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7册,第332页。《丁以忠传》还记载:“时征何亚八、郑宗兴诸贼,运筹裕饷,克成厥功。”又据《明世宗实录》(卷413,嘉靖三十三年八月乙未,第7191页)记载,朝廷论“广东擒剿海寇功”即是针对何亚八等番徒。笔者推测丁以忠此言的大致时间稍晚于嘉靖三十三年八月。丁以忠任广东右布政使的时间为嘉靖三十四年。(25)万历《广东通志》卷10,《藩省志十·秩官·右布政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7册,第250页。稍早之前,葡萄牙海商违禁潜住南澳岛显然是为贸易而来,汪栢受贿后纵容其继续停留。从动机、过程与结果来看,汪栢通过受贿令葡萄牙海商居留濠镜澳、南澳岛的行为也可视作“买港”。嘉靖三十三年,归有光作《论御倭书》曰:“在永乐之时,尝遣太监郑和一至海外,然或者已疑其非祖训禁绝之旨矣。况亡命无藉之徒违上所禁,不顾私出外境下海之律,买港求通,勾引外夷,酿成百年之祸。”(26)[清]孙岱:《归震川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49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78页;[明]归有光:《归先生文集》卷3,《书·论御倭书》,《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72册,第42页。从归有光的视角来看,“买港求通”的行为早在永乐时期就已存在,此后竟延续百年之久。
杨宜,嘉靖“三十三年,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提督浙直军务,三十四年致仕”。(27)[明]雷礼辑:《国朝列卿纪》卷105,《敕使并巡抚浙江尚书侍郎都御史卿年表》,《续修四库全书》第523册,第684页。俞大猷曾上书杨宜说:
市舶之开,惟可行于广东,盖广东去西南之安南、占城、暹罗、佛郎机诸番不远,诸番载来乃胡椒、象牙、苏木、香料等货,船至报水,计货抽分,故市舶之利甚广。数年之前有徽州、浙江等处番徒,勾引西南诸番前至浙江之双屿港等处买卖,逃免广东市舶之税。(28)[明]俞大猷:《正气堂全集》卷7,《揭·呈总督军门在庵杨公揭二首·论海势宜知海防宜密》,载《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65册,第142—143页。
对于正嘉时期广东征收市舶税的具体情形,不妨参照相关史料之后,再对俞大猷的此番言论进行分析。嘉靖四十三年(1564),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庞尚鹏上疏曰:
广州南有香山县,地当濒海,由雍麥至蠔镜澳,计一日之程,有山对峙如台,曰南北台,即澳门也。外环大海,接于牂牁,曰石峡海,乃番夷市舶交易之所。往年夷人入贡附至货物,照例抽盘,其余番商私赍货物至者,守澳官验实申海道,闻于抚按衙门,始放入澳,候委官封籍,抽其十之二,乃听贸易焉。(29)[明]庞尚鹏:《百可亭摘稿》卷1,《奏议·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9册,第130页。
广东地方官对贡船与随之而来的番商有所区分,进贡附搭货物比照前例抽盘,其余番商私带货物实行抽分。“照例抽盘”是指:“弘治间定,凡番国进贡,内国王、王妃及使臣人等,附至货物,以十分为率,五分抽分入官,五分给还价值,必以钱钞相兼。”(30)万历《大明会典》卷113,《礼部七十一·给赐四·给赐番夷通例》,《续修四库全书》第791册,第144页。又据嘉靖《广东通志初稿》载:
若国王、王妃、陪臣等附至货物,抽其十分之五入官,其余官给与之值,暹罗、爪哇二国免抽,其番商私赍货物入为易市者,舟至水次,官悉封籍之,抽其什二,乃听贸易。(31)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30,《番舶》,《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史部第38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16—517页。“水次”意为码头或港口。
自弘治年间起,明廷对朝贡使节附搭货物以50%的比例抽分入官,另外50%则给予相同价值的钱和钞。此类抽分针对的是贡船及贡使的附搭货物,自然不能与随之而来的番舶相提并论。正德四年,抽分制推行以后,依据旧例暹罗、占城、三佛齐、苏门答剌、锡兰山等五国的“正船并无抽分”,“旧例国王进贡,其王妃、王子、使臣人等搭货或上进者为正船,若余船皆以商论,此五国载入《会典》,它不载者不敢比例”。(32)万历《广东通志》卷69,《外志四·番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8册,第700页。尽管落实到不同朝贡国时略有差异,但从中仍可以看出,抽分制针对的是随正船(贡船)而来的番舶。
正德四年,总督两广军务右都御史陈金奏请对番舶以30%的比例抽分,十二年(1517)抽分比例降至20%,因此庞尚鹏的奏疏与地方志中所载抽其20%应该发生于正德十二年。从中也可见得,从番舶入港到“封籍”再到“抽分”,市舶税的征收存在一个较为完整的流程,其中征税的具体细节,据万历《广东通志》载:
番商舟至水次,往时报至督抚,属海道委官封籍之,抽其十二,还贮布政司库变卖或备折俸之用,余听贸易。隆庆间始议抽银,檄委海防同知、市舶提举及香山正官三面往同丈量、估验,每一舶从首尾两艕丈过阔若干、长若干,验其舶中积载出水若干,谓之水号,即时命工将艕刻定,估其舶中载货重若干、计货若干、该纳银若干,验估已定即封籍。其数上海道转闻督抚,待报征收如刻记后水号,征有不同即为走匿,仍再勘验船号出水分寸又若干,定估先匿货物若干、赔补若干,补征税银仍治以罪,号估税完后贸易听其便。(33)万历《广东通志》卷69,《外志四·番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8册,第701—702页。
番舶进入港口以后,由负责税务的官员测量船舶的长宽尺寸,查验船舶的吃水深浅,结果称为“水号”,同时令工匠将其镌刻在船身,还要估测载货重量、货物种类、纳税数额,查验与估测完毕便可封钉、登记。而后,征税官员将测算数据上报海道副使,再转呈巡抚、总督,批复后依据“水号”及其它数据征收20%的货物税。抽分制推行后,起初对番舶征收的是实物,隆庆年间才改为征银,征税官员抽分的具体做法有丈量、估验,从中也未见有除去抽分(货物税)之外的其它税种。此外,葡萄牙(佛郎机)不属于明朝的朝贡国,因此官方允许葡萄牙人载货前来广州沿海岛屿贸易属于特例,不过也同样适用于抽分制征收货物税。(34)据1556年1月15日(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初四),莱奥内尔·德·索札(Leonel de Sousa)在印度柯枝港(科钦)写给唐·卢伊斯王子(D.Luís)的信件称,他辗转中国三载,曾经与广东海道副使“商议的结果是,我们必须遵照习惯按百分之二十纳税并按国王的恩准在华完纳……除支付上述税率外,无其他苛捐杂税”。此处“国王”指明朝皇帝,按习惯纳税20%显然是抽分制的税率,此外无其它杂税。参见金国平编译:《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7、218—219、225页。
再回到俞大猷所说的“船至报水,计货抽分”,此言显然是对广东市舶税征收方式与流程的高度概括,而对其中的“报水”一词则较难理解。笔者推测存在两种可能:第一,可能类似于黄仲昭将“例钱”称作“报水钱”,因为相应官员索取番舶“例钱”“例金”的行为自成化至隆庆一直存在,俞大猷可能注意到了这种灰色收入并提议将其合法化;第二,结合征税细则与流程来探求“船至报水”概括之前的某些部分,“船至”应完整表述为“舟至水次”,也就是番舶进入港口,“报水”可能是测量“水号”以及据此和相关数据征税等具体做法的简化称谓,因为封籍之后需要将“水号”与相关数据逐级上报,批复后番舶征税如数与否,也主要是依据“水号”来确定。
本节所述“报水”的产生基础存在两条路径:其一,“报水钱”产生于互市贸易中随朝贡使团而来的番舶,可能是地方官借核算船货时索取的钱财,为地方相应官员的灰色收入,其起源时间不迟于成化时期;其二,与收受“报水”买港相类似,市舶太监、海防官员受贿纵容中外海商非法交易的行为可能早已有之,只不过具体时间尚待明确,目前能够援引史料论述的是,自成化起屡有发生,主要的收取者是市舶太监,兼及海防官员。
二、丁桐受贿案与“报水”量刑入法
明代中后期东南沿海走私贸易盛行,中外海商通过贿赂海防官员换取非法出入港口的权利,二者相互勾结成为东南海防的重要隐患之一。据董应举说:“查得嘉靖二十六年,福清冯淑等三百四十人泛海通番,朝旨查劾海道官,诏用朱纨为福浙巡抚。”(35)[明]董应举:《崇相集》,《议二·漫言(止言福海)》,《明别集丛刊》第4辑第52册,第214页。嘉靖二十六年(1547)七月初八,明廷为强化浙江、福建两省海防,特任命朱纨“巡抚浙江兼管福建福、兴、建宁、漳、泉等处海道”。(36)《明世宗实录》卷325,嘉靖二十六年七月丁巳,第6018—6019页。二十七年(1548)七月初一,又改朱纨为“巡视浙江兼管福建沿海地方提督军务”,“凡一切政务巡按御史如旧规行”。(37)参见《明世宗实录》卷338,嘉靖二十七年七月甲戌,第6167—6168页;[明]朱纨:《甓余杂集》卷1,《玉音·再改巡视》,《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44册,第365页。朱纨任内通过厉行海禁来强化海防,严厉打击各类不法行为,其中就有海防官员收受财物令商船非法进出港口的案件。
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丁桐与姚翔凤受贿案首先由巡按福建监察御史金城奏闻明廷,据《明世宗实录》载:
佛郎机国夷人入掠福建漳州,海道副使何乔御之,遁去。巡按御史金城以闻,且劾浯屿指挥丁桐及去任海道副使姚翔凤受金黩货,纵之入境,乞正其罪。诏以桐及翔凤令巡按御史执来京究治,防禁事宜,兵部详议以闻。(38)《明世宗实录》卷330,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癸巳,第6064—6065页。
丁桐与姚翔凤二人滥用职权,收受葡萄牙海商和漳州、泉州海商财物,令其非法出入沿海贸易。万历癸酉(万历元年、1573)《漳州府志》载:
二十六年,有佛郎机夷船载货在于浯屿地方货卖,漳、泉贾人辄往贸易,巡海道柯乔、漳州知府卢璧、龙溪知县林松发兵攻夷船不得,通贩愈甚。时新设总督闽浙都御史朱纨厉禁,获通贩者九十余人,遣令旗、令牌行巡海道柯乔、都司卢镗就教场悉斩之。(39)[明]罗青霄等修纂,陈叔侗点校:《漳州府志》卷12,《漳州府·杂志·兵乱》,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72—373页。
万历癸丑(万历四十一年、1613)《漳州府志》载:
嘉靖中,有佛郎机船载货泊浯屿,漳龙溪八九都民及泉之贾人往贸易焉。巡海道至,发兵攻夷船,而贩者不止。总督闽浙都御史朱纨获通贩者九十余人,悉斩之,而海禁严。(40)万历《漳州府志》卷9,《赋役志下·洋税考》,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影印本,第603页。
结合地方志的记载可以得出,丁桐、姚翔凤利用身为海防官员的职权,通过私受财物让葡萄牙海商的货船停泊在浯屿港,漳州与泉州二府海商得以前往浯屿交易,也应当是向丁桐等海防官员行贿的结果。(41)金国平编译:《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第208页)载:“把总某与葡萄牙人交易,并受贿允许当地商人去与葡萄牙人交易。他这样做,却向朕奏报说葡萄牙人是盗贼,前来朕的疆土专为抢劫……朕罚尔等戴赤帽发边。”金国平先生将把总注释为丁桐。这句话原文来自外文文献《中国事务及其特点详论》的第26章,本章简要记录了现已失传的嘉靖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明世宗下诏处理朱纨等人的圣旨,这句话即是源于外文记录的这道圣旨。丁桐、姚翔凤等人纵容中葡海商在浯屿岛贸易,这间接导致了闽东南海域安全遭受冲击。金城奏曰:“据漳州府报称,佛郎机夷人先于嘉靖二十六年四月内入境劫掠,去来无常,本年九月内又复入境劫掠”,经海道副使柯乔调集官兵攻防,“于闰九月初二日渐遁去”。(42)《都察院题本为夷船出境事》(嘉靖二十七年十月十八日),载朱纨:《甓余杂集》卷6,《章疏五》,《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44册,第503页。葡萄牙海商向海防官员行贿以换取出入港口贸易的权利,是东南沿海走私贸易的主要形式之一,此类行为可能发端于正德时期,而后一直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发生,海禁的松弛成为其滋长的土壤。
嘉靖中唐枢言:“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43)[明]胡宗宪:《筹海图编》卷11,《经略一·叙寇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4册,第278页。中葡海商与海防官兵因非法利益的结合构筑了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网络,此时海禁政策的严或弛便成为了走私贸易网络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嘉靖四十三年,福建巡抚谭纶回籍守制时曾上疏“宽海禁”曰:“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者愈众,私通不得即攘夺随之。”(44)《明世宗实录》卷538,嘉靖四十三年九月丁未,第8719页;[明]谭纶:《谭襄敏奏议》卷2,《条陈善后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9册,第632页。朱纨赴任后厉行海禁遂使海商“私通不得”进而转为海寇劫掠地方。据《明史》载:“至二十六年,朱纨为巡抚,严禁通番。其人无所获利,则整众犯漳、泉之月港、浯屿。”(45)《明史》卷325,《外国六·佛郎机传》,第8432页。总的来看,丁桐、姚翔凤的受贿纵容使得走私贸易网络得以发展,而朱纨的严禁则导致海禁政策之中官方与海商围绕贸易的博弈激化为武装冲突。葡萄牙海寇的劫掠行为严重威胁着东南海域安全,如何强化海防、保障海域秩序成为此时浙、闽地方官的首要事务之一,因此丁桐与姚翔凤受贿案引起了明廷及地方官的高度重视。
朱纨《甓余杂集》收录了都察院汇总丁桐案处理意见的题本,文中较为完整地记载了嘉靖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都察院左都御史屠侨等人的奏疏与十八日明世宗批复的圣旨,以及此前明世宗令都察院究问丁桐等人的圣旨,文中也引述了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金城关于该案的奏疏和十一月十六日明世宗批复的圣旨。据都察院题本载:
案照先准兵部咨,巡按福建御史金城奏:……臣又访得夷人初入境内,夫敢肆然直入,先讬接济之徒上下打点方敢入境。臣闻浯屿水寨把总指挥佥事丁桐受伊买港沙金一千两,见被洪惟统告发,按察司提问及访得先任海道副使姚翔凤贪残无厌、法纪尽隳,得受把总王畿等并卖放番徒田瑞器等金银,已该前巡按御史赵应祥纠劾,似此上下通同,惟财是竞,通番之徒遂公然田入而不知禁,似难轻纵,等因。奉圣旨:夷寇入境,地方官交通纳贿,好生不畏国法,丁桐并姚翔凤着各该巡按御史提解来京究治,防禁事宜,兵部详议了来说,钦此。(46)《都察院题本为夷船出境事》(嘉靖二十七年十月十八日),载朱纨:《甓余杂集》卷6,《章疏五》,《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44册,第503—504页。
从金城的奏疏中可以简要勾勒出,闽东南沿海走私贸易网络建构的过程。葡萄牙海商初来沿海之时,先是委托“接济之徒”也就是沿海的走私海商来引介,通过“上下打点”向海防官兵行贿以获取出入港口贸易的权利,当然也会存在海防官兵主动索贿纵容的情况。(47)金国平编译:《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第198—199页)载:“舰队的船长们得知以后,乘着夜色秘密派人来说,要想得到货物,先送点东西过来。得到这一口信后,葡萄牙人喜出望外,接着按他们的口信准备了一份厚礼并照着他们的嘱咐乘着夜色给他们送去。此后,葡萄牙人得到了许多货物,对此官老爷们佯装不知,庇护商人。因此,那一年,即(15)48年一直以此方式进行贸易。”1548全年对应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而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丁桐、姚翔凤二人受贿就已经事发被捕,倘若外文记录的时间正确,那么此处主动索贿的海防官员还应该另有其人。收取买港财物后,海防官员有时还会提供出入港口的凭证。(48)金国平编译:《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第49—50、199页)载:“据当时被捕者之一的‘喇卜的’(Gauspar Lopes)于1551年10月14日从梧州监狱内发出的函件,‘我们有大官的引票(patente)及金门(Cumay)官员给的中国国王的令旗’。”金国平先生将大官注释为海道副使姚翔凤,金门官员注释为浯屿指挥丁桐。其收受“买港沙金”的对象,既有葡萄牙海商,也有沿海的海商。金城将丁桐、姚翔凤贪腐事件奏报明廷后,明世宗下旨直接将二人押解入京处理。然而,明廷的高度重视却并未令海防官兵恪尽职守,此类受贿买港的行为依然存在。据《明世宗实录》载:
满喇伽国番人每岁私招沿海无赖之徒,往来海中贩鬻番货,未尝有僣号流劫之事。二十七年,复至漳州月港、浯屿等处,各地方官当其入港,既不能羁留人货疏闻庙堂,反受其私赂纵容停泊,使内地奸徒交通无忌。(49)《明世宗实录》卷363,嘉靖二十九年七月壬子,第6471页。
嘉靖二十七年,满喇伽番商得以又到漳州月港、泉州浯屿港等地非法贸易,正是地方官收取贿赂钱财后的结果。
海防官员的贪腐行为助长了东南海洋的走私贸易,从而成为海域安全的重要隐患之一。那么该如何处置丁桐等海防官员,并且制止此类行为再次发生呢?巡按福建监察御史金城和巡按浙江监察御史裴绅分别将丁桐、姚翔凤押解到京后,明世宗下旨:“丁桐等都察院究问明白来说,钦此。”都察院审问完毕后,嘉靖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屠侨奏曰:
丁桐纵容土俗哪哒通番,屡受报水,分银不啻几百,交通佛郎夷贼入境,听贿买路砂金遂已及千,海寇秉此纵横,居民数被剽掠,所据本犯情重,律轻不足以严儆戒。(50)《都察院题本为夷船出境事》(嘉靖二十七年十月十八日),载朱纨:《甓余杂集》卷6,《章疏五》,《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44册,第504页。
海道副使姚翔凤为文职官员,已经由御史赵应祥提出弹劾,正在等候进一步处理,因此屠侨的奏疏主要是针对如何处理丁桐。金城奏疏中说丁桐收受“买港沙金”,等到屠侨上奏时既说丁桐“屡受报水”,又说其“听贿买路砂金”。“报水”现身于奏疏之中存在两种可能:其一,嘉靖十二年(1533)四月初二至九月二十八日,屠侨曾任广东右布政使,(51)《明世宗实录》卷149,嘉靖十二年四月甲戌,第3422页;卷154,嘉靖十二年九月丁卯,第3494页。此时上奏比照互市贸易中广东地方官收取的“例钱”或“例金”,从而将丁桐收受的钱财称作“报水”;其二,嘉靖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至十五年(1536)二月初二,屠侨曾任福建左布政使,(52)《明世宗实录》卷154,嘉靖十二年九月丁卯,第3494页;卷184,嘉靖十五年二月丁亥,第3899页。对闽海事务有一定了解,或许在审问丁桐时发掘出更多细节,也可能是地方官员已经将收取商船的财物称作“报水”。奏疏中的“哪哒”意为船主或海商。(53)聂德宁:《明代嘉靖时期的哪哒》,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2期,第104—109页。丁桐收取“报水”的对象既有葡萄牙海商,也有漳、泉海商(海寇)。
对于如何处治丁桐,屠侨紧接着在奏疏中说:
查得《问刑条例》一款,汉人交结夷人,互相买卖、借贷、诓骗财物,引惹边衅,及占住苗寨,教诱为乱,贻患地方者,俱发边卫永远充军。为照例称,汉人不过腹里军民无有职官责守,其称借贷、诓骗亦止于结交、买卖等情,若有引惹边衅贻患地方者,尚拟边军永远,严遣示惩。今丁桐身为海寨防守之官,肆行受财枉法之私迥异于结交、诓贷,其引寇贻患情犯尤重,合无比照前例,定发边卫永远充军,子孙不许承袭,庶昭奸贪不法之戒。(54)《都察院题本为夷船出境事》(嘉靖二十七年十月十八日),载朱纨:《甓余杂集》卷6,《章疏五》,《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44册,第504页。
据弘治十三年(1500)《问刑条例》载:“川、广、云、贵、陕西等处,但有汉人交结夷人,互相买卖借贷,诓骗财物,引惹边衅,及潜住苗寨,教诱为乱,贻害地方者,俱发边卫永远充军。”(55)曲英杰点校:弘治《问刑条例》,刘海年、杨一凡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2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44页。屠侨援引《问刑条例》作为惩治丁桐的法律依据,同时突出“受财枉法”与“引寇贻患”表明其罪行深重。对丁桐受贿案的处理也反映出当时法律的不足,为防止此类行为再次发生,屠侨接着奏议以丁桐案为例作为今后处治类似案件的原则。据都察院题本载:
再照近年以来东南番贼、海寇,如浙江、福建沿海等处所在骚然为患,凡以例处极刑并边卫充军者,止严于下海通番之人,而守御等官有犯交通接引者未有定法,以故禁防先弛于有职人员,无以镇压于内外奸宄,海道之不靖实由于此。近日巡视都御史朱纨并前巡按御史金城屡有陈奏者,亦欲以振海防于玩废之余,而豫为之图耳,若不严加处治,将来祸患叵测。合无自今以后,凡系海防官员有犯,除真犯死罪外,有如丁桐赃犯深重者,悉照前例拟断总督、海道等官,不能查究纵容者,事发一体从重参奏罢黜,等因。嘉靖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本院左都御史屠侨等奏。本月十八日奉圣旨:丁桐定发边卫充军,议处海防事宜都依拟行,钦此。(56)《都察院题本为夷船出境事》(嘉靖二十七年十月十八日),载朱纨:《甓余杂集》卷6,《章疏五》,《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44册,第504—505页。
明代以往的律例严禁濒海民众私自下海与外国贸易,而对海防官员非法令商船进出港口交易,却并没有专一对应的法律来惩治,由此导致海防官员的贪腐行径成为海防废弛的重要原因之一。鉴于此,朱纨、金城屡次上奏预为谋划。都察院审理丁桐案结束后,屠侨也奏议今后再发生类似案件时,由总督、海道等官员比照《问刑条例》中的条款查处。而后,明世宗降旨将丁桐发配边卫充军,屠侨所奏其它事项也予以批准。明廷对丁桐受贿案的处治结果便成为此后处理类似案件的重要依据,并以明世宗皇帝圣旨的效力延续实行。
丁桐受贿案是“报水”量刑入法的重要契机,等到嘉靖二十九年(1550)重新修订《问刑条例》时,修纂官员就将海防武职收受“报水”的行为正式列入。据《重修问刑条例》载:
各该沿海省分,凡系守把海防武职官员,有犯听受通番土俗哪哒报水分利金银,至一百两以上,名为买港,许令船货入港,串同交易,贻患地方,及引惹番贼海寇出没,戕杀居民,除真犯死罪外,其余俱问受财枉法满贯罪名,比照川、广、云、贵、陕西等处汉人交结夷人,互相买卖,诓骗财物,引惹边衅,贻患地方事例,问发边卫,永远充军,子孙不许承袭。(57)曲英杰点校:嘉靖《重修问刑条例》,《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2册,第481页。
明代法律文献中的“报水”仅指收取的钱财,海防武职官员收受“报水”行为的正式罪名实为“买港”,对此类罪行的描述、量刑也正是来源于屠侨的奏疏。“买港”针对的是海防武职受贿后纵容外国海商非法进出港口交易,兼及沿海的海商,真犯以死罪论处,其余以受财枉法满贯量刑惩处,并且比照弘治《问刑条例》中的事例发配边卫永远充军。“报水”量刑入法以后,嘉靖四十二年(1563)重刊本《读律琐言》、万历十三年(1585)《真犯死罪充军为民例》、万历十五年(1587)《大明会典》中都有大致相同的记载,三处均将收受“报水”作为一种滥用职权的行为。(58)[明]雷梦麟著,怀效锋、李俊点校:《读律琐言》卷15,《兵律·关津·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75页;杨一凡点校:万历《真犯死罪充军为民例》,《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2册,第722—723页;万历《大明会典》卷167,《刑部九·律例八(兵律二)·关津》,《续修四库全书》第792册,第48页。
“报水”列入《重修问刑条例》以后,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月初九,南京湖广道御史屠仲律上疏曰:“臣闻倭之入也,岂尽无军之患,盖有军而移入便地者矣,有失于巡哨者矣,甚有买渡报水受其钩饵者矣。”(59)《明世宗实录》卷422,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壬寅,第7313页。屠仲律此言表明有些海防官兵甚至向日本商船收取“报水”,而后令其入境。地方官对海防官员收取“报水”的惩治,多以正式罪名“买港”记录。嘉靖三十八年(1559),福建巡抚王询等言:“黄崎、漳港等倭突攻福清、长乐,逼近会城……分守参将王麟受财买港”;十一月初十,明世宗下诏将王麟革职并“付按臣逮问”。(60)《明世宗实录》卷478,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丁丑,第7992页。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一月初三,经福建巡抚刘焘奏准,“听勘参将王麟谪戍”,也就是发配边卫充军。(61)《明世宗实录》卷490,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乙丑,第8150页。王在晋《越镌》记录了约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浙江审理的四起通番案。第二件为“定海擒获奸商功罪之案”,严翠梧等人的同伙林义“报关出洋而去”,在杭州购置违禁货物以后,便秘密雇佣船户马应龙、洪大卿、陆叶的海船共三只,“诈称进香,乘夜偷关驾至普陀,适逢潮阻,哨官陈勋等驾船围守,应龙等辄乘潮而遁,哨兵追之,乃索得叚绢布疋等物,纵之使行”。王在晋说:“有陈勋等之贪贿也,众商以倭为市,而众兵以商为市。……国家养兵防海,乃索买路之金钱,作海门之垄断,陈勋等不遣不足以告诫于三军。”接着,王在晋在第三件“普陀擒缉奸商功罪之案”中说:“官军利其贿,惟恐商贩之不通倭夷;利其货,惟恐商船之不至。”陈勋等哨官索取商船货物后令其非法出海的行为,适用于“买港”罪行惩治。浙江地方官将“陈勋、王本和、朱应纹、王金,以私受买港,受财枉法论”。王在晋也说:“普陀一带为入倭要路,商船入倭多由官兵卖放,谨其防闲,勤于哨探,此可不择总、哨之官乎。……受贿者若陈勋、王本和诸人,以买港遣。”(62)[明]王在晋:《越镌》卷21,《杂纪·通番》,《明别集丛刊》第4辑第78册,第287—292页。“官兵卖放”也就是海防官兵收取财物后令商船非法出入港口,此类行为正是收受“报水”的结果。王在晋还说:“计通倭之船未有不由港门而出,则未有不通同守把官兵而得,扬舲下海者马应龙等不贿陈勋,应龙岂得渡乎?”为禁止商民通番,王在晋规定:商船“经过关津私自放行者,罪及关吏;出由河港受贿纵脱者,罪及守把。……倘商船至彼纵放出洋,罪在参、游、总、哨,一体议处,著为功令”。(63)[明]王在晋:《越镌》卷20,《议·禁通番议》,《明别集丛刊》第4辑第78册,第273—274页。从浙江处理的定海、普陀两地通番案中可以得出,对于海防官兵索取财物的行为,也即收取“报水”的行为,地方官将之称为“买港”。
本节所引用的史料,其描述收取海商财物的主体为海防官员,“报水”指钱财,“屡受报水”也就是指“受金黩货”“受伊买港沙金”“听贿买路砂金”或者索取货物等。“报水”一词不能涵盖海防官员收受财物后,纵容海商非法进出沿海港口的行为,法律文献中对此类行为的正式罪名为“买港”。从闽、浙地方官处理该类案件的具体实践来看,王麟“受财买港”、陈勋等人“以买港遣”,官方文献中对海防官员索取财物(“报水”)的行为多称为“买港”。
三、“引税”并不由“报水”演化而来
官方与海寇争夺海洋利益,在史料中有踪迹可寻。嘉靖三十九年(1560),曾任阅视直浙军情通政使司右通政的唐顺之奏曰:
舶之为利也,譬之矿然。封闭矿洞,驱斥矿徒,是为上策;度不能闭,则国收其利权而自操之,是为中策;不闭不收,利孔洩露以资奸萌,啸聚其人,斯无策矣。今海贼据峿屿、南澳诸岛,公然擅番舶之利,而中土之民交通接济,杀之而不能止,则利权之在也。宜备查国初设立市舶之意,毋洩利孔使奸人得乘其便。(64)参见《明世宗实录》卷480,嘉靖三十九年正月丙子,第8019—8020页;[明]唐顺之:《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外集》卷2,《奏·条陈海防经略事疏》,《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74册,第552页。
唐顺之认为关闭市舶司驱逐海商是上策,不能关闭便应当由国家掌握番舶利权,倘若既不关闭也不征税,那么番舶利益便会为海寇所窃取,而且还会影响沿海秩序的稳定,因此唐顺之倾向于开设市舶收回利权。万历《漳州府志》卷9《洋税考》开篇也引述了唐顺之的这一段话,但是地方志的编纂者认为“市舶之与商舶,其说稍异”。市舶是“诸夷船泊吾近地,与内地民互为市”,如广东濠镜澳(澳门);而商舶则是海商载货“径望东西洋而去,与海岛诸夷相贸易”,如福建海澄(月港)。(65)万历《漳州府志》卷9,《赋役志下·洋税考》,第604—605页。郑晓也曾说:“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通华夷之情,迁有无之货,收征税之利,减戍守之费,又以禁海贾抑奸商使利权在上,罢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内诇,海上无宁日矣。”(66)[明]郑晓:《吾学编》卷67,《皇明四夷考》卷上,《日本》,《续修四库全书》第425册,第180—181页。郑晓此言也表明开设市舶、禁绝海商可以使官方掌握番舶利权,而关闭市舶则会导致海寇非法取得番舶利益。嘉靖中后期开海思潮迸发,有一部分官员主张有限开放海禁,也即开设市舶征收税银,希望借此消解部分海外贸易需求,以达到制止走私贸易和维护海域安全的目的。可是,主张开海的官员对此认识较为模糊,没有涉及到具体的管理措施,因而无法继续深入研究。那么“引税”与“报水”之间又存在什么关系呢?以下不妨接着对海澄贸易管理体制进行考察。
大体上来看,自洪武立国至隆庆开海前,官方是禁止私人出洋贸易的,等到明穆宗在位时,私人前往海外贸易才部分合法化。“隆庆改元,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海”。(67)[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31页。隆庆初年(1567—1569),明廷有条件有限制地局部开放海禁,将允许出洋贸易的海商群体限制为福建漳州与泉州二府,对内准许海商在福建、浙江、广东沿海贸易,对外许可海商前往的贸易区域是东、西二洋,而且明廷在严禁海商与日本有任何贸易往来的同时,也禁止一切外国商船载货前来海澄贸易。海洋政策调整以后,官府将“船引”作为海商出洋贸易的许可证,凡是前往沿海或海外均需申请相应类型的“船引”。万历二十五年(1597),福建巡抚金学曾奏曰:“福建漳、泉滨海人藉贩洋为生,前抚涂泽民议开番舡,许其告给文引,于东西诸番贸易,惟日本不许私赴。”(68)《明神宗实录》卷316,万历二十五年十一月庚戌,第5899页。可见,涂泽民请开海禁之时就已经实施了船引制。开海选中的地点,“先是发舶在南诏之梅岭,后以盗贼梗阻,改道海澄”。(69)[明]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第132页。此语只载于《东西洋考》,而不见于万历癸丑《漳州府志》和崇祯《海澄县志》,因而开海地点变化的具体情形,有待进一步详考。
起初官府并不对海商征税,海澄洋税始于隆庆六年(1572)漳州知府罗青霄的建议。据万历元年序刻本《漳州府志》载:
隆庆六年,本府知府罗青霄建议:方今百姓困苦,一应钱粮取办里甲,欲复税课司官,设立巡拦抽取,商民船只货物及海船装载番货,一体抽盘,呈详抚、按,行分守道参政阴覆议。官与巡拦俱不必设,……又于濠门、嵩屿置立哨船,听海防同知督委海澄县官兵抽盘。海船装载胡椒、苏木、象牙等货,及商人买货过桥,俱照赣州桥税事例,酌量抽取。……候一二年税课有余,奏请定夺。转呈详允,定立税银则例,刊刻告示,各处张挂,一体遵照施行。(70)[明]罗青霄等修纂:《漳州府志》卷5,《漳州府·赋役志·财赋·商税附(新行事例)》,第190页。
罗青霄提议征税的动机是减轻百姓负担,而后福建巡抚殷从俭等仿照赣州桥税事例草创海澄洋税制度。据《东西洋考》载:“隆庆六年,郡守罗青霄以所部雕耗,一切官府所需倚办,里三老良苦。于是议征商税,以及贾舶。贾舶以防海大夫为政。”(71)[明]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第132页。海澄洋税征纳制度最初源于赣州桥税,赣州东、西二桥关厂主要征收“盐税”与“杂税”。针对过往盐船,由“分守道印发船票下府收税”,商船“过关者各赴委官处,照票纳银,给票一纸,名曰季票,如系下流新船,名曰小票”。官方依据船只大小征收税银不等,同时发放“船票”作为纳税凭据,而后商船“过关随于船头烙印斧记,收票缴道”。另外,还有面向载运物品征税的“各项货物抽税则例”。(72)天启《赣州府志》卷13,《榷政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2册,第490—492页。殷从俭等仿照赣州桥税事例征收船舶税与货物税(即后来的“水饷”“陆饷”),但是并未明确涉及“引税”。据万历四十一年序刻本《漳州府志》载:
万历三年,巡抚刘尧诲题请舶税充饷,岁以六千两为额,委海防同知专督理之,刊海税禁约一十七事(时海防同知沈植条陈)。……于时凡贩东、西二洋,鸡笼、淡水诸番,及广东高、雷州、北港等处商、渔船引,俱海防官为管给,每引纳税银多寡有差,名曰引税(东西洋每引纳税银三两,鸡笼、淡水及广东引纳税银一两,其后加增东西洋税银六两,鸡笼、淡水税银二两。万历十八年,革商、渔文引归沿海州县给发,惟番引仍旧)。(73)万历《漳州府志》卷9,《赋役志下·洋税考》,第606—608页。
官府有时会将“船引”统称为“商引”,稍加区分可知:东、西二洋“船引”称为“洋引”,再加鸡笼、淡水的“船引”也可并称为“番引”;沿海经商、打渔的“船引”又称作“商引”“渔引”。海防馆征收“引税”也就是向“船引”征税。除此之外,还有根据船舶尺寸征收的“水饷”,依据进口货物征收的“陆饷”,以及特别向自吕宋回船所征收的“加增饷”。
其征税之规:有水饷、有陆饷、有加增饷。水饷者,以船之广狭为准,其饷出于船商;陆饷者,以货之多寡计值征饷,其饷出于铺商。……加增饷者,东洋中有吕宋,其地无出产,番人悉用银钱……易货,船多空回,即有货亦无几,故商贩回澚征抽水、陆二饷外,属吕宋船者,每船另追银百五十两,谓之加增(后各商苦难输纳,万历十八年量减,止征一百二十两)。(74)万历《漳州府志》卷9,《赋役志下·洋税考》,第608—609页。
从地方志的记载中可知,海澄洋税制度沿袭了南赣地区管理内陆河运贸易的做法。(75)参见李庆新:《地方主导与制度转型——明中后期海外贸易管理体制演变及其区域特色》,载《学术月刊》2016年第1期,第27—29页。其中,海防馆征收的“陆饷”“水饷”明确来自“赣州桥税事例”,“加增饷”也可视为特殊意义上的货物税,三者均与“报水”无关。而且,海防馆征收四种洋税的时间也不尽相同,具体分为出港前征纳和返港后征纳。“引税”是海商出港前申请“船引”时征收的,“水饷”是商船出港前测量船只尺寸时征收的,“陆饷”为进口货物税是商船返港后向铺商征收的,“加增饷”则是回港后特别向从吕宋返航的商船征收的。
从府志中也可看出,“加增饷”的征收显然晚于船舶税与货物税(即后来的“水饷”“陆饷”),那么“引税”又是何时征收的呢?隆庆六年开征洋税时,没有明确见得征收“引税”。万历二年(1574),刘尧诲上奏提议对经过南澳岛的船只,“委文职一员兼同抽掣,如近日南赣事例,每货值银一两,该税若干”,将所得税银充作军饷。(76)[明]刘尧诲:《刘尧诲先生全集》卷2,《抚闽疏·谨陈善之后之策以戢兵端疏》,《四库全书存目丛刊》集部第128册,第394页。可见,此时刘尧诲管理海洋贸易也未超出赣州桥税的框架。万历二年十二月,刘尧诲奏议将商税题充军饷,其中提到“漳州府海澄等县船货商税”,从中也未见有“引税”。(77)刘尧诲抚闽时面临军饷短缺的情况,提议扩充军饷来源。参见《明神宗实录》卷32,万历二年十二月甲子,第764—765页;[明]张学颜等撰:《万历会计录》卷43,《杂课》,《续修四库全书》第833册,第170页;[明]刘尧诲:《刘尧诲先生全集》卷2,《抚闽疏·奉旨建言民情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8册,第394—395页。具体落实到福建地方,崇祯《海澄县志》载:“万历三年,中丞刘尧诲请税舶以充兵饷,岁额六千。同知沈植条海禁便宜十七事,著为令。”(78)崇祯《海澄县志》卷5,《赋役志二·饷税考》,《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30册,第364页。迄今未见沈植条陈十七事的详细记载,万历癸丑《漳州府志》仅收录一条“禁压冬议”,(79)万历《漳州府志》卷9,《赋役志下·洋税考》,第607页。因此尚不能把握相关细节。据李庆新先生研究,“引税”的征收始于万历三年刘尧诲请税舶充兵饷。(80)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21页。其实刘尧诲奏准海澄“船货商税”改充军饷,仅是将海防馆征收的船舶税与货物税定为“水饷”和“陆饷”,每年定额取银六千两用作福建的军费开支,此时并不包括“引税”。隆万之际,自殷从俭起,福建军饷“每岁大约止完十五六万上下不等,陆续查取福州等府县并海澄番舶商税牙货,岁约三万三千一百有零,相兼支用”。(81)[明]许孚远:《敬和堂集》卷6,《抚闽疏·议处海防疏》,明万历二十二年序刊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第17b页。其中,“海澄番舶商税”充作军饷显然是刘尧诲奏议的结果,而“引税”改充军饷的时间则要远迟于此。万历二十一年(1593)四月中旬,福建巡抚许孚远奏曰:
该抚臣赵参鲁、张汝济先后酌议增船增兵,岁约费饷二十八万九千六十余两,其所不敷,议以站剩及盐帮助饷,海船引税、南台等处商税、仓粮改折、寺田散佃,百计搜求,凑前止得银二十七万四千三十余两,尚不足一万五千余两之数。(82)[明]许孚远:《敬和堂集》卷6,《抚闽疏·议处海防疏》,第17b—18a页。
自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年(1589—1592),连续两任福建巡抚筹划加强海防,由此导致军饷开支骤增,地方官也借此提议扩充军饷来源,期间就将征收的“海船引税”用作军饷。在此之前,“海船引税”可能部分留作漳州地方经费开支。
囿于史料的局限,目前还不能得知“引税”开征的动机及具体情形,但是从隆庆六年殷从俭等人的做法来看,海澄洋税是从原有陆上税收系统延用变形而来。在明代官府准许的沿海采捕中,一般仅对船只征收船舶税和货物税,同时给予相应的纳税凭据作为许可,并未特别向船只颁发某种专门的许可证并征税。迟至万历二年,浙江已对沿海渔船征收“船税”“渔税”“盐税”“旗银”。其中,征收“旗银”已经类似于“引税”。(83)万历《绍兴府志》卷23,《武备志一·沿海渔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1册,第21页。明代史籍中未见广东地方官合法征收类似“报水”名目的入港费,因此福建也不会将“报水”合法化,再转变为出港前征收的“引税”落实到海澄。而且,“报水”有时候也指官兵驻防内河或沿海时索取的超出正规征税之外的钱财,对此则更没有合法化的可能。嘉隆时期,收取“报水”均是以非法的面目见诸于史。
据隆庆《潮阳县志》载:嘉靖“三十四年,抚盗许朝光分据潮阳牛田洋,算舟征税。……又分据潮、揭、牛田、鮀浦等处,凡商船往来无大小皆给票抽分,名曰买水。”(84)隆庆《潮阳县志》卷2,《县事纪》,《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63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影印本,第17b页。许朝光就抚以后,其身份已经由海寇转变为海防武职,对商船“给票抽分”的“买水”行为已经属于官方职权。而广东将“票”作为本省沿海贸易的许可证,实际上早已有之。正德十四年(1519),两广总督兼巡抚杨旦称:“近海装货开洋往雷、琼等处,亦要给票依例盘诘,大概一如盐法,其一应事宜总于盐法御史统理。”(85)[明]张学颜等撰:《万历会计录》卷43,《杂课》,《续修四库全书》第833册,第175页。嘉靖时期,广东的海洋贸易又历经多次调整、演变,此处不再赘述。总之,许朝光正是借助海防官员的身份来扩展“买水”的范围,对此也可理解为许朝光滥用职权。而官方文献中对曾一本等海寇索取“报水”的记载,其时间也发生于招抚后。隆庆元年“二月二十六日,曾一本率众面缚诣军前请降”,接受广东总兵官汤克宽的招安。然而,福建巡抚涂泽民却认为曾一本“明系阴怀异志,假为说辞,不然既称投降,何又抢虏渔船,勒要居民报水”。(86)[明]涂泽民:《咨两广广东二军门》,载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354,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07页。据《明穆宗实录》载:
先是海贼吴平既遁,而余党曾一本突入海、惠来间为患,克宽倡议抚之。贼既就抚,乃从克宽,乞潮阳下会地以居,仍令其党一千五百人窜籍军伍中,入则廪食于官,出则肆掠海上人,令盐艘商货报收纳税,居民苦之。于是大家井氏陈世业、余乾仁等同率众叛,攻围揭阳县城,克宽乃调曾贼等兵剿屠之。……越七月,曾贼亦叛,执澄海县知县张濬,焚杀潮郡居民数千人。(87)《明穆宗实录》卷14,隆庆元年十一月丁巳,第379—380页。
隆庆二年(1568)九月,兵科给事中陈邦颜疏曰:招抚时,汤克宽“阴行曾贼重贿,纵令报水激变,居民侵突会省,宜正典刑”。而后,朝廷于初四日令御史将汤克宽“逮系至京问”。(88)《明穆宗实录》卷24,隆庆二年九月庚戌,第644页。曾一本就抚后既“乃从克宽”,又“廪食于官”,显然已经从属于地方官。涂泽民、陈邦颜所说曾一本勒索“报水”,应该与嘉靖《重修问刑条例》中所载“报水”涵义相同,指海防武职违法收取“报水”。最终,曾一本集团于隆庆三年(1569)六月被官府剿灭。(89)《明穆宗实录》卷36,隆庆三年八月癸丑,第916—918页。隆庆三年闰六月,俞大猷曾诘问踏头埔寨海寇头目:“汝既招抚,尚聚数千人为一寨,一寨之人生杀由汝,四旁乡村报水,贩盐船只抽税,汝当初为贼则宜如此,汝为抚民,即是良民,岂可如此?”(90)[明]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洗海近事》卷下,《书与巡抚熊及二道》,《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65册,第609页。尽管海寇已经接受招安,但索取居民“报水”仍属于非法行为。
隆庆三年十月,身为新会县人的工科给事中陈吾德也奏曰:
往岁夹剿吴平,总兵汤克宽不行策应,使余孽复肆则亦已矣。至乃卖水招抚,激变良民,歼无噍类,流祸至今。先该兵科给事中陈邦颜列其罪状,已被逮到京矣,而至今典刑未正,臣窃惑焉。臣闻克宽受贼金数坛,纵令报水,初未深信,及曾贼突犯省下,声言杀大家井有功,下浍非徒手而得,今官司负我耳,还我前银,即当退兵,此事昭昭于人之耳目也。……克宽受贿纵贼之祸深也。
而对如今招抚林道乾,陈吾德紧接着奏议:
往年当事者失于长筭,捐下浍之地以与抚民许朝光,报水至今遂启盗心,朝光去而曾一本邀之,一本去而林道乾又据之矣。……林道乾招抚一节,责令总兵郭成处置停妥,毋蹈前车,如其纵容报水贻祸地方,容臣等参究,治罪不贷。(91)以上两则史料,参见[明]陈吾德:《谢山存稿》卷1,《条陈东粤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8册,第420—421、427页;也可参照《明穆宗实录》卷38,隆庆三年十月辛酉,第962—964页。
十月二十一日,陈吾德条陈广中善后八事,“下户、兵二部覆议可行,上皆从之”,“克宽功罪下所司议处”。(92)《明穆宗实录》卷38,隆庆三年十月辛酉,第964页。“买港罪”惩治的对象仅是“守把海防武职”,因此身为总兵官的汤克宽需要相应“所司议处”。从奏疏中也可见得,汤克宽“卖水招抚”曾一本,通过受贿钱财纵容其“报水”。如此看来,许朝光的“买水”或“报水”行径也可能是地方官“卖水”纵容的结果。而“卖水”本身就是官兵受贿谋私的行为,据万历《雷州府志》载:指挥佥事凌登瀛,“万历四十二年,委管横山堡,卖水卖船纵放珠贼,追赃立功”;(93)万历《雷州府志》卷12,《兵防志一·军官》,《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1册,第323页。天启末,巡按福建监察御史兼理盐法周昌晋制定“盐禁”,其中“革需索”一条曰:哨兵“沿河索例……名曰烧纸,又有贿放私盐名曰卖水,均应禁革”。(94)[明]周昌晋:《鹾政全书》卷下,《盐禁》,《续修四库全书》第839册,第424页。由此可知,“卖水”为官府明确禁止的非法行为之一。明廷批准并实施陈吾德的奏议,实际上再次明确了禁绝就抚海寇索取“报水”的立场。具体到地方视角来看,自嘉靖三十一年(1552)以来,潮州屡遭倭奴、海贼侵犯,“官府苦于地方多事,兵力不暇,准其告招”。招抚后,朱良宝据南洋寨、林道乾据华林寨、魏朝义住大家井、莫应敷住东湖寨。魏、莫二人已经改行,而“林、朱则报水杀人如故,民甚苦之”。与此同时,地方官对朱、林二人的桀骜不驯、叛服无常也早有防备。万历元年,两广总督殷正茂议剿,林道乾闻讯逃往海外不见踪影,朱良宝叛逃南洋于翌年三月被官兵击毙,而后魏、莫二人也“相率毁巢散党,投官请命”。(95)万历《粤大记》卷3,《事纪类》,《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2册,第45—46页。由以上可知,海寇无论或叛或降,其索要“报水”始终不见容于地方官府。
综合来看,迟至隆庆开海前后,官方语境中针对就抚海寇的“报水”多指索取的钱财,同时也明确出现了向“给票抽分”行为模式转变的迹象,这类行为可能是模仿官府征税制度的结果。海寇就抚前后勒索钱财的举动并不足为奇,关键是官府如何认识、定名这类行为。官方视角著述的海寇勒索“报水”史事,可能是从法律文献中的“报水”一词延用而来,其涵义又稍有变化,逐渐延伸为指代海寇勒索钱财全过程的一部分。
再来讨论“引税”的来源问题,笔者推测明穆宗应福建巡抚涂泽民奏请,准许漳、泉海商申请“船引”出洋贸易时,就已经囊括了许可的含义,“引税”的设置应是海商申请“船引”时的手续费,也可视为行政成本的摊派。从制度立意来看,“引税”可能来自明代盐商申请“盐引”时交纳的“纸价”或“纸银”,也即由盐商承担印刷“盐引”用纸的费用。据李洵先生研究,官方从“正统三年(1438)令盐商起引时交纳盐引用纸纸价。成化时规定盐引纸价每引百枚,纳银一钱”。隆庆二年,屯盐都御史庞尚鹏还令“盐商必先纳引纸(印刷盐引用纸)于南京户部,然后取引”。(96)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69—170、180页。“引税”来源于“纸价”或“纸银”仅是笔者的推测之一,对此并没有十分确凿的证据。此外,漳州税课中“民间田土交易,官给契本工墨,令自填写盖印,亦收其税”,(97)[明]罗青霄等修纂:《漳州府志》卷5,《漳州府·赋役志·财赋·税课》,第189页。这背后所反映的官方意图也应当予以重视。地方官府介入契税征收有多重考虑,既有保障信用效力的因素,也有分担行政经费的因素。“引税”与“纸价”(“纸银”)或“契税”,三者开征的涵义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共通之处。
另外,据《虔台倭纂》载:“丙子、丁丑之间,刘军门尧诲、庞军门尚鹏调停贩番,量令纳饷。”(98)[明]谢杰:《虔台倭纂》卷上,《倭原二》,《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史部第10册,第232页。又据《海防纂要》载:“万历初年,巡抚庞尚鹏请开海禁,准其纳饷过洋。”(99)[明]王在晋:《海防纂要》卷1,《福建事宜·海禁》,《续修四库全书》第739册,第663页。刘尧诲是万历元年八月“到任接管行事”,正式行使巡抚职权。(100)[明]刘尧诲:《刘尧诲先生全集》卷2,《抚闽疏·恭谢天恩疏》、《抚闽疏·据时酌议兵食以保固海防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8册,第385页。庞尚鹏是万历五年二月十七日到延平府与刘尧诲交接政务,六年(1578)正月初九由福建巡抚升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101)[明]庞尚鹏:《百可亭摘稿》卷4,《奏议·恭谢天恩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9册,第247页;《明神宗实录》卷71,万历六年正月辛酉,第1519—1520页。万历四年、五年(1576、1577),刘尧诲、庞尚鹏调整海澄外贸的具体情形,由于没有相应史料佐证,所以目前还不能得知详情。新史料的出现或许能够深化我们对海澄洋税征纳初期的某些认识,对此笔者也将持续关注。
本节考察了海澄税务管理制度创建与完善的过程,海澄洋税是在赣州桥税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与“报水”并无直接关联。最初涂泽民请开海禁时,就已经将“船引”作为商船的许可证。而后,经海澄港出洋贸易的各项事务由漳州海防同知具体管理,同时并不征收任何税银。隆庆六年,罗青霄提议征收税银的动机是弥补官府支出和减轻百姓负担,因此很难说对“船引”从不征税到征税是源于“报水”,而且目前也没有史料能够证明是“船引”“引税”等名称替代了俗称的“报水”。此外,隆庆时期海寇就抚前后勒要“报水”始终处于非法境地。由此可知,地方官不会将“报水”合法化,那么“引税”的开征也与“报水”无关。
余论
“报水”可能早已有之,只不过囿于史料的局限尚不能得知具体细节。大体上来看,“报水”既产生于互市贸易中广东地方官对番舶索贿的“例钱”,又产生于市舶太监、海防官员受贿纵容中外海商非法交易的行为之中,其出现的时间不迟于成化时期。然而,明代史籍中的“报水”一词始见于何时尚不明确,目前能够追溯至弘治十六年《大明兴化府志》,黄仲昭作《陈燮传》将历来广东互市贸易中的“例钱”称为“报水钱”。弘治以后至嘉靖二十六年,“报水”一词却杳无踪迹,或许是史籍中多以“例钱”“例金”取代“报水”的缘故。
通过梳理丁桐受贿案的来龙去脉可以厘清“买港罪”确立的历史过程:嘉靖二十六年,丁桐“受金黩货,纵之入境”一案暴露出的法律漏洞成为“报水”量刑入法的重要契机;次年,屠侨奏疏中对丁桐“屡受报水”案的处治意见则是订立“买港罪”的主要依据;等到嘉靖二十九年,海防武职收取“报水”的行为就被冠以“买港”载入《重修问刑条例》。此后,“报水”才逐步多见于各类官方文献之中,既指海防武职纵容商船贸易时收取的钱财,又指驻防沿海或内河的官兵向渔船、盐船等索取的钱财。从闽、浙两省处理的具体案例来看,嘉靖三十八年,“分守参将王麟受财买港”,翌年发配边卫戍守;万历三十八年,哨官陈勋等“以私受买港,受财枉法论”。地方官将海防武职收取财物(“报水”)纵容商船贸易的罪行称作“买港”。而隆庆时期,官方文献中的“报水”则多指海寇就抚以后索取的钱财,同时也出现了向“给票抽分”行为模式转变的迹象。涂泽民、陈邦颜等官员所言曾一本勒索“报水”,本意是指海防武职违法收取“报水”名目的钱财。因为曾一本在接受招抚后,其身份已经转变为海防武职,自然不能再以海寇视之。
万历中期及以后,“报水”(钱财)的索取者,既有驻防官兵,又延及至海贼。万历三十年除夕(1603),东渡台湾剿贼凯旋的沈有容班师至金门料罗湾,有客问其曰:
贼据东海三月有余,渔民不得安生乐业,报水者(渔人纳赂于贼,名曰报水)苦于羁留,不报水者束手无策,则渔人病、倭强而番弱。倭据外澳,东番诸夷不敢射雉、捕鹿,则番夷亦病。(102)[明]陈第:《舟师客问》,载沈有容辑:《闽海赠言》卷2,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第38—39页。
万历后期,据董应举说:兵船巡查时,“今乃假协缉之名,酷索报水”;又说:“往时贼索报水,劫人取赎,岁不过一两次,今四季索报如征税粮。……今民以纳贼为固然,贼以索赎报水、因船于我、取人于我为固然。”(103)[明]董应举:《崇相集》,《议二·海课解疑》《议二·福海事》,《明别集丛刊》第4辑第52册,第169、196—197页。由以上可知,万历中后期,官兵、海贼索取的钱财均称为“报水”。
明末天启、崇祯时期,针对海寇的“报水”一词,其涵义逐渐由索取的钱财演化为给票抽分的行为模式。天启七年(1627)二月二十二日,郑芝龙突犯铜山寨,在“漳属一带,勒民报水”。(104)第285号:《兵部尚书王之臣等为官兵剿抚闽省海寇郑芝龙等失事并遵旨议处将弁事题行稿》(天启七年七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3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75页。四月二十八日,郑芝龙又遣其党羽侵犯海澄“横索报水”;据崇祯《海澄县志》载:“报水者,约略村居若干,醵金供贼为寿,冀无诛杀我。”(105)崇祯《海澄县志》卷14,《寇乱》,《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30册,第474页。与此同时,郑芝龙又进犯中左所并在高崎、浯屿、含英等处,“把截渡口,劫虏商船,沿海居民被其勒票报水”,甚至有内地居民“执持伪票展转售奸”。(106)第302号:《福建巡抚朱一冯为剿敌先须择将并举堪任将官事题本》(天启七年八月十二日),《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4册,第53页。郑芝龙将勒索钱财与发给票据相结合,从而使其控制海域、谋食海洋的方式更加完善。天启七年末,漕运总督兼凤阳巡抚兼理海防郭尚友奏曰:“近又福建红夷猖獗,海上大盗捉拏商船客货,十分抽三,名曰报水,广南泛海之货不来矣。”(107)[明]郭尚友:《漕抚奏疏》卷3,《查参武弁妄报钱粮疏》,明崇祯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本,第23a—23b页。至此,“报水”一词已经指代海盗向商船抽银的行为。崇祯二年(1629),浙江巡抚张延登题称:
臣细访闽船之为害于浙者有二:一曰杉木船……一曰钓带鱼船……官军不敢问,此二项船皆与贼通。贼先匿大陈山等处山中为巢穴,伪立头目,刊成印票,以船之大小为输银之多寡,或五十两、或三十两、二十两不等。货未发给票,谓之报水;货卖完纳银,谓之交票。(108)《兵科抄出浙江巡抚张延登题本》(崇祯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明清史料·乙编》下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第37—38页。
由此可知,浙江地方官也将海贼非法向商、渔船只“给票”的勒索行为称作“报水”。天启时期,随着郑芝龙等海寇扰乱海洋秩序,东南海域的权力格局呈现出官退寇进的局面。海寇在其活动的海域内,向过往船只和沿海居民勒索钱财,这是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之一。然而,即便是在崇祯元年(1628)郑芝龙接受招安后,官府也未能肃清海洋贸易中存在的非法勒索行为。晚明时期,具体针对海寇的“报水”一词,可能是从法律文献中的“报水”延用而来。总之,不能将海寇的“报水”行径与官方的征税行为相提并论,二者也并不存在可以转化的关联性。
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历史认识客体(史料媒介)是史学研究的基础。由此也引伸出新问题,即海寇历史的书写者明朝官绅,以官方视角著述的海寇史事,能否反映出真实的历史图景?现在讨论“报水”可以引证的史料是否恰当、充足,藉此还原的历史图景又能否充分反映出“报水”演变的主流脉络呢?以上问题成为限制历史认识主体认知历史的重要因素。综上所述,本文以目前能够掌握的史料为基础,通过考察“报水”一词的流变得出:“报水”源于历来广东互市贸易中的“例钱”,而后又历经演变渐次指代海防武职、就抚海寇或驻防官兵索取的钱财,万历中期又延及海寇勒索的钱财,至启祯之际遂演化为海寇给票抽银的行为模式;然而,“报水”无论是指广东地方官收取的番舶“例钱”,还是指海防武职收受的钱财,抑或是指海寇勒索的钱财,乃至指代海寇给票索银的行为,其始终都是以非法的面目出现于以往的历史图景,因而也不会存在是否合法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