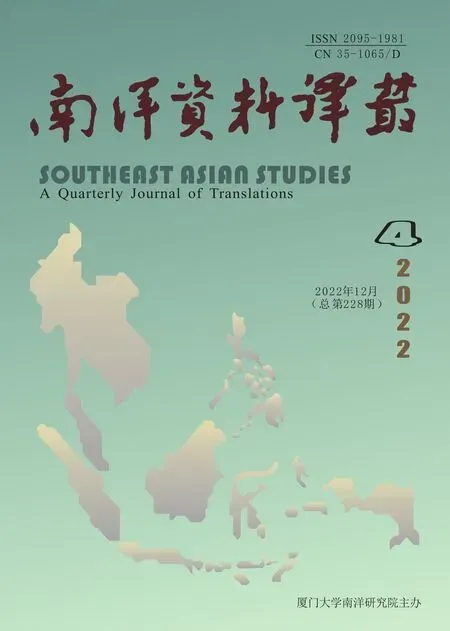撒迪尤斯·弗拉德关于泰国的马克思主义著述(1932—1977 年)
[美]彼得·F. 贝尔
1977 年12 月11 日,撒迪尤斯·弗拉德因癌症去世。在他生命中的最后10 年,一直致力于推动泰国的革命变革和抵抗美帝国主义。他的生平和著作揭示了美国教育与帝国主义政策之间的矛盾。这不仅因为他所写的文章,还因为他的生活和学术研究工作,超出了他所受到的保守和“不问政治”的教育,使他从学院式的学术研究走向政治斗争,从而打破了他曾经想象的大学职能的框框。美国在东南亚的帝国主义行径让他萌生出一种政治觉悟,这是他在所受的教育中从未学到过的。我希望籍此短文阐明他转型的宝贵经验,以供亚洲问题及其他领域学者从中汲取,并尝试对其在泰国研究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进行评估,从其生平和著作中借鉴可以推动我们共同斗争的政治经验。
在过去的10 年里,撒迪尤斯·弗拉德放弃了他的早期学术研究。此后,他试图打下一个系统化的基础,以否定美国在东南亚尤其是在泰国的政策,以及美国为达成其帝国主义目的而歪曲了泰国社会性质的美国学术研究。他还批判了教导他把知识和道德割裂开来的教育制度,并试图通过马克思主义学术和政治斗争将二者结合起来。他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和学者,是美国教育体系的最优秀成果中的一个,但他却在想方设法摧毁美国教育体系培养无脑学者、“道德阉割”的目标。
一、教育与理论发展
很难在弗拉德的出身和教育中找到他后来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原因。1932 年,他出生于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在一个坚定的共和党家庭长大,父亲是一名律师。后来弗拉德就读于名校,获得西雅图预科中学(Seattle Preparatory School)古典文学文凭和西雅图大学(Seattle University)哲学学士学位。在大学期间,他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并于1951 年至1955 年在朝鲜服役,当时正值美国反共情绪的高峰期。他曾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读研究生,获得国防奖学金资助,3 年时间专修日语、中文和泰语。在日本和泰国的研究生学习期间,弗拉德对日泰关系进行了广泛的档案研究。在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8 年中(1958 年至1966 年),他深受该大学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影响。从1966 年到去世,弗拉德一直在圣塔克拉拉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anta Clara)教授亚洲史。
在去世前几个月,他写道:“美国大学被认为具有百货公司的全部诚信。”回顾自己所受的教育,他发现其内在的弱点和完整性的缺乏源于其对“知识”的诠释:
当今世界充满着暴力、饥饿、贫困和死亡,其中很大一部分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教育(也可以理解为美国)对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平静,与美国对于“知识”功能的诠释直接相关。这种功能所固有的将知识与道德截然一分为二是知识交易的整体特征。“知识”,尤其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本质上被认为是离散的、碎片化的、孤立的“事实”的集合:科学领域和学科门类一经划分,就会随其基础数据的扩大而日益变窄……我们在教育体系中发现的那种碎片化、机械化的“知识”,永远与定性的伦理问题脱节……(弗拉德,1977b)
由于美国对东南亚的政策及学生反战运动,通过教学实践,他经历了自身政治上的转变。直到为一门东南亚历史课程备课时,他才认识到美国政策的不道德。他于1967 年投身政治,当时他正在教授越南史(“讲授被杀害的人”)。提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他说到,“完全是由于学生所提的问题引起的。这些问题使我想到许多事情,并提出我从未梦想到的问题来问自己。”在圣塔克拉拉大学的学生和几位同事的帮助下,他加入到美国的反战行列,并投身到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此之前,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学术生涯的:
在1967 年至1968 年投身政治之前,我一直从事于细枝末节、毫无价值、实证主义的超经验研究,给同样毫无价值的杂志写文章,从而获得职称晋升和终身教职;而这些研究同生活、同真实人类历史的辩证法毫无关联。一句话,它们是典型的美国学术研究。我的博士论文纯属此类范畴,事实上是令人作呕和没有什么理论的,只求获得学位而已……唯一的可取之处是,如果我或其他任何人想写一部20 世纪20 年代、30 年代或40 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在泰国的历史,它可以提供大量的原始文献,并且永远不会出现重复。但它完全不具备理论完整性。①1976 年9 月29 日致彼得·贝尔的信,附录也由此而来。
他的优势在于,他可以跳出旧左派遗留下来的传统正统学说而转向马克思,他能够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他说,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自己本人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冲突的人”;马克思主义是唯一一个连贯的理论框架,通过它,人文精神和现实理解得以融合,知识和道德得以统一。②私人谈话,1977 年3 月20 日,加利福尼亚州萨拉托加。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受新左派的影响,表现在其为一个更加人道、更加公正的社会的不懈奋斗,以及对反帝国主义的反复强调。同时他也深受法兰克福—布达佩斯学派(the Frankfurt-Budapest school)理论倾向的影响。
“批判理论”学派(从马克思到滕尼斯[Tonnies]、卢卡奇[Lukacs]、葛兰西[Gramsci]、戈德曼[Goldmann]和马尔库塞[Marcuse])为其激进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并渗透到他后来的所有著作中。因此,任何对他著作的评价都必须正视马克思主义这一特殊传统,以及它所指向的知识和政治方向。
在进行此类评价之前,关键是要认识到弗拉德在1966 年至1967 年之后的学术著作具有了直接的政治目的。他不仅深入参与反战运动,而且在1974 年春夏访问泰国期间,通过汶沙侬·本约塔炎(Boonsanong Punyodyana)与提拉育·汶密(Thirayut Boonmi)和诺鹏·素旺帕尼特(Nopphorn Suwanphanit)等泰国激进分子接触,积极发表言论反对1976年10 月夺取泰国政权的军政府。他与加州的激进组织有着广泛的合作,比如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以及泰人民主联盟(the Union of Democratic Thais)。他还试图通过在电视上频频露面以及写作来动员反对泰国军政府的力量。他在亚洲问题研究学者中传阅一封信,请求他们联合抵制1976 年秋天在曼谷举行的东南亚历史研讨会。
在整个过程中,他对社会主义秉持着一种特殊的人文主义愿景,这让他怀疑并远离宗派马克思主义政治,并对他所见到的亚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不人道行为提出了批评。泰国激进分子正在求索适合的社会主义模式,他本想通过讨论发挥更加直接的作用,事实上他是通过著述间接地达成了这一目的。虽然他非常赞同彻底的社会变革的紧迫性,但他不会被雄辩高谈和简单的解决方案所左右。
二、关于泰国与美帝国主义的分析
在1970 年的一次研讨会上,弗拉德发表了一篇关于胡志明的农村战略组织技术及其泰国经历的论文,这是他第一篇反映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撒迪尤斯的下一篇文章就是《泰国左翼的历史渊源》(The Thai Left Wing in Historical Context),发表在《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公报》(Bulletin of Concerned-Asian Scholars)上。这篇文章有两个显著的特点:(1)他试图削弱美国的泰国研究学术著作的既有结论,并指向反抗泰国社会剥削状况运动的持续性;(2)试图勾勒出关于泰国社会历史的理论诠释要素。
这是第一篇认真介绍泰国左翼的英文文章,并对激进的革命斗争思想史进行了梳理。他追溯了激进知识分子的历史渊源,以及城乡反抗运动的持续性和统一性。文章涵盖了对20 世纪30 年代至1976 年期间的主要泰文激进著述的研究,并探讨了迫使激进派入狱、流亡或逃入丛林的镇压浪潮。文章还概述了“美国反共无畏军”在协助镇压方面的重大贡献。
那些所谓的泰国问题“专家”(如大卫·威尔逊[David Wilson])认为泰国缺乏大规模反抗运动,弗拉德提出了与之相反的观点,他说明了这场运动的典型泰国特征、持久性和日益高涨的力量。他认为激进主义在20 世纪60 年代末和70 年代的复兴是西方自由主义解决方案的弱点造成的:“美国式自由主义与种族灭绝、干预和镇压革命的关联太明显了,即使是被剥夺了客观新闻来源的知识分子也能注意到这一点。(弗拉德,1975 年,第61页)
这篇文章的理论重要性在于其对泰国国家所提出的独特观点。弗拉德认为泰国左翼是出现于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即代表商人、外国资本家、军阀、官吏和旧贵族萨迪纳阶级综合利益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与之对立的是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在他看来,当代泰国历史的主要辩证法,是这个根深蒂固的官僚国家和工农群众之间的斗争。前者被灌输了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理性而非其社会关系,而后者由于那些具有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第一次形成了真正的革命力量。
这篇文章实际上否定了泰国的封建和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对前者的否定是因为当时没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地主阶级,对后者的否定是因为泰国农村社会的社会基础是基于特殊形式的地方自治主义,这种地方自治主义不会通向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相关讨论见论文《泰国左翼的历史渊源》,特别是第55 页和脚注7,以及附录中转载的信件中部分内容。)这构成了关于泰国社会历史的一个独特理论,我们唯有希望他能够如愿以偿完成关于该主题著作的撰写。这是对主导正统马克思主义讨论的历史发展单线论的明确排斥(即社会在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前必须经过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阶段),也是对将sakdina(萨迪纳)翻译为“封建主义”的标准的否定。①这些理论过去曾被用来解释“资产阶级”的发展阶段,并为国家资本主义辩护。
弗拉德对待泰国社会历史的态度清楚地表明,他的理论倾向于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Frankfurt Marxism),强调国家、意识形态和意识的作用,淡化社会发展物质方面的作用。其观点倾向于关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及其压迫性,而不是阶级斗争。如果有著者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是20 世纪50 年代以来泰国历史的主要动力,其社会阶级根源可以追溯到30年代,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家是这一发展的主要催化剂时,那么他与弗拉德的分析存在理论上的分歧。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似乎不仅主宰了泰国的城市中心(工厂里靠工资生活的工人和贫民窟里没收入者),而且还日益渗透到农村地区(随着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以及“绿色革命”等)。这种分歧是政治性的:弗拉德强调需要一支知识分子的先锋队来提高工农群众的觉悟,并粉碎压迫他们的官僚国家机器;第二种观点主张通过在田间和工厂进行广泛的阶级斗争以推翻现有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弗拉德主张从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而笔者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关系,并利用工农中已有的自主能量。这一目标与“教导”被压迫者的列宁先锋党模式背道而驰。笔者的观点是,泰国农村和城市的反抗运动历史表明,受压迫者了解自己的处境,并一直对其进行反抗。②这形成于彼得·贝尔的《美帝国主义和泰国阶级斗争的“周期”》,载于1978 年的《当代亚洲杂志》。
他在对美帝国主义的分析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弗拉德,1976 年),只强调了帝国主义的压迫性:意识形态控制、成立警察部门和军队以铲除左翼对手,等等。20 世纪50 年代和60 年代,帝国主义对泰国进行“现代化”的努力实际上是要把它变成一个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努力遭到了暗中反对。军国主义和中央情报局主导得到重视;有人可能会说,面对学生、城市工人和农民对整个资本主义框架的威胁时,泰国统治阶级不被看作是资产阶级,而是一些前资本主义时代争夺国家权力的小集团。这对理解革命斗争的方式有重要影响。推翻一个前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意味着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而是要清除这一权力结构中的某一特定部分。
在笔者一直引用的文章《美国与泰国军事政变》(The Unit ed S tates and t he Mi litary Coup in Thailand)中,弗拉德借鉴对泰国激进分子的分析,对美帝国主义政策(在军事、警察援助和反叛乱行动领域)与泰国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审慎的重组。他还指出了统治集团在争夺统治权过程中的内部冲突。他将1976 年10 月军事政变中泰国军队势力的卷土重来与美国破坏智利稳定的过程进行了比较,认为军队再次掌权是美国政策不可避免的结果。他忽略了1945 年以来泰国社会的物质变换,认为当时的军事政权与20 世纪30年代和40 年代的相似:
丑陋的现实是,反叛乱技术的大量应用催生了一种泰国政治体系,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30、40 年代政府和军队推行的法西斯主义。让美国感到羞愧的是,这种体系是25 年来美国对泰国人民命运干预的直接产物,尤其是通过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弗拉德1976,第7 页)
另一篇值得一提的学术论文是《泰国的越南难民:反叛乱中的少数民族管控》(The Vietnamese Refugees in Thailand: Minority Manipulation in Counterinsurgency),这是撒迪去世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其明确目标是:
帮助消除所谓泰国人民自己不能革命的神话,并且……揭露最近在美国发起的反叛乱项目帮助下泰国统治阶级仍然对这个(越南)少数民族进行管控的方式,……把问题的焦点放在它长久以来本应该在的地方:放在泰国人民身上,放在他们为尊严和社会正义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上。(弗拉德1977a,第31 页)
和他所有的作品一样,这篇文章的特点也是对学术细节的关注,它追溯了从19 世纪早期至今越南人在泰国的命运。文章不仅指出了美国学术研究的缺点,还揭露了美国和泰国把越南人作为自己内部问题以及叛乱发展的替罪羊的宣传目的,就好像叛乱受到了外部授意和引导一样。弗拉德一如既往,广泛借鉴了多语种文献资料(法语、泰语、日语和中文材料),写出了一篇具有开创性的文章。在文章中,明显可以看到他的其他知识来源(比如阿卜杜勒-马立克[Abdel-Malek])。
在他的个人转变和反战运动的蓬勃发展之后,面对70 年代中期的学生冷漠症,弗拉德变得悲观起来。在笔者之前引用的一篇未发表的手稿《美式知识:论美国教育中知识的道德阉割》(Knowledge American Style: An Essay on the Ethical Emasculation on Knowledge in American Education)中,他试图通过构成该教育的基础的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角度来解释这种被动性。他再次借鉴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的观点,认为国家已经行使了意识形态霸权,并实际地加入了激进运动:“在60 年代和70 年代初期曾经让人们走上街头的问题,现在只会让他们走进厨房再喝一杯啤酒……教育一直是所有团体机构中最有效的“中立化”……过去15 年的道德挑战。”
弗拉德本人持续参与争取人类尊严的斗争,这是对他自己的论点的最好回应。更重要的是,他的方法论使他忽视了60 年代的道德斗争到70 年代的报酬斗争(反对学费上涨等)的转变,而报酬斗争是当时学生激进主义的特征。在平息这些思潮和寻求知识真理的过程中,他对意识形态压制的力量过于悲观。
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涉及泰国社会的性质、国家的性质、目前阶级构成的物质基础以及社会主义转型的前景。对于后者,如弗拉德关于泰国社会的解释(见附录)所示,他持非常乐观的观点,他认为村庄层级的社会组织将有助于向社会主义转型。
他还坚信泰国人可以自己闹革命。这一点在笔者所讨论的所有著作中都很明显,在他对集·普米萨(Jit Phumisak)这位杰出的泰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颂词中一目了然。集是泰国人民强烈的革命愿望的楷模,弗拉德钦佩他不仅因为他的著名专著《泰国封建制的真面目》(美国版为The Face of Thai Feudalism,最近由泰人民主联盟出版,献给弗拉徳),还因为他对泰国文化的分析,比如他的著述《艺术为人生,艺术为人民》(Art for Life, Art for the People)。他写道:
在泰国,所有由美国设计、建议和资助的反叛乱技术似乎都不太可能成功地消除集·普米萨等人的想法。最重要的是,集·普米萨是一种思想信念,一种在泰国无产者和革命知识界的土壤中根深蒂固的信念。这种信念和革命都不会消失。(弗拉德,1977a,第14 页)
略加修改,这些话也适用于撒迪尤斯·弗拉德。尽管他对美国社会和教育感到悲观,但他却是美国社会矛盾活生生的例子。而无论这个社会做什么,似乎都不可能阻止优秀学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撒迪尤斯的一些工作可能将由查丁·弗拉德(Chadine Flood)来完成。这不仅是今后泰国研究的基础,因为他已经把这项研究提升到比他之前的任何人都更严谨的水平,而且它迫切需要被纳入有关泰国革命进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讨论中。这样,他的研究才会继续下去。
Bibliography of E. Thadeus Flood’s Writings
1965. (With Chadine Flood) Co-translator of Dynastic Chronicles, Bangkok Era, Fourth Reign (Tokyo: Center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1965-, 3 volumes.
1968. “Japan’s Relations with Thailand:1928-41,”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69a. “Sukothai-Mongol Relations: A Note on Relevant Chinese and Thai Sources (With Translations),”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Vol. LVII, Pt. 2 (July), pp. 203-255.
1969b. “The Franco-Thai Border Dispute and Phibun Songkram’s Commitment to Japan,”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Vol. X, No. 2 (September), pp. 304-325.
1969c. “Bangkok, December 8, 1941: A New Look at Thailand’s Hour of Decision,”Western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Tucson, Arizona, November, 1969.
1970. “Ho Chi Minh in Canton and Siam, 1924-29: A Note on the Origins of His Rural Organizing Techniques,” Asian Studies Pacific Conference, Oaxtepec, Mexico, June.
1971. “The Shishi Interlude in Old Siam: An Aspect of the Meiji Impact in Southeast Asia,” in David Wurfel (ed,) ( Meiji Japan s Centennial: Aspects of Political Thought and Action(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pp. 78-105.
1975. “The Thai Left Wing in Historical Context,”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Vol. 7, No. 2 (April-June), pp. 55-67.
1976a. “Jit Phumisak: Profile of a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 Indo-china Chronicle,Jan.-Feb., pp. 12-14.
1976b.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litary Coup in Thailand: A Background Study,”Indochina Resource Center, Berkeley.
1977a. “The Vietnamese Refugees in Thailand: Minority Manipulation in Counterinsurgency,”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9, No. 3 (July-Sept.), pp. 31-47.
1977b. “Knowledge American Style: An Essay on the Ethical Emasculation of Knowledge in American Educat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附 录
撒迪尤斯·弗拉德 著
……我认为,正相反,诸如泰国这样的社会的未来(其实也包括现在),与欧洲社会的情况迥然不同,恰恰是因为经济结构存在差异。这些地区的商人阶级(包括中国和印度支那,日本除外)过去不能、而且将来也永远不能攫取社会主宰权并强力推进资产阶级化进程。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西方国家飞地的存在(中国的条约港,六七十年代越南南部地区,如今的曼谷等地),但是从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角度而言,这些飞地都是杂糅而生的怪物。正如我在《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公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所言,泰国和其他这些社会都拥有其自身独特的社会历史,发源于灌溉稻作文化的生产方式和典型的乡村礼俗社会共同体,这彻底将其与西欧的历史范式区分开来,正如马克思的敏锐洞察。事实上,这些社会的主要特征恰恰就在于,其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并不是要像美国那样经由资本主义,而是一条避开资本主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它不是靠无产阶级在工厂里发动起义实现的,而是在农民阶级的支持下,由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知识分子组织和领导下实现的。由于资产阶级在泰国没有自己的社会使命,因此它不会形成马克思、滕尼斯、韦伯(Weber)、卢卡奇、赖希(Reich)、阿多尔诺(Adorno)、马尔库塞及其他评论家(弗里茨·帕彭海姆[Fritz Papenheim]也应提及)所称的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 society),即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或马克思的市民社会(Burgerliche Gesellschaft),一并还有其异化、物化和伪意识等。简而言之,就是美国的二手车推销员社会。让·谢诺([Jean Chesneaux]在其关于中国和越南的著述中)是少有的研究亚洲问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专家(另一位是阿努尔·阿卜杜勒-马立克[Anuoar Abdel-Allalek]),他认识到事实上这些社会不经过资产阶级化的社会变革,走向现代化也是非常可能的。
然而,要认清这一点,我们必须摆脱许多来自马克思关于西欧封建主义范式论述的概念,也包括他许多被误用误解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的附带说明。后者遭到韦伯以及诸如马季亚尔(Madyar)、司徒卢威(Struve),尤其是魏特夫(Wittfogel)等“亚细亚”共产国际专家的严重歪曲,最近的例子是魏特夫的门生、韦伯学派社会学家诺曼·雅各布斯对泰国的分析。他们都忽略了马克思的《形式论》(Formen),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忽略了马克思对亚洲农业社群(村庄)在没有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的人类潜力所持的乐观态度。他们聚焦拥有大型水利工程和徭役制度的管理型专制政府,但却忽略了灌溉在创造历史的真实层面的影响,以及在农民合作、社群主义、所有权意识缺失是常态的大众层面的影响。在我看来,这就是泰国历史辩证法的运行所在,正如在中国(谢诺《中国农民起义》[Peasant Revolts in China])和柬埔寨、老挝和越南那样。
绝非偶然的是,最具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转型已经在某些社会环境中发生,这种社会环境既具有显著的“前资本主义”特征,又在社会文化和历史层面上具有反资本主义特征。唯一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的事实是,在这些地区,包括泰国在内,在大众村庄层面显现出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人文社会组织。即是说,他们并不是太受美国社会科学界称作“现代价值体系”的市民社会—资本家社会(bourgeois-capitalist Gesellschaft)文化的外来影响,反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历史方位对这一来自外部的(一定是来自外部的)强加进行抵制。简要回顾欧美历史即可发现,从人文角度而言,那些没有过资本主义的社会并不因此就处于劣势。相反,这些社会没有过真正完整的资产阶级化,并且永远也不可能发生,这反而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强武器。
1976 年9 月29 日
(原载美国《亚洲问题学者通报》(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Vol. 10, No.1, January-March 1978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