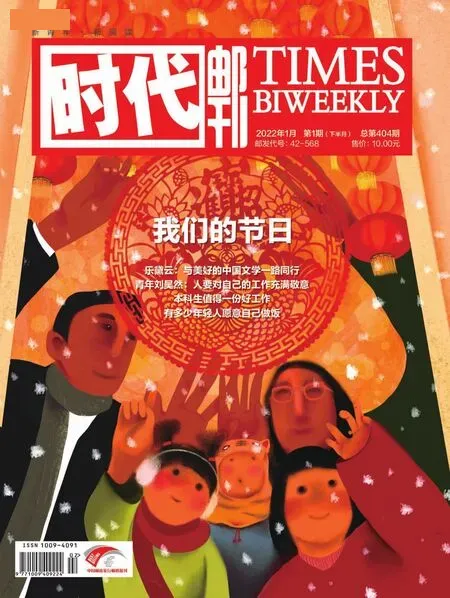一杯甜酒给予的快乐
文 张子艺

西北的秋天是很短的。冷风来了,将金黄色的树叶从树上吹走,萧瑟的冬天也跟着来了。
冬天也不仅仅是萧瑟的,它还是有一些趣味的。比如来暖气前的那几天,沉寂的暖气管里出现了断断续续的水声,仿佛宣告着好事情就要降临。等到暖气正式来临的那一天,整个世界的气质就不一样了。我们被一层看不到的温柔缱绻包裹着,阴冷的屋子变得和煦。
是时候取出青梅酒了。
酒是琥珀色的,晶莹剔透的冰糖已经化在了烈酒里,带着绒毛的青梅也有了浅而皱的纹路。尝一口,酸甜而温吞的味道在舌尖绽放,原来经过这么长时间,往日的烈酒也被“驯服”了。微微可惜的是,这味道未免过于温顺绵软,像面目模糊的老好人,不能说人家不好,但总是缺少了点什么。
这样的酒,就需要用冰来激一激了。有时候,冰会激发出食物更深层次的味道。投入冰块之后的青梅酒,不仅更加清冽,而且熠熠生辉,仿佛一枚小剑,划破庸常的生活。
青梅酒酿了两三年之后,琥珀色就会变成金黄色,酒也变得更加绵软,这是时光的力量。不过我从未喝过三年以上的青梅酒,统共就那么一瓶,哪里能等得了三年,不到一个冬天就已经见底了。
杨梅酒是红色的,时间越久,颜色越深。深红色的它自带强烈的戏剧效果,像舞台上深红的丝绒幕布,沉甸甸地遮掩住人生的戏码。等你掀开幕布浅尝一口,就明白了,那甜美可人的外观都是骗人的,杨梅酒的底子到底是烈性白酒,多喝几口,醉意就上来了。
杨梅酒给人的感觉很不“日常”,它的红是朱砂痣的红,是张爱玲笔下的红玫瑰的红,浓烈、热辣,像没办法过小日子的大小姐或电影明星。但其实,它并没有看上去的那样不接地气。在酒里浸过几个月的杨梅甚至有一种特别世俗的用法:做红烧肉的时候,从酒里捞几颗出来放在肉里,去腻增色,还有丝丝缕缕的暗甜和酒香,简直是点睛之笔。
去年秋天,一场疫情令身在兰州的我们经历了核酸检测和居家隔离。隔离的某一天,我一个人在卧室望着窗外。沉沉的天幕下,矗立在对面的那栋往日灯火通明的大楼,变成了沉寂的灰黑色建筑。里面的人,那时候正在某酒店隔离。我心中压抑,便去客厅的酒柜里随手摸出一小瓶甜酒,这是之前凑单买的一瓶莫吉托,一口气喝了半瓶。舌尖才辨别出糖的甜和柠檬的酸,我整个人已经迅速松弛下来了,那个瞬间,它就是我的“快乐水”。剩下的半瓶,我决定冷藏起来每天喝一口。
小时候看巴金的自传,他回忆过童年时家里的一个女佣,她对东家的孩子们非常温厚。她喜欢喝酒,年年都要泡桑葚酒。桑葚熟透了的时候,孩子们把黑甜的果子吃了个够,嘴巴都染成黑紫色。她把剩下的果子收拾了,塞到瓶子里去,每个瓶子里都有大半瓶的酒。
我小时候没见过桑葚,也不能想象桑葚酒的味道。但几十年过去了,我喝着甜酒的时候,偶尔会想起那个泡桑葚酒的中年女人。她存着那么多甜酒,到了冬天,一定会时不时拿出来,心满意足地喝上一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