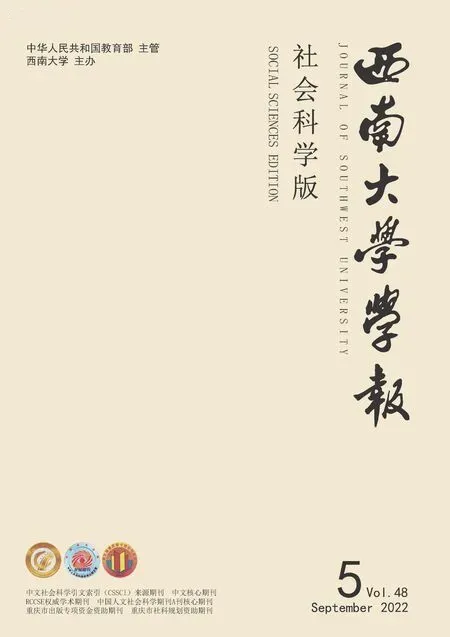明清商人传记中的侠义书写
——以明清碑刻资料为中心
宋 立 杰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400715)
一、问题缘起
侠的起源,似很难界定[1],出现于文本之中,则始于韩非子,他从国家统治角度对侠予以贬斥。司马迁与班固特设《游侠传》,以自己的理解与时代需求,构建了崭新的侠文化,但自此之后,侠远离了官方史书,代之而起的是文学之侠,当然并不是说官方史书中没有了“侠”,只是没有了侠士群体,但在人物形象塑造中充盈着“侠义”精神。由“侠”引发的侠文化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史书到笔记小说无一不描述了具有侠士风范的各色人物,造就的“侠”成为传统中国社会中一个特殊的存在,既有现实依据,又寄托了人类独特的精神向往。明清时期,侠义书写又发生新的变化。明清两朝是传统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其中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商人地位的上升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促使社会观念发生转变,既而影响到商人的文本形象。与前代不同,明清商人的文本正面形象渐多,也突破了以文学作品为主的范畴,大量出现于史传之中,呈现出诸多侠义形象。学界历来对明清商人传记研究颇多,大致呈现出两种研究路径,一种是探讨文本本身及其产生过程,一种是以其内容作为相关研究的论证史料[2]3-15,但相较而言,商与侠的关联似不被重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相关研究成果较少,也不够全面,或以汪道昆及其《儒侠传》为主,分析徽商的特征[3],或以“三言二拍”为切入点,分析侠商形象[4]。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撰写者应如何书写,选择怎样的事情进行裁剪,既能突显商人之优点,又能显示自己不是为钱而写?侠义遂成为商人传记重点关注与突出的特性。
二、明清商人行为的侠义化
翻阅明清商人传记,我们会发现有大量的侠义行为描写,甚至撰写者直接用“侠”来评定商人。彭启丰读完蒋士铨为蒋坚写的行状后,认为蒋坚“类古之豪侠好义者”[5]。陈光烈指出商人岑生祥“有古任侠风”[6]719。商人邓熇“有古任侠风”[7]。文本中商人与现实中的商人总是存有差距,这一点我们不能忽略,但也不能夸大。当然与文学作品中除暴安良、打抱不平、持剑江湖不同,史传中商人表现出来的侠义更多的是重然诺、乐于助人。与此同时,传主自己,包括他的子嗣、亲戚朋友、不相识之人都不可能对其实时跟踪,对他们所有的行迹与心理活动都了如指掌或者知晓,即使是他本人也不可能对自己的一生所有事迹都记忆如新,于是在这种背景下,撰写者利用可利用的资料,结合自己的了解与想象、社会现实与观念,对商人的人性进行书写。
(一)商人职业与商人人性书写
商人的职业身份与自身文本创作有着密切联系。商人对自己的职业、目标及其价值观可谓是理解透彻,职业的阴暗面和阳光面也都十分清楚。商人撰写者大都经商多年,在商海中沉浮,或致富,或一事无成,重新审视自己或者他人,为职业身份的成功与失败寻找原因。而且人具有社会属性,总是通过他人的反馈来审视自己,根据他人认可自己哪些行为来判断自己的得失成败。商人们也深知社会对商人职业逐利的批判,为彰显商人的社会属性,也使得他人重视商人,为自己或者其他商人的一生画上较为圆满的句号,故而在很多时候,他们都刻意回避商人职业逐利的本质,他们会有意识地书写那些顺应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行为。即使不认同自己的职业,但是多年的职业生涯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书写,影响撰写者如何选择事件、如何设定情景、如何体现自身价值。虽然有些商人的子嗣未从事这一职业,但是耳濡目染,以及生活在传统社会,也会塑造出积极正面的父祖形象。作为商人,可以说他们对商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努力改变商人形象,同时也将自己的职业行为与观念融入文本的商人人性想象与书写之中,他们将商人定格为国家与社会的有用之人,而不是碌碌无为、只知道追逐利润之人,否则还有书写的必要吗?本文拟选取六篇商人传主参与传记撰写过程的商人传记(1)商人传主参与传记撰写过程的传记包含四种类型:商人传主自志、由商人为传主撰写,传主在临终前以此事嘱咐子嗣或他人撰写,商人子嗣所写。以表现传主商人的侠义人性与行为以兹观听,详情参见下表。
由商人参与撰写的商人传记,他们力图展现出商人职业最佳的一面,也就是重点叙述传主待人以礼,以及对国家与社会的贡献,对经商行为的着墨也是渲染商人的不易与对侠义的坚守。王重新撰写的自述,以不到一百字的篇幅交待其家世与家庭背景,剩余篇幅刻意叙述了自己在公益慈善事业方面的捐款数额[8]。我们并不清楚捐款数额占据他总财富的比重是多少,对他而言是否只是九牛一毛,抑或是全部家产,当然我们不能否定他的公益慈善。张謇作为商人兼政治家,长期致力于实业救国的实践,期待出现一种合理有效的商业政策,他在为商人张颂贤撰写的墓碑文中,陈述了他关于盐法的措施,并感慨道:“今天下又多言西法西人之于盐也,征税产所均远近无二价,此岂非贤人君子之所乐闻而彼顾能行,何故?因表公墓并缀而纪之,以告中国谈盐法者”[9]55。他也期待更多的商人投身救国行列,所以在他撰写的商人传记中无不突出商人为国为民的行为,一方面是为改变商人的社会形象,一方面是号召广大商人仿效传主,“自营大生纺厂以来,当时同甘苦共忧患如沈君爕均、蒋君锡绅、林君世鑫诸人,先后继谢。方用怆恻而君又逝矣。后之来者,其能坚苦忠实如诸君当日之助我与否”[9]57?

表1 商人参与撰写的文本中对传主侠义的书写
(二)商人职业之外的撰写者与侠义书写
职业之外的商人传记撰写者们以儒家价值观为导向,对待商人职业的态度有所不同,在书写中出现了分化,或认同商人职业的独立价值,或将商人职业精神纳入儒家文化影响范围内,但皆无例外地刻画出有侠义之风的商人形象。由第三方撰写的商人传记中,我们往往能看到他们以“经商起家”“坚忍耐劳”等寥寥数笔带过传主的经商过程,他们重点关注的是商人起家之后,如何发展与转型。司马迁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10]这句话的意思大致是人只有解决日常生活问题,才能知道礼义廉耻;只要生活富裕了,仁义就自然而然地生成;人富裕了便要行仁义之事。明清时人非常重视司马迁及其《史记》,写传记往往会借鉴其思路,至于给商人作传,更无疑参考了《货殖列传》,并融入时代的新因素。徐世昌为商人刘凤舞撰写碑记,就点明:“昔太史公于货殖郑重而为之传,如我公者,岂仅以货殖称,直义侠而兼以忠勇焉”[11]。在对商人一生有了鸟瞰式的了解后,第三方撰写者以第三人称视角审视商人传主与商人职业,从中挑选出自己需要的事件,或者说是自己应该承担的、但苦于各种因素没有承担的社会责任,也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融入文本中,对商人职业的褒贬融入其中。在他们的笔下,商人的侠义无外乎以下几种:
第一,救人急难,慷慨施财。叶华晟称商人唐可才“虽起家纤啬,见苦为生难,而能不重弃其财。……平日自奉不薄,推以及物,建汤房,置义田,施义棺,遇岁欠,买谷赈贫,全活甚众。”又引用其语以彰显他的好义,“(财)自我得之,何妨自我失之。守财虏,吾不为也。”[12]351-352商人单纪乐于助人,他认为:“积而弗散,裕己而不以益人,非义也!”[13]117-123商人纪溁“乐为义举,遇贫不能婚丧者,出赀助之。旅困无所于归者,资给遣之。负贷不能偿者,辄焚其券。”[14]268-269
第二,果敢有为,为国事奔走。马启鹏在为商人米天成撰写的碑记中,如是写道:“公不第疏财,而且果敢有为。当甘省小丑跳梁时,不避霜戈直捣贼巢,皆箸而筹谋。皆中棨奉檄以往,顽无不格。虽无阃外之寄,居然干城之选,非公之武略素善而能若是哉”[15]?明朝中后期边事较多,而国家财力不足,商人苗志达勇于“输钱□盐,接济三边”[16]。亦有为商人之才没有被应用到国计,或者说是没有被统治者重用而感到惋惜。叶华晟便为商人唐可才的才学所折服,他声称:“昔与余尝杯酒论天下事,凡四方贞淫奢俭,与其得失利病之源,即所游历,入目留心,凿凿言之,令人倾耳忘倦,如读十五国风。夫计然之策,越以之霸,君仅施之于家,未获效之国”[12]351-353。撰写者唐灿在梳理商人郑汝城的事迹后,感慨道:“使幸而效职于朝,淂本其素所蕴蓄而大用之,将仁民爱物所以施,当时而泽浚世者岂其征□?”[17]80-81
第三,待人有礼,为人谦恭。商人郑汝城“生平以礼自待,以礼待人,远绝声色,不立宠幸,亲用往来虽习熟,童稚必具衣冠迎送之,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有古大臣正色率下之风。”[17]80-81商人黄璋“居常每自谦约,与人交若退然不过,而千顷之波,使人自醉。”[18]
第四,重然诺,讲信义。商人姚文瑞“尝与其友人顺义郭珍共利,后珍没,义士赍其所遗五百金,涉千里付珍子锐。”[19]杨一清如此描述商人纪溁的信义,“盖虽不废货殖,而恒持信义,义名满江湖,彻于朝省,子姓化之。有弗尔者,人曰:‘独不愧容庵乎?’”[14]268-269
时人以及作为后人的我们往往认为第三方撰写者受到金钱与人情的干扰,存在“谀墓”情形,大肆赞美传主。但是换个角度考虑,非大奸大恶之徒,或是窃国者,我们总是会不自觉地挖掘他们的闪光点,而不是只盯着他们的恶处,如同佛教所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当然,第三方撰写者们对商人之恶也不是置之不理,而是通过对比的方式,对商人职业提出批判,同时也更加突显传主之优。商人欧阳程告诫他的两个儿子:“阿堵物非吾所有,此天之优乎于我以周贫乏者,当留余以代天行化耳!”撰写者欧阳钦知晓后,指出他“见解之大,迥超流俗如此,宜上天之眷亦倍隆于他人也乎?”[20]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商人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民众既艳羡商人的富有,谈论他们的轶事,又在精神上予以鄙视;国家既利用商人互通有无,又在政策上予以限制;商人虽然被定位在社会结构的底端,但是受关注的程度却很高。之所以出现这些矛盾现象,原因就在于商人的财富与行为,在于他们如何获取财富以及如何利用手中的财富。在国家与时代面前,商人一方面为生存不断跨越道德底线,追逐利润,一方面通过行动改变自身形象,顺应主流价值观。故而在明清商人传记中,有关商人的侠义人性书写随着时代变迁呈现出新的形式与特点,做到了没有因善小而不为,尤其在民众危难之际与社会动荡之际,商人往往挺身而出,为国事奔走。
三、商何以称为侠
常理言之,商人与侠是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或者说是两个不同的职业与社会角色,但为何逐渐合流呢?犹如所谓的山人侠、文人侠、僧道侠一样,二者之间必然有相通处,如郭沫若先生便认为侠大抵源于商贾[21],他的立足点是有些侠士就是以经商谋生。我们去除这一角色与职业要求,他们都是自然人,在社会中,通过摸爬滚打逐渐成长;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认识与了解自己,认知自己的职业与角色,并根据他者的反馈,对自己的职业与角色扮演进行适当地调整。什么是侠,什么是商,不过都是他者的定义。
“侠”,首见于《韩非子》一书,至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侠文化发扬光大。虽然侠不绝于各种题材的文本之中,但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对“侠”的认知不断发生变化。相关研究成果表明,自晚唐开始,侠的道德化色彩逐渐增强,“义”的成分逐渐加强;自宋代开始,“侠”又与“忠”联系在一起[22]132-142。从侠的内涵演变来说,侠也许不是一个群体,只是一种身份认同,如同王国璎所言:“侠客显然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之社会阶级,上自王公将相,下至闾巷游民,只要符合重然诺、轻生死、拯人困厄、不矜其能之精神行为,即可誉之为侠客”[23]。明清时期,文学作品中的侠已不再是游离于国家与社会之外、恣意而为的群体,而是转变成符合主流价值观的群体,甚至是积极遵循国家法度、服从贤明政治或者清官政治、扶植社会伦理纲常的群体,但诸如打抱不平、救人急难、一诺千金等行为仍然不变。就此点来说,商人与侠确实有相通之处。商人为了发展,改变社会形象与地位,必须是要向政治靠拢,遵循法度,不成为现行秩序的反对者,与士人交好,以期融入主流话语圈。葛群曾指出商人与侠的精神文化核心都是“信”与“义”[24];韩云波先生认为中国侠文化中道义与人格评价的基本模式有三种:侠义人格、信义人格、自由人格[25],也就是说侠义与信义人格是侠的基本组成部分。杨继平等人以心理学视角阐释明清晋商巨贾的人格特征,立足于数据分析,指出“诚信义礼”是明清晋商巨贾人格的核心特质[26];张孝义也采取实证研究方式,得出“诚信义礼”是徽商人格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27],此外,他们专门设有“侠义的”人格特征一项,商人的相关系数都在0.58和0.77,也是较高的组成因素。上文所引事例也充分表明商人的侠义人格特征。因此,可以说商人与侠在侠义人格方面具有相似性。相似的精神文化核心基于相同的生活模式。
第一,流动性与侠义行为。侠的流动性自不用详说,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侠义小说与武侠小说都向我们展示了以四海为家的侠士。商人的流动性也很高,他们既有在家乡附近从商,又有远赴异乡经商,即使是在家乡附近,流动摊贩也是很多。商人钟铎“比壮,以贫故出游江湖,过豫章,下金陵,遍于吴越之墟,挟所有为服贾计”[28]112;商人杨焕文“弱冠时,为奉亲计,营药材业以运售参茸为重行,每往返吉祁两地……”[29]这便使得商人所看到的与听到的事情要远比一般人多,那么理所应当地遇见的不平之事、灾害也远超于常人。换句话说这无疑是向商人行侠义之举提供了一个前提条件,侠义之行并不能等着事情自动找上门,而应主动地探寻。商人王镇前往苏州贩米,适逢当地发生饥荒,于是他便将粮食赈济灾民[30]。侠士也是路见不平与知道他人危难,便仗义为之。流动性强也意味着商人可能名闻遐迩,也许会有人主动前来寻求帮助。“附近贫困居民凡有求助,”商人郭恩布一一应允[31]。再者,商人在他乡经商,为了生存与发展,则必须要有所为与有所不为,既要获得官方支持,也要获得民意,获得舆论的认可,不能兼顾一方,最好的办法便是义举。而且他们在异乡经商致富,传统社会观点一般认为社会财富的总量是固定的,你致富了,也就是相当于你抢占了本属于他人的钱财,因此必须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也是我们查阅各种史料后,发现很多商人在异地展开公益实践。
第二,广交游与信义。人是社会性生物,需要在人际交往中发现与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一点对商人尤为重要。商人职业的目标就是把商品贩卖给他人,所以要形成稳定的客源。如只是为免除饥饿之困,仅限于一隅足可,但要成为富商巨贾,并免受外部的侵扰,他们必须要扩大交游面,并维持友情。维系友情的发生有很多种,投其所好是较为成功的方式之一。我们翻阅商人传记都会发现商人多精通文学曲艺,商人钟铎“每读书为歌诗,多所自得,尤究心小学一书”[28]112。这些行为的指向对象也很明确,即士人。商人唐可才“素好客,善谈论,宾朋宴会,投辖尽欢,伐木之章,可与歌也”[12]351。商人单纪“喜承接大夫、士,南北舟车过者,多为馆谷,礼意周洽……”[13]117-123笔者尚未发现商人召集普通民众举办聚会之记载。这固然是要走入士人官员的圈子,也是为通过他们扩大商业规模。但真正能维持友情的方式只能是信与义,对人真诚,重然诺,而不是虚伪狡诈。文人雅士往往也最为看重这一点,他们在商人传记中也重点铺叙。商人冉文魁“公性平直,与人交无二言,始终见重”[32]。撰写者总结商人王逍的人性特征是“为人襟度,恢廓磊落,诚信质直,绝无一毫矫伪”[33]91。侠士交游遍天下,或者其名闻天下,无论走到何处都有崇拜者与追随者之根本也在于信义。
第三,豪气。豪气往往与武术相伴随,侠之豪气是众所公认的,在我们的固有观念中,构成侠士的一个组成元素便是武术,山人与僧道等群体因为一些原因都要具备此种元素。相对而言,商人群体则缺少这个元素,或者准确地说武术不是商人职业必备的元素,那为何还要称之为商人侠,或者侠商,甚至是商人的侠客化呢?原因有二,一方面在于传统中国文化对侠内涵的认知与构建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一方面在于二者确实存在相同之处。冯媛媛指出,传统中国社会后期评判侠的基本标准是他们的精神,“能否称得上‘侠’,关键不在其武艺的高强与否,而在其行为是否符合‘义’的判断标准”[22]133。商人的豪气体现在勇敢、豪放、热情等方面。商人唐可才意气风发地说道:“大丈夫不能封侯万里外,亦当贸迁江湖,营素封业,与千户侯等。安能困守闾里,作乞儿态,向富室求活耶。”[12]351-353商人王逍也认为:“大丈夫生而上不能开基以光世德,下不能垂裕以启后人,□何益也?”[33]91
与豪气对应的便是容忍,商人不是遇事不忍、恣意妄为的群体。我们常说侠客“纵性情”,实则不然,连韩信也都有胯下受辱之情形。商人内敛,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面对他人的辱骂挑衅,往往能笑而应对,颇具儒家所倡导的人格魅力。“闾里间有恶少,肆为诟辱,傍观者扼腕不平,(商人李梦祥)翁怡然受子,毫无介蒂,异日恶少悔罪负荆,翁以理谕之,仍厚以赠之……”[34]他们礼遇文士、温厚谦恭、待人有礼,不仗势欺人,这也是侠所具备的内涵与品质。
四、社会变迁视野下的明清商人人性书写
明清时期处于转型社会时期,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表现便是大量的普通民众选择经商以谋生,甚至一些儒士因为孝养父母、科举无望等原因而选择经商。农民弃农经商,士人弃儒业商,从人员结构方面大大丰富了商人的来源,使其多元化。农民本身便是社会运作的基石,国家历来重视农民与农业;士人又掌握着话语权,继而从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商人形象与提高了商人地位。当然这些都只是抽象化的概念,实质性的表现便是国家与社会离不开商人与商业,我们通过明清国家商业政策的变化则可一览无遗,以至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不断有学者对传统中国采取重农抑商政策这个观点持质疑态度,甚至有学者指出明清时期是重商、通商的。[35-36]这一深刻的社会变革影响到商人对自身职业及其价值观的反思,也影响到士人如何看待商人。
(一)商人自身的应对
商人很早便是一个独立的阶层,商人传记也不是明清时期方才出现,在唐宋时期便已产生,只是数量较少。唐宋时期就有文人为商人正名,指出商人的价值所在,但受制于传统社会结构及其稳定性、国家政策、民众心理等因素,商人的自我职业价值观还没有成熟,商人职业的独立性人格也没有确立。直至明清时期,情形方有所转变。一些商人逐渐拥有较为成熟的职业意识,也敏锐地注意到时代发展脉络及其需求,他们开始勇于提出自己的主张,如商人王文显便对自己的子嗣讲道:“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只要修高明之行便无可厚非[37];商人李濬功指出“四民之业,各有所讬以成名”[38]441。同时商人们还勇于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为乡里与国分忧。晚清以来,国家备受外国势力的欺侮,一些士人痛定思痛,寻求中国落后的因素,最后他们认为是西方重视商业与商人,方得以富强,于是他们振臂高呼,号召发展商业,国家与社会重视商人之价值。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商人自然而言地被尊重,成为实现富国、强国目标的最佳践行者。而商人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积极奔走,利用各种渠道扩大自身影响力,与士人、官员平起而坐。
在这样的现实环境面前,商人群体做了不同的选择。有的行为侠义化,为国为民,越来越多的商人逐渐形成独立的职业价值观,就是那些没有形成独立职业价值观的商人也意识到了商人职业的价值与功用,而不是无用之人。发展实业、发展经济、招揽工人、救助民众、为国奔走,成为商人的重要目标。商人李文邦直言道:“国家有事,民输委,分也。”[39]商人庞元济之父光禄公指出:“义庄者,为一族计耳。夫为一族计,则何如为一乡计,为一国计乎?”[9]147有的只顾追逐利润,将商人职业始终作为一个谋生的手段,或者是证明自己的工具。女商人李楝台劝慰其夫:“昔贤伯赣尝以货殖名倾诸侯,今世农工商复与士并重,夫子既不乐仕进,盍继先人业,异日倘以富雄一时,亦丈夫快心事也。”[40]即使是侠义化的商人,他们也不能忽视追逐利润,否则一事无成。不过在追逐利润的现实需求下,他们没有迷失自我,积极承担其历史责任,努力践行社会理想。他们知道要实现自己的角色定位,势必要以自身职业及其财富服务国家与社会,为了使国家与社会给予商人更多地关注与正面评价,于是他们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写入文本中,努力实现商人职业的价值,而不仅仅局限于自身价值,商人萧一经便言:“赀恶,其弃于地。吾既幸获丰饶,即当为有用用,不当为无用用”[41]。此外,他们广泛宣传,号召更多的商人投入到此行列中。当然商人们也清楚自己的财力与交游范围,他们多立足于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为身边有需求的群体提供各种帮助。商人孙衡甫便说道:“吾位卑,力不足以利泽天下,其施于吾宗与吾乡庶乎其可。”[6]724-725
(二)士人的应对
商人职业给商人撰写者提供了同情与认同心理,第三方撰写者虽然不曾经商,但丝毫不影响他们对商人职业的想象与书写。我们谈论明清士商关系时,往往指出士商相混,但又指出部分士人仍是在精神上鄙视商人,这些都无可厚非。即使是商人的职业意识也不可能全部一致,都存在肯定者,又有否定者[42]。且不管第三方撰写者持怎样的态度,都不能回避商人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与日俱增的现象,也不能回避国家与社会对商人与商业的依赖,也不能无视包括撰写者在内的民众对商人的矛盾心理。明清时期,国家不再需要游离于秩序之外的群体。在各种体裁的文本中,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是撰写者——赋予侠的内涵也发生转变,不再是恣意妄为的群体,而是与国家合作;即使身在江湖,侠也尽量不触碰国家秩序。现实生活中,士人也不需要破坏秩序的商人侠,秩序只能由他们来破坏或者改变,因此他们在书写商人的侠性方面,极力渲染他们对国家的依赖,对现行秩序的遵守。他们也反感商人凌驾于他们之上,凌驾于社会秩序,所以他们在书写的过程中,总会通过各种方式,把商人纳入国家秩序之内,或者说是置于士人之下,构建一种以士人(儒学)为主导的社会关系维度,塑造以士人为主导的士人与商人和谐相处,实现一种共赢的局面。如沈一贯在为商人刘得保撰写的碑文中,叙述县令邀请他为乡祭酒,但为其拒绝,沈一贯引用其一句话道明原因,“吾起田更老于贾,敢与邑主分庭益我盩,不可”[43]。也就是刘得保认为自己的职业身份卑微,不适合担任乡祭酒。因为刘得保“清醒”的自我认知,使得时人更加尊重他。如何共赢呢?也就是商人的行为符合士人或者说是儒家的标准,商人积极回馈国家与社会,积极顺应士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
第三方撰写者参与商人传记的撰写,不仅仅是为了人情、为了钱财,也不仅仅是为了重塑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与影响力,也是有一定现实目的,为了实现士人行“道”之人生目标。同时,第三方撰写者还刻意叙述商人传主好儒这一特征,以此强调传主的侠义行为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应对商人的强势。兹选取四名商人好儒行为以证之,详情参见下表。

表2 商人传主好儒情况一览表
在这一目标的驱动下,第三方撰写者努力构建一种新型商人形象,进一步说是构建新型国家的民众形象,即民众都应承担起属于自身的责任,为国家与社会的安危而有所作为,犹如顾炎武所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撰写者欧思诚不提捐纳制度的不良影响,而是强调商人的为国效力,强调民众羡慕商人可以为国效力。商人何聪响应纳粟之例,“输金数百,授奉训大夫,五品散官,峨冠花带,乡里大以为荣。又先后与其二子,俱援例为太学生,一时荣盛。人皆羡公能济国家之急也。”[44]面对民众苦于接待官兵,商人李濬功说道:“若者为国家靖疆土,□能食风饮露耶,其避之也?”于是“大治牛酒相与劳之,至再至数,所费不资,亦无难色。使人尽公也,何难令军士出死力以争先矣。时鲁令君嘉其行谊,赐冠带,表厥宅里”[38]441-442。不仅是商人传主本身如此,他的子嗣也要如此,如能步入仕途则更好。很多商人鼓励子嗣参加科举步入仕途由此得到了国家的赠官,这些都是与统治者合作的表现。县中举行乡饮酒礼,当地官员与士大夫都邀请商人王才参加。嘉靖三年,他以子“惟臣贵,受封如其官。南道赵侍御得祐辈十九人,铨曹丰主政坊辈二十人,相率为文为诗,为椿萱图,以遥祝焉。先是大学士邃庵杨先生,石斋杨先生,及都宪渔石唐先生,道经咸阳,必往顾之。渔石又有诗以赠”[12]183-184。换一个角度来说,商人如果没有侠义行为,没有为国效力,没有子嗣辈荣登进士,没有展现出良好的面貌,也许便不会有商人传记了。
明清国家的强盛,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生活方式的丰富化,虽然使得每一个民众受益,但受益程度有所区别,在无形之中拉大了民众之间的差距,国家越限制商人职业,但经商致富的现象越来越多,一些富商大贾的高调行为将其财富显露无遗。差距的扩大无疑会导致民众心态与行为发生变化,也许这便是明清时期,包括官员在内的民众纷纷经商的原因。限于信息传递方式与效率、政府行政程序的繁琐,在很多情况下,包括士人在内的民众处于无人接管的状态。明清时期又是第四个小冰期,自然灾害增多,虽然国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救助,但往往没有实现既定目标。这一切问题也是“侠”在中国传统社会与文艺作品中始终不曾消失的一个原因。明清文学曲艺作品的发达,使得普通民众更容易接触到侠的世界,在文本中,侠总会不计个人荣辱得失,帮助他人。现实中,民众也需要有侠来帮助他们,当然不一定就是报仇、打抱不平,更多的是生活上的帮助与关怀。士人也是如此,虽然士人位于社会结构的第一层,但明清时期士人的生计异常艰难,只有少部分士人可通过科举入仕,通过儒学教书,实现人生的飞跃与生活质量的提高,更多的则是在生计上挣扎,他们也需要侠的帮助,包括生活上的与行政上的。士人在文学作品中描写侠,增加其世俗化色彩,增加其道德伦理内涵,也是将现实需求反映到文本之中。然而虚幻的侠只能带来心理与精神上的满足,读后带来的是心理失落,犹如常庭琪自言:“间尝披览遗史,见所称为义侠者,每心焉向往,不禁有闻斯语不见其人之叹”[45]。他们需要活在现实中的侠,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商人的出现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们的愿望。上文提及第三方撰写者描述商人的侠义行为,除却为国事奔走外,其余几点更侧重于日常生活,通过点滴事情突显商人的侠义与价值,修路、修建桥梁、建学校、施粥等行为更是具有地域性,多是围绕商人传主的生活区域而展开。这一切都使得侠士不再像小说中那般虚无缥缈,而是变得更为真实,大家都能力所能及与感受得到。撰写者们往往也会在文中直接点明自己的意图,以激励商人亦或是其他民众观摩效仿。刘四达为商人李树鹏作墓表,文中写道:
先生劳劬数十年,而家始粗裕。其囊底金钱,固非若掘地得之者。然人之以急赴者,必委屈筹划之,以遂其求,而未尝栩栩然有德色也。嗟嗟世风之下也。匹夫拥多金,蓄厚赀,美宫室,耀裘马,朋党酒食相征逐,及逢贫苦亲,不为分多而润寡,反视之而若不相识者。以视先生之勤俭自守,而施与不吝者,其人之贤不肖为何如也?[46]
第三方撰写者试图通过为商人作传,铺叙商人的侠义行为,制造商人的一种从众心理,或为了获得士人的认同,或为拥有一个可以流芳百世的名声,或苦于形势不得已而为,采取一系列的行为。富而好礼的商人,或者说是急于改变形象的商人,困于传统社会结构的商人充当了“侠”。文人也在有意识地打造商人侠义之风,通过文本宣扬商人的精神价值观,号召更多的商人践行商人职业的人文精神。
五、结 语
明清商人传记的撰写者身份较为多元,有的撰写者以商人为职业谋生,职业之外的撰写者通过自己的理解与需求书写自己心目中的商人,他们通过对社会各类人群与事情的观察,用文字表现自己的精神世界。也正是基于此,撰写者笔下的商人,都是作为商人中佼佼者的形象出现,不计个人荣辱得失,一心为国为民,但同时商人也缺少了侠客对现行制度抗争的一面。撰写们将商人职业群体的众生相呈现出来,塑造出不再是只为追逐利润而对国家与社会无用之商人职业形象。同为商人的撰写者深知商人不再是只顾利润之角色,而是拥有崇高理想的角色,商人职业也不再仅仅是谋生之道,而逐渐走向主流化,他们更是在文本中书写自己的价值观,书写商人的侠义人性,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侠义精神进一步下沉,使得每个民众都意识到侠似乎就在我们的身边。但我们要注意,无论政策怎么改变,士人怎么高歌商人,实际上都只是国家将商人职业当作一种工具,士人在对待商业、商人的态度也非常多元。按照黄开军的统计,明清时期为商人作传的“拥有庠生以上功名的作传者占86.36%,而拥有进士功名的作传者占44.86%”[2]166,虽然他们在传记中对商人与商业呈现出认同的态度,但归根结底,他们只是将商人职业当作一种工具,一种暂时性的工具,而不是长久性的工具,商人职业与商业发展的需求必然要附属于政治,商人必须依附于士人与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