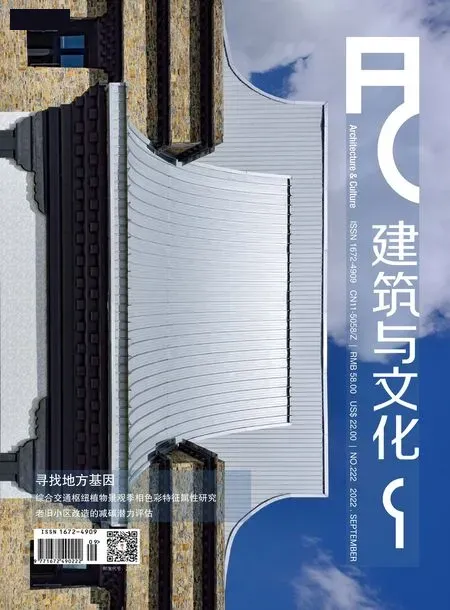乡土传统的多种诠释
——刘家琨、王澍建筑设计中乡土角色的差异
文/潘沈佳 浙江工业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
郭子瑜 浙江工业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
姚冬晖 浙江工业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 教 授(通讯作者)
引言
在当下的建筑师中,刘家琨和王澍是堪为类比的两位,他们的实践多饰以传统的乡土材料,而“乡土”这一关键词更是不断地出现在他们的建筑思考和设计诠释之中。然而,对于思想与实践看似如此接近的两位建筑师,“乡土”这一概念不但是他们共同的关注,也是深入辨析他们设计思想关键差异的切入点。而对于两位建筑师乡土视角与乡土运用方式的比较研究,也能展开对“乡土”这一概念范畴的、多维内涵的、更深刻的理解。
1 刘家琨建筑设计中的乡土角色
1.1 刘家琨认知乡土的视角
刘家琨认知乡土的视角植根于他所谓的“近期”观点,此种“近期”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平民社会和日常生活,亦即当下普通大众成长的日常环境。刘家琨讨论和关注的乡土范畴常被他称为“近期传统”,以区别于更久远的理想时代中的乡土传统,也即他称为的“古典传统”。对于这两种以时间久远不同区分的乡土范畴,刘家琨以王澍的设计作类比,并戏谑地谈到,“‘近期’离现代更近一些,王澍讲的有点像‘孙子’讲‘爷爷’,我就讲‘我爹’吧。”[1]刘家琨认为,在建筑实践中去追溯久远的乡土传统,这并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事情,而是每代人都必须要做的。但对于当代建筑师来说,更重要的是近期和当下文化的承接,这恰恰是当代建筑实践最急迫、最核心的文化传承问题。因此,刘家琨提出先缝合“近期传统”的文化断层问题,再由后来者去探索更远的“古典传统”的文化传承问题[2],这就是他关于“近期传统”和“古典传统”两种乡土范畴的态度和立场。
正因为此种立场,刘家琨反对“舍近求远”地去看待中国现代建筑实践中的文化传承。在他看来,“古典传统”更多的是一种理想化的想象,甚至都不能算做是一种回忆,它是一种文化乡愁而非现实传统。与之相反,作为普通大众集体记忆的“近期传统”,却要比那些理想化的“古典传统”,更能帮助当代中国建筑建立起对日常生活与传统文化之间积极关系的反思。正是在此基础上,刘家琨关注的乡土建筑范畴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每一个普通大众(everybody)的日常性(everyday)房屋及其建造传统。
1.2 刘家琨设计中的乡土运用方式
从对新中国普通大众日常性房屋及其建造传统的关注中,刘家琨将启示其建筑设计的乡土对象概括为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是20 世纪50到70 年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留给今天的一些空间记忆;二是在中国当下民间涌现的一些‘普遍的’建筑元素和空间模式。”[3]而他实践中运用乡土的方式也呈现出如下特点: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普通大众的日常性房屋给予刘家琨形式上的启示,对这些日常建筑的原型借用和形式转化正是刘家琨缝合当下建筑文化断层的策略。刘家琨对这些乡土的形式原型采用了抽象、简化等陌生化处理手段,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既不能简单仿造以假乱真,又不能突兀张扬喧宾夺主”[4],对此,刘家琨借用的是形体、布局等乡土形式的抽象化,而对于材料、细部、肌理等立面语汇,刘家琨却不照搬乡土,而是选用更适合于建筑实际功能和建造的现代语汇,这是一种“当代手法、历史记忆”[5]的建筑理念。而对于这些形式原型的借用和转化,在刘家琨手中体现了面对“此时此地”的灵活和智慧,它们既可以被转译为胡慧珊纪念馆这样最小的纪念建筑中,也可被转化为西村大院这样大尺度的商业综合体,吻合新的功能和城市活力。
在这其中,一方面,从成都平原最普通的灰窑到罗中立工作室,从四川地区普通的工业厂房到四川美术学院新校区的艺术设计馆,从集体居住的大院形式到成都西村大院,计划经济时代的日常建筑给予刘家琨以形式借用的原型;另一方面,从江南农村中常见的农民自建房到南京CIPEA 客房中心,从四川城市中常见的平民聚落到水井坊遗址博物馆,从汶川地震中普通的临时帐篷到胡慧珊纪念馆,当下普通人的民居及临时性建筑同样给予刘家琨以形式转化的启示。
其次,这些普通大众的日常性房屋之中蕴藏的民间智慧,在形式之外同样给予刘家琨以建筑概念和策略上的启示。他认为,这些普通人的房子尽管无序、简朴甚至笨拙,却包含了一个时代普通大众的集体记忆,蕴含了中国式生存智慧,以及为实现基本需求而运用手边资源解决实际问题的中国式生存哲学。而对于这些集体记忆和民间智慧,正是刘家琨所立足的“此时此地”,因而刘家琨建筑中乡土运用的另一方面即是融合民间智慧、运用于材料和建造中的低技策略。再生砖、小框架和再升屋是刘家琨在汶川地震后新的经济和建造条件下转化传统以处理现实的一种手段。再生砖来自计划经济时代民间土砖窑的烧砖做法,即利用破碎的废墟为骨料,以秸秆为纤维制成的廉价水泥砖。小框架和再升屋是一种师法农民自建房的建造智慧,先将结构加大以便应对未来增建可能的结构体系(图1)。刘家琨的低技策略面对现实,选择技术上的相对简易,关注经济上的廉价可行,向中国社会中广大简易而自发的民间建造学习。

图1 刘家琨对“小框架”的图解(图片来源:参考文献[10])
而这些源自民间建造的低技策略也被运用在正统的、甚至商业操作的建筑之中。以西村大院为例,刘家琨谈到再生砖在建筑和景观中的大量运用。
建筑山墙、局部实墙、景观铺地、院墙等。断砖加工方式使再生砖的内部骨料得以暴露,成为独特的材料表现。除再生砖外,将大孔砖孔朝上用于屋面种植,而孔朝外用于机房通风和通透围墙;将小孔砖孔朝侧面,利于垂直绿化;将多孔砖孔朝侧面用于展廊墙面,利于展品固定;以及将常用于基本填充的煤矸砖作为清水外墙等,均是对基础性材料非常规应用的发掘和表现[5]。
最后,除了上述两种倾向,刘家琨的建筑还呈现出一种民间乡土宽容又人情化的建造立场。比如在鹿野苑石刻博物馆中,面对农民建造粗陋的现实,他没有强迫浇筑一堵垂直的混凝土墙,而是运用了外置木模板,与砖墙作为内衬模板再浇筑的“弹性化”方式,以容忍相对不精细的建造现场,宽容地处理了不职业的建造者浇筑混凝土的困难。而在西村大院中,刘家琨并没有对自发性的商业店招充满抗拒,而是宽容地将建筑立面退隐到阳台和走廊之内,在保证建筑体量完整的前提下允许未来业主对建筑立面自发地改造和个性表达(图2)。

图2 西村大院在保证建筑体量完整前提下对商业店招的宽容(图片来源:参考文献[11])
2 王澍建筑设计中的乡土角色
2.1 王澍认知乡土的视角
与刘家琨扎根于“近期”的平民社会和日常生活不同,王澍的乡土视角更聚焦于久远时代经典化、理想化的乡土传统。同时,与刘家琨对城市和乡村中的乡土传统一并关注不同,王澍尤其关注那些在自然与乡村环境中的乡土传统,这也影响了王澍认知乡土的两个层面:
首先,立足于中国传统的自然与乡村,使王澍选择在浙江这样一个能葆有江南“经典化”乡村环境和乡土想象的地域中,而非上海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大城市中实践①,这是以传统乡村的乡土文化对全球化趋势下普遍性与趋同性的一种抵抗。
其次,王澍批判当下乡村建设的无序和混乱,伤痛于传统村落的消失和乡村环境的破坏。在表达对宁波博物馆选址的感受时,王澍谈道:“场地位于一片由远山围绕的平原,不久前还是稻田,城市刚刚扩张到这里,原来这片区域的几十个美丽的村落,已经被拆得还剩残缺不全的一个,到处可见残砖碎瓦。”[6]这表达了一种对于当代无序建设对理想中乡村田园破坏的“黍离之悲”和深切痛惜的文人情怀[7]。
正是因为如此,王澍的乡土视角总是唤起一种对经典化、理想化的乡村田园的文化身份认同。乡土在王澍的表述中总是处在一种被灭绝的危险中,这也构成了他乡土语境中强烈的抵抗意味。如刘家琨所戏谑的,王澍的乡土是一种“孙子讲爷爷”,一种理想中的“经典乡土传统”,它不是近期或当下集体大众的日常生活,而是在物质传承之外更具精神性的文化身份认同。正因如此,王澍建筑思想中认知乡土的视角尤其体现出对中国建筑民族特征和地域特性的强调。
2.2 王澍设计中的乡土运用方式
关注久远时代经典化、理想化的乡村传统,寻求民族和地域的文化身份认同。正因如此,王澍把自己视为那些把乡土民居与文人园林一并思考的中国建筑先辈的继承者,他对传统村落、乡村民居的讨论总是和文人学者的园林甚至山水画夹杂在一起。一方面,他的工作室名为“业余建筑工作室(Amateur Architecture Studio)”,强调师法非建筑师、非专业化的乡村传统和业余方言;另一方面,正如他多次强调自己是一位“来自晚明的学者(scholar)”一般,王澍同时表达了自己品鉴园林、山水画的学者风雅传统。这种“业余和学者”的并置也构成了王澍乡土运用方式中的独特性,并呈现出如下特点。
首先,园林、山水画的风雅传统与乡村民居业余方言的混合构成了王澍设计中的形式语言。王澍建筑的意象源头、环境关系往往来自山水画,他的建筑空间受到了园林的启示。以世博会滕头案例馆为例,其内部空间场景不但直接生成于山水画中山林洞穴,而空间路径同时也是园林中蜿蜒游廊的转译。在此之上,来自乡村民居的材料、细部和肌理更构成了王澍建筑中最明显、也最具个人特征的标示性。
王澍曾对浙江乡村民居的立面材料与视觉呈现进行深入调研。他关注民居中砖石的砌筑肌理,夯土来自自然的气息,也喜爱填补墙面的碎砖瓦的艺术感,并称之为“匠作之道”。他谈道,“(这些传统)来源于我们最原本的乡土山川,可是它却属于一种几乎快要被我们遗忘了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关乎乡土营造的诸多方面。”[8]
而这些称为“匠作”的乡土营造,构成了王澍建筑中具有个人特征的立面材料、细节的视觉呈现。以富阳文村的乡建为例,王澍分别运用了“石头打墙”“夯土墙”“竹制露檩架”“楠竹栏杆”“木檩窗”“石库门”等等来自乡村民居的立面材料和细节,以及这些材料细节的组合与拼贴。这构成了文村这一农居群落从色彩、材料直至形式细节上,丰富多样的视觉呈现与画境般的乡土意境。
其次,正因为对经典化和画境般的乡土视觉呈现的强调,这种称为“匠作”的乡土营造往往是当下真实建造体系之外的视觉表皮。以中国美院象山校区为例(图3),刘家琨曾谈到他对王澍在建筑立面上使用屋顶材料小青瓦的看法:

图3 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小青瓦披檐的装饰性使用(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王澍可以直接引用或“错用”小青瓦,而我更想用当代正在广泛使用的材料……(王澍)有些是改变了做法,有些是表征性做法。比如,王澍的体育馆其实是钢结构屋面全部做完了,再在上面做立铺和防水等都没关系,它是一个时代、文化的表征……你把拱片瓦放上墙的时候,这就不是它最本真的用途,当你把它放上墙的时候,它的装饰性可能会大于它的本真性。
因为处在这个时代,他更情愿用当下的砌块或再生砖。传统的材料有点像成语典故……他不想用成语,对“错用”和“引用”也挺犹豫。他更愿意用家常“白话”[9]。
事实上,王澍那些经典化的乡土材料、细节之中的“匠作”,其首要关注的是文化身份的装饰性表征,至于其技术来源是否真正出自乡土传统反而显得不重要。比如富阳文村乡建中带来文化身份表征的夯土墙技术事实上来自法国,而非真正的本土建造传统,其建造和造价同样不像乡土民居一般实用经济。
通过对经典化和画境般的乡土视觉呈现的强调,王澍在设计中不断提取理想化的乡土形式旨在寻求当下中国的民族和地域的文化身份认同。而这种理想化的乡土形式正因为是理想化的,它不会随着建筑的功能和场地、尺度和环境“此时此地”地发生转变。因而,无论是在行政中心区的宁波博物馆、在城市中的公望美术馆、在小镇中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还是在山村中的富阳文村乡村建设,王澍面对不同体量尺度、不同功能、不同基地环境时,建筑的立面、材料和细节都保持了具有个人风格标识的视觉一致性,这也正是王澍在建筑中力图建构的理想化、经典化的乡土视觉语言。
3 结语:刘家琨、王澍建筑设计中的多维乡土角色
通过上述两位建筑师认知乡土视角和设计中乡土运用方式的分析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刘家琨思想实践中的乡土内涵是一种“近期”普通大众日常建造的文化延续,是面对“此时此地”的集体记忆和民间智慧,而非那些时空遥远的经典化、理想化的乡土传统,或是文化乡愁和身份认同。同时刘家琨的建筑有一种乡土赋予的人情化倾向,他学习民间建造的宽容谦让,他的建筑没有专业者的强迫,也并不介意显露出普通人房子般的弱点甚至错误。
刘家琨的建筑强调的是普通大众的日常性、集体记忆和民间智慧,而至于乡土表达地域的特殊性,对全球化与普遍性的抵抗,事实上刘家琨根本没那么执着。他的乡土观念中最重要的层面就是文化的植根和延续。在他看来,当下建筑实践最急迫、最核心 的任务应该是“近期传统”的文化传承问题。而乡土在他的思想与实践中不但是一种“形式模型(Formal Model)”,也是一种文化传承和人情化的“概念模型(Conceptual Model)”。他立足于“此时此地”,因此他建筑中的乡土内涵既不过于强调地域特殊性,也并非时间上的怀旧。刘家琨的乡土思想显现出其关怀平民社会的价值倾向,即在经济性、适应性的前提下,让建筑赋予普通个体以身份感和社会尊严。
而与之对比,在中国当代乡土启示下的建筑实践中,王澍是抵抗意味较强的一位。他的建筑有对官方样式的抵抗,对建筑师正统语言的抵抗,对现代社会过度的工业化、产品化和商业化的抵抗,而更为明显的是王澍对于全球化和普遍性的抵抗,以及对中国建筑民族特征和地域特性的强调。事实上,王澍的乡土视角堪为当代中国地域主义者的典型,而这多层面的抵抗角色是由王澍的乡土视角决定的。关注久远时代经典化、理想化的乡村传统,寻求民族和地域的文化身份认同,这种乡土视角必然构成对逝去传统的怀旧和对杂乱现实的批判。
因而,王澍在实践中提取乡村田园中经典化的乡土视觉语言,并构建理想化的乡土形式旨在寻求当下中国民族和地域的文化身份认同。因此,他更关注材料、细节这些视觉上呈现出的乡土感觉和形式风格,而非具体功能,乡土在他的思想和实践中主要作为一种表达民族和地域身份立场的“形式模型(Formal Model)”,也是一种对理想化、经典化的乡村田园形象的文化认同。
无论是“形式”还是“概念”,也正是通过刘家琨、王澍两位建筑师设计中不同乡土角色的对比,“乡土”这一范畴在当下中国建筑中的多层语境也能够得以更好地展开和审视。
注释:
①2012年王澍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GSD)名为“Geometry and Narrative of Natural Form(自然形态的几何和叙事)”的演讲中提到,为什么他在杭州而非上海职业和实践时,充满抵抗性地提到,“因为上海不是中国,杭州代表的江南才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