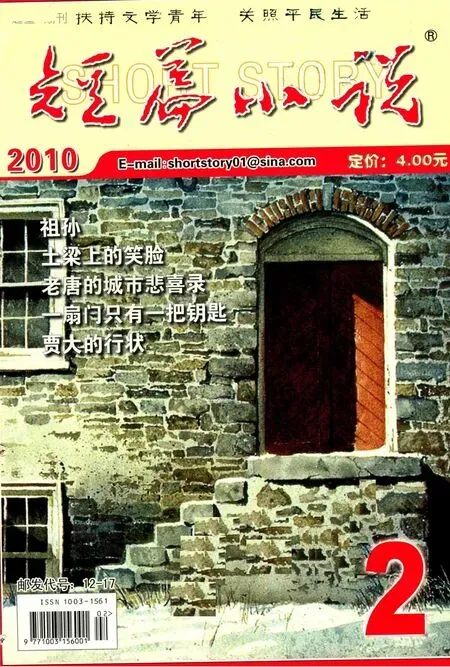1993年的录音机
◎梁永奇
我毕业的那一年,正是中专毕业生包分配的最后一年。班主任说,你们这一届简直太幸运了,再晚一届可就得自己找工作,自谋出路了。我和同桌互相瞅了一眼,眼神里荡漾着嘚瑟,就跟买彩票意外中了大奖差不多,好像一下子抓住了幸运的尾巴。

我学的是与交通相关的专业,自然要分配到交通系统的岗位上。去当地的交通局报到那天,几片云彩在天空中散着步,微风亲吻着树叶,就连太阳都乐呵呵的。这当然跟我的心情有关,想到马上就要参加工作了,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心里那个美啊。交通局人事处有个小眼睛厚嘴唇的中年妇女 (后来听人说是位副处长)接待了我。
她随手翻着桌上的一摞文件,漫不经心地表示,实际上,交通系统哪个单位都不缺人,甚至许多单位早已超编,上两届的毕业生都还在排队等着上岗呢。
我说,你的意思是我还上不了班?
她说,是的。
我问,那什么时候能轮到我?她不咸不淡地说,等通知吧。
我又问,大约要等多长时间?
她斜视着我,又瞅瞅眼前的文件,撂下一句:这谁说得好。也许明年,也许三年五年。
接下来的事情可想而知。那位副处长随意撂下的话如同一只兔子,就在我的前面跑,不远也不近,不急也不躁,大约一百米。我跑,它就跑。我停下来,它也跟着停下来。真是拿它没办法。继续追,总也追不上,想放弃了又觉着可惜。我认识的好几个中专毕业生,尽管学的专业不同,跟我的情况大概差不多,也是整天追一只兔子。追来追去追烦了,不想追了,爱跑多远就跑多远吧,跑丢了拉倒。他们背上行李转身去了火车站,买车票,乘坐绿皮火车,铁了心要去南方闯荡。
我的同桌给我来信说,咱们追那只兔子可能比守株待兔强上那么一点。话说回来,即便追上了又能怎样,那种一眼望到头的生活有啥意思,不如去大城市追牛追羊,城市里牛羊多得很,说不定都能把一个牛群或者羊群追到手,到那时候我们便成了都市放牧人。
是的,我也想去大城市,我也想做城市的放牧人,去他妈的那只兔子吧,我实在不想跟它较劲了。可我老爸说,等等吧。交通局的工作是铁饭碗,人家花多少钱买都买不来,你这说不要就不要,是不是脑子有毛病了。去外面闯荡,今天这个公司明天那个公司,你以为容易,有保障吗?沟通有代沟,说不服他,我就想偷摸去。
老爸早看透了我的心思,干脆把我的身份证藏起来。这下掐住了我的七寸,没有身份证,哪儿也去不成。于是我到处找,翻箱倒柜,犄角旮旯都找遍了,就是找不着,真是邪门了。难道能藏到天上去?
我的家在一个偏僻小镇上。这小镇,不过是地球上的一粒尘土,所以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它的名字。一条东西街和一条南北街交叉的地方是小镇的心脏,就好比北京的心脏是天安门。站在这里吼一嗓子,全镇人都听得见。
那时候,镇长的儿子常常拎着一台录音机经过这里,总要停上十分钟或者八分钟,喇叭里传出的歌声顺着街道沿着胡同流淌到家家户户,又钻进人们的耳朵里。
我也想拥有一台录音机,也想像镇长的儿子那样拎着录音机,播放着流行歌曲穿过街中心。可事实上我只有艳羡的份儿。我爸爸不当官,也不做生意,只是在街上的供销社干点杂活,哪里有钱给我买录音机。即使有钱也不会给我买,他认为这是糟蹋钱。买吃的买穿的买用的,就不会买录音机。
他在饭桌上说过几次,一根筷子敲着桌子如同舞台上敲边鼓的:我跟你说,别跟镇长的儿子学,像他那样的,早晚会出事。说完又嘱咐我,他说的话不能说出去,烂在肚子里。没多久,镇长的儿子果然出事了。他一只手提着录音机骑着摩托车和一辆卡车撞到一起。录音机粉身碎骨,零件散落在马路上,录音机的把手被紧紧攥着,不舍得松开。
总是闲在家委实没多大意思,我打算打一份工,挣了钱买一台录音机。镇南边曾是一片荒地,坑坑洼洼,野草丛生。几年前有人在这里建了个砖厂,几座土黄色的砖窑成天冒着浓烟,砖窑跟前垒着一摞摞的砖坯和出窑不久的红砖。我托熟人介绍在这里干了两天。
别人一双手可以夹十块砖,我只能夹五块。别人一天能搬七八千块砖,我只能搬四五千块。即便这样双手还是起了好几个血泡。第三天上午,我刚到砖厂,老板说,你这个大学生,哪是干活的料。你以为这钱是好挣的?塞给我二十块钱算把我打发了。
我从砖窑厂垂头丧气地出来,经过一片小树林,便进去找块草多的地方躺下来。阳光从树叶间洒下来,让人浑身懒洋洋的。我用草帽盖住脸,竟然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感觉鼻子痒痒的,睁眼一瞧,有个姑娘捏着一根头发正撩拨我的鼻孔。她说,呵,终于醒了,睡得真香啊。我一下子坐起来,愣了一会儿便知道是谁了,高中同学沉香。好几年没见,听说她高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了。
我说,你怎么在这?
她也问我,你怎么在这?瞧你这一身脏兮兮的,哪像个大学生,就跟砖厂的工人差不多。
我说,你说对了,我就是刚从那里出来。
她问,你去那里干什么?
我说,干活。
她问,真的假的?你怎么想起去砖厂干活?骗人的吧?
我懒得解释,又问,你不是打工去了吗?
她说,是啊,五月份从南方回来的。
我说,那你不去了?
她说,不去了。
我说,为啥啊,南方打工不好吗?
她说,怎么说呢,我出去好几年了,想歇一歇。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点点头,那你就一直在家闲着?
她说,没有,这会儿在镇上的毛巾厂上班。
我说,这下离家近了。
她说,还是离家近好,想回就回了。你真去砖厂干活了?
我说,是啊。
我伸出双手给她看手掌上的几个血泡。
她说,哎呀,弄了好几个血泡。瞅你这细皮嫩肉的,哪能干那粗活。
我说,我就想挣点钱买台录音机。
她咯咯笑了,我当因为啥呢,不就是一台录音机吗?我家就有,从南方带回来的。
沉香家在镇子的最东头,院子外面长着三棵大杨树,树荫刚好把她家的院子都覆盖了。院子里四间瓦房,她的闺房在最西边那间。走进房间,我看见桌子上的一台红色录音机,长方形,四个喇叭。还看见一位十六七岁有点害羞的小姑娘。她说这是我妹妹书香,好看吗?我说好看。她俩笑了。我不好意思了,忙说,我是说录音机好看。她俩又笑了,笑得扭动着身体。沉香故意问,难道我妹妹不好看吗?我说,你俩都好看。她俩又大笑,笑得我直挠头。
沉香问我有女朋友没有,我说,没有。
我给你介绍一个吧。
好啊,介绍一个漂亮的。
哎哟,要多漂亮的?你脸皮真厚啊。
她摁一下录音机的按钮,喇叭便开始唱了,是费翔的歌曲。
我说,声音再大些。她调高了音量,这样行吧?
我说,再大些。她又调高点说,你们男生就喜欢大声音,不嫌震耳朵。
我说,声音大才听得过瘾听得带劲。我翻了翻旁边的几盘磁带,都是专辑,有张明敏的,成方圆的,毛阿敏的,邓丽君的,程琳的,还有小虎队的。
她说,好听吗?
我说,好听。
我问,有齐秦的磁带吗?
她问,谁的?
我说,齐秦。台湾的歌星。
她说,没有。
我试探着问,录音机能借给我听两天不?
她说,你拎走吧,借给你半个月,记住过了半个月还给我。
回到家里,真不巧,停电了,心急火燎等到晚上才来电。我摁下录音机的按钮开到最大音量,四只喇叭嗷嗷叫,震得屋墙直掉土。幸亏老爸不在家里,去县城干活,一个月才能回来。我妈这个人,脾气好,也觉得我大了,所以基本上不干涉我的事。不一会儿邻居的大人小孩都跑过来。有人问,你啥时买的这玩意?我说,不是买的,借的。有孩子伸手想摸一把,被我拦住了。
第二天,我又骑着自行车去城里,在市中心广场的一家音像店,买了一盘齐秦的歌曲专辑。专辑的封面:齐秦留着一头披肩长发,身穿黑色皮衣,戴着墨镜,特别个性。
夏季白天长,晚上九点多的时候,商店还都亮着灯,逛街的人还不少。我拎着录音机经过镇中心,并在那里停留了十多分钟。当时录音机的喇叭里,齐秦唱着“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街上的几个小混混大声喊叫,狼来了狼来了!便有人跟着起哄学起了狼叫。一时间狼声四起。人们围上来,包括那几个混混,当时的我很得意。
一个混混跟我不错,见面老打招呼,因为眼睛很小,都叫他小眼。他说,哥们儿,这是啥歌?还有狼叫?
我说是一个台湾歌星唱的北方的狼。他说,还真有狼。台湾人咋啥都唱?
另一个长头发的混混说,是母狼还是公狼?
我说,你懂什么?
这下把他惹毛了:你说啥?再说一遍?我说,你懂个屁。
他说,有种。你信不信我把这录音机砸了?
我说,你敢?砸一下试试。
他说,你看我敢不敢。接着弯下腰去找砖头、石块。
小眼拉住他说,算了,算了,都是一条街上的,抬头不见低头见。
那个混混说,你看他牛的,一点面子也不给,问这街上我怕过谁。
小眼又来劝我,小声说,走吧,他就这个脾气。你只管走。我暗笑这帮人文化低、没见识、土包子。我想我就是一匹狼,我要去寻找美丽的草原。
半个月时间里,录音机就放在床头上,几盘磁带反反复复地转。我熟悉了这些磁带正面反面的所有歌曲,记住了歌词也记住了旋律,一张口歌声就从嘴里淌出来。我成了一台录音机,走到哪里唱到哪里。
我把录音机还给沉香的时候,还带去了一网兜国光苹果表示谢意。当时书香也在,她拿出来当即用水洗了三个。递给我一个,我不吃。她俩吃起来,吃相明显不同。沉香大口大口地啃,如同梁山好汉,大口吃肉,大口喝酒。而书香一小口一小口地嚼,如同大小姐,生怕自己吃多了变胖,也可能怕别人说她吃相难看。我说这苹果像书香的脸蛋。书香就笑着追打我,追得到处藏,我只好假装求饶,她才肯放过。
沉香说,这下听够了吧。我说这下过瘾了。书香说,应该再借给他,让他多送些苹果。沉香说,我才不呢,等你买了录音机,你再借吧。书香说,买就买。沉香说,拿啥买啊?书香说,你会打工,我就不会?
接着沉香便说起给我介绍女朋友的事。毛巾厂里正好有一个女孩,比我小两岁,个子高高的,模样俊俏。今天正好厂里休息,不如现在就跟她去厂里见见面。我瞅瞅身上说,要不要换身衣服?沉香说,没事,你这身衣服挺好的。
所谓的毛巾厂不大,就是个小院子,十来间厂房。她直接带我去了她们的宿舍。没想到坐了一屋子的姑娘,大概有十来个,估计听说我的来意,一准儿来起哄的。姑娘们一道道目光排山倒海般汹涌过来,我简直招架不住,坐在那里局促不安。
沉香介绍的那个女孩子叫春燕。姑娘们都说春燕站起来迎接啊,人家大老远来了,还不倒杯茶,招待一下?看见她们推着一个高个子女孩站起来,我慌乱得没有看清她的脸。春燕说,你们咋不招待啊?有人说,人家来看谁的,如果来看我,我就招待他。春燕说,我拿啥招待,没烟也没茶。有人说,到厨房提一壶开水过来不就行了。
沉香说,亮子,唱歌吧,春燕想听你唱歌呢。
她们都说,就是,春燕早想听你唱歌呢。
春燕说,甭听她们瞎说,她们都想听你唱歌哩。
我就开始唱,唱了一首又一首。齐秦的那盘磁带所有歌曲我都唱了一遍,还唱了费翔的,成方圆的,程琳的,张明敏的。这简直是我的个人演唱会。我也不管她们的评价如何,反正就是唱。我这人就是这样,平时见人挺拘束的,只要唱起歌,全都放开了,什么人也不在我眼里。她们也不评价,就是催着我唱下一首,好像我就是个录音机,摁下按钮会不停地唱。
那个叫春燕的,一直低着头,再也没有说一句话。中间有人逗她,春燕,你咋脸红了,听入迷了吧?
春燕说,讨不讨厌啊你。
出毛巾厂的时候,她们又叫春燕送我。沉香说,春燕,你送亮子吧。人家唱了那么多歌,唱累了。春燕就站起来送我。我在前面走着,她离我有一步远。
她问,你那些歌从哪里学的?
我说,跟录音机学的。
她说,我也有台录音机,刚买没多久。
我说,哪天借给我听听?
她说,你自己不会买吗?老借别人的。
我就不好意思了,但也有些生气,我借不借关你什么事,用得着你来教训我,更何况我们刚认识。
我生硬地说,就送到这吧,你回吧。说完转身走了,一直没有回头。
不过,回到家里,我还是给她写了一封信,里面写了好多。写的什么,无非是些甜言蜜语、山盟海誓之类。有自己想的,也有从书上摘抄的。托沉香捎给她,她并没有回信。我有些失落,但很快就忘了。因为我并不了解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甚至连她的模样都没看清。她愿意回就回,不回就算了,没啥可伤心的。一个星期后,我再去找春燕,她却已经离开了毛巾厂。我问沉香咋回事?沉香说她也不知道,忽然间就走了,听说去外地打工了。她到底怎么想的呢?很奇怪的一个姑娘。
后来倒是书香老来找我,我常常在屋里待着无聊时,她便推门进来了。她初中毕业就不上学了,一直在家待着。我问她,咋不上了?她说,没意思,学习不好,老师老骂我。我说,你咋不好好学啊?她说,谁不好好学了,就是学不会。我说,你准是谈恋爱了。她说,你太讨厌了,谁谈恋爱了?有时我俩一起打扑克、下跳棋。她不太会玩这些,我只好故意输给她,要不她就不想玩了。有时我们就是干坐着,你看我我看你,不觉得厌烦,也不觉得时间长。她说她早晚要出去打工,挣了钱也要买一台录音机,借给我一个月。我说干吗一个月,最少半年。她说,你自己不会买吗?我说,要不一辈子算了。她的脸红了,跟喝了好多酒似的。
我知道我是不爱她的,和她在一块儿就是因为寂寞,因为孤独,整条街没有一个人能说上话。那时候觉得钟表出了问题,走得特别慢,日子长得望不到尽头。我和她一块就是消磨时间,把大把大把的青春时光消磨掉,像扔掉一件件旧衣服,一点都不感到可惜。
每次都是她来找我,陪我聊天或者傻傻看着我读书。有一次我拉住她的手,她没拒绝,我就抱住亲她。她像个小猫一样瘫软在我怀里。接着我把她压在床上,动手解她的腰带。她不让,拼命抵抗,尖利的指甲狠掐我的手,我忘乎所以地进攻,竟然忘了疼痛。我俩僵持中,她的腰带遽然断了。我正要进一步行动,她说话了,别硬来,今天晚上在镇南面小树林里吧。我放开她,她起来找根绳系上裤子就走了。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小树林静得很,到处是昆虫的鸣叫声。我从八点就坐在树林边上等她,一直等到十点也没见她人影。心想,她一定在骗我。正想起身离开,却听到了脚步声,一个黑影越走越近,是她。她坐到我身边说,你等我多久了?我说,干吗等你。她说,那你等谁?我说,谁也不等。说完起身走了。我一路走着,一直很生气。谁料她跟在我后面了。她问了几次,你怎么了?我终于站住,冷冰冰地说,没怎么,你走吧。她愣了片刻,转身走了。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件事,就觉得不可思议。和一个女孩约会本该是快乐的,我怎么会生气,又怎么会冲一个女孩发火呢?到底是年轻气盛。
第二天,在街上远远看见她在一家小商铺前站着。她朝我这里望着,看不清她的表情,一会她又扭过头去。她再也没有来找我。我去找过她一次。我问她,你咋不去我那里玩了?她没有回答,只是笑笑,笑得很淡然。我说我挺喜欢你的,她又笑笑。我想拉她的手,她笑着甩开。
我想也许我把她的心伤了。
老爸通过熟人关系给我在县城交通部门安排一个临时工作,还说等到有空编了,马上安排我正式上班。上了两个月的班,工资加一起一百多块,我就买了一台录音机。周末,我提着录音机穿行在县城里,喇叭里的歌声流淌在大街小巷,许多人扭头看我,我相当骄傲。不久又在单位谈了一个对象,约会时我常常提着录音机。恰好对象也喜欢齐秦,喜欢他唱的 《大约在冬季》《花季》《冬雨》等歌。
两年后的冬天,沉香结婚了,邀请我去参加婚礼。我在婚礼上见到了书香,她笑问,你啥时结婚啊?我说,等两年吧。我问,谈对象了吗?她说,没有。我说,该谈就谈。她说,不想谈,没意思。那天在酒桌上她喝了不少酒,脸被酒精烧得通红。我俩还碰了一杯,她一口干了,好像把过去的事全忘了。
又过了一年,我回镇上办事遇到沉香,聊了几句。她的样子很消沉,好像一下子老了不少。我说,书香呢?现在干啥呢?她说别提这个死妮子,她不是俺妹妹。我一下愣在那里,她扭头就走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书香跟沉香的老公一块儿私奔了。镇上的人都知道这事,小姨子跟姐夫私奔,成为一时的笑谈。